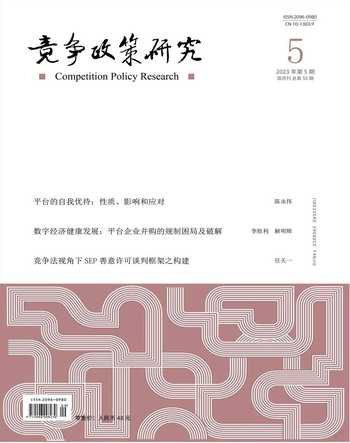Google、Facebook等公司:反垄断法视域下的数据及算法力量
【德】托尔斯滕·科贝尔 丁庭威
摘要:在过去的30年里,互联网的成功造就了众多新的服务,并大幅增加了消费者福利,也为企业创造了许多新的机遇。然而,种种担忧亦接踵而至,即一些大型数字公司及其使用的算法可能获得过多的影响力。全球各国通过各种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反垄断法和监管法对潜在的竞争作出回应。在德国,立法者曾两次(2017年和2021年)修订《反限制竞争法》(GWB),以更好地涵盖数字市场和商业模式。对此,当时的重点是改进对权力滥用的监督。在欧盟,立法者选择通过《数字市场法》(DMA)对数字守门人进行监管,该法案自2023年5月2日起生效,并提列了众多禁止条款。本文将德国的法规(特别是《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与《数字市场法》进行比较,并批判性地对这两部法规进行评估。
关键词:互联网;算法;数字巨头;守门人;竞争法;德国《反限制竞争法》;欧盟《数字市场法》
一、研究缘起
若看到诸如“算法的力量”此类讲座标题,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想到几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例如Google(或Alphabet)、Amazon、Facebook(或Meta)、Apple和Microsoft,简称“GAFAM”。市场力量集中在商业模式中并不鲜见。早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就有人担心铁路和石油行业的市场力量集中,例如在重组标准石油托拉斯(Standard Oil Trust)时,就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上无法控制的垄断。为此,美国在1890年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反垄断法案——《谢尔曼法》,该法案至今仍存在,禁止卡特尔和反竞争手段的垄断。如今,几乎每个反垄断法案中都可以找到规制卡特尔和滥用市场力量的规定,在过去的130年里,它们在保障市场良性竞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22年6月,鉴于汽油和柴油价格高企,德国联邦经济与气候保护部(BMWK)出台了新的规定,企业拆分将不基于滥用行为并且将通过针对垄断行为衍生利益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矿物油市场再次成为德国反垄断辩论的焦点。
在数字经济领域,市场力量集中也并非是新鲜事。即使互联网只有30年的历史,人们对Microsoft的市场霸权依然感到担忧。在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担心微软会利用其在操作系统市场中的力量来主导其他市场,如网络浏览器、媒体播放器和流媒体,并最终主导整个互联网。而在2000年1月10日,媒体集团时代华纳(Time Warner)和互联网接入提供商美国在线(AOL)宣布其合并计划时,有人便担心这个新集团将可能掌控整个互联网市场乃至重要的舆论市场。然而,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担忧都被证明是空穴来风。虽然微软仍然是第二大市值的数字公司(仅次于苹果)。但如今主导互联网的是其他公司,在媒体播放器和流媒体领域,微软更是无足轻重。具有话语权的其他公司是YouTube、Netflix或Spotify。而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计划也被证明是失败的。早在2002年,时代华纳就因此遭受了大约450亿美元的亏损。美国在线在2009年被拆分,并在2015年以4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美国在线并没有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成为互联网垄断者,而是同样陷入了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
如今,人们的担忧主要集中在Google、Amazon、Facebook以及Apple这几家公司身上,有时也包括Microsoft,简称为GAFA或GAFAM,认为它们可能会主宰数字经济、互联网以及媒体领域。Google成立于1997年,其可能利用在搜索引擎市场的领先地位,以此作为筹码来征服其他市场,如地图市场(Google Maps)、视频内容市场(YouTube)或比价市场(Google Shopping)。这已经引发了人们十多年的激烈辩论。此外,Google(或Alphabet)還掌握着安卓系统,它是目前最为成功的移动操作系统。Amazon成立于1994年,其从原先的互联网书店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并且通过亚马逊商城(Amazon Marketplace)运营着面向第三方卖家的最大销售门户之一,同时为其制定规则。Facebook(或Meta)成立于2004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平台,也是这个尊贵俱乐部(GAFAM)中最年轻的成员。除了对Facebook经济权力集中的担忧,人们还担心其潜在的“媒体权力”。自从Facebook并购了WhatsApp和Instagram这两个更为重要的社交平台后,这一恐惧和隐忧便更为突出了。
就像在Microsoft案例中一样,这些服务受到强大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影响,即“自我强化效应”和其他因素,而这些效应尤其对数字平台具有重要意义。详细探讨这一点已经超出了本讲座的范围。但是,德国的GWB(《反限制竞争法》)在第18条第3a款已列举了(包括但不限于)适用于数字市场的相关因素。在此,仅举两个例子:第一,网络效应与规模优势(GWB第18条第3a款第1项和第3项);第二,获得竞争性相关数据(GWB第18条第3款第3项和18条第3a款第4项)。
无论是操作系统、社交网络还是即时通信服务,拥有越多的订阅者并能与他们交换信息,就能运作得越好。另一方面,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还会越受广告客户的青睐,这一进程被称为“网络效应”。任何曾考虑从WhatsApp转移到其他服务的人就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使得新公司很难立足于市场。它们不仅要为硬件、服务器和程序进行大量的投资,而且还需要在用户市场(如新的社交网络)和广告市场都赢得足够数量的客户,并最终说服他们从已经建立的“每个人”都在使用的服务中切换过来。然而,这并非不可能。Google曾经并非始终是领先的搜索引擎,Facebook过去也并非一直占据社交网络的头把交椅。两者都“推翻(entthront)”了原先占主导地位的竞争对手。Microsoft在2011年并购Skype之后,曾短期占有90%以上的即时通信市场份额。然而现在,WhatsApp或Zoom等其他服务已主导了市场,虽然它们都具有网络效应,但它们之所以成功,只是因为它们更好。
近些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GAFAM公司拥有的所谓“数据权力”。数据在任何行业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Google和Facebook这类互联网服务公司来说尤为如此,因为它们向用户免费提供服务,并通过广告的多边业务模式来融资。用户数据被用来优化产品以及有针对性地、进而更成功地投放广告。易言之,用户数据是这些公司算法能够良好运作的重要原材料,最终形成能够控制产品和广告的人工智能(AI)。但与其他材料或资金不同,数据是“非竞争性的(nicht rival)”,因为金钱花掉就没有了,石油也会因燃烧或加工而消耗殆尽。换言之,金钱和石油只能被一方或另一方使用,这些消费品是具有“竞争性”的。但对于数据而言,情况往往截然不同。因为大多数据可以多次传输给不同的公司,所有公司可以同时或相继使用这些数据。为了在竞争中保持抗衡能力,也并不必须拥有像Google和Facebook那样多或甚至相同的数据。但肯定需要“充足(genug)”的数据来训练人工智能(AI)。在此,我们谈论的是“最低最佳的数据量(mindestoptimale Datenmenge)”的概念。而“数据网络效应(Datennetzwerk effekte)”是否真的存在,还存有疑问。
鉴于这些因素和GAFAM的庞大规模,如今人们仍然担心这些公司已经获得了无法撼动的竞争优势,而小型企业正变得落后,尤其是德国和欧洲的公司。例如,因为它们缺乏数据而难以跟上,或者因为GAFAM会以自身为优先。这种隐忧体现在德国《反限制竞争法》新的第19a条以及欧盟《数字市场法》(DMA)之中。还有人担心,创新的初创企业将因GAFAM并购而被“吞噬(geschluckt)”,进而限制技术进步以及产品多样性的发展。最终,人们普遍担心作为市场参与者的我们无论是在资金方面抑或是数据方面都将被剥削。
二、反垄断法
无论如何,一旦存在公司“过于庞大(zu gro?)”的危险且不再受到市场和竞争的充分控制时,反垄断法便会像1890年那样发挥作用。由于本讲座的听众并非都是反垄断法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先简要介绍反垄断法能够且打算做什么,以及它不能和不打算做什么。
反垄断法旨在保护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作为一种有效互动的市场力量,有效竞争确保了供应受到需求的控制,有限的资源能够在大众经济中得到最明智的利用。历史告诉我们,市场参与者(包括私人和企业)由市场激活的“群体智慧(Schwarmintelligenz)”在实现这种协调方面远比通常以假定知识为基础的国家计划更为出色。市场是一种“基层民主(basisdemokratischer)”的调控机制。同时,相对于大公司乃至(更大的)国家,竞争也是保障自由的一种手段。
当竞争发挥作用时,它会促进低价、产品多样性以及创新。简言之,它能提升消费者福利。有效的竞争会不断迫使公司降低价格、改进产品和流程,否则它们将失去市場份额,甚至可能从市场上消失。正如自然界“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基本法则一样。创新和高效的公司不断成长,而其他缺乏创新和效率的公司则“倒闭(pleitegehen)”,这正是市场运作(Funktionieren)的体现,而非市场失灵。
为了确保竞争的运作和有效性,反垄断法(Kartellrecht)顾名思义首先禁止的便是卡特尔(Kartelle),卡特尔即企业之间旨在限制竞争或施加影响的行为约定,如固定价格协议(Preisabsprachen)。
其次,反垄断法尝试防止由于违背竞争的企业并购(Unternehmenszusammenschlüsse)而导致的权力集中(Machtkonzentrationen)。这便是并购管制所关注的主题。例如,若某家GAFAM公司感觉受到一家创新初创公司的威胁,为了“摆脱”该竞争对手而干脆将其“吞并(schluckt)”,该行为可能会被禁止。当然,细节决定成败,这样的并购也有可能促进创新,并且也很可能是初创企业梦寐以求的。一家只有几年历史的初创企业,谁不梦想着能以数亿甚至数十亿的价格被收购呢,就如当初的WhatsApp一样。这种前景可以成为创新和对创新投资的强大激励,进而推动进步。因此,在实践中并购(Fusionen)很少被禁止,这是合理的。
最后,这让我们看到了该议题的本质,反垄断法禁止滥用权力是为了防止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不受竞争的充分规制,从而滥用权力阻碍竞争对手或剥削市场伙伴。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做出仔细的区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竞争中取得成功会导致有些公司变得更大而其他公司失去市场份额。因此,反垄断法并不禁止通过竞争获得的市场力量。如若不然则意味着对成功的惩罚。一家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主导地位,仅仅是因为它比竞争对手更具创新性、更有效率、更为“优秀”。在此情形下,市场力量本身甚至垄断都是被允许的。因此,要解散这样的公司,即使它没有滥用市场力量,正如人们一再要求对GAFAM公司以及现在德国联邦经济与气候保护部(BMWK)对矿物油公司的要求一样,这是有悖于反垄断法的一种错误做法(kartellrechtsfremder Irrweg)。美国和英国曾尝试过这样的拆分,但几乎从未取得持久的成功。反垄断法不能也不应与市场背道而驰,而只能为市场上的自由竞争设置“护栏(Leitplanken)”。因此,更有效的做法是,依据反垄断法密切关注那些不再受到竞争充分规制的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公司,以识别、防止并惩罚这些公司滥用市场力量。只有在这些措施无效的情况下,才可以根据现行法律,在反垄断法框架下对具有重复滥用行为的“严重违法者(kartellrechtlichen Intensivt?tern)”进行拆分。
三、 “务实主义的反垄断法”和数字市场
反垄断法是以一般条款为基础的。这适用于禁止卡特尔(《反限制竞争法》第1条,《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也适用于禁止滥用行为(《反限制竞争法》第19和20条,《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这是一件好事,因为针对技术现状的特殊标准很快就会被实践所取代。对数字市场来说,一般条款尤其适用,因为数字市场是非常动态的,因此,如果有一部专门的“数字反垄断法(Digital-Kartellrecht)”很快就会变得过时并需要修订。相反,反垄断机构和法院可以根据实践的发展灵活地适用一般条款。
然而,反垄断法有关滥用权力的禁止条款存在一个“不健全之处(Pferdefu?)”:由反垄断机构或法院执行必须以滥用权力行为已经发生为前提。易言之,禁令只能在事后适用。所以有观点认为,现行反垄断法做得“太少,太迟”,并且无法在数字经济中跟上时代的步伐。当反垄断法最终介入时,竞争已经陷入了困境,例如在涉及GAFAM公司的情况下。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Google Shopping诉讼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此案件中,从竞争对手Foundem在2009年11月3日投诉至欧盟委员会至2017年6月27日作出决定,已过去了近8年,然而该案件还未得到最终裁决。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11月10日在欧洲法院获胜,但欧洲法院(EuGH)有最终裁定权。相较而言,最近德国联邦卡特尔局(das Bundeskartellamt)只用了约9个月便完成了对Amazon的诉讼程序。这证明实际可以快很多。两个案件都是在“旧”反垄断法基础上进行且都是针对数字公司的,但为什么第一个案件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而第二个案件进展如此之快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2022年的欧盟委员会和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权力和能力比2009年强得多。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Google Shopping诉讼案中,政治干预阻碍了Google和欧盟委员会之间达成一致的协议(尽管双方都愿意达成),并迫使欧盟委员会在争端中作出决定,而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Amazon和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能够寻求并找到一致的解决方案,这自然无需进行冗长的法庭审理程序。这表明,政治独立对于快速的竞争保护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如此,应用权力滥用规定的确非常复杂,需要全面的经济和法律分析。而且滥用行为往往也难以证明。这也适用于数字市场并且可能更为明显,因为数字市场往往更加复杂。在一个“普通”的市场中,供应商和需求方面对面交易(如汽车经销商和买家),而在数字市场中,多个市场页面往往跨平台联网。如,在Google的安卓操作系统中,就有五个相互影响的市场页面。尽管如此,2019年和2020年为德国联邦经济与气候保护部(BMWK)以及欧盟委员会准备的多份科学报告认为,对现有反垄断法进行适度调整、数字化赋能和加速就已足够。然而,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和欧盟委员会试图扩展其能力,并且政策制定者寻求对美国公司进行更大的干预,以改进德国和欧洲公司的竞争机会。因此,德国和欧盟制定了法律,对大型数字公司或者被认定为守门人(Torw?chter)的企业进行事前监管。在德国层面,这样一项规定在2021年1月19日的第十次《反限制竞争法》修正案中成为法律,以第19a条的形式规定。在欧盟层面,《数字市场法》的最终文本已于2022年10月12日在官方公报上发布,并将于2023年5月2日起实施。鉴于这些规定的復杂性,本文在最后一部分将对这两套法规进行概述性和批判性的比较分析。
四、题外话:并非总需适用反垄断法
必须强调的是,反垄断法并非解决数字(或其他)市场问题的“万能药(Allheilmittel)”。通常来说,其不适用于此目的,或者至少不如其他法律更为适用。这一点可以从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正在审理的Facebook案件中看出,该案件主要涉及不当的一般商业条款与条件(AGB)以及数据保护违规行为。问题在于相较于适用反垄断法,应首先适用一般商业条款与条件以及数据保护法。因为公民在面对任何公司时都会受到保护,防止一般商业条款与条件被滥用以及违反数据保护规定,而不仅仅针对守门人企业。然而,在此案或其他案件中仍然经常诉诸反垄断法,一方面是由于存在强大的执法机构,而其他标准(如一般商业条款与条件法律)的执行只能通过诉讼来实施。另一方面是依据反垄断法可以对处罚对象施以高额罚款,在欧盟委员会提起的三起Google诉讼中,罚款金额总计高达82.5亿欧元。
因此,在数字化领域各种错综复杂的新规定中,反垄断法的持续调整只是微小的一部分。例如,欧盟已经发布或“正在制定”大量的法规,这些法规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数字市场。仅举最重要的几项:2018年欧盟颁布了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其中第20条就涉及关于数据可移植性的规定。同样在2018年,欧盟颁布了关于非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第2018/1807号规定。2018年还颁布了《欧洲电子通讯法》2018/1972号指令,其中包含了诸如即时通信程序和互操作性的规定,最近已经在新的《电信法》2021年版中得以实施。随后欧盟在2022年还出台了旨在促进跨境数据共享并规范中介机构的《数据治理法》(2022/868号规定),以及针对在线平台内容规则的《数据服务法》(2022/2065号规定,DSA),即根据平台的规模进行分级,旨在打击所谓的“仇恨言论”或通过所谓的“暗模式(即互联网陷阱)”对用户进行误导,该法案将于2024年2月17日起生效。然而,最重要的是上文已经提到的《数字市场法》已于2022年完成,其目的是限制互联网守门人的经济权力,并以类似于反垄断法的方式确保市场的竞争性和公平性,尽管它在第10条和第11条的介绍条款中强调自身并非反垄断法。除此之外,处在立法过程中的还包括有关在互联网上进行数据收集的《电子隐私条例》,该条例将取代现有的“Cookie指令”2002/58号规定。它原计划于2018年与GDPR一起颁布,但一再推迟。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数据法》和《人工智能法》,前者旨在为欧盟的数据访问和使用制定通用规则,以确保数据互操作性并实现数据交易,后者旨在监管和限制人工智能的使用以保护公民,特别是在产品安全、歧视和数据安全方面。
这些法规并非总是相互协调的,甚至与各国现行的法规也不始终一致。对于大型企业而言,这无疑是麻烦且代价高昂的,但又是可行的。而对于律师来说,这甚至是好事,因为它为未来的咨询需求和法律争议开辟了一个黄金时代。然而,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初创公司可能会因此不敢进入市场,或最终被迫退出市场或被并购。一言以蔽之,过多的调控,虽然初衷旨在促进竞争,但最终可能反而导致更强的企业集权,从而减少竞争。
五、依照《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和《数字市场法》对守门人的监管
《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和《数字市场法》的新规定旨在解决上述事后应用反垄断法而被认为缓慢且复杂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对特定的“大型数字公司”作出并非在滥用行为得到证明后才会生效的规定,而是事先(事前)对这些公司进行“束缚”;另一方面,通过减轻举证责任来简化反垄断机构的执法工作并提高执法效率。与此同时,这些法律希望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以提高小型竞争者的竞争机会,尤其是对德国和欧洲的竞争者而言。通过这种方式,旨在促进市场竞争和市场公平。原则上,对此并不存在什么反对意见。然而,细节乃成败的关键。
(一)依照《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第1款和《数字市场法》第3条规定的守门人决议
首先必须确定的是新的事前规定的适用对象。两部法律都对此作出了特定的规定并且都要求当局作出决定。两者都规定可以通过行政行为来宣布公司成为标准的适用对象。这是可取的,因为企业需要法律上的确定性。然而,在德国法律和欧盟的《数字市场法》中,这方面的标准极为不同。
二者使用的相应术语也有所不同。《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第1款提到了“具有显著跨市场竞争影响的公司”,缩写为?MB公司,而在德国联邦卡特尔局(BKartA)被缩写为“?müB”。在这方面,也可以称之为“数字守门人”(正如《数字市场法》所称),因为根据说明备忘录的规定,其所指就是“大型数字集团企业”或者说白了就是美国的GAFAM公司。易言之,这是对大型数字互联网平台进行监管。为了回答“谁”的问题(译者注:即规定的适用对象),《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列出了一些定性因素,作为可能表明“显著跨市场竞争影响力(überragende marktübergreifende Bedeutung)”的指标,包括市场支配地位、财务实力、一体化、数据获取和平台实力。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必须调查这些要素。最终作出自由裁量的决定并发布一项行政行为,将某个公司定性为?MB公司,初始期限为5年。不出所料,《反限制竞争法》生效后的第一年,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就对Google、Amazon、Facebook和Apple发起了四起诉讼程序。Google早在2021年12月、Facebook(Meta)在2022年5月以及Amazon在2022年7月分别被划定为?MB公司。而针对Apple的诉讼程序仍在进行中。
此外,根据《数字市场法》,由“某个政府机关”即欧盟委员会来决定谁是守门人,该决定有效期为三年。不同于《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数字市场法》第2条列出的“守门人”仅适用于特定的互联网服务,即所谓的“核心平台服务(zentrale Plattformdienste)”。第2条列举的“核心平台服务”包含了许多服务,包括在线中介服务、在线搜索引擎、社交网络、视频分享平台、即时通讯服务、操作系统、网络浏览器、虚拟助手、云计算和在线广告等。笼统地说,几乎涵盖了GAFAM公司的所有业务。欧盟委员会与德国联邦卡特尔局不同的是,如果提供此类核心平台服务,欧盟委员会不一定要对“显著跨市场影响力”进行全面的定性评估。其可以依据《数字市场法》的第3条第2款的规定,即若某家公司超过一定的定量门槛,即三年内在欧盟范围内的营业额至少为75亿欧元,或者市值至少为750亿欧元(第3条第2款第a项),并且过去三年在欧盟范围内每月至少有4500万活跃的终端用户以及每年1万个活跃的商业客户(第3条第2款第b项和第c项),则可以推定其为守门人。理论上,虽然被推定的守门人可以证明自己即使满足这些标准仍不是守门人,但实际上要求相当高,在实践中几乎无法成功。
乍看之下,《数字市场法》比《反限制竞争法》提供了更多的法律确定性,因为其列出了涉及的服务并且具有明确的定量门槛。特别是对于小型服务提供商来说,它们很容易就能确定自己并不受《数字市场法》的规制。但是,这些标准有些过于粗糙。第一,《数字市场法》混淆了公司规模和“守门(Gatekeeping)”的概念。一旦某家公司规模足够大,即使没有明确指定它所守护的门,也会被宣布为守门人。第二,这些门槛标准对所有服务都是相同的,尽管4500万月活跃用户对搜索引擎来说几乎不算什么,但对其他服务来说可能是很多的。第三,这些定量门槛标准并没有基于任何经济上的合理事实。它们纯粹是政治协商的结果,与2020年12月的《数字市场法》草案相比,这些门槛标准还被提高了,可能是为了尽量少地涵盖欧洲公司。
(二)依照《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第2款和《数字市场法》第5、6和7条对守门人的监管
如果某家公司被首批行政行为宣布为守门人,会发生什么?在此,这两部法规也显示出相似性和差异性。虽然禁止目录相似,但执法程序的设计却是不同的。与反垄断法使用灵活的一般条款不同的是,《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第2款和《数字市场法》中包含了全面且部分极为详细的要求与禁止目录。就《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第2款而言,就列举了七项,其中一些通过不同的衍生和规则示例可以进一步加以细化:自我优待(第1项)以及在准入和采购市场中阻扰竞争者(第2项),“席卷”市场(das “Aufrollen” von M?rkten),即基于擁有优越的资源而通过快速的内部增长占领市场(第3项),通过使用数据阻碍竞争对手(第4项),拒绝或阻碍产品或服务互操作性和数据可移植性(第5项),向其他公司提供不充分的关于自身绩效的信息(第6项),以及向市场合作伙伴“揩油(Anzapfen)”,即要求不合理的好处( 折扣或数据使用权)(第7项)。《数字市场法》的第5、6和7条甚至包含了约30条非常复杂的要求和限制条款,这些条款在某种程度上与前述目录类似,在此就不详细列举。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目录是反垄断机构的一种“精选列表”或“愿望清单(wünsch dir was)”,因为它们反映了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或欧盟委员会大部分仍在进行的反垄断程序中的观点。例如,第19a条第1款(自我优待)显然是受到欧盟委员会的Google Shopping案的启发,而第4款(数据使用)则是受到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的Facebook诉讼的启发。几乎所有的禁令都可以追溯到类似的起源,在《数字市场法》的背景下,这一点显得更为明显,因为它声称自己并非反垄断法,而仅是对反垄断法的补充法规。
这两项法规中列举出来的行为规则将在未来用于禁止守门人,且并不需要事先费力地证明它们滥用权力。初步听上去不错,但实际上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仅举几个例子:首先,虽然禁止自我优待符合欧盟委员会在Google Shopping诉讼中的观点,但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其他领域一直宣称此类自我优待符合竞争法。第一,最重要的是我们并非始终明确什么是“自我优待(Selbstbevorzugung)”。若我想独自使用自己的数据或自己的服务器,这是一种应被禁止的自我优待吗?Google的搜索算法对结果的排名不同于Bing,这是一种自我优待吗,还是说仅仅是搜索引擎之间的竞争呢?第二,类似的问题也适用于“数据滥用(Datenmissbrauch)”:若我使用合法获得的数据而不与竞争对手分享,我是否阻碍了竞争对手?那么后果将是什么?我是否必须共享这些数据呢?或者,我自己也不再被允许使用这些数据,即使这意味着我对用户的服务会变得更糟?第三,在对互操作性有要求的情况下(如WhatsApp之类的即时通信服务)这种不明确性并未减弱:即使像WhatsApp这样的即时通信服务能够与其他即时通信服务实现“互操作性(interoperabel)”并實现多宿主(Multi-Homing),这就真的符合用户利益吗?从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是矛盾的,因为一方面它可能导致竞争对手通过遵循市场领导者的规范而非通过创新来与之竞争,另一方面它也增加了垃圾邮件、恶意邮件和安全漏洞的风险,因为各方在此可能有必要就“最低限度共同标准(kleinstengemeinsame Nenner)”达成一致,并且在问题出现时可能无法迅速作出反应。这并非意味着在这方面不存在竞争问题,但它确实表明,不能仅仅通过制定明确的规则和禁令就简单地“完全界定(wegdefinieren)”数字世界的真正复杂性,并且“不带附加条款(ohne Wenn und Aber)”地约束守门人。
特别是在执行要求和禁止条款的问题上,《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和《数字市场法》存在显著差异。《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第2款不包含任何根据法律直接有效的禁令。因为该标准只是一个授权基础,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可根据这些禁止目录通过进一步的行政行为对?MB公司发布要求或禁令。这使得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有机会根据具体情况做出适当调整措施,以避免过度监管或监管不足。然而,与传统反垄断法不同的是,德国联邦卡特尔局不必证明?MB公司的违规行为。?MB公司只要触及了这些行为,就会被认为是滥用。因此,举证责任是颠倒的。这里适用的是“有罪推定(gesetzliche Schuldvermutung)”,?MB公司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从宪法的角度来看,鉴于上述许多要求和禁令在竞争上的模棱两可,这种举证责任倒置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里涉及国家干预的问题,而国家必须根据宪法的一般规则证明国家干预的正当性,而非反过来要公司或者公民来证明。但根据《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第2款第2项,这些公司至少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客观地为他们的行为正当性加以辩护。
《数字市场法》展示了还可以比德国立法者在《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中做得更糟糕的情况。与《数字市场法》相比,《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是审慎和权衡的典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数字市场法》已经使用了一种“一刀切(Holzhammer)”的方法来定义守门人的地位,因为守门人的属性仅仅是基于规模推断出来的,甚至都没有定义其所守的是什么门。不幸的是,《数字市场法》在要求和禁令的执行方面也延续了这种方法。其为了尽快实施,认为这些要求和禁令应该直接依法适用,易言之,它们应该是“自动执行的(self-executing)”的,并根据“一刀切(one size fits all)”的方法适用于所有市场和所有守门人。换言之:所有的守门人都被“混为一谈”而不顾及不同的产品、商业模式、市场以及实际市场竞争情况。若一家公司被宣布为守门人,它必须在六个月内履行《数字市场法》第5、6和7条的所有义务,并加以证明(《数字市场法》第3条第10款)。虽然欧盟委员会可以通过行政行为更为详细地界定《数字市场法》第6条和第7条的要求和禁令,但这并不是必须的(《数字市场法》第8条)。这些公司亦不具备客观地为自身行为进行辩护的可能性,也无法证明例如若不履行这些要求和禁令并不会限制竞争、创新和消费者福利,反而可能会促进它们。在法律上就已将“开脱或无罪证明(ist gesetzlich ausgeschlossen)”排除在外。即便按照法律执行将明显不利于促进竞争以及提升消费者福利,公司也必须遵守这些规则。不过在极为例外的情况下可能得到豁免(《数字市场法》第9条),但这也只能适用于保卫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数字市场法》第10条)。简言之,法律适用速度优先于法律适用质量以及对基本程序性权利的保障。这与数字经济的复杂性是不协调的,在现实中,它也不会比德国的方法更快地产生影响,因为它引发的法律纠纷可能会持续多年,就像Google Shopping诉讼那样。
六、结论
当《数字市场法》于2023年生效时,数字化的西方有消亡的威胁吗?当然不会!对于那些对数字化和反垄断法感兴趣的人来说,好消息是,通过《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尤其是通过《数字市场法》,肯定会带来新的一轮法律咨询和解决权利争端的需求。反垄断专家将继续是一种非常稀缺的高薪职业。
《数字市场法》是否会促进竞争,数字冠军会不会在德国和欧洲涌现呢?也不太可能!因为德国或欧洲的巨头无法通过“监管(herbeiregulieren)”而产生,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欧洲之所以尚未出现这样的巨头绝不是因缺乏监管,原因可能恰恰相反。
守门人监管本身可能非常有意义,甚至在某些领域可能是必要的。但是,监管不应该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而应该量体裁衣。德国法律在这方面明显比《数字市场法》更好地满足了这一要求。
整件事情让人想起一段描述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之间心态差异的妙语,它诞生于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其中一个版本是:当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集结在战场上对抗拿破仑时,局势不利,普鲁士将军让他的同事报告说:“情况很严重,但并不是没有希望(Die Lage ist ernst, aber nicht hoffnungslos)。”奥地利人回答:“情况是没希望了,但并不是很严重(Die Lage ist hoffnungslos, aber nicht ernst)。”欧盟委员会以普鲁士的方式,将形势描述为严重但并非没有希望,并试图通过《数字市场法》来应对。但这种情况更接近于奥地利式的“无望但并不严重”:因为试图通过“监管方式(wegregulieren)”消除GAFAM公司或削弱它们的霸权似乎是一项相对无望的努力,只要终端用户仍然偏爱它们的产品。
但正因如此,局勢也并不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严重,因为被认为是“守门人(Gatekeeper)”的公司后来也被证明是Snapchat、TikTok或Zoom等公司的“敲门人(Gateopener)”。这些新兴公司能够克服经济上的重重险阻、实践中的逆境以及政治上的悲观,仅仅是因为它们比那些势不可挡的、看似坚不可摧的“巨头(Platzhirsche)”及其产品都更好。这就是竞争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
Google, Facebook & Co: The Power of Data and Algorithms in the Context of Competition Law
Abstract: The triumph of the internet over the past 30 years has enabled numerous new services and brought significant benefits to consumer welfare. It has also created many new opportunities for businesses. However, concerns have arisen that some major digital companies and the algorithms they use could gain too much influence. These issues are being addressed worldwide through various laws. Potential competition problems are being tackled through antitrust and regulatory law. In Germany, the legislature revised the Act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GWB) twice (in 2017 and 2021) to better address digital markets and business models, with a focus on improved abuse control. At the European Union level, the legislature has opted for the regulation of digital gatekeepers through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DMA), which has been in effect since May 2, 2023, and sets out numerous prohibitions.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German regulations, especially § 19a of the GWB, with the DMA and critically evaluates both regulations.
Keywords: Internet; Algorithms;Digital Incumbents; Gatekeepers; Competition Law;German Act Against Restrictions of Competition; 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