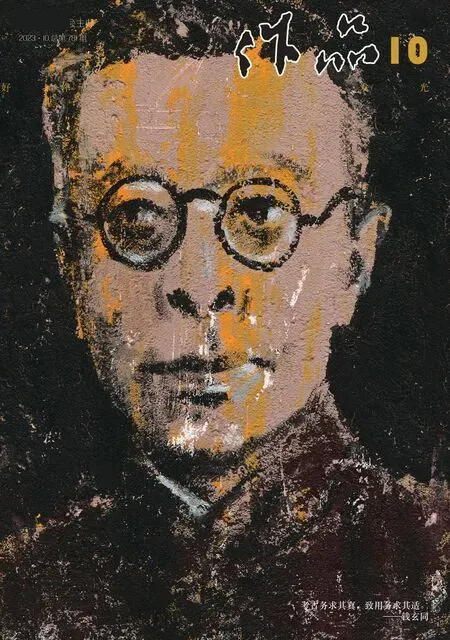复仇记(短篇小说)
杜峤
1
下午睡醒睁眼,新郎告诉我已经过了两天两夜。一骨碌坐起来,几乎叫出声。颈椎像把断剑,直刺头颅。左右臀部火燎一样疼。两膀脱力。大腿内侧酸痛。会阴发麻。一点点撑坐起来,新郎喂我喝两口水,意识被凉意一激,清醒多了。我让他扶着慢慢走出去。天光云影,近树远山,都沉静下来,凝固下来,让人不习惯。之前几天,眼瞳里只有白茫茫盖下来的日头和灰扑扑欲尽还生的国道,两侧的风物因疾驰与高温变得血肉模糊。从南京出发,经湖州、杭州、宜春、安江、贵阳、富源,新郎在昆明接我们。一辆二手嘉陵JH125L,近三千公里,整整七天。他妈的,这罪我这辈子绝不受第二次。
得找个机会复仇。这念头就在这时候萌发了。
我爸呢,还躺着吧?我问新郎。他摇摇头,笑着说,爸精气神可大好,早你一天醒,吃完午饭下楼看花去了。穿过小区里植物迷宫般的曲径、片片锦云缠挽的古罗马风大理石花架,终于,我们在一面三角梅花墙下找到他。他像早知道我们要来一样,回头缓声吟诵:昆明的三角梅/展在空中/像燎原的大火/南京的三角梅/栽在盆里/像蜷腿的雕塑。新郎鼓着掌阔步走上去,说,爸,一来昆明就作出这样的好诗!父亲说,我一直希望女儿嫁个昆明人,或者嫁个诗人,结果你看——不仅是昆明人,还懂诗!新郎一脸骄傲,说,昆明确实是个好地方,不仅是文化高地,也是人间仙境。滇池,石林,西山,翠堤春晓,金马碧鸡,联大旧址……太多了,等周末办完婚礼,我俩带您到处都游一遍。新郎数着指头说景点的时候,我看到父亲喉结翻动,连咽口水,似乎有点紧张,又有点疑惑,像个听老师报成绩单的学生。新郎每说一个景点,父亲就不由自主地点一下头,但似乎一直到最后,都没听到想要的答案。新郎看出他的异样,不明就里,停嘴看他。父亲试探性地问,这儿,有……抚仙湖吗?我听出他的声音有点颤抖,像夜风中的叶子。新郎说,好像是有这么个地方,但我没去过。父亲补充道,应该就在昆明旁边,不会错的。新郎跑上楼去查地图,一会气喘吁吁奔来说,查到了,距昆明市区大约70 公里,我骑摩托载您,一个半小时。有首同名歌,歌词写得有点像诗:转身而去的瞬间,是天涯,你说这一刻,就在这一刻。他掏出一只紫色三棱柱形MP3,按下开关。歌声袅袅中,父亲好像完全笃定了,是的,就是这个抚仙湖,再没第二个抚仙湖。新郎连忙附和,是了,抚仙湖这么美的地方,爸您沿湖走几步,诗思一运,好诗就像抗浪鱼一样划破湖面纷纷跃起,像春草一样从湖畔湿泥里争相冒出来。等一办完婚礼,我们就陪您去。
没人注意到我略带鄙夷的厌烦目光。他俩无论聊什么,最后都会回到“诗”上。父亲业余写了几十年诗,新郎大学读的中文系,在文学社写过几年诗。他们之前写信互动,新郎给父亲买了一台爱立信之后,父亲就戴上老花镜,把这些年写在小纸片上的诗一首首读给他听。当一个老人(同时是准岳父)这样艰辛地要你看诗时,吹捧,无论出于情分还是怜悯,都显得合理起来。新郎还谙熟更自然、更高级的吹捧技巧,即吹捧老人的品位。您最喜欢的诗人是谁?然后把那个名字重复两三遍(最好换成昵称或爱称,就像清人总叫苏轼“坡仙”,这种诗迷间的暗号总能迅速拉近彼此的距离),太巧了!我也爱他!可能带有主观性,但我偏执地推举他为当代最棒的诗人!新郎在跟我复述这段他预想的对话时眉飞色舞,好像他越卖力地寻法儿恭维我父亲,就显得越爱我。但问到实际情况时,他却有些蔫,似乎开始怀疑自己屡试不爽的阿谀技巧。爸每次都守口如瓶!他说,我想不通,一个爱了几十年诗的人,怎么会没有自己最挚爱的诗人?如果有,又怎么能忍住,不让那个名字脱口而出?
诗不诗的我不关心。平时可能会礼貌性地关心一下,现在则心怀芥蒂。我自认不是什么娇花弱柳,但至少是一个即将参加婚礼的新娘吧。途中吃住都是就近就简,包火腿肠的塑料皮和半白的女人发丝,都在炒面或盖浇饭里吃出来过。每晚一找到小宾馆我就倒在洗洁精味与精液味混杂的床单上昏昏睡去,而父亲脖子夹只手电筒,捧那本牛皮本,身形拗硬得像把被卡住难以收回的折叠刀,几乎彻夜不眠。凌晨四五点就把我从梦中摇醒,说,要准备出发了吗?我边打哈欠边抱怨,他说,我们既然要回乡,就应该日夜兼程。在贵阳的某片山旮旯里迷了次路,导航所指被重重山壁截断,我在不可挽留的夕光和随之篡位的厚重夜色里几乎急得哭出来,而父亲从后座跳下来,说,绸缎般的风从抚仙湖上吹来,疲惫的身躯被托起时,我们都变成在异乡飘零的雪花。如果没遇见村民指路,那晚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实上,整个旅途中,这种反差已成一种常态。阳光有种密不透风的裹覆感,汗滴悬在下巴上,又痒又腻,歪脖子用肩峰蹭,冲锋衣不吸汗,我一直想停车扯掉手套,拿条毛巾好好揩一把。父亲则情绪高涨,一反往日的讷言,小孩一样望天指地,大惊小怪地唤我看飞掠而过的景色,好像这样的路途比在机舱里看时尚杂志更舒坦一样(如果是我一人独行,本应如此)。有几段颠簸的石子山路,我怀着某种隐秘的报复心理(彼时,我想的还只是报复,而非复仇),恶狠狠沉身压轮碾过去,但父亲似乎毫无感觉,明明后座比前座更颠簸啊。现在回想起来,我终于有点摸清了他的状态,他像打了鸡血,像无酒自醉,像误食了令人致幻的毒蘑菇,像灵魂出窍入了无人之境,像个谵妄患者,又像个圣徒。我终于明白过来,这种不拘小节的激动与亢奋绝不是因为他即将参加我的婚礼、见证我的幸福时刻,而是因为这是他这么多年第一次远行,并且即将见到他魂牵梦绕的抚仙湖。想到这儿,嫉妒不可抑止地滋生漫衍开来。嫉妒什么呢?嫉妒父亲像没事人似的,我却浑身酸痛、元气大伤?嫉妒他这种心荡神驰、超世绝俗的精神状态?还是嫉妒他即将实现理想?嫉妒抚仙湖,嫉妒它抢了我婚礼的“风头”?嫉妒诗,嫉妒它霸占了我父亲的生活?有太多可以嫉妒的事物了,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种。但确凿的是,这种嫉妒成了我下决心复仇的最后一根稻草。
2
父亲在我婚礼的那天晚上喝多了。他把我的手交出去时一直不敢紧握,我于是也就虚虚地搭在他的手腕上,隔着纱,一层西服,一层衬衫,还是可以感到偶尔的颤抖。你知道,人老了就时常容易颤抖。我不想去探究这种颤抖的含义,拘谨,紧张,激动,不舍,还是愧疚。这么多年,我和父亲完全没有父女间的亲热(贴心与娇纵之类的东西),更像貌合神离的夫妻,在一个屋檐下形同陌路。有好几次,我想抢过话筒吐出一些“爸,你这辈子是更爱诗还是更爱我”之类的质问,我几乎能摹想出他那张因无法回答而尴尬涨红的皱脸。但很庆幸我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不想打草惊蛇吧,我潜意识里认为这只会是一个小小的惩罚,作为复仇还不够分量;也可能我注定就是一个蹩脚的复仇者。从小到大,我总是不懂如何找准时机发泄积怨,只会在每次错失良机后窝进被子边回想边默默拧紫自己大腿。这种笨拙让我的社交生活如有神助,也帮助我和父亲和平共处了这么多年。但现在,我不想再这样窝囊地活下去了,复仇将重振我生活的士气。众所周知,复仇是一项古老的事业,且从古至今都非常人所能为。踩在巨人们的肩膀上,我的复仇美学自滥觞之始就臻至成熟:我比勾践卧薪尝胆的时间更久,比豫让更擅长伪装与藏匿,比哈姆雷特更浅薄也更坚决,比伍子胥运气更好。我明白我需要极大的耐心与克制力,屏息凝神,藏拙守愚,一刀致命。那刀一定要短、快、狠,不在无关的血肉间滞留,目标只有一处:心脏。古话说得好,“匕首寸铁,刺人尤透”,我不要盛大的、鲜血喷溅的劈砍,只偏爱精微的、直击人心的穿刺。我要他心慌、心酸、心荡、心悸、心寒、心痛、心碎、心死。而此刻,虽然父亲上台前就已微醺,走路略带摇晃,但他的发言完整得体,真诚动人。我找不到机会发难,或者说,直觉告诉我不要打草惊蛇。
父亲清清他常年被滞涩诗句噎堵的嗓子,开始说:
在祝福他们之前,我必须先感谢这对新人。熟悉我的亲朋们知道,我是个被工业文明唾弃的废人。年轻时的一次创伤让我跟绝大多数机动车绝缘。人包铁尚可,铁包人不行。高速旋转的车轮与地面每一寸或大或小的坳洼或凸石摩擦产生的颠簸,会把我的肾结石震成齑粉,让我瘫软成一滩水蛭。被钢铁包裹的窒息感,会把我拉回梦魇,让我的心脏变成跃跃欲试的活火山。这种症状随岁月流逝愈加严重。按理说,我这辈子就被困在南京郊区的小镇了。但正如你们所见,我出现在了昆明,出现在你们面前。这是因为我的女儿,今天最美丽勇敢的新娘,骑一辆二手摩托载我翻山越岭来到这里。而我们儒雅俊朗的新郎,这些年来以一种老虎饲养员的勤谨陪我一个老头子谈诗、读诗、写诗,重新点燃了我的暮年岁月。他还说,明天一早他俩就陪我去抚仙湖。我没有儿子,他就是我的儿子。新郎新娘,我的儿女,他们用爱拯救了我,把我带到昆明这个梦乡,明天还将把我引向那片梦乡之梦乡,那个被称为“抚仙湖”的地方。从少年起,我就在脑中一草一木、一时一刻地摹想这一天。现在,这一天终于近在咫尺了。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它又与我的儿女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如此临近,不能不感叹这是多么伟大而美丽的缘分。我有点激动,再说下去可能会语无伦次,但我必须要说出最后的祝愿:祝我眼前的这对新人永远健康,无论身体或魂灵;永远幸福,无论青春或衰老;永远快乐,无论深刻或肤浅;永远心意相通,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永远能看清自己的内心,面对生活像面对镜子;拥有宽恕一切的能力,永不生怨怼;心中永存美的种子,像一首诗一样活着,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活着。
说实话,听到有些句子的时候我由衷为他高兴,听到有些句子时又有点感动。有一瞬间我或许心软了,产生了“要不就不复仇了吧”之类的想法。但他说完最后一句时,我蓦然醒悟,自始至终他的心里只有诗,我们只是诗的附属品。我在桌下狠掐自己婚纱下的大腿,提醒自己女人最珍贵的品质就是清醒与决绝。这是我自己悟出来的,没有任何人教。在我尚未萌生记忆时,就被父亲从辽州带到南京,从未见过母亲的脸。几十年来,父亲对此只字不提。在我想来,要么是父亲抛弃了母亲,要么是母亲背叛了父亲。他要么是个薄幸的男人,要么是个窝囊的男人,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可想而知,为了掩饰懦弱无能、转移痛苦绝望,他将全身心完完整整地交给了诗,一点都没留给我。当然,我也恨母亲,不恨她背叛父亲,而恨她不够清醒决绝,不然不会有我。
但我依然和新郎一样,在父亲讲述时用眼睑蓄着热泪,讲完后拼命鼓掌,把手心拍得鲜红。父亲下来后,我迎上去与他拥抱,指甲在他的西服衣领上留下五个印。接下来我们都喝了很多,新郎特意准备了几瓶换装雪碧的国台,跟我一桌桌敬过去。新郎父母都喝的雪碧,父亲不要,梗着脖子硬喝。新郎想劝,我想,越醉越容易露出破绽,就说,我爸今天高兴,让他敞开喝吧。奇异的是,今晚父亲的酒量远超平日,喝到最后一桌也没有眩晕或身体发软的势头,只是越来越亢奋,好像在他那个超脱世俗的境界中越升越高。最后,新郎家属去招呼留至最后的一撮客人。父亲把我们俩叫到靠近舞台边缘的角落,找一桌已散的客席坐下。他坐在我们对面,中间隔着乱葬岗一样的残羹冷炙。父亲说,今天你们结婚,我没准备什么礼物。不是忘了,是觉得你们什么都不缺——哈哈,你们今天都收了多少蚕丝被和德国进口炊具?你们的生活是如此丰饶,至少看上去是这样。我所能做的只是把我自己完整交给你们,我的秘密,我的核心,我的罪恶,我的幽暗,我的愧怍,我的孤独。一切迷人或危险的东西,都献给你们,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这是一个故事,也不算故事,只能说是一段往事。但它能解决你们以往的所有疑惑、一切因为我缄口而产生的隔阂与猜忌。它是一切的缘起,是神的赐予,也是魔的诅咒。你们有耐心听吗?我和新郎对视一眼,看到彼此激动好奇与郑重紧张交缠的神情。我深吸一口气,说,爸,您说。
3
他说,你们知道朝圣吗?我俩对视一眼,我迅速摇头,新郎只好充当抛砖引玉的捧哏,跪行去布达拉宫?
他摇头,那个时候西藏还没现在这么火。不过刚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也以为是那种朝圣。
1969 年冬,新年刚过,隔壁林场的张永全就死了,死于火铳。除了个别猎户,只有民兵队有火铳。上个月调查团来辽州,组织过一场辩论会。具体辩的什么已经记不清,只记得张永全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好像十分激动,一共站起来三次,手指像枪尖点扫,出了老大风头。第二天各林场就传开他外公偷渡到台湾去的消息。他说他立即写信到家里问清事由,请大家不要相信谣言。但很快他的死就没人理会了。好像一夜之间,林场的年轻人,尤其是知青,都被“朝圣”这个词攫住了。它好像有种魔力,任何一副唇齿,一旦嘟囔着把这两个字说出口,就会上瘾般不停说下去,坐树墩上休息时说,回屋烧柈子时说,啃每一口烤软的冻馒头的间隙也说。说的时候,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毕剥燃烧的松明子。但与这种狂热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讨论在实质内容上几乎毫无进展。几天过去了,仍然没人能说清朝圣到底是什么,只模模糊糊地知道它跟诗有关系。
正月十五下午,我们拿一张黄大仙皮换了半包水果糖,脚步轻快,准备晚上到张琳琳家吃饭。上午我旁敲侧击问了几次,王哥都没接茬,神色凝重,显得忧心忡忡,敷衍我说不知道。我才不信,别人不知道朝圣,王哥指定知道。无论是我俩原来待的三沟河大队,还是现在被借调来的万年青林场,提到诗歌这一块,王哥就是权威。他看我嘟着嘴耷拉着眼皮,露出点笑说,琳琳说晚饭有狍子肉吃,张叔昨天打到的,咱们今晚准能吃圆肚子。我不为所动,甚至听他“琳琳”“琳琳”叫着更不舒服。上次他把跟我打赌赢来的像章转手送给张琳琳,我气到现在也没消完呢。怄啥气呢,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憋屈。前半顿饭吃得没啥印象,嚼肉像嚼木炭,“朝圣”和“琳琳”两个词仍然在我脑袋里横冲乱撞。酒喝了几轮,张琳琳说我有点蔫,笑着问我是不是昨晚跑马(梦遗)了,边说边用尖刀割了块狍肝扔进碗里让我补补。我脸唰一下涨红。王哥这时竟开口给我解围,这小子是听说朝圣的事,整天亢奋得吃不香睡不着。我霎时间精神了,问,朝圣,到底朝的什么圣?张琳琳看看王哥,王哥看看张琳琳。显然她已经知道些什么了。一种奇异的妒意一闪而过,但很快就被求知的渴望冲散。在我炙热目光的央求下,王哥终于挥挥手,清清嗓子,示意我把头凑过来。我在余光里看到张琳琳摇头皱眉,在桌下掐王哥大腿,但王哥还是开口了。
月球你知道吧?他说。我点头。月球是当时最火的诗人,每个知青都爱他的诗。王哥的朋友遍布天下,每月能收到几十封信,每逢月球有新诗,他都能最先搞到。更能耐的是,每次他搞到的诗都比别人多,比别人全。好像月球写诗时他就站在旁边,将其愿意公开的和不愿意公开的作品都一股脑记下来。我们反复讨论琢磨,都觉得多出来的这些诗才是月球作品中的精髓,像《烛光》《我们离开的地方》《抚仙湖三部曲》等等。我们把诗抄下来,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晚上各自回宿舍读。白日里,我们休息时最常讨论的也是那些晶莹剔透的句子。王哥曾问我,你说月球最好的诗是哪首?我想了半天,不知道,都好。他说,你就想想,哪首写得最美?我又想了半天,还是说不出来。好像无论什么事物,一旦落到月球笔下,就像蒙在茫茫大雾中,浸在粼粼波光里,射向它们的光线不是被消解就是被弯曲了,完全辨不出其真实面貌。还想辨别出哪个最美,就更不可得了。王哥看我久久痴想不作声,便拍拍我肩膀叹口气,一点悟力都没有。然后站起来,上前两步,宏声说出自己的答案:《抚仙湖三部曲》是月球最好的诗,它比月球其他任何诗都要好。他说得斩钉截铁,每个字落到地上都发出铮铮金石声,至今回想起来仍让我心服。跟他在一起时,我读诗的声音往往也因被感染拔高了几十分贝;而回屋一个人读的时候,复又压嗓收声,像只口渴的鼹鼠。现在回想起来,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是隐隐觉得美的东西都沾点反动,但只要有王哥在的场景,那种懦弱和畏缩就被冲淡了。
月球和朝圣有什么关系呢?我问。王哥又用那种“一点悟力都没有”的手劲拍我的肩膀,说,朝圣总要有个目的地吧。我老家的哥们上周写信过来,说月球就在昆明,已经有不少知青从各地逃出来,去昆明附近的抚仙湖朝圣。湖畔有片牛棚,月球就住那里,近作《抚仙湖三部曲》就是这期间写的。天色刚灰亮时,他就在“展身手,战湖荒”的口号声中惊醒,被几百具无灵魂的躯体裹挟着去翻荒地。诗人用羸弱的臂膀挥高铁锨,但每次只能入地两三寸。汗从手心脚底渗出来,由热变冷,由冷变热。被大雪覆盖的茫茫四野像倒置的天空,将诗人囚禁于无边无际的囹圄。一个诗人,为何要经受这等折磨!他立在抚仙湖畔,像一只蚁,又像一尊神。抚仙湖结成冰湖,变成一面可鉴天地、可鉴众生、可鉴自身的大镜。诗人悄然离开狂热的人群,奔到湖边跪下。他像是第一次来这儿,又像是回到故乡。他不敢看冰面映射出的世界、人群和自己,闭上眼开始挥动手中的铁锨,一下比一下用力,冰面的裂隙逐渐由细碎到深长。就在他睁开眼,看到长久未见天日的湖水在这个冬天第一次揭去面纱的那一瞬,两膀蓦然被巨力向后锁住。诗人的逃离被发现了。人们像拖一件农具般将他倒着拖回去,回到看不见湖面的地方。但他知道自己看见了。两只女人的眼睛向他微笑,两条女人的白臂像绸缎一样向他抛掷过来,一个女人像湖心嘟嘟沸腾冒泡般的喃喃预言。就像《抚仙湖三部曲》里写的那样:“仙子一样的湖水,和湖水一样的仙子。接引一样的抚摸,和抚摸一样的接引。抚仙湖一样的明天,和明天一样的抚仙湖。”
听他说完,我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拨动了,怦怦跳得厉害。但还是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说,昆明不是叫春城吗,冬天能有那么冷?王哥拍拍我,有诗的地方就有雪。就像此时此刻,我们读诗的声音越亮,雪就下得越大。我被这些话震慑了,愣了半晌,第一次对生活与命运产生了疑问与迷茫。狍肉再吃不下一块了,张琳琳弄来的土烧也再喝不下一滴。后半个晚上我一直浑浑噩噩,依稀记得张琳琳和王哥在争论什么,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张琳琳站起来,用几乎是斥骂的语气说,你就是个烂人,我是瞎烂了眼,你让我怎么办?说完瞥我一眼,摔门而出。放在平时,王哥跟张琳琳关系出现裂痕,我指定心中窃喜。但现在好像都不那么重要了。我和王哥彼此扶持着出门,走进诗里那样的茫茫雪原中。我像个毫无主见的木偶般问他,哥,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去抚仙湖朝圣吧。好像有两个声音。在他张开嘴唇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在心里默默说了。但随即就被自己吓了一跳。这成什么了?林场这边视我们如仇寇,探亲假肯定批不下来。直接去?跟逃兵没有两样!抓回来就得关禁闭,想想那帮人的德性,别打算全须全尾出来。就算出来,这辈子都回不了城。如果没被抓,堕落成盲流,粮油肉票没有,工作找不上,游魂一样能活几日是几日,又有什么盼头。我把这些顾虑一股脑吐出。王哥也醒了酒,或者说他根本没醉过?这些事情我全想过,但其实全没必要想,因为这些都是抵达抚仙湖、见到诗人以后的事了。你见过哪个信徒会想朝圣之后该怎样?我怔了一下,说,那抵达了又会怎样呢?见到诗人又会怎样呢?他说,那时候你就不是现在这个你了,孔老二都知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到那时候,再把你抓回来被民兵队毙了你都愿意。我有些怀疑,还是觉得风险太大,最好从长计议。王哥走近一步扣住我的肩胛,生疼,我下意识想拨开,却发现他的手像铁石一般。没时间了,他咬牙切齿地说,再不走,你我就是下一个张永全。我眉头一皱。他说,我怀疑最近要有动作,专打出头鸟。张永全一死,下一个就轮到我。你跟我在一块儿,也落不着好。我沉默不语,有点窝火。他问,你爸以前在当铺里做过朝奉吧?我说,那是他十几岁的时候,而且不是朝奉,是学徒。哥你什么意思?他拍拍自己胸脯,我爸是二地主。能派到这个地方,我们这一批里头,哪个身上没有点原罪?不走就是砧板上的肉,切片还是剁馅,今日吃还是明日吃,全看人家心情。我说,不至于吧?有人整咱们,也有人照顾咱们,像张叔和琳琳姐。王哥冲我吼,你他妈到底爱不爱文学?爱不爱诗?我终于哑口无言了,嗫嚅着问,那你说怎么逃?他说,计划早就有了,打磨得天衣无缝。火车每月运一次木材,这个月就是明天。我们先回去收拾东西,打个小盹,养精蓄锐。两小时后起来,预先潜到铁轨右侧的密林里。贮木场的卡车一趟趟把木材运过来,装进车厢。他们走后,司机会打亮手电检查绑绳松紧,排除木头中途滚落的可能。确认无误后,他会返回车头,启动火车。他往回走到火车发动的这段时间,我们从林中钻出,攀上车厢,动作一定要快。等出了山,我们就跳下来,记住一定往前跳,落地一瞬间小跑几步,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刺猬,团身滚几圈,一点伤没有。之后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最后他说,那半包水果糖,临走前放到张琳琳他们家门口,留作纪念。我说,你去放吧,她跟你好。他笑着说,你去放,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我凌晨两点就醒转坐起,写了一张纸条:无论天南海北,愿革命友谊永存。水果糖剥了一颗含嘴里,甜得不真实。剩下的都包起来,纸条塞进去。准备把王哥喊醒,却发现他一直没睡。
后来怎么样了?你们到抚仙湖了吗?见到月球了吗?
父亲摇头,那天我们从密林中钻出来,王哥在车厢外壁一蹬,两手上攀,腰腹一弓一弹,就猫一样落在一根根合抱粗的原条上。我那时身矮力弱,试了几次都上不去,眼看司机就要走到车头。我绝望地压嗓跟王哥说,我去不了了。他没说话,从车上跳下来,撑车壁扎马步,把背弓成一个土坡。我踩着他的背,头终于与那些伟大的巨木齐平。木头上的枝丫都被削净,不好着手。我在黑暗中拼命摸索,摸到一根粗绳,触手牢实,像抓到救命稻草,攥紧把身体悬住。直到把绳子拽得松脱,终于爬了上来。王哥也在火车开动前一瞬跃上来。我俩一人一边瘫倒在巨木和车厢的间隙,放声大笑。笑声被火车的隆隆声掩住,没人听到。但很快我蓦然停住,开始在黑暗中摸索刚才那根绳子,没有,从头摸到脚都没有。我带着哭腔对王哥喊,我们回去吧,我们不去朝圣了。他大概没听清,问我有什么事,我努力抚平声音,说没事。我把身子贴紧冰冷的车壁,闭上双眼,像蒙头扎进沙海中的鸵鸟。但全无作用。老人说一个人极度恐惧时感官会比往常敏感数百倍,没骗人。车轮每次与铁轨的媾和与告别,车厢每次与隆隆声融为一体的颠簸震颤,车头每次经过铁轨接合处发出的咯噔声和顿挫感,都事无巨细地从四面八方渗入我的毛孔,成为我日后恐惧的根源。我开始祈求自己的性命,向毛主席,向月球,向狐黄白柳灰,向我所知的一切神祇,好像真的在进行一场朝圣。什么都没有发生。又过了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车身转弯时有根巨木往旁边滚了一下,把王哥压死了。他被碾成一张新犁的地皮,像泉眼一样汩汩冒血,一句话没说就咽气了。我当时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往前跳,落地一瞬间小跑几步,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刺猬,团身滚几圈,一点伤没有。跑回林场时,天灰蒙蒙刚要亮,没人发现我离开过。几天后王哥尸体被找到,问我,我说,他想回家探亲,拦了,没拦住。晚上张琳琳来敲门,问,糖和纸条是你留的吗?我说不是,王哥的。他临走前说要感谢你们家的照顾。她说,是你的字,我认得。我说,王哥说他字丑,托我写的。她说,他根本不是探亲,是丢了魂去朝圣,我知道。他原先要带我走,被我扇了一耳雷子。昨晚他嘱托你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张琳琳没再说话,走了。一个月后,张琳琳结婚,跟隔壁林场的老徐,组织上撮合的。婚后,早产诞下一女。老徐婚前是出了名的老面兜儿,婚后却发了凶性,经常跟张琳琳动手,骂她狗娘养的婊子,还扬言要将女婴溺死。再后来,母女从林场失踪,自此音讯全无。我从此在那片土地再无牵挂,拼死逃回南京。再后面的事情,你们都知道的。
后来我感觉啊,从1969 年开始,我就不是一个人活了。我做不到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王哥是我的另一半,是真正意义上的另一半,我的一半是个庸碌男子,一半是个诗人。我的日子是我自己活的,我的诗是王哥借我的手写的。不是你们今天说的另一半,我和你妈只算萍水相逢,她生前一直都明白。人这辈子很多事一旦发生,你周围的景物就会迅速变幻,变成另外一个世界。即使你当时没有意识到,但变化不会因此停止,你终将被揉进另一个人。过去三十年里,我不坐车,不用木制品,屏蔽有关月球的一切,我的生活慢慢被诗侵蚀啃噬。到后来,读自己写的每一个字时,我都要强忍呕意。但我没法不写。是你们拯救了我,明天之后,我就再也不用写诗了。他的声音慢慢平定下来,像跳水运动员跃下后逐渐静止的跳板。
4
讲完之后,父亲似乎年轻了十岁,带着一种容光焕发的疲惫,好像刚射完精一样。我们也都很疲惫,有很多话想说,但最终又没说。
躺在婚床上,我用手抚摸新郎的胸膛,但他好像没有反应。我侧过来,看出他有话想说。说吧,我说。爸说的故事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困意一下消散。新郎说,我大学读的中文系。那时我脑筋很死,文学史背得烂熟。过了这么多年,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漫漶了,但有一点我很肯定:月球从没来过昆明。要是他这么大的诗人来过昆明,我一定有印象,昆明一定有印象。我一屁股坐起来,启动电脑,打开谷歌,输入“月球”,找到它属于诗人的官方词条。月球,山东鱼台人,朦胧诗代表人物,被誉为“朦胧诗鼻祖”与“新诗潮诗歌第一人”。再往下翻,1969-1971 年,月球与21 名北京知青落户山西汾阳杏花村,其间诗作被朋友及插队知青辗转传抄,流行全国,被称为“知青诗人”。曾有知青从全国各地赴杏花村拜访他,称为“朝圣”。因为不堪劳扰,月球于1973 年被北医三院确诊为精神分裂。接着,我在整个网页搜索“昆明”“抚仙湖”,显示“未找到与搜索项相关内容”。我又找到《月球诗歌全集》,搜索发现,他从未写过《烛光》《我们离开的地方》和《抚仙湖三部曲》。脑中轰轰雷震之后,狂喜如喷泉涌现。我知道那把匕首已经铸就,复仇的时刻即将来临。我要把血淋淋的真相掷在他眼前。所谓“朝圣”,不过是一场拙劣的模仿秀。所谓为诗歌献出生命的少年诗人,不过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我已经想象出父亲的惨相:精神矍铄的面庞委顿如腐烂猕猴桃,吟诗的唇舌僵冷如旧书签中封存的陈年花瓣,眼瞳从两粒珐琅彩珠变成两颗无花果果核,浑身病痛从精神麻药的镇压下逃脱出来。他终究会变成一个正常的、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此之后,我会摒弃前嫌,拾起子女的孝悌本分与新郎一起赡养他,一切都会如抚仙湖的湖水般静美。但意外发生了,当我在黑暗中叩开房门,残忍地将这一切告诉父亲时,他却显出一种奇异的平静,问,你想不想知道自己的身世?
次日,我们一起去了抚仙湖。他第一次坐轿车,像小孩一样频频将头伸出窗外。湖水莹滑,微风如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