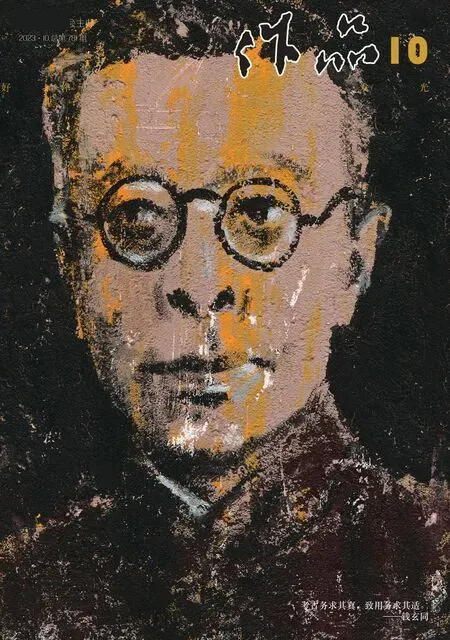康坎小说评论小集(评论)
熊焕颖 李天奇 张男 李思雨 邓程浩 张同远 杨林鸿
越界、缝合与奇幻——“博尔赫斯式”的康坎小说
广西/熊焕颖
对于一位小说新手,我不想谈他形成了什么风格或者有什么特色,因为这不仅可能助长吹捧的批评风气,也有可能粗暴地否定他写作的开放性以及风格生成的无限可能性。但在反复阅读康坎发表在《作品》杂志的五个短篇之后,我还是做出一个直率的判断:这一批小说确实是“博尔赫斯式”的。这个判断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康坎找到了一位可以模仿和致敬的伟大小说导师;另一方面是他确实把握住了博尔赫斯小说的某些品质并自如地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康坎小说呈现出的“博尔赫斯式”品质正是越界、缝合与奇幻。
第一,越界。托多罗夫在《奇幻文学导论》中将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的小说称为“奇幻体”,并指出:“奇幻文体允许我们跨越某些不可触及的疆域。”博尔赫斯小说的重要品质之一便是“越界”,跨越历史与虚构、科学与想象、真实与虚幻、理性与非理性,甚至生与死、阴与阳、过去与未来等边界。显然,康坎是不断尝试越界的写作者,他在小说中展现出了超越现实生活中诸多界线的冲动。在《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里,大学生“我”按导师余勒提供的线索到清源山的一处洞穴寻找卡夫卡的手稿,但是不管计划多么周密、准备多么充分都无法寻觅其踪,反而是在放弃理性、放弃现代工具、放弃推测方向之后,竟凭直觉找到了洞穴并遇到“永生”的清源山野人。进而言之,该小说要探讨的问题似乎是如何实现从文明到自然、从现代到荒野、从理性到非理性等越界,让现代读者能重新体验自然、荒野和非理性。《麒麟,或消失的劳伦斯》则通过讲述劳伦斯如何写小说的故事到“我”祖父去世办丧事的转变,试图跨越科学与迷信、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等边界。康坎的其余三个短篇无一不是处理了类似的越界问题,带领读者进入边界森严的现实中不可能触及的疆域。
第二,缝合。由于在奇幻小说中发生了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越界,那么如何缝合这条横贯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裂缝便成了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在博尔赫斯小说中我们往往能看到他在短小篇幅中来回穿梭于不同边界,自由地处理历史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真实与幻想的关系,如《小径分岔的花园》开头从《欧洲战争史》英军推迟进攻德军的原因“滂沱大雨”引出虚构的余准博士证言,便是巧妙地缝合了历史与虚构的关系。康坎在小说中同样意识到在越界之后谨慎处理好这些边际性问题的重要性。他小说中反复出现“荨麻疹发作”的情节便是一种重要的缝合手段。我像小说的人物一样也患有荨麻疹,深知这种病的诱因极其复杂和神秘,甚至连现代医学都无法给出明确解释,而荨麻疹的这种特征无疑是一种缝合越界裂缝的良好媒介。当然,康坎在小说中还用了其他缝合手段,比如《阿德拉商店的招牌》中通向仓库的拥有“异乎陡峭的梯级”和“好像悬在半空”的木梯又如《地下酒馆或斗狗场》中通向血腥残忍斗狗场的“六边形古井”。但不管通过什么媒介或手段去缝合越界后的裂缝,至少康坎已经大胆地给出了自己特有的处理方式。
第三,奇幻。在访谈中康坎坦言自己越加相信的是“语言本身即骗局”,这个看法与传统的“文以载道”“反映现实”等观念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也更符合奇幻文体的特征。博尔赫斯在《特隆、乌巴克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中说:“特隆的玄学家门追求的不是真实性,甚至不是逼真性,它们追求的是惊异。他们认为玄学是幻想文学的一个分支。”此话道出了奇幻文体的本质,即追求一种似是而非、亦幻亦真的“惊异”美学效果。这种效果给人直接带来的便是震惊、诧异、神奇等陌生化的体验。康坎在小说中往往是从“真实”进入“幻想”,如《奥黛丽魔方》从“失恋”这种非常真实的体验到见识类似神奇“阿莱夫”的奥黛丽魔方,从而使小说变成了一个美丽而神奇的谎言。那么,奇幻文体仅仅是语言游戏和骗局吗?其实,不管在古代的中国还是西方,人、神、鬼等之间的诸多边界并非不可逾越的,但在现代之后作为神鬼居所的天堂和地狱已然消失,更不用说越界抵达这些疆域了。换言之,现代人的心灵被各种各样的边界分割得鸡零狗碎,越来越多的疆域变得不可触及。作家在语言世界中越界进入某些超验的、非现实的甚至禁忌的领域,从而使现代社会中异化的人重获人性和精神的深广,让人变得更广阔、更丰富、更像个人。
主观视角笔下的荒诞色彩——简评康坎《阿德拉商店的招牌》
河南/李天奇
作为一名年轻的作家,康坎笔下的故事明显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学中的荒诞主义色彩,围绕阿德拉商店,讲述了一则近似魔幻的杀人案。
在我看来,康坎的这篇小说是荒诞的。场景荒诞、人物荒诞、故事荒诞,文中作者大量运用这一写法,让雨天阿德拉商店的荒唐景象重播,最终达到作者的隐喻目的。这有些像加缪的《局外人》和马克·李维的《偷影子的人》中的写法,通过对爱情和现实生活的织补,制造出两个世界的故事感。
这篇小说中,康坎创造性地用多个故事线,在故事内为我们争取荒诞的反差。爱情与暴力,本身毫不相干,在前半部分缠绵的叙述中,以下楼的视角引入第二世界。这世界污浊、动荡,所有人都释放了自己的欲望,比方说,有仇必报,所有人都有自己狭隘的一面,比方说,荒诞的愤怒。正如梭罗所讲:“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决定了他的命运,指向了他的归宿。”在文中的仓库,康坎对人性设下一个解放但压抑的试验场,这里的人们奇怪,充满暴力,冷漠,斤斤计较,且充满命运的卑鄙。
第一人称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为荒诞的联系性创造了环境,它生动地将人们带入这种联系中,并对爱情的仰慕和人性丑恶的一面做出反差,这种设计是具有思辨性的,但也造成了画面感的割裂,比如在地下室为什么那帮恶人没有伤及主人公,为什么当他们逃出时雨水滴在他们身上主人公会担心淹死,这种撕裂使得逻辑线断裂,并在故事的画面感上,也出现前后相接不够流畅的问题,即使作者已在极力规避这种语言逻辑上的漏洞。
那么如何解释呢?如何解释康坎笔下的这篇“人性试炼场”,如何将善与恶之间的反差处理得恰到好处?唯一的解释便是梦境或者幻觉,但文中康坎并没有将这一问题说清,由此可见得这篇小说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剧中所有的荒诞、所有的离谱都是有迹可循的,因为他的本身目的就是割裂,将理想和现实割裂,将生活与体验割裂,由此创造出新的语境,并在其间以造物者的身份设计。
正如弗洛伊德主义所说的那样,文中的情节多持解放的态度,这种偏向生活化冲动的或有或无的意识,恰好可以填补在情节设计上因为篇幅限制而缺少的叙事内容。带着这种视角,我们便可以精准地得到这篇荒诞小说的具体内涵。
雨天阿德拉商店是一座“孤岛”,店外是恶劣环境所带来的风雨,而店内亦是风景,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多是以人性为主要基点的。梯子上是爱情、是生活,梯子下也是生活,但却充斥黑暗、暴力,甚至血腥。由梯子所割开的两个空间,便是阶级。
梯子上的人们热情包容,但在需要物资时却向下索取。梯子下的人粗鄙,但亦有自己的道义,但身处黑暗中的人免不了精神的压抑,所以脱离棋牌、弹珠等低级趣味后,他们变得暴力、猜疑,甚至嫉妒。这都是由环境导致的,由大环境,也由人物内心的挣扎。
那盏昏暗的灯,是起初这个空间唯一发亮的地方,它代表秩序和稳定,同时也代表希望。当虎面龙等人矛盾激化时,灯也由此破碎,当唯一的光明被打破,情绪积压的人们彻底失去秩序,从而制造出血腥的开始。而蜡烛的出现,实际是一种对于秩序的挽救,但仅仅是理想,当秩序被彻底打破之时,微量的挽救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
作为旁观者,主人公想要拿起手机报警时被阿德拉拒绝,这也代表了阿德拉对此的默认,当代表整个荒诞世界的变化球发生变化,这场临近死亡的闹剧才就此结束。
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这场闹剧中,作为楼梯下潮湿之地生存的这些人,其实也是在为了利益争斗。因为利益,他们变得狭隘,因为利益,他们难以逃脱这片困境。
康坎这篇小说在主观视角下设计了一种“牢笼”,人性是其间的产物,荒诞也是,阿德拉荒诞的袖手旁观,楼梯下的人们荒诞的相互攻伐,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使这篇小说不仅充满极强的艺术性,还拥有独特的社会批判意义。
我们在无限地靠近迷宫——读康坎《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有感
辽宁/张男
笔者已有许久未能静下心来,细读曾经着迷的外国文学经典作品,因此,当康坎这篇小说的开头出现有关卡夫卡的“学术轶闻”时,自然饶有兴趣地想一探究竟,猜想这部作品会有怎样令人惊奇的情节走向。此刻,原本燠热的夏日午后陡然狂风大作,几片夹杂着闷雷的乌云压到窗外天空,显然要有一场雷雨降临。这也令笔者有了一个恰当的理由,足不出户,来沉浸在康坎编织的文字世界中。
笔者阅读的速度不快,读到作品三分之一时,渐渐察觉文本和预想的场景大有不同,沿着作者看似流畅的叙事漫步,却走向了“小径分岔的花园”。其实,康坎这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作为中文系在读的主人公“我”,由导师余勒处得知,文豪卡夫卡曾来到一处中国洞穴并在此遗留作品原稿,而这处洞穴恰巧位于其就读的学校操场后侧清源山的背部。为了找到这处伟大的文学和历史遗迹,主人公信誓旦旦地踏上了寻觅的道路。
而和大部分寻宝题材不同的是,作者显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主人公探寻过程的际遇曲折上,甚至寻宝的结局也不在较真的范围内。倘若说寻宝的英雄主义情结是进入叙事的一个因由,但整个叙事的过程却变成了对于寻宝主题的消解,主人公对于真相或者意义执着,恰好在孜孜不倦的探索中变成了一个无法抵达的现场。正如文中提到:“在没有方向里挨过的时间越久,我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迷宫里的兜圈,一种奇怪的重复。”笔者不禁想到卡夫卡作品《城堡》中的K,他本应聘到城堡中担任土地测量员,却遭到了现实中的重重阻挡,K 用尽各种办法,却至死也难以进入咫尺之外的城堡里去。与卡夫卡创造的K 形象有所不同的是,康坎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最终和寻觅的洞穴人有了一次相遇,只不过主人公的这次偶遇混淆在作者刻意创造的情境之中,让事情真相在梦与醒的界限周围变得扑朔迷离。
譬如主人公在登山之前的兴奋和疯狂,在一次次进入清源山后的失败中变为无穷尽的烦躁和懊悔,原本绝望地近乎舍弃的火苗,在某个夹杂着古怪意象的梦境中重新燃起焰火。主人公曾感觉进入清源山的自己,“如同一颗石子,慢慢落入一个和尚衣袖里沉甸甸的布袋”,那么所有的事件的发生,就如同硬币两面的清晨和傍晚,不仅给主人公带来同样的“眼花缭乱的寂静”,还在浓密植被的掩映和潮湿林木的包围下,更多的出现在某些偶然的时刻,或是意识流转的波涛之中。
作者熟稔地创造了许多现实的镜像,这些镜像折射出几种虚幻的真实,而现实和真实在相似的情节中不经意地变异,由此衍生了更多混淆视听的假面。小说中,主人公“我”爬到清源山山腰不规则的石墙后,曾在最近的大榕树上用匕首画上标记,而十分钟的爬行之后,带有标记的榕树周围却再没有石墙的踪影;历经艰苦跋涉后,主人公在自己的脚踝和腹部均受到严重的外伤,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反而在微弱的亮光中到达了苦苦寻觅的洞穴。读者在阅读中,经常发觉日常事物仿佛在时间的路径中变了形状,组合成难以捉摸的发生可能。这在不断叠加的叙事技巧下愈加强烈,小说尾端,主人公和洞穴人的交谈像是一场奇遇,其具体内容在小说中都有细述,此处不必重提,但值得玩味的是,洞穴人所描述的主人公“我”一路寻找的过程,和最后搜救队把“我”从山中救出的场景完全相似,而主人公遇到洞穴人的具体情形,却在回归日常生活后变成了一个有待确认的事实。
作者用几处相同的具象搭建了几种不同的情形,而所谓的真相正处于几种交叉重叠又相互矛盾的情形之中。显然,作者并不执着于带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答案,或者,作者有意识模糊事实的边界,更是另一种“寻找”的抵达,它启发读者在星罗交织的现实中,去重新理解时间和空间创造的可能。从这一点说,作者的想象力是充满实验性的,他用丰沛的想象力搭建了一个文本氤氲的迷宫,也让本文的思想意蕴有了更多探索的维度。
命运的无常与恒常——评康坎《地下酒馆或斗狗场》
湖南/李思雨
在康坎的笔下,命运是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强有力者,诡谲多变,搅弄风云。更令人无奈的是,在它的无常底色下,它的悲剧性一代又一代地重演,制造了一场又一场无解的噩梦,这便是命运的恒常性。地下酒馆与斗狗场的悲剧色彩就是如此穿越时间传递的,在二者看似毫无联系的表面下,涌藏着相同的暗流:欲望的放纵、时间的消逝,人任由身上的动物特征显现,将文明与知识包裹之下的人性自我驱逐。
叙述者在故事的开头便已点明人物身上兽性与人性交织的二重性——马楼曲解“我”的拘谨,认为是姑妈的年轻漂亮导致“我”与往常不一样的表现,女性在这里被他作为一个客体,血缘与伦理让步于男性对女性的凝视。马楼无视“我”进入酒馆后的紧张,断论“我”能够像平常一般如鱼得水地融入这里。这是一家江南式样的酒馆,门口的木门与长廊营造了与江南风格一致的静谧,可在这扇门后,却是声色的纵情与情欲的乱流。在更换了古老名字的偏僻码头处所建立的酒馆,历史和时间本该赋予它落寞与缄默,但它却在酒精的穿肠过肚间解剖人体,将他们空虚的胃部填满喧嚣的欲望。
这与若干年前的斗狗场并无二致,在热闹的马戏团的背后,坐落着充斥着血腥、金钱与暴力的斗狗场。命运的残忍之处在此体现,无论时间如何变化,某些深击心脏痛处的尖刺永远也不会被拔掉,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挂在头顶,人类仅仅需要一次懈怠就能让自己堕入深渊。作者在一开始就指出了这种命运的传递性——
“而我确实只感到‘为时已晚’的恐惧与错觉。”
“如今我常想,要是从那之后我果断地拒绝阿枪哥,之后的事是不是就不会那样糟?”
被马楼带进酒馆的“我”正呼应着多年前被阿枪哥带入斗狗场的男人。在酒馆之内无所适从的“我”发现了同样拘谨的男人,故事中的故事由此展开,同类之间的相同磁场使得男人对“我”放下心防,讲述起他第一次讲的故事。这时文中的“我”由一个叙述者变成了他人故事的记录者,这种奇妙的身份变换也似乎佐证了酒馆与斗狗场的相似性。
在男人的故事里,似乎除了失去联系的阿枪哥,其余的每个人都获得了悲剧性结局。在佳佳、阿枪哥的爷爷和灵儿的身上,这种悲剧结局正是命运无常的写照,他们在巧合中偶然被卷入他人的失足中,甚至是被迫承担这份“连坐惩罚”。而其他人,永远活在悔恨中的男人、被烧毁的马戏团以及或许会愧疚的阿枪哥,他们的惨状很难归因于命运无常之下,他们屈服于逐渐膨胀的欲望,摘下命运标好的价码,走入这场豪赌势必要承担满盘皆输的结局,这是命运的恒常。
男人故事讲述的延宕处理也十分出彩,在邻居家的小狗佳佳被出卖给马戏团,他和阿枪哥赔偿了邻居米和肉时,故事在这里突然停住。“故事絮絮叨叨,本该就此结束。到这儿称不上完满,至少也并不悲哀。”这是这场故事开始后所能实现的最好结局,男人曾经触手可及,但他最后也只能在虚幻的诱惑中深感“为时已晚”。在故事暂停时,“我”又变成了叙事者,马楼再次出现,满身酒气,被穿着性感的女孩挽着手臂。他将自己驱逐在声色犬马中,并试图拉“我”沉溺其中。这又一次构成了地下酒馆与斗狗场的呼应。
男人接着讲述斗狗场的故事,这是一场十足的纵欲,对自行车的渴求让他越来越迷失了自己,一边愧疚一边把第二只“佳佳”送入死亡(给第二只取名“佳佳”也验证这种命运的传递)。最后的斗狗场终结于一场两败俱伤的动物撕咬,人类也在与命运的纠缠中无一例外地、恒常地走向死亡。作者对命运的感慨由此达到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无力。
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和那枚代表了时间的明朝玉石一样,它被深埋地底,它本应带来的经验与教训也不见天日。历史日复一日地上演,错误犯了又犯,人类继承祖辈的劣根前行,由前人的生命换就的故事被不屑一顾地换成金钱,时间实现了它的贬值。记忆的归宿是遗忘。
以象征为笔,追忆卡夫卡的往事遗风
云南/邓程浩
“寻找”这一文学作品的主题从来都是具有象征性的,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梅特林克的《青鸟》,都要求我们对“寻找”这一动作作出更深层次的解读:借用这一动作来象征对理想事物、理想领土的追寻及其过程,当然也要体会出其中的辛苦、迷惘和牺牲。《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这篇小说也不例外,不仅人物本身具有象征性,就连寻找的过程和对象也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但这篇小说中的象征远不止于象征含义的本身,而是通过象征这一方法来促使文本的生成和表现饥饿艺术家的艺术追求。
先简单说一下小说中各个意象所包含的象征意义。整个追寻的旅途可以看作是对卡夫卡写作风格的承袭;旅途中的“我”和“饥饿艺术家”本人是形成对照的,饥饿艺术家由着艺术的自觉而拒绝饮食,目的是要完成更好的表演,“我”想要得到崇高而伟大的“手稿”而把自己置于险境,险些身亡;手稿所象征的对象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个面:追寻过程中“我”的情感表现(这些情感促使“我”继续着行动)以及手稿可能带来的社会意义。
熟悉这些意象之后,我们便可以跟随叙事主人公的脚步,开启“寻找”之旅了。
在“我”行动的那一刻,小说的故事也就开始了,而文本的生成和对饥饿艺术家艺术风格的表现也从这里开始。这里要指出的是《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这篇小说就相当于卡夫卡的艺术宣言——为追求极致完满的艺术牺牲掉自己的一切,因此,将饥饿艺术家看作是卡夫卡本人也未尝不可。这样上述两件事的关系便明朗起来: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叙事主人公追寻着卡夫卡的往事遗风(甚至因此负伤,险些身亡)——这是故事时间的流动;作者和读者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一篇具有卡夫卡风格的小说,即通过文本形式对他的艺术风格进行了表现——这是文本时间的流动,我们可以从小说中荒诞性的蔓延看出端倪。
借用人物余勒的原话:“这项任务的伟大与荒诞注定了探秘过程也是近乎伟大和荒诞的。”这里他恰好描述了追寻对象以及过程的荒诞性。这种荒诞不是停留在“我”和余勒通话的那一刻,而是蔓延在整部作品、整个行动以及涉事人物当中的。例如“我”第一次探寻失败之后,又开始接下来的一次次探寻,在这些探寻中,“我”逐渐进入一个个梦境之中(其实“我”再一次进入清源山直到被警察发现期间,都是处在梦境当中),这些梦境要么是现实的扭曲,要么是由梦境本身所幻化出来的现实:“为了证明不是梦,我用匕首在左手手背上轻轻划了一道口子,结果真的渗出鲜血”,身处梦境的“我”依靠现实中的逻辑来辨别梦境的真假,这本身就是荒诞的。
当然,最精彩的部分自然是“我”与洞穴人的相遇,这场相遇也带有荒诞色彩。且不说洞穴人的话语和认知与其所处的环境和历史之间相悖而产生的荒诞性,就从他的本质来进行分析:他其实是潜意识借助梦境塑造的另一个“我”,“我”在现实中知晓了卡夫卡的手稿及其细节(表现在他也知道卡夫卡的故事并且借用自己的形式向“我”说了出来,其中自然也有想象和推理的成分),但由于路途的艰难,“我”并未到达旅途的终点,只能借助梦的补偿机制来完成“我”追寻手稿的旅程,但在最后洞穴人——也就是“我”拒绝向大众提起这里的事情,这也意味着,这次的“寻找”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社会意义,可余勒和“我”的出发点便是这件事的社会意义(伟大的任务只有在社会语境下才能彰显其伟大),因此“我”的潜意识和表意识是相悖的,也即是荒诞的,甚至可以由此衍生出“荒诞人”的形象。
但还没有完,这样的荒诞逐渐弥散到我们读者的思维当中,我们不得不暂时抛弃常理的逻辑,按照小说给出的非现实的逻辑进行阅读,但越发这样,我们对这一系列形象和意象的认知和感受就越发强烈,于是,一篇极具卡夫卡风格的小说也在读者的脑海中生成了。
好在作者最终并未狠心将我们抛弃在小说当中,他听从了自己潜意识的呼唤,将那个盒子做了“抹杀”性的处理,也将我们带回了现实和理性的思考之中:在过度狂热的追寻中迷失自己,是否可取?
长生不老的人活成了一条狗——从《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到《永生》
江苏/张同远
永生,用民间话语来说,就是长生不老的意思,是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和追求,却被博尔赫斯用他的文笔、思想和梦境演绎为,长生不死的人活着还不如一条狗。
如果秦始皇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伤心难过?也可能十分高兴,因为他的人寿有数,但天寿无限,他所开创的家族事业表面传递了二世,其实却代代相传,到光彩照人的唐宗宋祖到狂野的成吉思汗,一直到可怜巴巴的爱新觉罗·溥仪,永生不死,阴魂不散。
《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这篇小说是从新发现的一页卡夫卡日记开篇的。《灰色的寒鸦——卡夫卡传》一书提及1917 年卡夫卡解除婚约前一个月不知所终,这就成为他来到中国清源山旅游的一个证明。为此,“我”在导师余勒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寻找卡夫卡踪迹的探险之旅。这里并不需要象征,哪个写作者不需要寻找大师,发现他们的创作和人生的秘密?博尔赫斯需要荷马,需要普林尼,康坎则需要博尔赫斯、卡夫卡,需要马尔克斯。
安杰勒斯曾说,玫瑰是没有理由的开放,作者康坎也说,那么叙述的方式、情节、用词、节奏也是没有理由的。这些话语同样适合这篇小说,如果不是过多的中国元素,我一定会认为新发现了一篇博尔赫斯的作品。
通往清源山的无数道路都寻找过了,每一条都是岔路和踌躇,无法在藏宝图上画出通达的线条。这种寻找过程艰难却令人兴奋,因为“我惊奇地幻想伟大文学和历史的遗迹竟然就深埋在平日我常去散步的另一侧”。
面对人类有限的生命,一座山就是永恒的。普通的脚步又如何抵达永恒呢?于是只能借助于想象、梦幻和文字了。这些轻盈的工具帮助我们摆脱三维世界,到达人类的更高纬度,那里的时间是永恒的,空间是无限的,那里的人不再普通,而是具备神性。可是让博尔赫斯失望的是,他见到的永生者竟然是一群最原始的穴居人(后来知道,那是永生者达到了绝对的平静)。
而“我”见到的穴居人是有记忆的,并用博尔赫斯的话语诏告天下:“一个永生的人能成为所有的人。”穴居人知道诸葛亮,知道张飞桃园结义时左手在上等奇怪的事情,穴居人是一只穿山甲、一棵苦楝果、一道瀑布,是格里高尔,是富内斯,是蒲松龄,是作者康坎和我们这些评论他的人,是哲学家,是魔鬼,是世界,换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法,什么都不是。这篇小说脱胎于博尔赫斯小说的《永生》,博尔赫斯认为,每一个举动(以及每一个思想)都是在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举动和思想的回声,或者是将在未来屡屡重复的举动和思想的准确预兆。经过无数面镜子的反照,事物的印象不会消失。
但人类苦苦追求的永生又具备何种意义呢?博尔赫斯甚至认为是一件痛苦和低下的事情,因为“除了人类之外,一切生物都能永生,因为他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在《永生》中,人类对自己创造的文明是多么地厌倦,他们建造城市又把它们丢掉,宁愿回到原始的穴居状态,这和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思想何其相似。永生的荷马不再神圣,活成了原始的穴居人,活成了一条狗。
《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中,当“我”获救后,回到文明社会,文明人忙忙碌碌采访、反驳、赞叹,制造出“我”所描绘的洞穴模样,只有“我”和教授明白,那只是谎言之后的想象和建造,目的只是把旅游者吸引过来,赚到几张小小的钞票。为了五斗米,这个国家、社会和它的子民们不断地折腰,折腰,就像一个杂技演员把腰变了一个来回,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
小说中的许多BUG 或许是作者故意的设置,比如生命探测仪,已被“我”早早丢弃,后文中又想作为礼物留给穴居人,或许,生命探测仪探测的并不一定是生命,只是一个摆设,什么也探测不了;比如时间似乎在倒流,先是“十点二十分,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表”,后面又出现了“手表上的时间停留在九点十五分”。反正对于永生者来说,时间和空间不重要,可以分开,也可以混为一体。
“我”并不敢查看永生者留下的书箱,情愿交给又聋又哑的爷爷。因为对一个聋哑人来说,文字什么都不是,幻想和历史也没区别,什么都不是。或许我害怕阅读后成为真正的永生者,就像一个不死的荷马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像一条野狗一般难受。
没有死亡,人类竟然失去了活着的意义,丢失了挽歌式的、庄严隆重的东西,永生从而成为了虚无的话题。这个世界充满迷宫,却是对称的,有一条赋予人们永生的河,某一地区应该有一条能消除永生的河。罗马执政官鲁福经过世代永生,发现了一条清澈的河流。他尝了尝河水,手背被树刺划破,流血了,他又成为了有生有死的普通人,却“感到难以置信的幸福”。
小说的最后,博尔赫斯和康坎探讨了文字的意义。肉体的永生,终究低级,人类用自己创造的逻辑符号——文字来到达永生,不管是谁写的,不管是从笛卡儿到达了博尔赫斯,还是从博尔赫斯到达了康坎,不管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接近尾声时,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
梦与现实纠缠下的荒诞——评康坎的小说《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
山东/杨林鸿
读康坎的小说,你会发现他在力图摆脱小说创作的传统模式,行文更加自由、恣肆。在他的小说中你读不到那些中规中矩的东西,却有一种年轻作者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康坎无所顾忌,但却是真诚的,笔端流淌着对生活、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和阐释。他的胸怀是敞开的,他的小说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花园,一种神秘感吸引着你走进去,花园的花未必多么奇特,但是,你能从里面嗅到和其他花园不同的信息。康坎的短篇小说《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刊于《作品》杂志2023 年第4 期),就给了我这样的感觉。
康坎把卡夫卡的手稿及其小说《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和“我”去清源山探寻野人这毫不相关的故事,利用自己的丰富想象,用荒诞的梦与现实的纠缠和敏锐的思辨色彩,穿针引线,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小说世界。康坎试图用小说这一形式来传递他的人生观和哲学观。我们能从他的文字中读到他内心想要表达的情怀和腔调。他对世事的看法就存在于字里行间。如:“凌晨被一团任意拼凑而成、毫无道理的梦搅得说不上滋味;醒来时才感到神魂颠倒。”“这项任务的伟大与荒诞注定了探秘过程必然也是近乎伟大与荒诞的”“我日复一日地在得意、兴奋与近乎狂热中出门,又日复一日地在疲惫、猜疑与自怨自艾中回到房间。”“我因发烧而惊醒,明白自己的野心在梦中原形毕露。与其说,我对那份百年弥足珍贵的手稿朝思暮想,不如说余勒导师的期待更使我不甘就此失败。我渴望做英雄。”“夜晚实际上并没有这么恐怖,使它显得恐怖的同样是阴影、重复、庞杂、不谐调、我的不熟悉与胆小。”……这些耐人品味的句子富有哲学意味,更有思辨的色彩。这在一个年轻作者的文本中出现,真是难能可贵。也许,作者的年轻会让他的哲学观和世界观不成熟,但他的积极探索是富有成效的。
人生就是一种探秘的过程,比如找工作、失业、碰壁、爱情、婚姻、家庭等,比如成长、衰老、孤独、伤感、抑郁、痛苦等,比如自由、美好、谎言、欺骗、丑陋等。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必经的。我们都要独自承担岁月在心灵和身体上的刻痕。康坎用一腔沸腾的热血,写就了自己眼中和心灵里的青春以及青春中的挣扎与无奈。
读康坎的小说,有一种快意的感觉。他说出了自己想表达的思想,说出了年轻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没有左顾右盼,没有瞻前顾后。也许他内心是孤独的,所以他就写出了他的感觉。在孤独中我行我素。“我”对清源山野人的探索,其实就是一个人生挑战的过程,挑战着现实中的秩序和小心翼翼遵守的生活规范。“我”宁愿失去安全感,也要做出不同凡响的事情,目的无非是要发现自我、反省人生、重塑生命。探寻的过程,历经风险,但是却实现了价值。小说从外国的“饥饿艺术家”到中国的“清源山野人”,跨度久远,所处的环境各异,但是命运的处境却是一样的:与社会格格不入或被社会孤立。换句话,就是他们都是孤独的,被异化的个体。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作者对人生的探索与阐释。作者以这样的文本,为我们展现了“我”的探索世界的过程。那些荒谬的梦,那些不堪的现实,那些摆脱不了的纠缠,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的失望和无助。
康坎的《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是跳跃性思维。从一件事跳到不关联的事,合情合理,毫不突兀。语言的张力,以及不时冒出的精彩的哲理句子,总是让人不由自主深陷其中。康坎依靠富有思辨力的文字,传递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哲学理念。“寓言的创造总是先于对其寓言的理解,故事本身或许比故事的命意更为重要。”这是康坎对这部小说的最后总结,更是他对世界、对人生的阐释。我们有理由相信,康坎会以此基础,构建出一幅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小说风景,这幅风景值得我们去看、去探索、去品味,去研究。
——读《博尔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