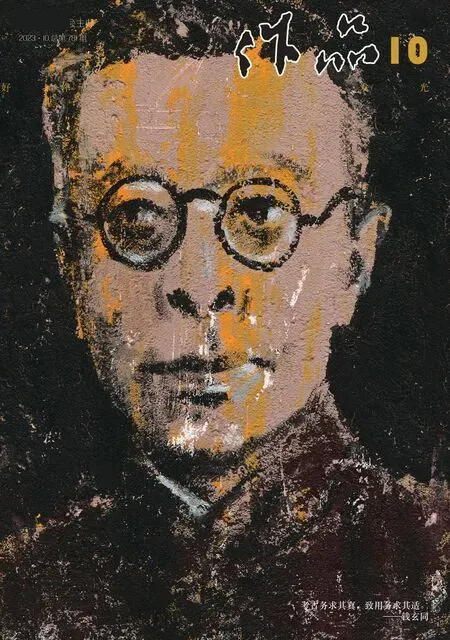她们的诗
安乔子 一地雪 白小云 郑皖豫 宋德丽
安乔子的诗
◆洗云记
云在水中,当我把手伸向水中
我的手在那些云之间摆动
好像在洗云,云在手上流过
安静得只有水声
好像洗干净一片云,就洗干净了内心的尘埃和疲累
当我离开,我看见一个个洗云的人走向那里
他们拿出内心那朵云,洗了又洗
洗过后,又放回心里
然后继续赶路
◆牧云记
有多少人像我这样
在一场场无用的奔跑中
追赶着白驹过隙的云
有多少人像我这样
做着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事
却把它当成了理想
有多少人像我这样
投向风的怀抱,却一次次被撂倒
有多少人倒提着天空
有多少泪水倒流回眼睛
而仍不悔改
像一个了无牵挂的人,拿着鞭子
把整个天空都当成牧场
把云朵当成白马,豢养一匹永远看不见的猛兽
◆弹棉花的人
一次,我站在天堂山顶看云
天空仿佛一家棉花店
那些云一团团蓬松地飘在空中
我想起了一个弹棉花的人
他弹的棉花就像眼前的云朵
天空那里一定很冷
所以他把棉花也弹到了天上
他的手艺又增长了
棉花松软、整齐,怎么都不会掉下来
当云朵开始松动时
我又一次想起,他举起棉花弓
开始在天空弹棉花了
木槌击打在弓弦上,弹出了古老的诗意
在天上弹棉花的人
他弹出了朵朵好看的云
云朵是永恒的赞美,它安慰着天空
◆去云间
他多么想坐一趟火车去云间
云间,恍若他生活过的地方
白云像他睡过的那床棉被
那些漂泊不定的云,像曾经的居无定所
靠近海边的云屋是他一直想过的生活
他可以一会儿去云中走走
一会儿从云中走出来
做一个云卷云舒的人,不必太在乎大地
云间有我们的故乡、羊群、河流、稻田
以及海阔天空,一切都有
云里也有他爱的人,当他抬头
那人便在云中呈现
云间会在某一刻垂下天梯
一条向天大道或一列通往云间的火车
这人间的肉身,需要在某一刻,去云间走走
◆看云记
他每天都出门去看云
以此填补生活的空白
他有一双孩子般纯净的眼睛
用来赞美云朵
即使是乌云,也是顺其自然的美好
看云的人,同时打开了一扇天窗
看一看天,心就大了
地上的事就小了
看云的人,心里装着云朵的事
他要在云朵下面找一条河
他要随一条河去很远的地方
一直到河水去了天上
天上的河水往下流
当他再次回到起点
他已不是站在同一个地方
他乐此不疲,即使两手空空
看云的人,他是在寻找一道缝隙
他在那里进进出出,像自由飞翔的小鸟
◆一朵云
想一朵云,想什么它就是什么
顺着风,我追那朵云追到天空尽头
一直追到云朵纷纷陷落
追到云贵高原,我爱的那朵蓝还在
天空很好,阳光很大
我如一只在人间迷路的飞鸟
追一朵云,我动用了所有的交通工具
爱一朵云,我几乎动用了整个天空
◆草莓田
那天我们在郊外的草莓田里
摘草莓,我们都爱草莓
红红的草莓,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
一颗草莓正在谈论两颗草莓
或者三颗草莓的故事
一颗草莓退到深处,一退再退
直到我们视线模糊,草莓像突然长大的女儿
这是多么骄傲的事,我们从田里走出来
坐在公路边聊起我们的晚年
以及可能失去的一切,薄雾淹没了草莓田
公路那边,一排婚车驶过地平线
云朵献出白色的婚纱
我们爱过的草莓将披上它出嫁
我们离开草莓田,我们仍然爱着
◆群山之中
当阴影掠过群山
也许是落叶,也许是飞鸟
当你站在一座山上,喊另一座山
我如何回应你,白云纷纷从天空落下
总有一朵落在山顶的寺庙上
而你知道的,群山是庇护,也是归途
当一群蚂蚁抬着一具尸体爬上山
是落日安慰了群山
◆人群里的羊
人群里的羊
低头走在人群里
目光温顺,并不说话
任人驱赶、鞭打,并不说话
它们会默默地落泪
梦见过一把垂下的刀
风一样把它们吹倒
人群里的羊走过陌生的公路
有喇叭愤怒地驱赶它们
它们惊慌失措,仍然低着头
那颗奔跑的心
已找不到远方的草原
它们眼里的落日
照着陌生的异乡
当它们在人群里往前涌动时
像一群白云,无法承受地
从天空的尽头飘落人间
是的,只有羊看见了羊
只有一只羊听见另一只羊
在人群里的哭泣
当它们的身体彼此摩挲时
是羊毛安慰了它们
◆送别之诗
白云之上没有巅峰
鸟群之下没有永恒
玉兰树的叶子悬在空中
秋天还没有被催熟
天气很好,鱼在池塘里
轻微地搅动着短暂的湖面
时间追赶着背影
它随一辆出租车远去
我们都要回到各自的生活里
在想象的两地,在同一棵树上
我们像一片叶子吹起了另一片叶子
并彼此交换了花朵和果实
◆时光飞鸟
那年,我坐在树上摘荔枝叶
用它吹一种好听的声音
像这些年我在回忆中寻找鸟鸣
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鸟,在童年的树林里
它收留了我,给我卑微的快乐
那时我不懂什么是苦难,泪水也是甜的
鸟的快乐如同我的快乐
现在我从远方回来,站在树下
那棵陪我长大的树,它的树叶已经掉光
被砍伐的部分呈现出廉价的肉体
是的,它们早已在岁月中被榨干了血肉
我仍然能吹出好听的声音
但我再不能爬到树上
并坐在上面长久地看鸟从天空飞过
时间让我羞愧,又让我着迷
生活已经不能再来一遍
时光飞鸟依然在那里不停地鸣叫
岁月既让人感到安静,又感到伤心
◆另一种可能
无论见与不见
麻雀高飞
大海归于平静
天空里有你的小镇
有人在种白云
而山下的稻谷已经成熟
你在等
另一种可能
你静静地站在门槛上
倚着午后的门框
你眼里的远方有一片白桦林
小屋也在
一场雪正落在你的小镇
一地雪的诗
◆中年
在月季的摇曳里我吃它时光
被焊枪粉碎。
工厂正在吃掉我
我的中年。
我的中年在
车间门口一簇月季对粉尘
殷红的吞咽细嚼里。
我的中年在省道上,汽车
用飞烟掩埋时速。而
幸福的光影
在我嘈杂的记忆里一点点反刍
工业园的静谧。
◆银丰路
请允许银丰路上的冬青树
发福。它们用年渐肥壮的腰身
向我炫耀时光之疾。
我无语以对。
请允许火棘的枝条向背发射
绿色的枯萎。火红的果实
喂养一只只雏鸟。它们的
叫声从半空掠过幸福。
我如此羡慕。
请允许,允许这路肩上
石砖鳞次伸向远方。
从砖缝里冒出的草芽
冷不丁撞上你的脚尖。
让我对这世间心存怜惜。
也允许路边的工厂冒出
几缕浓密的粉尘。它们不小心
陷入活命与环保的怪圈。
我从那群黄色工装里
看见一双双炯炯浑浊、多皱的眼。
我无法想象一个极其消瘦的人
开着叉车,每天在厂区奔忙
而脑血管却拥堵。锈蚀
不放过钢铁,更不放过劳动者。
我的心被悲悯的惊悚悄悄穿透。
在银丰路上。我允许——
它短暂,悠长,
它喧嚣,静谧,当我一次次走过
与那些满载货物的卡车比肩。
允许我看见的,和没
看见的事物一天天活着,
死去。他们不悲哀也不
欢愉。允许一片雪花
从酷暑等到寒冬。
◆赤膊开车的青年
那个赤膊开车的青年
胸前挂着一块护身符
(是否他母亲所赐?)
不知为何让我想起父亲。
古铜色的胳臂,把方向盘
抱得紧紧。凸起的肋骨
像小白杨的两排细枝。
他眸子里饱含一汪清水,让我
想起顽皮的儿子。
当我们对视,邂逅在荒寂的午后
沉默的尘烟在老柳树下簌簌坠落。
一匹骏马轻轻跌宕在银丰路上。
那个赤膊开着卡车的青年
在我眼前闪过。只那么匆匆一瞥,一闪
只那么匆匆。为什么,
在我心底种下疼痛?
◆午后散步
粉色的木槿花像几只停在
枝头的蝴蝶,聆听
沉默。慢慢飘来的那只
黑蝴蝶是它们的
国王。它采蜜,吮吸光阴
掌控流浪者的眼眸。
这是银丰路。
此刻与城市脱离
孤独在机器喧嚣的脊背上。
那摇曳的柳丝是衰老的
骨笛。低矮的灌木丛是放牧鸟鸣
的田野。有神
开垦着我心中的荒地。
土地芬芳。风顺着
安详越过铁栅栏
带来流水的足迹。
◆带一个花朵般的姑娘在车间穿梭
一定是看见了两只蝴蝶,
弯曲在机床边沿的那些花萼
挺直了腰。
一定是被清新陌生的香气
冲昏了头脑,那些蓝色工装
个个像鼓起的风帆
振翅欲飞。
一定是渴了,两条裙裾
拍打出涓涓小溪,
他们的眼睛在小溪中扎着猛子。
一定是看见了姑娘雪白的腿,
而我穿了黑色丝袜,但
最终也没逃脱他们嘴唇的审查。
当车间主任在办公楼
碰到我,责问那个女孩是谁
他要我们为车间里
魂不守舍的工人们还魂。
◆献词——致我热爱的X
我听到她的词苍白地跳跃虹浮现。
小饭馆依然
有许多吃午餐的工人。
而我们的车间锁着门
虾虎鱼逆流攀爬岩壁。
工人们在白茫茫的夜里遥望
星空中的马蹄铁。
她如果活着
或许创造出更多
苍白的虹,让词语的跳跃
变得新鲜瑰丽。蝴蝶的
天梯登上暗物质。
哦我是说
如果我吃掉她的文字能裹腹
如果那个偌大的工厂变成
一只老虎
丛林里那许许多多
寄生于老虎身上的虫子
就能活下去。
再没有比这开心的事情,
秩序的轨道伸入诗丛内部。
当然,她的文字要苍白地跃出虹
美过一尊铁神。
◆窗外
它的手在抚摸
抚摸我肉质的衰败。蓝色的行吊
颔首屋檐。鸟儿一前一后飞离巢穴。
它的手有时绕过行吊
将我的办公桌悄悄刷屏。
光线慵懒
梳理着我埋头工作的身影。
在这小小的办公室里,
在窗棂上的日出、日落间
我偶尔会为窗外的蓝天、行吊、鸟巢
而凝神。它们就像你的手指
次第伸开,将我的光阴
牢牢撑起。
◆午时阳光
这午时阳光的击打伸出滚烫之手
隔着一扇玻璃门
玉兰和大白菜默然相对
它们也许沉浸在光波刺眼的厮杀之烈
它们正朝向阳台外
透过尘埃扑满的玻璃窗凝视那最后
一棵瘦竹的枝叶闪烁。
多好的阳光啊
诱惑我伸出绵软之手将内心的灰烬写下
在明亮的宁静中缕缕旋转出细微的火花
而这一切在我这首诗落幕时
又还原为一个黯淡的世界
哦世界在明亮的黯淡中越发饱满
◆幸福书院
这里层峦叠嶂,雾霭苍茫。
这里水重山复。
檐牙高啄。这里只有一间茅屋
它被我的梦裹于幸福。
这竹简一根根通往天堂的曲径。
炊烟从打坐的蒲团上升起。
安卧的蝉鸣为竹林领鼓。
木鱼在孩儿的手中,敲响世间
真纯,良善,与悲伤。
这里不用低头,或举头。
一切均可平视。因为天和地
都装在胸间,它蕴含了万物的胆量和柔情。
它们皆平等,博爱,自由。
毫无粉饰。哪怕一只蝴蝶的振翅
也干净得让你颤抖。
这里没有历史。所有的时钟
敲打着昨天,今天和明天
它们共同拥有此刻。
此刻的安宁,富足,神怡。
白云亲吻着流水。
每一粒尘埃就是永远。
这个清晨,我再次从噩梦中惊醒
跌入这非我的梦幻
并为我的梦幻感动得暗自流泪。
——至少,我还有冥想,
日渐衰老的躯体内尚存一座
幸福书院。虽然不为人知
却无物不晓。
◆鸟鸣
第一声鸟鸣
抬起我的颈项,光在枝叶上震颤。
第二声鸟鸣
把我的忧郁染蓝,苍野如波涛涌来。
第三声鸟鸣
割断我沉积的混沌,我的躯壳回到我。
这是美好的时刻
一只鸟站在孤独的小树上,树笔直
鸟微小
再叫一声——
我的紧张消失于空旷。
叫一声,我变成了另一只
飞来的鸟——
我们站在人类的树梢
空灵。笃定。
天地宏阔
万物沉醉其中。
◆木椅
这是一张木椅,纹理光滑似荡漾着水波
依桌临窗。我把你抱上椅子,你画小鸟
小鸟很快就飞过来
透过窗玻璃晃动着脑袋和你耳语。
但我等不到你把我抱到
椅子上,反复触摸椅子弯曲的肢体。
(那时我将依然爱着这把木椅
它的纹理,弧度,沁人心脾)
即使等到那一天,
我也不能像你,把鸟儿画过来。
一脸沧桑喜悦于这张
木椅的金色暮年。
白小云的诗
◆夏雨
大地接受突然袭击
被关在暴雨的笼子里,反复敲打
因为附属者的骄傲
石榴花、栀子花、紫薇花们
跟着一起挨训
恐吓、照亮和清洗
审判者不分昼夜到来
电闪雷鸣,对时间内的所有
实行严厉的鞭挞
变深,变绿,变宽,变成唯一……
洪水的记忆弥漫,石头碰撞石头
河水冲刷河水,树枝掰折树枝
一边信任,一边质问;
一边迎合,一边抵抗;
激烈地争吵,日夜不息
真正的热爱如此灼人
它容不得片刻犹豫
◆宇宙的目的
假如宇宙自己生长
自己衰败
自己扩大
自己缩小
他的意志是万物运行的规律
人类这小小细胞
在风中流淌
风,是宇宙血管里的回声
那么宇宙是不是活的?
是不是庞然大物
是不是也会有他的目的
就像你让我讲讲我的目的
你不明白宇宙的目的
就像我的细胞们不明白我
孩子这样说
◆花园
大楼顶部,城市的空中
它们被风弃在水泥楼板的隔水层上
生根,努力寻找并不存在的泉水,黑暗里
如果有那么一丝甘甜,它们就可以
对迎面吹来的沙尘报以轻松的一笑
尤为困难的时刻正是现在
它们摇晃在怀疑中,也许是不明真相
恰好挽救了它们,毕竟虚无
要比面对容易得多
珍珠缀满枝头,露水即将绽开
命运不等它们明白
小甲虫们叹气,看见它们被巨手碾压在
高架桥的水泥路面上,摩擦
◆止疼药
他放弃了一次新的选择,陈旧的生活
已经使他快要腐烂,他急于挣脱
霜从哪里开始凝结?他推开窗子
寒气迎面而来,推动风的手几乎推倒他
这次他任性了一些,不再把他们的喜欢
当作自己的,包括他们要他爱的人
要他知道的世界和塞进他嘴里的甜
他的疼,因此似乎好了一会儿
◆秋千架上
风从前面、后面、四面八方来
凌霄藤蔓的阴影,在我们的头发、衣服、
胳膊、腿上……摩挲徘徊不去
逐行书写初夏午后的荫凉
树叶在高处摇晃,得意地俯视
蚂蚁们经过它们创造的阴影
——小不点和它们的远方,被高处一眼看尽
像被挠痒痒后的小小挣扎,风穿过时
我们笑起来,服从一瞬间的幸福和空想
不要让它们明白
◆尾气
行走在车流中,流线的数码的烟尘
快速甩你而去——一颗水珠被大海吞没
他欣享高楼间闪烁的霓虹,它们构成夜晚最美的
人间,天上银河也莫过于此。你拥有过一些错误
是彼时彼刻最完美的选择,譬如现在
他缓慢行走在车流中,冒险看见
接着我们大笑起来,一种即将被光阴篡改的笑、
即将被发明成灯盏的笑,有种复杂逐渐丰富的笑
沙沙……沙沙……沙沙沙……
◆爱如是
猛虎凝视,小兽学步
跃过来又逃回去,巨掌藏着针
胆大妄为者踟蹰不安
讲述最细微的回忆
却不能概括树木外的森林
无法俯视博览的风景
无法收放自如的闪电
只见太阳或只见阴影的能力
哲学的时刻,是那思念的时刻
悲伤弥漫时,激情就是全部
海浪扑向岸边,水里藏着火焰
谁的玉碗空着,谁在倾倒珠宝
◆哀怨
去活去爱去死,你说
我听见蛙声从黑夜深处传来
它们在求偶在交配,在往更幽深处
传递肉体短暂的一生
怎么办呢,你问
夏午的风暖烘烘,吹着绣球花叶
它们今年只开过春天,现在满盆绿色
剪去繁密侧枝时,它们蓬勃的欲望
让我心疼又心狠了一会儿
鱼儿正穿过眼前水域,它们沉默
看起来默契又快乐
但“如鱼得水”“鱼水之欢”……
也许是几千年的误会
水和鱼都没有表过态
一时间我们无话可说,因为
一些无名的挫折
◆疼
像风暴掠过灌木丛,它尖叫着
跳到马路中间,张开的爪子挠破了什么
有两星亮光靠近,即将相拥燃起时
必然有雨滴扑落。再无重现的可能
它开极致的玫瑰之形,却无法得到欣赏
蒲草如丝,别的芳香闻不到
它盯着两只小鹿的雕像,拱它们
蹭它们,盼望这对陌生母子回头
万年青逐渐枯萎在盆中,好养活的名字
幸福草也如此,正丝丝缕缕地稀疏着
昨日的烟灰还在,倒上今天的咖啡末
作为日子必然的残件,灰与灰的相遇
有时被称为余生
我们一起走在把伞当作拐杖的路上
有时两朵花相依盛开,有时竹杖支撑在泥路
有时两个泡沫缓缓升起,彼此轻轻礼让
避开同归于尽的碰撞
◆蓝色的夫人
她翻开信纸——不再拒绝远方的暖流经过
这个冬天,她全副武装了自己
毛披风、皮手套……其实,这并不是唯一的冷
许多个冬天她都沉浸在更多保护中
此时如果凝神在那些成对的寒鸟上、枯木上、
冰冷的杯子上,那绝对是偶然的巧合
她把目光从信纸上移走,纤细的水墨字迹
逐渐晕开,当年场景有了写意风格
她终于要回去了,回到丢失花边围巾的
夜晚、的草场、的马驹、的小夜曲旁
等她转身的门不知道朽塌在哪里
旧信纸上的心情也已旧了
虽然此刻,她有新鲜的决定
郑皖豫的诗
◆雨夜的机会
昨夜下了雨,
没有雨声也没有雨痕,只有夜归的
人
晓得。
他一夜未睡。两个屋的空调响,
嗷嗷地,他希望灭掉一个。
他灭掉了
自己房间的敌人。于
凌晨两点钻进她的卧室,犹如
一只流浪动物爬进她的梦境,和她,
和狗,挤在一个空间——
一个密闭的空间,三只动物,相安
无事,
因为夜晚,
就是要人沉默。
◆天使去哪儿
她常常失去方向,在
生活中,
为生活这一
理由。因它的一日三餐,
盲目地奋斗和爱
人。为一颗艺术之心
生活的不肯透析。犹如
坐在船上,
而船没有地图,太阳给了
一切,
一切只是山水——
她惶恐,坐在了荷叶上,她不是
荷花,或蛙,
仅仅是一滴露。
◆乌鸫
一截黑管。取自黑夜。
太阳特意为它安装了喙——
黄色的阳光泥。它不言也不语,
樱桃树上的风车五月里
挥手着它的飞离。在
芭蕉林,银杏林,水杉林,
在悬铃木,电线上,
在任意它想去的
季节和无家可归的
地方,在任何的
合奏外,及一个三岔
路口。
◆乌鸫和女人
有没有不痛苦的事物?
——近二十年,
她绕着她的小区散步,从
它的新陪着它旧,悬铃木上
的乌鸫,
不知道换了多少代;野猫
历经穿越。她陪着自己去迎接
死亡,死亡里面的
另一个她。
雪仅仅降了几十次就
降到了她的头上,还会继续降在
她的头上,直到她对于这世界毫无
眷意。
◆七月的夜晚
接受命运比抗拒命运更
悲壮,它使我显得平静和悲伤,
犹如黄昏来临时,未找到
栖所的鸟只,在任何一棵树上
向内心流露着它的失意——
这个世界就是
有比你强大的力量搅动着
洪流,而你
无法找到自己的树叶。
◆一次散步加晚餐
一碗麻辣烫烩面代表了一切。我
和他的此刻,围着一张油腻的方桌,
矮坐,
灌木丛的蚊子,无论成年幼年,
也无论肥的瘦的,
都被邀请——
我们四条腿呢。门店
小房间有架铁炉——
一家火烧店,老板就在
里面的小窗内,没有舍得
开空调。这张方桌,
盖棺了过去我和他的,一切
黑暗以及人性;无法预测
未来。
◆最激烈的动物
我知道——
现在是她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我
最艰难的时刻,我们是
艰难的闸口,我们这些
明亮的女人。犹如蝉
在地下,
我们仅须沉默;沉默是
我们的白翼。
◆一个早晨
太阳直接带着早餐来了:
给树——
女贞和水杉,及水杉颈上的巢球;
给她的一天的开始,
给
她的眼睛,
送上一颗启明星,并祝福
她的死亡,像缕水蒸气,还会
期待她像一颗新星
出现在哪里,
跟随着宇宙,像只小鸭
呱呱在它的圈里。
太阳
隔着云递过来早餐。
宋德丽的诗
◆身体
紫气东来
一些素食主义梅竹兰
清理人体内的垃圾
风生水起洗尽铅华
给思想松土 身体浇水
根深蒂固抱紧岩石
春身温如玉 柔韧青如瓷
干净的身体种植梅竹兰
尘世间散发各自的馨香
◆摆渡一个春天
推开窗一两声鸟鸣
摆渡一个春天
素描中漫步的女诗人
画笔如刀刻画山水
一个云南的写真集
装满山的灵秀 水的史诗
春天鸟鸣声声
唤醒沉睡的人世间
◆青色
森林中草木、荆棘、藤蔓
坠满鸟鸣声 回荡山谷
白云、羊群行走在
喀斯特地貌的悬崖、山坡
低头的牛羊面朝青草
双眼青色的牧羊人
放牧云朵和羊群
鞭子摔打日落的山坡
空旷的大地满面黄昏
收拢苍茫如幕的内心
和沧桑的人世间
◆花与天空对影
顺着风的方向一直走
炊烟的腰带如花与天空对影
袅袅身姿清澈摇曳
没有翅膀 隐形风中
薄薄的影子弥漫
敞开胸怀 石头中取火
温暖的泉水
清洗一个干净的灵魂
黑木炭火燃烧的灰烬
飘洒大地
炊烟袅袅升起人间烟火
◆草木深处
一条山间小路
寻找一座山 一朵云
草木深处
草的味道从根茎弥漫
天空的白云
敞开花的味道
触摸草木醒来的鸟鸣
清洗干净的天空
天涯寸土 草木独醒
人烟之上
跪拜脚下的土地
一声鸟鸣唤醒人间
聆听大地
百鸟凿穿人世间的悲喜
◆花草的语境
一张纸折叠人生的厚度
秋水草木一生
花草的语境
月光的长影
往返红、黄、白之间
折叠人世间的喜怒悲伤
堆积内心的泥土
掩埋一生
刨开高原的泥土
阳光下晶莹露珠坠满鸟鸣
沉入大地的根系
吸吮全身水分
伸入泥土盘点词语
哗哗的水声流淌山河
葱郁的绿色覆盖山河
伸进岩缝
吮吸泥土中的草木
一条条根系的思想
顶开一滴露珠
诞生一首诗
◆静默的眼睛
静默的眼睛
收藏一首诗
月亮隐居 群山起伏
眼睛覆盖沉默
诠释生活的痛
关闭瞳孔
遮盖所有的忧伤
今夜为谁死一次
◆影子在地上在墙上
影子在地上在墙上
阳光下形影不离
沉入水中的影子
挣扎无语的身体
一片落叶浮在水面
水中剥离沉落的影子
没有骨肉的影子
随身体舞动露出水面
一个真实的身体伴随
影子行走在大地上
万物的影子在虚无的界限中移动
打捞群山之宝
翻阅辞典
一盏灯点燃沉默的大海
词语畅游蓝色的海洋
◆眼底的黄斑区
眼底的黄斑区
折射七彩的人生
黑亮的眼睛沉淀世界
清晨睁开双眼
清晰的图案
沉默的眼底
收藏内心的伤口
一些词语从眼中浮出
眨眼的星星幽静的珍珠
◆盘点自己的身体
盘点自己的身体
树干长出枝叶
清晰的年轮
一节一节摇晃
梦的枝条
体外的伤痕滞留心里
断崖悬念通向空空的躯壳
神的眼睛穿越云层
一生一世空空如也
声音抵达
烛照206 块骨头
支撑的灵与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