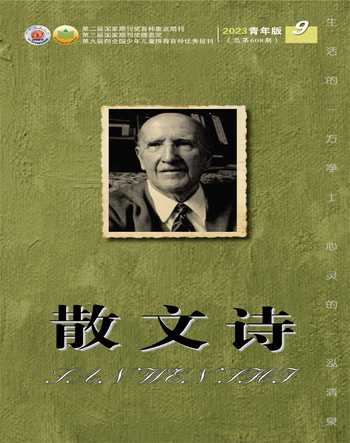雅竹,俗竹(外一篇)
贾雨霏

庭院西南面的小土坡上密密地长了野竹,东边也有一点。爷爷劈了木头做栅栏,把院子围个结结实实,只在南偏东处留一缺口,当作院子与外界通行的过道。
那些竹子简直太过显眼。
竹子们长势颇好,自我有记忆以来便越长越高,大粗瓷碗般的枝干耸起蓬松繁郁的叶,像一行大大扫帚般聚在一起。夜晚听见飒飒声,影随风动,竹就低头,一下一下在窗户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年少胆怯的我只得蜷缩在被子里偷盯着窗户,生怕一不留神,就会溜进来什么魑魅魍魉。
竹,何为竹呢?《说文解字》里的注解是: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其造字法极其简单自然,象形而已,二干四叶。
中国人是爱竹的,最早听到国人对它的赞美是有关于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之类。人们爱它中空外直和四季长青,不曲于人言,不凋于凛冬,辅之以不媚不娇、自强不息、虚心劲节的赞誉。
有竹,雅兴也。宋代大文豪苏轼在《於潜僧绿筠轩》中很诙谐地写到了这一点:“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根据苏轼的话来说,住所处无竹是万万不可的,不然,就容易使人“庸俗”,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夸张的表达。刘禹锡还曾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呢,他不也没说自己家门口到底有没有竹吗?中国古典园林在对于布局与美学考究上也偏爱竹,因此,栽竹是相当常见的。以竹造园,竹因园而茂,园因竹而彰;以竹造景,竹因景而活,园因竹而显。在园林中,绿竹与水体的搭配让人感到宁静亲切,与假山、景石相佐更显山林叠翠。要么阶下翠竹深数尺,桃花海棠疏疏杂入,留下如“竹外桃花三两枝”一般的俏丽,花开时也能蹭得点点香雪;要么参差斜入插寒梅妩媚其旁,也添些岁寒三友、四君子的风骨。更妙的是,若以窗墙为卷,任凭竹疏影横斜作画其上,幽幽竹径,归雁成行,人行其中,只感竹声清越,微飔清幽如临秋水。
但当竹脱却那一层艺术化的外壳,离开文人墨客的雅室后,还能有那么“雅”么?换句话来说,“竹”也可以俗么?
爷爷做竹篾的手艺跟竹是脱不了关系的。多少年后回顾童年,犹记得有那么一盏苍白且明亮的灯垂在院子里,爷爷和我守着院中的那些苞谷。我坐在竹编小板凳上撕开深绿嫩黄的苞谷叶,时不时还从里面滚出一只胖乎乎的幼虫来,我心一惊,撇嘴将它抖落。混着草木香的晚风拂过他的白发,灯光将我们俩笼罩,勉强拨开周围的夜色。爷爷在燈下劈竹,烤竹,捆竹,串竹,一套动作下来,他支起一只新的抓耙喜滋滋地观赏。第二天,爷爷用劈剩的细竹条给我捉几只“风车虫”回来。那虫依附在竹上,整日吸食竹的鲜嫩汁液,但极其好捉。这种虫肥大无毒反应慢,你只需将它从翅膀处轻轻一捏,便可活捉。逗孩子嘛——在它的脚上穿上竹条,你握着竹条左右晃悠,那虫便急忙张开翅膀欲飞,但徒劳,翅膀扇动的气流不小,对小孩来讲全当解闷儿,美其名曰“风车虫”。
起初,我对竹是无感的,觉得它可有可无,但之后却大为改观,只因它曾经救了我的命吧。小时候爱发烧,爷爷奶奶就用土方给我治疗。什么土方呢?即随便到外边砍一根竹回来,截断后,放在火上慢慢炙烤,竹便滴出“药”来,其下放一个碗接,约莫小半碗,就足以让我喝后康复。我抬起酸胀的眼皮去瞧淡青色的汁液,表层还浮着几粒碳灰。大人们在我身旁催促,我闭眼一口喝下,咂吧咂吧嘴,怪味是没有的,唇齿间萦绕着一股淡淡的竹子味道,跟生啃没什么区别。但病确实好了。后来得知,竹子烤出的水也确实有解渴消暑和解毒的功效。
少年时代兴致来了,喜欢观赏静物,也常喜听雨赏花,但大多时候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孰料天下之看灯者,皆看灯于灯外;看烟火者,亦皆看烟火于烟火外。我做不到像王阳明那样格竹,一格就是七天,只因他深信朱熹所讲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但只观就能把“理”给观出来吗?最后,王阳明亦明白,“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不少人对此举大为调笑,可又有谁知晓其甘愿“坐得板凳冷”的一“格”到底的求知精神呢?于不通理学的世人而言,“格竹”难免是俗事;于王阳明自己而言,“格竹”又是雅事么?
想必那些精心栽在雕楼画栋里的“雅物”,与胡乱长在鸡圈菜畦边的“俗物”本就是同一物。芸芸众生中,宜乎众者千千数,可唯有竹做到了雅与俗的兼容。那些从或贫瘠或肥沃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宽容谦逊和清正不屈,令中国人对竹的喜爱延续千年而不绝,国人的血脉中,也因此浓缩提酿出了某种最为温良的品性。而这又是什么的缩影?
那些吟诵着李杜文章的后人早已深谙其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见贤思齐,取法乎上。我回头看那一丛丛影子迎风摇曳,撩人心魄,也确实不输白堤、苏堤。才子夜读
人近晚年,难免也会因多想而忧虑。如此看来,子畏确实是怕了。是夜,花儿收苞,蛙声虫鸣渐起。子畏走到绿纱窗前探头向外看了看,只见月辉倾泻,群山墨染,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理理衣裳,便向平常写作的桌案走去。
铺纸,压镇尺,磨墨,舔笔。自己好像许久没写诗了,写点什么好呢?子畏对着宣纸思虑了很久。他提笔:夜来欹枕细思量,独卧残灯漏夜长。墨香无声,在白纸上氤氲开来,俊逸挺秀,也巧在细微跳动的烛火下映出一片苍白风致。
唐寅,字伯虎,小字子畏,又号六如居士。他有三种身份:画家,书家,诗人。他有三种悲剧:仕途,年岁,命运。子畏为明朝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商的家庭,从小玩世不恭,却又才华横溢。成化二十一年,考中苏州府试第一名进入府学读书。弘治十一年,考中应天府乡试第一入京参加会试。弘治十二年,卷入徐经科场舞弊案,坐罪入狱,遂贬为浙藩小吏。从此,子畏割断了他与科举说不清楚的缘,纵然举身赴往山水终成一代诗画名家。子畏晚年的生活穷困,需依靠朋友接济。回首他的前半生,有人说他恃才傲物,有人笑他风流成性,但也无妨有人欣赏他的潇洒自如。就如俞庆曾不仅说他“懒把文章传后世,只喜寻花问柳”,也赞他“小谪须知蓬莱客”。
子畏是爱桃花的,他爱到亲自为桃花写诗。年轻时的那一抹嫣红经历过岁月的洗涤,到如今也已然淡如云烟。他瞟了一眼残灯,挽住袖子轻轻将笔尖的残墨抹去,又添上几笔:深虑鬓毛随世白,不知腰带几时黄?是啊,时光一直在流逝,而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身负功名呢?此时的子畏不过知命之年,却悄悄生了白发。这两句的情之致,意之切,充斥着他对博取功名的向往。在四书五经为根本大纲的朝代,单纯的情寄山水不理仕途确然也太过荒谬。而子畏呢?在游历了多少名山大川之后,在这样一个静谧冷月的夜晚仍旧会偷偷燃起对科举入仕的念头。子畏,你是真的渴望,还是真的不甘呢?科举儿们在面对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时,谁又能不深怀满腔热血不渴望大展宏图呢?但是,也有那么几人,他们自觉是科举的弃儿,渴望从另一角度替自己完成新生。子畏,你就是那其中的一个。那时候的你走出了书房,美景将你的魂给托向更宽阔的地方。于是,你为了记录下这些美景开始了作画,执笔写一曲山水悠长。你在这段不同寻常的路途上邂逅了多少个明月夜,途经了哪几个杏花村?观你笔下,落霞孤鹜成为奇景,简单如杏花茅屋也被水墨定格。春山是你的伴侣,秋日金风为你执扇。你用尽了细秀的笔墨创造出舒朗秀逸的布局,只为画出你眼中的镜花水月江南。
窗外,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尖细地啼叫几声,惹得几丛翠竹摇曳,洒下清光。你搁下笔,用剪刀将已烧完的烛芯挑掉,果然,烛火比先前明亮了几分。“剩仙馆,桃花如旧?”子畏,你又想起先前为桃花写诗的时候了罢。“就算晚年又怎样?”你冷哼一声,挥毫写下: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我唐子畏不仅可以种得桃树折花卖酒,而且区区写文章的事,怎么难得倒我?”
原来,子畏,你没怕啊。
犹记桃花仙人酒醒花前坐,酒醉花下眠。子畏喜欢李白,不知是否与你的性情相似呢?你说“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永远诗情洋溢的你从不妄图沾染半分铜臭与浮势,但也偶尔叹息“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英雄豪杰么?无花无酒怎么行?桃花是料峭春天里最璀璨的一抹红。早时缱绻舒展开放,晚时又洋洋洒洒尽数飘落。
名也,功也。你抬眼掠过一排排书架与卷宗,一张白纸已经快被填满,砚中的墨悄然映出你眼中闪烁的光。墨快干了,你急急于砚台舔笔如行云流水般书下最后两句: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而这决绝的最后两句竟将你的才子本色全然显现。
子畏啊,古今多少才子佳人,或迷茫,或逍遥。而你很矛盾,我能说你和科举藕断丝连吗?我不能。你有你的执念,也有你的桃花源。你前期偏于儒家,后期偏于佛性。但是,读书仕途的愿景始终萦绕在你的心头,无论走过多少山川,也换不回。
你总是在月夜下负箧赶路,可散在幽丛中的萤火又吸引着你的目光。青天之上的月始终照不清楚瓣瓣桃花,但你能把书箱子丢了去寻花吗?你,不能。你想写文章,你想画画,但是,这一定是写你自己想写的,画你自己想画的。于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你写了一诗,名日《夜读》。子畏,你读了什么呢?
嘉靖二年,唐寅病逝,时年五十四岁。
子畏,在你的画里,山上孤亭才落日,门前高柳系行舟。在你的梦里,花前花后日复日,酒醉酒醒年复年。
有花有酒,才是才子的标配。子畏可知么?千百年来,无论在怎样的夜里,这世间总有才子在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