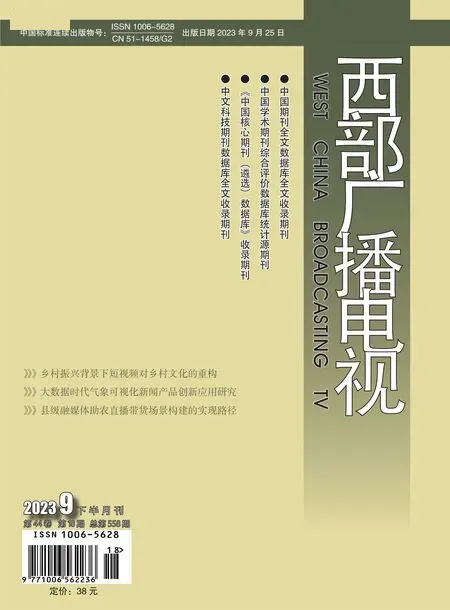《宇宙探索编辑部》叙事特点研究
黄 晴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宇宙探索编辑部》由孔大山执导,讲述了坚信外星生命体存在的科幻杂志主编唐志军,和一群看似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同行者踏上寻找外星人之路的故事。影片斩获平遥国际电影展多个奖项,并先后在第51 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第46 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第12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获得好评。不同于其他科幻类别的影片,《宇宙探索编辑部》没有华丽炫目的特效和惊心动魄的反转剧情,而是在虚实穿插之中讲述了普通人对于宇宙奥秘的探索。该片在看似荒诞不经的叙事中,包裹着庄重严肃的内核,同时在影像表达上也体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
1 虚实相生的叙事方式
影片从一段20 世纪电视台记者采访唐志军的新闻画面引入,复古的视觉特效和画幅比都暗示这是一桩真实的“旧闻”。随着画幅比的变化,凋敝的《宇宙探索》杂志社和中年唐志军进入观众视野。不同于彼时电视画面中意气风发的杂志主编,此时的唐志军面临着杂志社难以存续的状况,不得不靠财大气粗且对科学毫无敬畏之心的赞助商出钱挽救杂志社。这是影片中一次较为直白展现唐志军内心矛盾挣扎的情节,也是长久以来他所面临的困苦现实与理想之间矛盾冲突的缩影。
导演通过虚与实、现实与超现实的叙事穿插呈现这种“对立”。影片故事情节发展由现实逻辑的时间线索驱动,却多处存在着无序的、超越现实认知经验的荒谬情节拼贴。唐志军在精神科病房看到的身着西游记服饰蹦迪的“患者”、开着游乐玩具车却与唐志军一行同步出现的“陨石猎人”等,它们仿佛是平庸的现实速写画上出现的斑斓墨迹,二者之间充满了对立与撕裂,却又在影片叙事主题的统一下交织融合,使“荒诞”感成为影片的特殊风格。
波德维尔将时空的关系视为理解故事的关键因素,时空的连续性剪辑,使得空间和时间的同质性与叙事的连贯性得以保证。《宇宙探索编辑部》按照线性时间顺序来结构叙事链条,其情节发展遵循现实时间的流动,这种时空上的同质性使得其叙事逻辑得以连贯。导演通过粗粝冷峻的画面和纪实的拍摄风格,还原现实语境下人物作为社会边缘“失语者”的生存状态。不同于追求画面精致度而选择固定机位拍摄,《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导演大量采用手持拍摄,轻微的晃动感带来了强烈的临场感和纪实性。回溯手持摄影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它与电影拍摄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手持摄影自诞生便代表着对传统拍摄方法的反叛,在20 世纪60 年代法国新浪潮运动和纪录片领域的真实电影运动中,作为具有革新面貌的新生事物——手持摄影大放异彩,摄影机体积的缩小和录音设备的发展使得大量普通人也能记录生活,为青年电影人作者化的影像表达提供了便捷的途径[1]11-12。20 世纪90 年代,轨道、摇臂和斯坦尼康等专业移动拍摄设备相继出现,如何让摄影机运动已不再成为难题。但这并不代表手持摄影被取代,手持摄影最初主要的目的或许是解放摄影机,但其实本质上代表着一种革新的勇气,是对于传统拍摄方式的颠覆。“道格玛95”运动沿袭了手持摄影的真实美学,坚持对抗传统精致的影像美学,将手持摄影再次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如今手持摄影已不再是小众文艺的拍摄方式,它被商业电影广泛吸纳,不少主流好莱坞电影中也可见其身影,成为商业电影的噱头。或许反叛性已不再是其主要标签,但极高的画面自由度和纪实感仍是其难以被取代的影像风格。手持摄影使得摄影机不仅作为银幕空间内的旁观者而存在,同时进入人物本身,还原其心理、情绪和境遇,这使得影片更具情绪张力。手持摄影将客观的写实主义与主观的心理刻画结合,深入挖掘人物的情感和存在状态,并在最大限度上将其还原表现[1]22-23。
在20 世纪末,影界兴起了一股以《女巫布莱尔》为代表的伪纪录片风潮,极端的“晃动”和粗糙的拍摄手法极大地增加了真实感,新奇刺激的视觉体验迅速俘获观众从而风靡全球。伪纪录片电影是以模仿伪纪录片的创作手法而进行创作的叙事电影,但其又并非是完全虚构的叙事电影,它承袭于法国“真实电影”纪录片美学流派,倡导的是与“旁观”截然相反的纪实美学——“在场”[2]。伪纪录片得益于手持摄影的发展,同时也将手持摄影美学的特点发挥到极致。在伪纪录片中,摄影机不再“隐身”,影片中的人物不再刻意回避摄影机的存在,影像和现实不再完全独立,荧幕成为观众与摄影机世界的交互界面。在《宇宙探索编辑部》中,人物面对观众剖析内心世界,透过银幕与观众对话。影片以采访唐志军作为第一个画面展开,在后续叙事中也延续了该形式。这种拍摄方式将唐志军等作为社会世俗语境下的边缘群体置于叙事中心,通过采访这种不可逃避的人际交流展露内心,组织影片叙事开展。贾樟柯在拍摄《二十四城记》时也采取了类似的叙事方式,即根据叙述者所描述的极具时代特征的细节来再现时代场景。这种用虚构表现真实的拍摄方式,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感知体验。《宇宙探索编辑部》中粗粝、未经修饰的西部乡村荒凉实景和纪实性拍摄手法共同创造了影片疏离忧郁、冷峻客观的情感氛围。
《宇宙探索编辑部》中存在大量超乎常理,用现实理论无法解释的事件和现象,赋予影片迷离奇特的超现实色彩。不管是日食与石狮子的传闻,还是在山谷中突然出现的悬挂着胡萝卜的驴等,这些无一例外都是超越现实中人们常规认知的事情。在无序、错乱的叙事线索中,影片将观众既往的视觉经验打破,触动观众的潜意识介入思索。这种迷离的、荒诞的超现实表达引导观众深刻介入影片意识空间,与作者共鸣,与自己对话。正如1924 年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写道:“超现实主义,它是纯粹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人们通过它,以口头、书面或任何其他方式表现出思想的实际功能。它是对思想的支配,而不受任何理智的控制,它超脱任何美学或道德的追求。”[3]
整部电影都侧重于通过人物内心建构情节,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分界并不明晰,处处充满含混的表达。影片末尾,唐志军独自前往山林深处寻找外星人,误食毒蘑菇后,看见了孙一通,看见了麻雀落满石像,看见了宇宙,看见了自我。观众很难辨清现实与非现实,这种“自由穿越”,其实就是将魔幻当现实一样来写,将超现实叙事当作真实叙事一样来处理,也即“用叙述真实事物一样的语调叙述神奇的东西”[4]。通过这种迷离玄幻、亦真亦假的叙事安排,整部影片在现实之上超越现实,在现实中看到理想的倒影。
2 互文倒映的镜像叙事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通常指不同文本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或一个文本向其他文本产生扩散性影响,也称为“文本间性”。1966 年,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研究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文章《词语、对话、小说》中,首次提出了“互文性”一词,她认为“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5]。随着互文性理论的不断发展,“文本”不再局限于传统认知的文学范畴,渐渐地拓展到音乐、绘画和电影领域,文本与文本之间复杂相融的关系使得文本的解读维度被大大拓展,也为电影文本提供了另一重读解方式。而在电影艺术领域中,互文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影响的文本之间的关联性,后来的文本参照现有文本,现有文本某种程度上源于对其他文本的参照,大多数电影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互文[3]。
《宇宙探索编辑部》的英文译名为“journey to the west”(西游记),其在人物塑造和叙事上也都体现出与《西游记》的互文。影片中众人在精神病院见到的“唐僧团队”、成都街头的悟空形象扮演者,都是极具辨识度的西游记符号。电影充分运用互文关系来建构主要人物形象,使得人物特征更加鲜明,彼此之间的人物关系和形象也更加丰富立体。这种基于人物间相似的性格特征和生存境遇的互文,打破了单一文本的边界,加深了观众对于人物、文本内涵的理解,拓展了文本的意义层次和解释空间。唐志军和孙一通的姓氏与人物关系明显体现出与唐僧和孙悟空之间的某种微妙对照。两组人物间具有极为相似的经历和价值追求,唐志军坚守理想,甘心孑然一身前往西部山区寻找外星人,途中遇到了多重虚实阻碍,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而孙一通的生存状况和世俗的眼光是一座无形的“五指山”,他是不被世俗接纳的且具有“原生之罪”的,而唐志军的到来给予了他价值和意义。这种人物之间关系的互文使得文本内涵被拓展,观众更加深入文本之中。
从主题互文的角度看,二者也共享着极其相似的主题内容模式。叙事主线上,影片中唐志军一行一路向西是为了寻找外星人,这与《西游记》中西天取经的故事线索相类似。《宇宙探索编辑部》中,唐志军不顾一切出发寻找外星人的目的,一方面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顽固坚守,另一方面是旨在探寻人存在于宇宙中的意义。从本质来说,不管是唐僧还是唐志军,他们终其一生求索的并非完全是某种物质上的实体,他们真正追寻的是关于人生和存在的意义。
导演孔大山曾说电影的主题曲只能是《生活倒影》。生活的倒影,它既是生活的一部分,脱胎于生活本质,却又在“水”这个介质的影响下倒映出另一重人生。唐志军等人边缘化的社会身份是生活的真实,为理想一路向西求索是执拗的浪漫。人物和主题的双重互文使得电影文本边界得以拓展,加深了观众对于影片内涵的理解,同时使得影片具有更加深层的表达空间。
3 荒诞如诗的叙事风格
诗意电影是一个被频繁提及却又难以厘清的概念,意大利电影理论学家帕索里尼认为电影诗意来源于“非理性”,电影在实质上和本性上是诗意的。诗意电影在创作上有其独特的拍摄形式,而更为鲜明的特点是其具有更深层次的美学追求和哲思。如同诗歌一般,诗意电影在表达上也追求言外之意和表层叙事之上的意境之美,并在此基础上上升到对于生命本原和生存哲学的体悟。
电影以镜头画面为基本表达单元,作为声画融合的艺术,其相较于诗歌具有更大的表达空间,通过镜头语言和配乐等为影片注入诗意。毕赣在创作《路边野餐》的“荡麦”部分时,采用了长达40 分钟的长镜头拍摄,这不仅是对于既有电影规则的打破,对于观众观影习惯的挑战,也是导演对于时间哲学理解的彻底影像化呈现,并最终以诗意形式表现。《宇宙探索编辑部》中的高潮部分——日食片段孙一通倒数着扭过头来,最后一帧定格并直视摄影机,穿过荧幕向观众发出闭眼指令,配合着诡异肃穆的音乐和画面,观众不自觉卷入这一场庄重的“仪式”。这不仅打破了“演员不能直视摄影机”的电影规则,还打碎了二维平面与三维立体、虚构时空和现实时空之间的屏障,这也是本片具有突破性的摄影风格之一。
电影中的画面通过剪辑相互组合,不同的镜头按照“句法”进行串联排布,共同构成完整的影像。《宇宙探索编辑部》多处采用跳切的剪辑方式,快速且明显的跳切产生了如诗一般的节奏韵律,而留白和省略使得影片更具诗歌“弦外之音”的意境之美。影片中人物所有的荒诞和苦闷都融化在影片隽永的诗意中,在现实与理想倒影之间,导演采用诗歌作为介质进行连接。大量的诗句“漂浮”在影片中,不仅通过人物之口说出来,还直接成为画面的一部分展示在荧幕上,作为影片诗意感鲜明的符号和叙事“预言”。例如,“破碎蛋壳的月光被潮汐收回深海”“隐匿的爆炸吞噬了灰尘”等,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文艺色彩,还是叙事发展和现实状态的隐喻,具有强烈的预言性。
音乐是电影里的重要元素,塔可夫斯基曾将音乐比作诗歌中的叠句,“叠句让我们重温初次进入诗之世界的经验,使它在创造的同时立即得到更新”[6-7]。古典乐的使用,使得《宇宙探索编辑部》拥有了更加隐秘和自由的另一层表达空间。唐志军对着电视上的雪花点,用木讷严谨的语气说出“电视上的雪花点,是宇宙大爆炸后的余晖”,此刻,巴赫的D 小调协奏曲BWV974 响起。BWV974 是巴赫根据意大利作曲家亚历山德罗·马切洛双簧管协奏曲而改编,这是一首具有巴洛克时期浪漫风格的曲子,轻柔的忧伤具有强烈的诉说感。唐志军因破旧的宇航服陷入生命危机时,消防吊车将他从二楼窗户吊起,此时导演采用多个机位拍摄唐志军的“降临”,配乐采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慷慨激昂,带着某种神圣感的庄重管弦乐配合着略显荒诞的情节,在矛盾感之外,暗含着影片对于理想主义者的某种自嘲与致敬。而孙一通朗读诗歌时,配乐采用了《圣母颂》,仿佛上演着一场与现实割裂的剧目,预告着即将彻底到来的超现实浪漫。这种“弦外之音”使得影片如诗歌一般具有意境之美,激发了观众更深层次的思索。
4 结语
《宇宙探索编辑部》讲述的是关于科幻的故事,但不同于体现电影工业水平,有着超强视觉特效的“硬科幻”电影,它更像是一首朴素的、娓娓道来的“科幻诗”,它所讲述的也仅是普通人对于宇宙奥秘的追寻。影片没有炫目的视觉特效和夸张的剧情反转,其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形成了标志性的美学风格,彰显了新一代导演的创造活力。其中虚实相生的叙事穿插、互文倒映的镜像叙事和荒诞如诗的风格也拓展了电影文本的广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