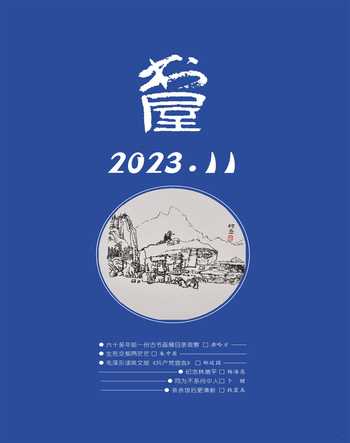我与李庄廿三年
一
周谷城在为“民国丛书”所作《序言》中说:
民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新旧思想冲突,产生了许多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五四”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乎变成了世界学术的缩影,各种主义、党派、学派、教派纷纷传入,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一个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在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中央研究院是为增长国家实力、促进科学事业的进步而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一成立即标志着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那些“书生”摆脱“仕进”与“独守”之桎梏,开辟出一条集团研究、知识立身的道路,胡适称之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傅斯年称之为“新学术之路”,并创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迁往重庆。南京和北平、上海等地一批学术教育机构一再播迁,栖息长沙、昆明等地,最后竟在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傅斯年语)——四川南溪县李庄落籍。
长江边上的古镇李庄,以山水的柔情与静默,接纳并呵护民族的“衣冠”。镇上“九宫十八庙”驻扎同济大学,乡下祠堂农舍分布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单位。这批学者,或乘一袭滑竿,或挟一把油伞,行色匆匆,出没乡间泥泞。其中有“中国社会学奠基人”陶孟和、“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博士、“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博士、“中国民族学开创者”凌纯声博士、“中国体质人类学奠基人”吴定良博士,“中国建筑科学之父”梁思成以及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永、巫宝三、梁方仲等。这批先生在后辈学人许倬云眼中,是“希腊精神与儒家修养结合的君子人”。他们大多生于晚清,系出名门,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恫瘝在抱,忧国忧民,目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有学术救国的情怀,其立足点是贯通中西,研究方向是“中国问题”。
那时,小镇李庄与南溪县、宜宾(专区)、重庆,甚至世界,意外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同有了共同的根须、共同的叶脉、共同的呼吸。海外邮件只要写上“四川李庄某某信箱”便能准确寄达;同盟国一些科研机构常收到寄自“李庄”的交换刊物书籍。印度学者狄克锡曾在板栗坳史语所度过一段难忘的访学时光。外国教授史图博、魏特、鲍克兰、史梯瓦特、陈一荻等,跟随同济大学迁徙李庄,风雨同舟。波兰籍犹太人魏特教授成了葬在李庄天井山的孤魂。李约瑟来到李庄,获得了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史料,并从史语所挖走一个叫王铃的青年,成为他日后重要的合作伙伴。外籍友人费正清、费慰梅、翟荫等曾造访李庄,并与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董作宾、童第周等保持长期联系。
板栗坳绿荫丛的“田边上”掩隐着一座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藏有十七万册中西文图书。一大批学人追随至此,含英咀华,依靠图书資料,写出高质量论著。“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柏木牌匾,曾挂在栗峰书院一户农舍门前,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王明、杨志玖、王叔岷等,在那里苦读数年,完成研究生学业。后在南洋执教的校雠学大家王叔岷晚年感叹,身为北大研究生,竟一生未迈进北大校门。
偏僻山村,远离炮火硝烟,但愚、贫、病、匪等魔影会随风潜入,伺机作祟。李庄民智不开,一次“下江人吃人”的谣传,山山水水都回荡着惊恐;举办“太太客厅”的林徽因,曾光焰万丈,语惊四座,而在李庄月亮田,她是吃尽当光、卧床不起的病人;梁思成的兄弟、考古学家梁思永,胃病肺病并发,躺在担架上被抬着离开那片土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的两个女儿,两年间相继在昆明和李庄病逝;川南匪患不靖,在刺刀的保护下,那些一心向学的谦谦君子终不免战战兢兢,艰难前行……
乱世烽烟,板荡不已。破庙祠堂,庠序如旧。当代学人陈平原认为,战时教育科研机构内迁,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在组织上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搬迁;精神上不是逃难,而是弦歌不辍;教学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战时如平时”,着眼于战后建设与人才培养。同济大学依靠这张宁静的“大书桌”,为国储才,培养了战后建设的一大批精英。中研院、中博院和营造学社学人,“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把家仇国恨化为案头研读、笔下文章,扛鼎之作《殷历谱》《六同别录》《居延汉简考释》《上古音韵表稿》《博物馆》《远古石器浅说》《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等,在李庄完成并石印出版;一批开创性著作,如《中国建筑史》《撒尼倮倮语语法》《明清档案研究》《中华民间工艺图说》《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太平天国史纲》等,在李庄完成前期准备,甫一出版即声名鹊起,至今被学术界奉为圭臬。
李庄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小山村,而是衣冠南渡、文化抗战的重要场域,是一大批学人一大批学术成果的汇聚地。今日学界仍在传承其学脉和精神,仍在吸吮“李庄”的隔代或异代养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读懂李庄也是读懂中国。
二
《发现李庄》,发现是个动词,是不止歇的过程。
二十多年前,写《发现李庄》,不识前路,亦无同道,单枪匹马。书一面世,托荫先贤,在受到学界认同、学人嘉勉的同时,作者也得到粗浅的学术规训。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给我提供过演讲平台,帮助我知晓“发现李庄”的学术与学术史意义。原中研院研究员、历史学家何兹全,梁思永先生遗孀李福曼,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等,曾接受我的专访。逯钦立的遗孀罗筱蕖、陈寅恪的长女陈流求、李济之子李光谟、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董作宾之子董敏、石璋如的公子石磊、李霖灿的公子李在中等,与我成了忘年交。学者余英时、许倬云、王汎森、罗志田、王明珂等给我鼓励甚至点拨。这些来自各个方面的恩典与助益,也形如一根根缰绳,一副副鞍鞯,鞭策我这匹老马,不得不奋力前行。
拙作《发现李庄》出版后,在收获肯定的同时,也遭到批评。同济大学当年的教务长薛祉镐是宁波鄞县人,工学博士。其子薛恭稼从杭州致信作者:李庄地处丘陵、坎坷不平,外地迁入安置点极为分散,丁文渊和傅斯年等出行皆坐滑竿……材料不等于史料,史料未必真实。“治史如断狱”,薛先生的信让我醍醐灌顶。
当年,我用虚构想象“场景还原”,写“十六字电文”产生背景、过程和影响,成了其后李庄故事的开篇。这当中,聚会场景、人物语态表情,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后来始知,“十六字电文”虽查无实据,而事出有因,且不胜枚举。如现在宜宾档案馆就存藏有卅二位乡绅给四川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冷熏南的请愿书,要求把李庄镇上的公产拨付同济大学使用。这都需要以同情心、同理心,辨析清楚,表述公允。
一段时间,李庄旅游宣传把月亮田营造学社旧址标识为“梁林故居”。在李庄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梁思成的孙子梁鉴说,把营造学社旧址说成是“梁林故居”不恰当。那时不光有梁思成,还有刘敦桢。法式部和文献部是中国营造学社两大支柱。刘敦桢留学日本,有别于留学欧美的梁思成等,但这一建筑学派也自成风格。当年,中国营造学社依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为博物馆下属的建筑史料委员会,这段史实几近湮没。
史语所中的一些学者去了台湾,他们被称作“史料学派”,重视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发布,历史文献保存完整,因此李庄叙述占了绝大部分。留在大陆的社会所,资料阙如。1949年后,社会所整体转为经济所,原社会所的资料文牍被掩藏。这种情况,直到2019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建所九十周年才得以改变。随着一批史料浮出水面,社会所的李庄故事也开始露出冰山一角。
同济大学重视与李庄联系,近二十年更为亲密。也有很多人参与对李庄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但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时间段对史料有不同解读。
《发现李庄》三部曲,是集二十年时间,无数人辛劳的新的史料、新的发现、新的表述。
三
2004年5月10日,《发现李庄》在李庄举行首发式。十天后,我接到李庄友人左照环电话,说今早一点罗萼芬在宜宾去世。据说前一天他读完《发现李庄》,昨天一早就去宜宾城会晤东北返籍探亲的九姐罗筱蕖。“在九孃(罗筱蕖)寓所当夜发病,送到医院就去世了”。我颤抖着把电话打到罗萼芬家,他儿子罗建新接电话,说:“父亲读到书很高兴,说认识你是这辈子的幸运,一家人都感谢你。”还说:“父亲和九孃姐弟见面,太激动了,说了一夜的话,直到说不出。”一本书,带走一个老人的生命,我一生愧疚不安。
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年轻时他告别父母,独自回到大陆,退休后曾一趟一趟地前往李庄,为追忆过去,缅怀亲人。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我有幸与其成为忘年交,随之出游湖北钟祥、北京清华园与北海蚕坛、山西西阴村,以及李庄……这都是他父亲李济出生求学工作食息的重要地点。没有这些因缘际会,不会有拙作《李济传》问世。2013年11月某日,我接到李光谟电话,说他在石家庄的一个好友走了,他们从在李庄读同济附中结识,友谊持续六十余年。光谟先生声音低沉,希望我到北京陪陪他,或有话要说。半个月后(12月7日),得到他去世噩耗,我即赴京扶灵,陪送老师最后一程。而今,灯下枯坐,徒有追忆与涌出的悲情。
劳榦之子延煊、延炯兄弟,是我未曾谋面的朋友,两次通信后即肝胆相照。有一段时期,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兄弟俩一封或两封信,早上醒来开手机读电邮,成了我的一个习惯。他们告诉我关于李庄的很多细节,比如傅斯年家,最早不在桂花坳,而是在板栗坳礼堂旁边。送他们来李庄的轮船泊在江心,再用小划子把行李一船一船运到岸边,再顺着高石梯一步一步挑上去。他们跟我讲了很多有趣故事,如向达之子向延生和李方桂之子李培德打架,张官周之子被“绑肥猪”等。细节就像屏幕上的像素点,个数越多,清晰度越高。
李霖灿之子李在中,研究李庄起步晚,但作为“学二代”,自幼耳濡目染,接触材料上手快,成果丰盈,写中博院的专著《朵云封事》出版即洛阳纸贵。他有时间有能力有条件,从加拿大到中国台湾、四川、云南、南京、北京,满世界寻找知情人,打捞与核实资料。我们相见恨晚,一见倾心,有过很多次坦诚讨论,比如“十六字电文”的真伪,如何评价李济与梁思永考古发掘的贡献与局限,如何看待傅斯年的霸蛮,如何看待李济去台后主编的《中国上古史》等。有共识、有分歧、有争论、有保留,全都恪守公义。他无私地给我提供了很多高清照片,有的是他不遗余力收集来的,有的是他发动学人后代如李光宇之女李前珍、董作宾之子董敏、李光涛之女李幼萱等人提供,经他扫描汇总的。李在中比我长两岁,我们都直道而行、不假辞色。我们偶有争论,一次甚至拍案而起,不约而同地说,十年以后看谁对谁错,错了,一定当众认输。2020年3月16日,董作宾之子董敏在台湾去世。在中在QQ上给我留言:“疫情的蔓延更使人走得凄凉!”像是谶语,同年8月8日,在中在加拿大去世。董敏晚年患有帕金森病,早知会有这一天,而在中兄不曾有任何先兆,竟不辞而别。呜呼!再没有可以和我辩难的朋友了。
“故人笑比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清金农诗),被年年秋风掠走的,还有李庄的芳草良木。
傅斯年在桂花坳住过的是一普通农舍,后来的房主、永胜村六组村民张家友是土改后分到此屋的。不过,他们家与傅斯年还真有缘分。二十年前,我先认识他哥张汉青。当时,他在红苕地里理苕藤。他给我讲他父亲张海洲当年给傅斯年抬滑竿,傅斯年如何体恤乡亲的故事。几年后,张汉青悄然谢世。2007年秋日,我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第十任所长王汎森来到桂花坳,见到张汉青的弟弟张家友。回台以后,王将一本《傅斯年先生文物资料选集》寄赠这位未必识文断字的村民,并亲笔恭书“家友先生惠存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汎森赠 2007年11月”。张家友无负海峡那边的情谊,将此物视为拱璧,决不轻易示人。据说有人出价两千元,他坚决不卖。2021年春日,大学同学组团到李庄,我当导游,当我们兴冲冲走到桂花坳,围过来的乡亲告诉我,张家友几个月前刚刚病逝。
发现李庄,是一场场肃然悲壮的告别仪式。当年我采访过的李庄友人,相继去世的,有板栗坳村民鄧素华、陈金辉与母亲李婆婆,门官田村民张执中,以及原镇党委书记孙远宾、驾驶员周建东等。
“生命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会停止。”(卡夫卡)西人不惧死亡,“死亡,使灵魂脱离身体这个牢笼,上到天堂,与诸神同在”。我的一位亲人死了,是我的一个部分死了。我的朋友故去,他带走了我与世界的一部分。季羡林在回忆北大历史系教授、宋史泰斗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一个词“后死者”——这是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也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后死者应承续先行者的历史“托付”,有责任和使命,接着往下讲,往下做。
自第一次寻访李庄,转眼过去二十多年。那时我未晋知非之年,而今已逾古稀,黄昏薄暮,来日无多。但文本《发现李庄》三部曲会留下来,会有更多的读者化为作者,汇入更多阐释、批评,进一步发现、充实。
(岱峻:《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一张中国大书桌》《一本战时风雅笺》,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读岳南的《那时的先生1940-1946 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
——李庄古镇代表性应用图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