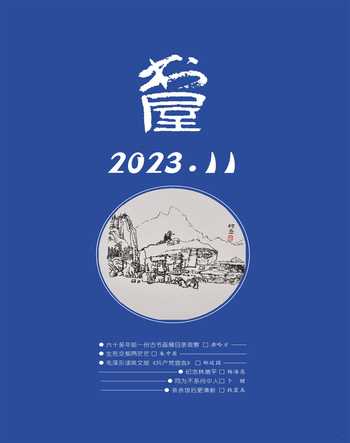茶余饭后更清新
钱震来
又至奥斯卡
杨紫琼入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为自己拉票,本无可厚非,但媒体评论说,以“族裔”或者“划时代”为理由,站不住脚。与她竞争的最强对手是澳大利亚的布兰切特,曾两次获奖,她在新片《塔尔》中演技极佳,无可挑剔。冲着杨紫琼是首位提名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华裔,我兴致勃勃观看《瞬息全宇宙》,但只看了个开头,便逃之夭夭。行家预测说,虽然布兰切特应该获奖,但杨紫琼会最终抱得奖杯。据说两位是亲密好友,看来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了。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颇值得关注,这是2022年爱尔兰、英国和美国合拍的黑色讽刺电影,讲述爱尔兰内战期间一座小镇的两位好友突然结束了彼此间的友谊,导致发生冲突,断的不只是友谊,还有拉小提琴的手指。这是一部奇怪至极的电影,倒不是情节曲折怪异,而是简单却令人震撼。因不知历史,也无兴趣去补课,只能说电影既血腥又美丽,既暴力又温馨,人物既极端又多情,既可气又可爱,是此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中最与众不同、令人回味无穷的一部,有点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的味道:一样的与世隔绝的地点,一样的时间停滞,一样的疯狂的人物,行为怪异,但对人性有着更深入的剖析。其他如《猫王》看后一点印象都没有,斯皮尔伯格的《造梦之家》耐着性子看了十分钟,也败下阵来。对好莱坞投票人品味不敢恭维,似乎影片但凡差到看不下去,就有得奖的可能。果不其然,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不但杨紫琼成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而且《瞬息全宇宙》包揽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七项大奖,真可谓是拿奖拿到手软,因此重睹“芳容”再探究竟,成了义不容辞的任务。上次是两分钟,这次硬着头皮再看《瞬息全宇宙》,足足坚持了三十分钟后,还是彻底放弃。尽管是华裔演员做主角,对话中也有不少汉语,可我一点都看不懂,这已不是最佳不最佳的问题,而是有评为最差影片的“资质”。别看片名唬人,但毕竟不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又是时间“瞬息”,又是空间“全宇宙”,看不懂不是其内容高深,而是逻辑不通,不知所云,有点像是中学生编剧在异想天开,想一出是一出。情节拙劣,画面粗糙,又像是业余网剧。与其听赞美者硬将其与《红楼梦》的“水中月,镜中花”扯上关系,还不如说此乃“大世界哈哈镜”在“还魂”。不过可喜可贺的是,尽管姗姗来迟,勤劳务实的华裔还是终于踏进了“荒诞派”的门槛。托尔斯泰说,艺术的本质是将自己所体验到的情感传达给别人。想必《瞬息全宇宙》的作者也有所体验,电影有一种“半成品”式的混沌,还在未能自圆其说时便迫不及待地抛了出来,成功地演绎出“痴人说梦”的境界,让观众头晕目眩。据悉有相当一部分观众难以接受,败下阵来。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这回可真是彻彻底底傻了眼。其实将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译成“瞬息全宇宙”完全是在迎合年轻一代人的口味,相当有误导性。如果照字面意思老老实实翻译,应是“一切事物,一切地方,全撞在一起了”,可不就是“乱作一团”吗?小年轻们尽可乐在其中,年事已高的观众,还是不来凑这个热闹为好。相比影片《塔尔》或《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巫》等佳作,《瞬息全宇宙》简直是笑话,如果这便是华裔电影的最高境界,那就太可悲了。这样的作品居然包揽奥斯卡众多奖项,简直是黑色喜剧的现实版。身为华裔,看着领奖人在台上欢呼雀跃,喜极而泣,实在是五味杂陈,太让人尴尬了。我们本应該也有能力做更好的呈现,如果这便是世界对华裔或亚裔的定义和期盼,那就太侮辱人了!
现代派之烦恼
好的旋律全被写完了,好的画作全被画完了,好的故事全被讲完了,但作曲家、画家、小说家也得有饭吃,也得有存在的理由,于是开辟出新战场,什么无调性、现代派、荒诞派,加上经纪人疯狂炒作,为了赚取佣金,顾客就成了被宰的羔羊。当然其中也有真正的天才艺术家。无奈人生有限,欣赏古典艺术还来不及,即便活到七八十岁,也不会有再去“逐臭”的紧迫感,更无必要吃力不讨好,去与我们的本性作对。无调性音乐会让人头痛欲裂、神经衰弱,即便大名鼎鼎如毕加索的画如果挂在卧室中,也会让你噩梦连连,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没必要为“赶时髦”而跟自己过不去的。
每日一弹
二十岁在农场劳动时便想着退休,难怪过了而立之年,我会一边在电影乐团拉小提琴,一边又找了专业老师助我重拾钢琴,未雨绸缪地计划着遥远的某一天,我能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与世无争地与钢琴相伴,安度晚年。小提琴真是一件“残酷”的乐器,大师帕尔曼说,拉小提琴在生理上是最不自然的,你得将琴扛在肩上,下巴夹住,左臂抬起反向扭转,右手横向左手竖向朝不同方向运动,为揉弦左手还得抽风似地前后摇晃,等千辛万苦把音拉准,你已七十岁了。的确,拉小提琴像是耍杂技,惊心动魄,差不得一毫半厘,如同走钢丝、翻跟斗,比快比灵活,等着别人啧啧惊叹。十几首协奏曲翻来覆去、精益求精,练音准一丝不苟、吹毛求疵,永无止境。可惜不论多么完美,终究还是“孤掌独鸣”,缺了其他声部,或者说缺了四重奏中的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音乐“是不完整的”。付出了大好年华,得到的只是无可奈何的缺憾。相比之下,钢琴则更像是一个独立王国,几乎能满足你对音乐的一切幻想。即便单独演奏,也会有千军万马就在十指下。对疏于交际者,弹钢琴也可以是非常个人的事,你避开喧嚣,离群索居,一头扎进书本堆里,博览群“谱”,游弋于浩瀚的音乐海洋,与大师交朋友,向高人提问讨教,请求释疑解惑,收获精神上的成长与富足,与他人无关。原本就不打扑克,不会搓麻将,从没玩过电子游戏的我,在人生的暮年,还是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大玩具”,在童年时会玩一点儿的钢琴上,煞有介事地弹起了巴赫的平均律曲和肖邦的练习曲,外加几首李斯特名曲。不知算是“如愿以偿”还是“现世报”,小时候怎么也不肯练琴、钢琴老师见我头痛的场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弹巴赫是为了还债和给自己定规矩,弹肖邦是因为喜欢,弹李斯特是为了痛快。巴赫是“排列组合”的巧匠,又是转调大师,尤其在著名的《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中,每逢单一音型的古典舞曲乐章,这两种手法表现得更加明显:或是每每“模进”三五次后,便必节外生枝,调整音序,小换花样。颠来倒去苦折腾,貌似小打小闹,却是偷梁换柱,暗度陈仓;或是临时升降号层出不穷,在不同调性之间牵线搭桥,让它们眉来眼去,暗通款曲,却又游离于任何一调之外,若即若离,行进在“遗传与变异”、好事多磨的路上。至于为何如此劳神费力,想必部分原因在于小提琴这一以单声部为主的乐器的局限性,只能苦心经营,把戏做足。不过在考验着自己“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能耐时,巴赫总能另辟蹊径,不但化险为夷,还常有别出心裁的意外收获。他的《平均律钢琴曲集》,原本是为证明“平均律”能带来全方位的转调自由,却无意成了器乐作曲的百科全书,其内容之原创性和丰富多彩成了后辈取之不尽的宝藏,包括奉巴赫为音乐宗师的肖邦也受益良多。肖邦除了有异常敏锐的听觉外,更有对“美”天生的感悟。表现力更强的现代钢琴的出现,已让他无需留意巴赫稍嫌枯燥的“排列组合”,这些本来就与肖邦的浪漫气质不合。而巴赫特有的“调性游离不定”的灵活性,或者说模糊性,在肖邦手中则迎来了华丽大转身,蝶化出了色彩斑斓的诗篇:每进入一个新段落,不再含糊其词,而是“更上一层楼”,“柳暗花明又一村”地立足于某种“确定无疑”的新调性上,屏气凝神地等着肖邦美妙的旋律,或者说他心中的天后女高音的闪亮登场,肖邦的四首《叙事曲》便是最好的实例。说到底,肖邦是意大利歌剧迷,对肖邦而言,歌剧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同时代的歌剧作曲家贝利尼、唐尼采蒂、罗西尼对肖邦的影响大于贝多芬、李斯特或者舒曼。调性分明、声情并茂的咏叹调才是肖邦心目中的“芳草绿地”和重心所在,而非巴赫那种偏重于器乐性的“循序渐进”,偏重于过程本身而踌躇在宣叙调上的流连忘返。易受伤害、极度敏感,又让肖邦的音乐触及心灵深处,纵然曾被批评为“病态”,却绝对是内容与形式或者说“灵与肉”的完美结合。相对于巴赫辨不出哪是哪的什么Allemanda(阿勒曼德),Corrente(库朗特),Gigue(吉格)等古典舞曲样式,肖邦的马祖卡、圆舞曲、波兰舞曲,更是显得轮廓清晰、性格鲜明,甚至还有《降A大调英雄波兰舞曲》那样的石破天惊。总之,肖邦的乐曲既继承又创新,既理智又浪漫,从中世纪走向了现代,从宗教走向了人性,从矜持走向了奔放,被誉为“鲜花丛中的大炮”。肖邦的音乐打开的又是一扇通向“象牙之塔”的门,相比之下,其他大师们的作品都略嫌粗糙,连贝多芬都显得“强词夺理”,更不用提什么震耳欲聋的流行音乐了。
乐圣与贵族(1)
网络上偶然刷到惠悦聪先生取笑贝多芬,称其为“混入贵族圈失败的典型”,原话如下:“钢琴在传统欧洲社会中,属于贵族的一个附属品,甚至说是一个奢侈品,但凡能来学的,地位都比你高,但凡能来学的,你都不敢怎么着,所以贝多芬那么多怒火呢。贝多芬他的一生的梦想,其实就是想混入贵族圈的,但他是混入贵族圈失败的典型。”什么时候贝多芬成了小丑,成了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剧中的“贵人迷”了?幸好贝多芬不懂中文,暂且毛遂自荐,来翻翻贝多芬与贵族的恩怨史吧!
在古典主义时代及之前,成功的音乐家必须要有教会或王公贵族做靠山,即所谓的赞助人制度。巴赫、海顿、莫扎特均有贵族雇主,但莫扎特追求的是创作自由而不是像海顿那样奉命而作。不听话的莫扎特最终被萨尔斯堡大主教解雇,怀才不遇,命运多舛。贝多芬运气则好得多,或者说时代在进步。1800年,贵族金主们担保每年给贝多芬六百荷兰币作“过渡”,直到他找到一个正式职位。但贝多芬从未获得过任何正式职位,自1792年他初到维也纳直至1827年去世,几乎一生都接受着贵族的赞助。他是维也纳新贵,也是唯一享有特权的作曲家:不用赶日期,不接受定制,想写才写,没心情就不写,是金主们付钱请他赏光在维也纳生活与创作。换句话说,贝多芬在贵族的资助下,实现了莫扎特的梦想,成了既不缺钱又不缺自主权的自由作曲家。当然拿了人家的手软,贝多芬也会屈尊去迎合听众及赞助者的兴趣,写些应景之作,但他的主要大型作品毫不妥协地坚持了艺术家的自主,最后总是他说了算,这种我行我素在其晚年弦乐四重奏作品中实施得更为彻底。
这些赞助人是一群独具慧眼的伯乐,多少预见到了贝多芬在音乐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押对了宝,因赏识贝多芬的天赋,心甘情愿地忍受着贝多芬难以相处的性格、出了名的坏脾气以及他政治上的反贵族的立场。原本献给拿破仑的《第三(英雄)交响曲》因其称帝而告吹,皇帝从来非“英雄”,贝多芬坚定的信念毋庸置疑。贝多芬的贵族金主中很多人本身就是颇有水平的音乐家,比如鲁道夫大公(奥地利皇帝小儿子),本身就是钢琴手,一直是贝多芬的学生,还在贝多芬指导下作过曲;拉祖莫夫斯基伯爵,乌克兰贵族,俄国驻维也纳大使,本人是优秀的小提琴手,还会弹乌克兰低音鲁特琴;伯爵的姻亲马克西米连也是小提琴手;亲王李希诺夫斯基,本人既是钢琴手又是作曲家。不管是为了什么,这些赞助者不但慷慨解囊,而且對贝多芬崇拜得几近五体投地。亲王李希诺夫斯基是贝多芬早期的主要金主,他甚至邀贝多芬来府同住,地位如同家人,对比萨尔斯堡大主教将莫扎特视为仆人,真是天差地别。投桃报李,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悲怆奏鸣曲》等均题献给李亲王。但贝多芬的报恩并非无底线,1806年,因被要求为亲王的客人一位法国军官演奏,贝多芬大发雷霆,操起椅子砸了过去,引起轩然大波,回家后仍怒气未消,又砸了李亲王的半身塑像。但亲王事后竟然不计前嫌,偷偷到贝多芬在维也纳的寓居门外,静听贝多芬在钢琴上即兴弹奏,可见贝多芬在亲王眼中的地位。
贝多芬同情当时的革命,又不能与贵族金主闹翻,但即便如此,关系到自己的尊严,贝多芬仍语出惊人:“你成为你是仰仗于偶然性的出身,我在于我,全凭自身的奋斗,皇亲国戚现在有,将来还会成千上万地有,但贝多芬就只有我一个。”这是艺术家面对权势与贵族的豪言壮语,流传千古。究竟贝多芬是“贵人迷”,还是贵族中的佼佼者是“贝多芬迷”,不言而喻。多亏了贝多芬,这些贵族金主也有名有姓地流芳百世了。
乐圣与贵族(2)
年代稍早的莫扎特也是一位旷世奇才,天分在贝多芬之上,却遇人不淑,运气差得多,我们对莫扎特的了解也并不准确。记得儿时读过匈牙利剧本《安魂曲》(原为《莫扎特》),毕竟已过去六七十年,印象模糊,但仍记得催人泪下的剧终:莫扎特贫病交迫,在昏暗的油灯下,死在爱妻怀中。父亲说1942年他在重庆看过曹禺、张瑞芳出演的话剧《安魂曲》,演出极为轰动。但我们所熟知的莫扎特形象却被1985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莫扎特传》彻底颠覆。影片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展示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莫扎特:永远处于长不大的青春期,不宜相处,树敌过多却又是无与伦比的音乐天才。不幸的是,莫扎特受雇于萨尔斯堡大主教,大主教视他为仆人,请客时让莫扎特同厨房下手一起用餐,还不允许他在皇帝面前演奏,以至于莫扎特无缘获取相当于他在萨尔斯堡年薪的一半的演出报酬,难怪莫扎特对他的家乡萨尔斯堡从未有过好话。后来的萨尔斯堡大主教不得人心地实施节制政策,提倡简朴,限制教堂音乐的长度,对擅长歌剧的莫扎特来说很不是滋味,莫扎特自由散漫的性格更是与大主教的道德束缚格格不入。莫扎特的姐姐这样说自己的弟弟:“这位在早年就充分发展成最高水平的艺术家,在其他所有方面都仍是个孩子,直到生命的尽头,他都没有学会成人最基本的对自己的约束。”美国音乐学家梅纳德·所罗门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莫扎特的两面性:一面是不屈从于世俗行为规范的叛逆性,另一面则是作为音乐天才的神性。他引用小提琴家卡尔·霍兹于1825年所说:“除了音乐天才之外,莫扎特在其他任何方面都为零。”二十世纪历史学家俄夫冈·希德夏默说:“莫扎特对世俗理性和人际关系一无所知,他像孩子一般仅追随一时一刻的当下目标。”这些评价也解释了莫扎特对权势的不买账,崇尚波西米亚风格的生活态度和对共济会理念的认同。
后人还对莫扎特做了很多医学及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各种假设及医学论文层出不穷。从各项研究来看,莫扎特似乎是苦于“重性抑郁症”,至于是否同时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则不太确定。不过莫扎特的情绪变化起伏极大,做事冲动,疑似有“分裂型人格障碍症”(Schizotypal Personality Disorder,简称STPD),还有人认为莫扎特患有“抽动综合症”云云,均为医学术语,此处不再一一道来。当然也有人反驳道:莫扎特虽易走极端,但他奇特的行为也可能是被夸大了的,与其说是精神病症,还不如说是他的性格特征,尤其考虑到莫扎特幼儿时便被父亲带往各国作为神童示人,缺失了少幼年阶段正常教育这一环。
不论莫扎特如何不谙世事,或者说正是由于他太不懂人情世故,他的音乐更像是来自天国,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天然美。一如爱因斯坦所说:“莫扎特的音乐是如此之纯真与美丽,在我看来这反映出了宇宙的内在之美。”其名Amadeus,是“上帝之爱”之意,上帝派他人间走一遭只有三十五年,没能遇上惺惺相惜的知己,却碰上了趾高气扬的萨尔斯堡大主教之流,短短的一生因恃才傲物并不如意。1781年莫扎特在给父亲的中写道:“如果他们不再需要我,没问题……但大主教让他的管家——伯爵阿克将我摔出门外,还在我后背踢了一脚。简而言之,从今以后对我来说,萨尔斯堡不复存在。”历史记住了这一天:从此,萨尔斯堡少了位奇才,音乐史上多了个恶棍,莫扎特的音乐流传千古,大主教的教诲早已灰飞烟灭。谁才是人世间真正的贵族,时间给出了最终答案。
汉英对照
不知是因来日无多,还是见多不怪,读文章越来越没耐心,所有铺垫、引言均不客气地跳过,只看关键句,甚至只看几个字,便可大概知道有几多“干货”。新鲜食材必不可少,如何烹饪则不劳作者操心。英语报道有个好习惯,素喜“先果后因”,开门见山点出主题,正合“老朽们”的口味。他那厢无意故弄玄虚,你这边也就省去了味同嚼蜡的阅读铺垫。阅读中文尤其适合一目十行,汉字排字紧凑,惊鸿一瞥,尽收眼底,且没有附加词尾来标记一个词的词性,不用画蛇添足,能简则简,释文辨意全靠上下文语境,甚至“不言而喻”,省却了多少语法上的繁文缛节。当然也有弊端:一句话有多种解读,易引歧义,甚至无法读懂。记得有位老美律师曾兴致勃勃给我一本无标点古文书卷,好像上有钟馗插图,满怀期待地让我解释,我看了半天,感到抱歉,字似乎都识,但仍不知所云,老外的失望可想而知。古文之难不仅在于没标点,当今白话文即便引进了标点,仍与西洋文字有重大区别,即书面语字与字之间没有空格,而对英语来说,字间空格是生死存亡之必须。英语如去掉空格便成了天书。不过中文无空格也会有自己的问题:一个字既可以与前面的字组合,又可与后面的字组合,又可是单字金鸡独立,而且可能是两个字的组合,又可以是三个字或四个字的组合,选项未免太多,对错全凭经验。英文貌似随和,但每个单词前后都有间距,壁垒分明;汉字看似方块,铜墙铁壁,却是来者不拒的“百搭”。汉字则更为简练,仅红绿蓝三原色,便可混搭出“五光十色”,灵活机动,让洋文望尘莫及。但优点同时也会是缺点,中文常有“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尴尬。汉语特有的四字成语更是言简意赅、生动形象,“指鹿为马”之类的成语甚至还谈古论今讲故事,但何尝不也同时在“隔前断后”,起到标识醒目的效果?缺了四字成语还真不是地道的中文。回看自己,寫东西不但喜欢搜肠刮肚找成语,还每每用很多引号,大概是受英语的影响,既是强调,也是下意识地在“阻断”吧!颇为有趣的是:英语字与字分离,行文造句反而更强调“组合”“联系”,句中有句,一句套一句,一表三千里。英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小说《贵妇画像》《华盛顿广场》的作者,以长句著称,近二十行的段落仅为一句。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于1983年在其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中写出了带有一千二百八十八个字的句子,荣获“文学类最长句子”奖。汉字比肩接踵,抱作一团,不免会过分拥挤,透不过气来,喜好短句,来个“断舍离”,也没错。当年侯宝林有个逗趣的相声,室友间起夜对话:“谁?”“俺!”“咋?”“尿!”简短到极致。当然,也必须提一下以短句著称的海明威,简洁克制。总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