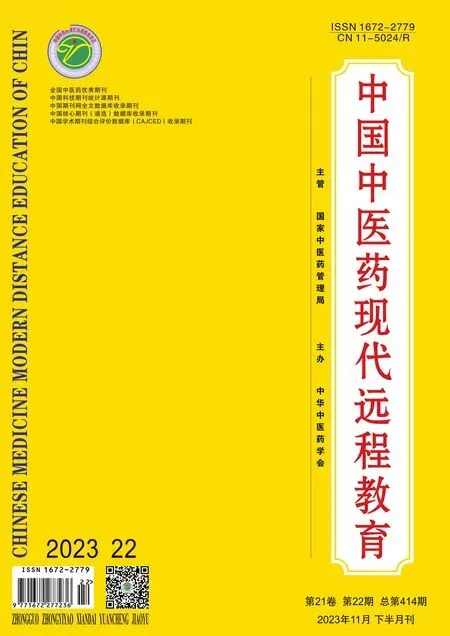刘铁军教授运脾托毒法辨治气虚型功能性便秘经验 *
苏博扬 熊 壮 王 松 黄旭鹏 王俊惟 刘铁军※
(1.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2.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脾胃病科,吉林 长春 130021)
功能性便秘(Functional constipation,FC)是临床上常见的消化系统功能性胃肠道疾病,不属于器质性病变,表现为大便量少、硬、排出困难,且伴有腹胀、腹部不适、食欲不振等。便秘对生命威胁较小,但对生活质量以及精神状态影响明显,且精神因素亦是便秘发生的常见原因,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对便秘患者造成心理、生理的双重负担。
气虚型便秘的发生与年龄呈正相关,老年人发生气虚型便秘的几率更高[1,2]。刘铁军教授认为,气虚秘的根本原因在于后天之本的脾胃之气不足。一方面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老年人脏腑功能减弱,气衰血少,大肠失于濡养,传导无力;另一方面,随着年龄增加,脾胃腐熟水谷、运化精微的能力下降,使体内停滞的糟粕之物增多,且大肠主津,吸收水分后,粪便干结而难以排出。相比其他粪邪停滞于内的“实秘”,虚型便秘病机则是以脏腑功能下降、脾胃之气亏虚为主,具有持续时间较长、易反复发作等特点。此外,长期便秘会增加结直肠息肉发生率[3],结直肠息肉是癌前病变的表现,因此对便秘患者的关注、检查及治疗是十分有必要的。刘铁军教授临床使用黄芪类方治疗气虚型FC 效果显著,现将其对本病的认识及治疗经验总结如下。
1 病因病机
1.1 多脏致病 脾胃为本《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饮食水谷经胃腐熟,精微物质通过脾布散,最后再由大肠传化为糟粕之物,排出体外,称为“变化”[4]。《素问·灵兰秘典论》对大肠的生理功能进行了简单的描述,认为大肠是传输运送的器官,是机体排泄粪便的重要通道。大肠传导功能失司,是便秘的主要病机,与肺、肝、脾、肾等多个器官有密切联系。
“肺与大肠相表里”,自然界清气的纳入、水谷精微之气的吸收是推动宗气运行的根本,肺不纳清气则大肠浊阴不降。《四圣心源》有言:“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郁”,肝失调达则百病由生。刘铁军教授基于“脏毒腑秽”学说中,大肠可排出体内糟粕形成的“浊毒”来保证“六腑中轴”的正常运转的理论,认为若大肠传导功能失司,无法将浊毒排出体外,毒邪将通过“肠肝循环”进一步损害肝脏[5,6];毒损肝络,使肝脏疏泄功能失常,继而肝木失于调达;木气郁阻,气行不畅,又易导致便秘情况的发生。如此往复,形成恶性循环,是“因病致郁,因郁致病”的典型体现。《医学正传·秘结论》曰:“夫肾主五液,故肾实则津液足而大便滋润,肾虚则津液竭而大便结燥”。肾主五液,肾气的充足与否影响体内津液的布散,从而对大便的性状、形态都有一定影响。此外脾胃腐熟功能受肾阳的蒸腾影响,肾阳又需要脾阳的资助才能化生,故在治疗虚寒型胃肠病时,刘铁军教授鼓励脾肾同治[7]。补土派著名医家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提到:“脾胃虚则九窍不通”“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刘铁军教授认为脾阳升则上窍荣、胃阴降则下窍通,维持脾胃之气充足,保证其通降之性是推动“六腑中轴”正常运转的基础;若脏腑功能受损,使脾清气不升,胃肠浊阴不降,则水谷运输通道不畅,上逆于口故见呕吐,停滞于胃脘则见痞满,不行于肠道是为便秘,诸多消化系统疾病都与脾胃升降功能有关。老年人肾精不足、天癸衰竭,先天之本乏源,更加依靠后天之本来维持脏腑功能的正常运转、阴阳的平衡、清浊的出入,故维持脾胃之气的正常运行,对气虚便秘的治疗至关重要。
1.2 阴阳失调 气血失和《伤寒论·辨脉法》最早从阴阳出发,将便秘分为“阴结”“阳结”。后世医家张景岳对此种分类表示认可,《景岳全书·秘结》有言:“盖阳结者,邪有余,宜攻宜泻者也;阴结者,正不足,宜补宜滋者也。知斯二者,即知秘结之纲领矣”[8],认为便秘辨阴阳足矣。刘铁军教授认为,诸病皆有阴阳之道,寒热虚实易辨、阴阳错杂难察,调节二者间的平衡可有效改善便秘。阳气主升、主动,下焦阳气不足,传送无力,阴凝于下导致的“阴结”,当以滋补为宜;反之由于阴液不足,或下焦之火耗伤津液,以致水不行舟导致的“阳结”,则可以采用攻伐之法。气虚则阳不盛,气虚型便秘多见“阴结”,景岳之法中肯得当,当以补为要。但临床常有阴阳交互之象,故当详查慎辨。
《圣济总录》将便秘分为风、虚、冷、热4 种类型,其中提到“因病后重亡津液,或因老弱血气不足,是谓虚秘”,将气血亏虚导致的便秘归类到虚秘的范围。刘铁军教授认为气血失和是气虚型便秘的常见病因,尤其是老年患者,其脾胃功能减弱,气血生化之源不足,气衰血少,大肠失于濡养,则传导无力。总结来说,便秘并不是单纯的大肠功能障碍,是阴阳失调、脏腑气血失和而致肠道传导无力、失于濡养的一种表现,是多种病因综合表现的结果。故在治疗方面应司外揣内、审证求因、四诊合参,善用“通法”,而不拘泥于逐粪。
2 治以益气行滞 运脾托毒
针对气虚型便秘,刘铁军教授认为应善用“通法”。《医学真传》有言:“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所谓通法,并非狭义方面的通下之法,《素问·至真要大论》谓:“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不可遇寒治寒、见虚补虚,治疗疾病须溯本逐源,从根本上了解疾病的发生机制,方可投剂辄愈。刘铁军教授提倡以“三因学说”理论指导治疗便秘,即“正气”“气血”“瘀滞”[9]。《素问·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气虚型或是老年性便秘,究其原因首先是年老体衰、正气不足;其次是气血,“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的正常运行是维持机体生理活动的基础。气虚则大肠传导无力,血虚则肠道失于濡养,导致大便艰涩而积滞于内。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健不在补,而贵在运”[10],改善脾胃的功能状态是恢复正气、补益气血的根本。刘铁军教授认为“瘀滞”是“腑浊”的一种,若其久居人体,则有可能演变为“腑毒”,毒不除,则病不去,并提出从腑气不降状态论治脾胃病。但对于气虚患者,切不可急行攻伐之法,恐伤正气,使病情加重,应复健脾胃之气并行通下之品,化攻为辅,做到真正的托毒外出。“六腑以通为用”,运脾使正气得复,托毒外出则病邪自除。脾胃升降有序、气血生化有源,脾阳得升、浊气得降,既治脾胃气虚之本,又缓魄门堵塞之标,病情安有不愈之理?
3 气虚便秘 衷于黄芪
气虚型便秘是在便秘的基础上兼见神疲乏力、面色萎黄、便后汗出、舌淡苔白、脉弱等气虚证表现。针对此型便秘,刘铁军教授善用通法联合黄芪类方,并根据患者病情程度适当提升黄芪用量,斟酌使用通下之品,治疗效果颇佳。黄芪作用较为缓和,且不良反应较少,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提到黄芪“能补气,兼能升气”,《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刘铁军教授认为黄芪可补肺脾之气,升脾胃之阳,推动粪邪排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通天气以吸入清气为用,大肠通地气以出为主;肺气充足则大肠通降有源,大肠出浊使肺纳有容[11]。二者升降相合,一出一入,维持体内清气的平衡。《临证指南医案·便闭》谓:“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盖太阴之土。得阳始运……东垣大升阳气,治在脾也”。若想改善气虚便秘,首要升提脾胃之阳,使脾得运,则气行得顺,六腑通畅。此外,黄芪具有行滞通痹、托毒排脓之功。刘铁军教授认为其行能胃肠之气滞、托脏腑之浊毒,结合“脏毒腑秽学说”,黄芪可升提“腑气”,帮助“腑浊”排出。综上所述,能够升阳补气、入肺脾之经,又可通降腑气、托毒外出的黄芪自然成为刘铁军教授治疗气虚型便秘的首选药物。
除FC外,老年人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易发人群,且便秘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意外事件的发生。现代研究[12]证明,黄芪具有保护心血管系统、改善血液系统功能的作用。可谓是一药多用,未病先防,也体现刘铁军教授“先安未受邪之地”的治疗思路。
临床便秘若伴有胸闷、心慌、便后喘促等表现,常给予升陷汤;若神疲、乏力、少气懒言明显,可予补中益气汤;若口苦舌干、不思饮食,考虑升阳益胃汤;若有恶风以及感冒后便秘加重者,常在玉屏风散的基础上加味。
4 医案举隅
王某,女,57 岁,个体工作者。2020 年11 月13 日初诊。既往有高血压病病史10年,收缩压、舒张压最高达170 mm Hg(1 mm Hg≈0.133 kPa)、110 mm Hg。以“排便困难3 年,加重5 d”为主诉,就诊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门诊。患者自述5 d 未行大便,既往排便无力,便后乏力、自汗、气促,肛门有轻微坠胀感,排便不尽,平素乏力、恶风、心慌、胃胀满、烧心、口干、纳眠可,小便稍黄,大便3~4 d 一行、质稍干,服药可2~3 d 一行。平日借助通便药物维持,每日服用1次,具体药物不详。1 d前排便时发生昏厥现象,其女叙述患者昏厥时出冷汗,手足不温,10 min 后自然苏醒,近1 年内此症状发生过2 次。舌淡、苔薄白,脉弱。中医诊断:便秘(气虚型)。西医诊断:老年性FC;排便性晕厥。方用升陷汤合桂枝汤加味。处方:黄芪80 g,北柴胡15 g,升麻20 g,桔梗15 g,知母20 g,党参片15 g,桂枝30 g,白芍10 g,生姜10 g,大枣10 g,甘草片15 g,大黄2 g。上药7 剂,每日1 剂,水煎300 mL,每日2 次,早晚分服,每次150 mL。并嘱患者可停服平日通便药物,不欲便不可强便。
11月21日二诊,患者自述排便无力感明显减轻、乏力缓解、排便周期缩短,但仍有排不尽感,偶有排便困难,烧心、口干症状轻微缓解,余症、舌脉同前。于上方基础,大黄调整至3 g,加用生石膏30 g,防风15 g。继服7剂。
12 月1 日三诊,患者自述排便无力感、排不尽感明显改善,大便1~2 d 一行,肛门坠胀感消失,烧心、口干、恶风明显缓解,余症皆减轻,舌淡、苔白,脉滑。效不更方,再投上方10剂。
12 月12 日四诊,患者大喜,自述未见任何不适症状,排便状况明显改善,仅有1 次便后乏力,且在治疗期间未见昏厥、心慌等表现,特来道谢。嘱患者饮食调适,善避风寒,舒缓心情,适当锻炼。
按语:本患者为中老年女性,已过七七之年。《素问·上古天真论》曰:“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太冲脉弱,阳气不足;天癸枯竭,肾精亏耗;加之脾胃气虚、气血生化乏源,致肠道失于濡养、传导无力则排便困难。脾胃升降功能失司,糟粕停滞于内,浊阴不降、清阳不升,阴阳不相顺接,则脑海失养;加之素体亏虚,排便努张,使气机逆乱,故见晕厥。治疗过程中患者虽有粪便停滞、胃胀满等“实”象表现,究其根本仍是脾胃气虚,属本虚标实之证,不可妄自通下。刘铁军教授以益气扶正、运脾托毒为治法,选用升陷汤为底方。黄芪为君,配合党参补益脾气是改善案中气虚表现的关键;柴胡为少阳之药,配合升麻能引气上行,使清阳得升,脾胃功能恢复,则气血相合、阴阳顺接。以往中医治疗观念中,脾胃虚弱之人当慎用下、吐、泻等法,刘铁军教授在使用升陷汤的基础上予以小剂量大黄,实则是“以通为补”。从腑气不降状态论治脾胃病,大黄有推陈出新的作用,少量的应用可清除肠道毒性物质,有助于人体正气的恢复[13],且在使用大黄过程中,大黄几乎不后下,使锐药得缓、化攻为辅,改善肠道症状,帮助人体正气恢复。久病必瘀,若有排便困难、日久不愈的患者可更换为酒大黄,增加其逐瘀通经的功效。
5 小结
刘完素有言:“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随着社会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气虚型FC的发生率大大提高。社会精神压力增加、饮食不规律、贪凉饮冷、久坐缺乏锻炼等不良生活习惯易耗伤脾胃之气,使肠道蠕动无力,毒邪积滞于内,进而影响排便。诸多患者不予重视,常使用刺激性泻药以维持排便,长此以往不但会产生耐药性,而且一味泻下会耗伤人体正气,导致便秘进一步加重。刘铁军教授治疗此病经验丰富,效果显著,认为健运脾胃正气、清除胃肠之毒是治疗气虚型便秘的根本,扶正不忘祛邪,通降腑气以恢复正气,维持“六腑中轴”的正常运转,则疾患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