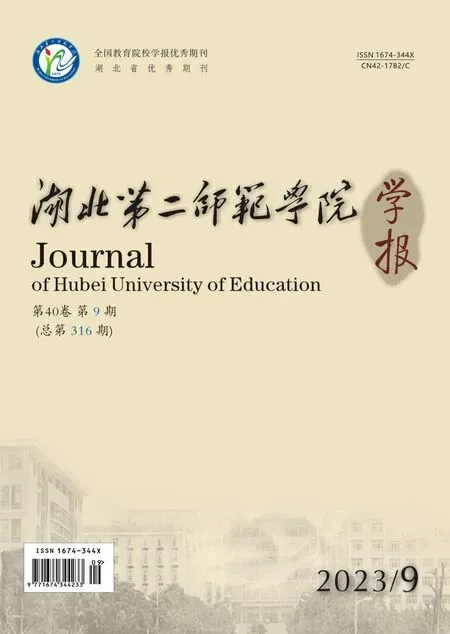接受环境对《八十天环游地球》清末民初两个译本翻译策略的影响
俞欣媛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州 350202)
引言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今译《八十天环游地球》)出版于1873年,是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讲述了英国绅士福格为了赢得和朋友的赌约,与仆人路路通在80天内环游地球一周回到伦敦的故事。这本小说在中国至今仍经历不断的重译和再版,如今已成为经典的少儿通俗读物。但是当追溯到晚清时期,这本小说初次进入中国语境时,主要的读者并不是少年儿童,而是晚清文人群体。
晚清时期是凡尔纳译介的肇始期,梁启超、鲁迅等知名文人翻译家都曾参与译介工作,译作数量众多。在晚清文人的推动下,掀起了凡尔纳小说在中国译介的第一次高潮。①其中,《八十天环游地球》是第一部被译介到中国的凡尔纳小说,重译和再版次数在“五四”以前译介的凡尔纳小说中位居前列,引人注目。[1]从晚清到民初,这本小说重译三次、再版多次②。《女界钟》作者金天羽、小说评论家寅半生都曾是这本小说的读者,足见其受中国读者欢迎程度。民国时期对凡尔纳的译介进入低谷期,译本数量大大减少,这本小说是仅有的几本在民国仍有新译本问世的凡尔纳小说之一。晚清时期也是中国科学小说的发端。该小说是第一部引进中国的科学小说,为中国文学引进了一个全新的小说类型,使国人第一次认识科学小说的面貌,在近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该小说在清末民初时期的译本情况,郭延礼对该小说的译本考证有所遗漏,忽略了时报馆译本[2];还有学者将时报馆译本误当作陈寿彭、薛绍徽译本。[3]笔者将两个译本对照后发现,时报馆译本和陈薛译本内容并不相同。因此,《八十天环游地球》在清末民初时期已知存在三种不同的译本,按出版时间顺序分别为陈寿彭、薛绍徽译本《八十日环游记》(1900 年上海经世文社首版,1906 年小说林社再版时改名为《环球旅行记》)、1907年时报馆记者译本《环球旅行记》、1914年叔子译本《八十日》。
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八十日环游记》译本,已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研究集中于女性形象构建、翻译规范、翻译策略、翻译改写等,但对《八十日》译本缺少关注,对两个译本的明显差异及原因更是鲜有关注。笔者发现,晚清的《八十日环游记》和民初的《八十日》在翻译策略上有着明显差异,呈现出对原作的不同程度的“创造性叛逆”。基于此,本研究选取这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主要从接受环境的角度分析导致翻译策略差异的原因。希望通过本次个案研究,能够进一步加深对清末民初小说翻译历史语境的了解。
一、晚清的《八十日环游记》:晚清文人的西学启蒙读物
陈寿彭、薛绍徽夫妇合译的《八十日环游记》1900年出版,原著者署名法国房朱力士(今译儒勒·凡尔纳),译者署名逸儒口译,秀玉笔述。据郭延礼考证,该译本为桃尔(M.Towel)和邓浮士(N.D.Anvers)的英译本Around the World in80Days转译[4],出版时间早于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是较早引入中国的西方小说。译者陈寿彭的译著主要是一些地理、历史、农学类的西学书籍,此书是他与妻子合译的仅有的两本小说之一,另一本为英国言情小说《双线记》。当时的译者翻译出版小说多署笔名或干脆不署名,有论者认为:“在当时译者看来,翻译外国小说主要是为了启迪民智、输入文明,……并不是为流传后世,……所以在他们看来,原作者和译者的署名与否则是无所谓的事情。”[5]但陈氏夫妇却坚持署真名,原著者和转译者的名字也悉数标明,在晚清独树一帜,可见其严谨的翻译态度。
这本小说的翻译策略即便放在整个晚清出版的翻译小说中来看,也是极具特色的。
首先,笔者对比了该译本与英文转译本后发现,该译本虽然是传统章回体,用浅近文言译成,人名的翻译有中国化痕迹,但和晚清的大部分翻译小说相比,相当忠实于原文,除每回添加的七字回目和一小部分受限于传统道德礼法的改写以外③,少有删节和随意的增添。原文中与情节关联较小的西学知识也最大程度地得到了保留,在“五四”以前“豪杰译”盛行的环境下实属难得。郭延礼曾评价道:“这部小说的口译者陈寿彭十分忠于原著,笔述者薛绍徽态度也十分严谨。我曾与197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沙地的另一中文译本对照过,除文字更加精练外,几乎无懈可击。”[2]这与1914 年的叔子译本大幅删减的翻译策略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处以小说第三章开头一段福格用餐的描写为例,陈薛译本将菜肴忠实译出,向读者展示了英国上层阶级的饮食文化,但叔子译本没有译出:
陈薛译本:福格至素坐之桌坐定,桌上铺设早备,其膳则一小旁碟,一盘炙鱼,和以酸橙酱;一盘红烧片牛肉,拌以蘑菰;一盘葵菜,并金樱子酸味。又复饱啖牛乳饼,润以数杯名茶,计食十三分钟乃毕。即起步,向大厅。[6]
叔子译本:肴馔一一上,不饮酒,以佳茗代之。十二时四十七分,食事毕,入休憩室。[7]
其次,英文转译本并没有注释,但陈寿彭在中译本当中添加了大量详细的注释,囊括丰富的西学知识,其详细程度在同时期的其他凡尔纳小说译作中也极为少见。遇到外国新名词时,译者一般采用直译策略,用音译和加注的方式处理。加注的范围甚广,包括地理新名词,如大洲、大洋、国家、城市、山川湖海、铁路、港口等,读者边读边可想象其方位和范围,产生对世界地理位置的初步概念,因旅行路线主要在英国殖民地境内,读者对英国的全球殖民地范围也能有初步感知;注释还包括科学名词、外国货币、公元纪年等,译者针对后两者标明了如何换算,便于晚清读者理解。除此之外,旅行沿途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宗教也有详细注释。陈寿彭在序言中提到“间有意义难明者,并系以注,至注无可注,姑付缺如”[6],足以看出译者认真严谨的翻译态度。现摘录几例书中注释,以见其注释之详尽、知识之丰富(括号内为译者原注):
1.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壬申),有非利士(名)福格(姓)者……
2.福格既知天下事,当知有两物相擦之事(此系电学语,犹言阴阳交感也)……
3.由苏尔士迳至亚丁(本亚剌伯海埠而属于英者)……
4.因印度之防范较少而较难于亚得连剔(乃英海西畔之大海,分隔欧非与南北墨洲。或译为大西洋是也)也。
5.……我却不费半库郎(英国银钱名,值五先令,犹言不费一文钱也)。
6.……取一钟毋亦士忌(乃大麦小麦或黍稷所制,产英之北方者良,美国亦有之)酒,或亚尔(乃一酒饼,安于杯中,以水冲之即溶化,味甘色光洁。或译为啤酒者,误也)酒以饮之。
7.宁测尼伯潭(大恒星名,距日28 万5 千迷当,164 年半始绕一周。相传其神为土星之子,专司乎海洋者)……
8.福格急握其手,阿黛不忘佛兰诗士之惠,以脸与温者数次(西国男女亲爱则亲嘴为礼,次则以脸偎脸,欲亲未亲,殆即亲嘴之渐)。④
译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来译介这本西方科学冒险小说,传播严肃的西学知识。和英文转译本相比,由于大量注释的添加,小说的知识性大大增强,科学性和知识性消解了一部分娱乐性,使得该小说在晚清产生了西学启蒙的效果。
但陈寿彭对小说翻译的严谨态度并不是一以贯之,笔者曾将他翻译的另一本小说《双线记》与原作A Double Thread对比过,发现译文远远偏离了忠实标准,随处可见错译、漏译、语句不通顺之处,任意删改,也没有添加任何注释,并没有显示出西学启蒙的功用,与《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策略相差极大。毫无疑问,陈寿彭对待《八十日环游记》这本小说的态度是特别的,他曾在译序中称赞其“非若寻常小说仅作诲盗诲淫语也。”[6]
如何解释《八十日环游记》译入晚清语境后被赋予的强烈的西学启蒙色彩?谢天振曾在《译介学》中论及接受环境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时说到,这是一种“译者为适应接受环境而作背离原作的变动。……在这种叛逆中,媒介者也即译者所作的叛逆是被动的,更多地出于客观环境的制约。”[8]因此,笔者将把译本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分析接受环境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因素。
《八十日环游记》出版于1900年。1900年以前,大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的西学知识依旧匮乏。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潮中就有西方地理学著作传入,但影响范围有限,局限于徐光启、李之藻等少数士大夫以及教会学校学生,未得到大多数士大夫的回应。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最早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编撰了《四国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书籍,但传播范围不广。1873年出生的梁启超,在光绪十六年(1890)18岁经过上海时,购买《瀛寰志略》进行阅读,才第一次知道五大洲各国的存在。[9]西学书籍专业性较强,对于大部分缺乏西学基础的传统知识分子来说,阅读门槛较高也略显枯燥乏味,但此时西学入门书籍和教科书十分匮乏。1904年清政府颁布施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鼓励民间机构自编教科书,在官方推动下教科书事业才有了较快的发展。
在民智未开、西学书籍匮乏的时期,陈最初翻译此书意在将其作为妻子的西学入门书籍。薛绍徽不通西学,在跟随陈寿彭游历上海见识了汽轮、电灯等现代科技后,遂受启发,欲学习西学。陈寿彭在译序中提到薛氏“及见汽轮电灯,又骇然欲穷其奥,觅译本读之……乃从余求四裔史志”[6]。陈认为这本小说浅显易懂,阅读门槛低,适合作为西学入门书籍,便为妻子口译此书:“余以为欲读西书,须从浅近入手,又须取足以感发者,庶易记忆,遂为述《八十日环游记》一书。”[6]鲁迅后来在《<月界旅行>辨言》中也阐述过科学小说易传播知识的优势:“经以科学,纬以人情。……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10]
而薛绍徽从固守传统儒学到学习西学新知的心态转变也是其他晚清开明的知识分子的写照,他们缺乏西学基础,但又渴求学习西学新知,《八十日环游记》的译介出版恰好为晚清文人群体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这本小说涉及的世界地理名目繁多,在冒险情节中穿插丰富的西学知识,“中括全球各海埠名目,而印度美利坚两铁路尤精详。举凡山川风土、胜迹教门,莫不言之历历,且隐合天算及驾驶法程等。著者自标,此书罗有专门学问字二万。……他国亦有译之者,愈传愈广,殆因其中实学足以涵盖一切欤。”[6]正因为这本小说的科学性,向来轻视传统小说的陈寿彭对它刮目相看。
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作为西学知识传播载体的功能进一步得到论述,甚至有人提议将小说列为学校的教科书。有人认为美、英、法、日、德等各国列强的学校对待小说“无不珍璧视之,甚而奉为教科书之圭臬”[11]“迩来风气渐变,皆知外国得小说之功效,且编以为教科书”[12]“观各国诸名小说……甚至学校中以小说为教科书,故其民智发达,如水银泻地”。[13]他们引用外国学校的例子论证小说具有和教科书类似的知识普及功能和教育功能,进而呼吁中国的“学校教育当以小说为钥智之利导”,“编其有密切关系于人心世道者,列为教科”[11],借小说之力实现“社会知识之进步。”[12]这些晚清小说理论家强调小说的启蒙功能,将小说与教科书并列,构想出“小说救国”的美好图景。
正是因为秉持传播西学知识的目的,陈寿彭在翻译时添加大量注释介绍西学知识,以至“注无可注,姑付缺如”。[6]值得一提的是,1900年陈寿彭在宁波储才学堂主讲西学,期间还曾翻译在美、日学校中广为流行,甚至被政府列为中学教科书的世界通史《万国史略》作为学堂教科书,由他口译,学生抄写。[14]而《八十日环游记》在同一时期译出,有可能被他用作新式学堂学生的补充读物。
不过,自陈寿彭译出《八十日环游记》之后,“晚清的其他凡尔纳译本多是采用“译述”方式,其忠实原文的程度值得怀疑”。[2]为何处于同一接受环境中,梁启超、鲁迅等人译介凡尔纳小说时却没有采用与陈寿彭相同的翻译策略呢?因此,除接受环境外,媒介者即译者本身的知识背景也需要纳入考量。
其一,晚清的其他凡尔纳小说译者大多为留日背景,如梁启超、鲁迅,译本多数从日译本转译,而日译本又转译自英译本,经过了三重转译,小说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十五小豪杰》为例,英译本相对于法语原著来说删节颇多;日译本相对于英译本来说情节不变但有缩写;而汉译本对日译本的变化则在于添加了许多内容。[15]但陈寿彭曾公派留学英国三年,精通英语,英语翻译水平较高,译本直接据英译本译出,更忠实于法文原著。
其二,陈寿彭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在英国专攻海军法,具备西学专业背景,又随兄长陈季同在欧洲各国游历,熟悉西国的风土人情。但晚清的其他凡尔纳小说译者大多缺乏如此的专业背景和知识储备。仍以《十五小豪杰》为例,原著中关于地理科学、航海技术以及动植物的知识,在日译本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而梁译本则删减大半,所剩不多。[15]其删节原因固然有强调冒险精神、宣传政治思想的成分,西学知识不足、力不能及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三,陈寿彭本人对翻译工作的严谨态度也很重要,他具备了职业译者必需的素质,译书于他不仅为糊口,也是事业。[16]
从读者接受效果来看,译本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译本的笔述者兼读者薛绍徽在译序中赞赏该书以惊心动魄的情节传递西学知识,“以惊心骇目之谈,通格物致知之理”。[6]该译本在晚清受到了读者欢迎,首次出版六年之后再次由小说林社出版,《女界钟》作者金天羽、小说评论家寅半生都曾是该译本的读者。该译本也确实在读者群体中发挥了世界地理启蒙的作用。金天羽曾为该小说作七言诗《读<八十日环游记>》,[17]其中一句“三大名洋四大洲”表明金天羽对世界地理已有了基本认知,已走出了“天下观念”,建立了“世界意识”。
进入20世纪后,新式教育和出版印刷业发展迅速,西学知识传播渠道增多,小说被赋予的强烈启蒙色彩开始减弱。报纸杂志成为小说发表的新渠道,小说的娱乐消遣功能逐渐得到强调。《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新译本《环球旅行记》于1906年开始在《时报》上连载、1907年由时报馆出版单行本。该译本显示出了教化功能减弱、情节趣味性增强的倾向,注释减少,对原著中与情节关联较小的西学知识多有删减。这一变化从时报馆先前公布的选材宗旨可见一斑。1904年《时报·发刊例》说明了该报纸“以助兴味而资多闻,惟小说非有益于社会者不录”的收稿宗旨,虽然仍强调小说的启蒙功能,但娱乐消遣功能“助兴味”位列“资多闻”之前,似乎更为重要。《时报》编者陈景韩在1905年撰写的《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提倡刊载“有味与有益兼具”的小说作品,惟有二者兼具,才能“开通风气”,后成为该报刊登小说的指导思想。[18]国难当头,小说“开启民智”的功利性仍需标榜,但时报馆敏锐地捕捉到了读者口味和需求的变化。在办报实践中,“有味”成为“有益”之外评判小说的重要标准。新译本《环球旅行记》的推出恰好迎合了市场需求,做到了“有味与有益兼具”。
进入民国后,译者的翻译策略进一步发生变化,译本的娱乐消遣功能超越启蒙教化功能占据上风。
二、民国的《八十日》:茶余饭后极良好的消遣品
民国新译本《八十日》在1914年分别作为“新译”系列之一和《说部丛书》四集系列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1915年随《说部丛书》再版发行。随《说部丛书》出版时封面题“冒险小说”,共二十六章。译本署叔子译述,目前学界未考证出叔子为何人。该译本所依据的底本尚不清楚,笔者推测应是据日译本转译,译文中的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分别用“水曜”“木曜”“金曜”“土曜”表示,上午翻译为“午前”,下午及晚上翻译为“午后”,这些词明显直译自日文。
叔子译本为节译本,对原作内容删节幅度较大。陈薛译本和时报馆译本都保留了原作的37章,但叔子译本经过删节和压缩之后只剩26章。笔者将叔子译本与陈薛译本对照后发现,叔子译本保留了惊心动魄的冒险情节,但原作中的地理知识、风土人情以及环境描写、人物外貌心理描写等内容被大量删减,且没有添加注释。目前并不清楚叔子所据底本是否为节译本,但是署名“叔子译述”仍透露出译者并没有忠实于原文。译者为何采用译述的翻译策略?凡尔纳的这本小说在晚清已有两个译本且多次再版,也曾在沪上知名报纸《时报》上连载,受到晚清读者欢迎。商务印书馆为何还要在1914年推出新译本?为何将书中的科学知识几乎删减殆尽,并重新定位为“冒险小说”?
要解答这些问题,还需要从接受环境出发,在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
科学小说译介在进入民国之后经历了退潮。据统计,民国以前凡尔纳小说有14种译本,民国之后“五四”以前仅有4种,“五四”之后便只有译自《两年假期》的3种译本了。[1]除凡尔纳以外,晚清译介较多的科学小说作家还有日本的押川春浪,他的科学小说译介主要集中在20世纪初三、五年内,民国之后便无新译本。实际上,近代翻译的世界各国约80余种科学小说中,大部分都是在1908年前译介出版的。[2]
科学小说译介退潮背后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变。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革命话语日益膨胀,改良话语渐渐式微,各种新的社会思潮在此时涌现,主张用科学小说开通民智、改良社会的改良思想渐渐落于下风,许多原先支持改良的知识分子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例如鲁迅,对译介科学小说逐渐失去兴趣。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随着民营印刷业和现代教育的发展,西学书籍得以大规模传播,教科书编纂和出版体系日趋成熟和完善,官办或民办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西学知识有了更多的传播途径,因此科学小说承载的启蒙意义被削弱,小说渐渐回归它原本的娱乐性、文学性。
更重要的是,民国时期的小说读者群体发生了变化,读者的阅读需求随之转变。晚清的新小说读者群体主要还是由传统知识分子构成,如徐念慈所说是一群“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但进入民国之后,大都市逐渐形成,市民阶层兴起,成为小说消费的主力军,与肩负家国使命的晚清文人不同,他们对小说的需求主要是“消闲”。为了适应读者需求,小说市场上也涌现出大批用于“消闲”的通俗小说,小说的娱乐功能俨然跃居启蒙功能、社会功能之上,“鸳鸯蝴蝶派”也是在这时兴起的。1915年,就在《八十日》首版的第二年,梁启超发表文章《告小说家》,批评了新小说在民国时期的堕落:“而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19]
在激烈的出版业竞争中,商务印书馆明确地将追求盈利作为出版原则之一,读者“消闲”的阅读需求直接反映在了商务印书馆的小说出版策略和广告宣传策略上。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类型看,数量最多的是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和冒险小说,因为这类小说往往情节曲折离奇,娱乐性强,适合消遣,在当时最为热卖,利润最为丰厚。商务印书馆的售书广告常强调小说的情节中心主义,频繁出现“情节变幻离奇,致足骇心娱目”“深情婉致、哀艳动人”等宣传语,后期更是把小说定位为“遣此闲暇时光”的消遣品。[20]例如,1911 年2月9日,上海《申报》刊载广告称小说为“新年消遣之乐事”“本馆编译小说无虑数百种,当兹新年无事之时,围炉披读,最佳之消遣法也”。[21]
《八十日》被编入《说部丛书》出版,也必然符合商务印书馆对《说部丛书》的定位。1907年7月,《扫迷帚》单行本上的《说部丛书》广告称:“本馆所印说部丛书皆系新译、新著之作,饶有兴味”,突出的是小说的“兴味”,即娱乐消遣功能。[21]此外,《八十日》的出版页刊登有一则《小说月报》短篇小说合集的宣传广告,广告强调这本合集为“最有兴趣之小说”“茶余饭后极良好之消遣品也”[7],可知商务印书馆对《八十日》的定位也大体如此。
总之,《八十日》的译者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为了迎合读者搜奇猎艳的阅读趣味,将书中枯燥的西学知识删去、只保留惊险曲折的冒险情节,并将小说打上“冒险小说”的标签,最终突出娱乐功能、弱化教化色彩,这样做能够更好地吸引读者、提高译本的销量,符合商务印书馆把小说视为消遣品的定位。
三、结语
《八十天环游地球》在清末民初的译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个案,证明了翻译活动其实是译入语文化根据自身需求有目的的选择的结果,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受到译入语接受环境中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当接受环境发生变化,翻译策略也随之变化,使同一本外国小说的译介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直译、忠实的翻译标准去对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进行价值评判,而应该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下,去揭示“创造性叛逆”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