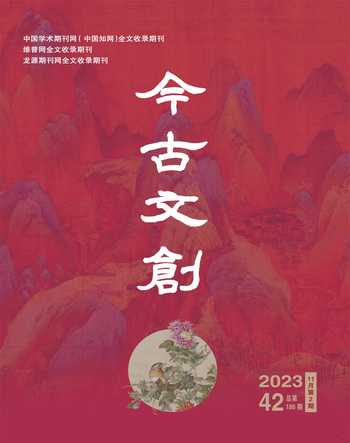《伤逝》中启蒙者的看与被看
揭维舒
【摘要】《伤逝》作为鲁迅唯一的爱情题材小说,其主题思想隐晦而丰富,至今尚无定论。结合鲁迅作品的重要核心“启蒙”来看,在这篇小说中,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身份很明朗。本文将以“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为基础,借用后殖民主义的思路对双方行为和思想惯性进行分析讨论。
【关键词】《伤逝》;启蒙;鲁迅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2-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2.001
《伤逝》是鲁迅唯一一篇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由于鲁迅思想和经历的复杂,以及作品本身的隐晦曲折,对这篇小说主题思想的讨论也仍在继续,但都绕不开对小说两个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关系的探讨。
涓生与子君的关系,一般地来说被认为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无论这种“启蒙”实际上是出于何种目的、又达到了何种程度,大家都可以很显然地在文本中看到二者存在着这样一层很显然的关系;而“启蒙”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乃至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中,都是一个尤为重要的话题。在目前对《伤逝》的研究中,大多对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婚姻观、人物性格心理以及女性的生存条件等方面问题做了挖掘。本文将借鉴后殖民主义的思路对《伤逝》进行讨论。
19世纪,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理论,认为人的意识形态是被统治阶级通过学校、国家机器等被构建的。大致同时期的理论家葛兰西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认为,在某个阶段,“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为了确保他们社会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利用霸权作为手段,劝诱被支配阶级接受它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 ①马广利在《文化霸权:后殖民批评策略研究》中认为资产阶级就“成功地运用意识形态的优势来获取大多数人的‘同意’,获得了统治‘合法性’”。基于这些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萨义德构建了自己的东方学。在西方殖民者推出东方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国家用自己的文化框架去衡量和定义东方文化,东方文化迫于西方的政治军事强权,文化上的缺乏话语权和不自信,导致它们认同了西方对自己的定义和评判,从而真正成为文化弱者。“五四”时期,启蒙不仅是对西方的理性、科学、民主的呼唤和对中国的迷信、封建的祛魅,还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定义和评判,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输出,是一种二元的权力结构。在《伤逝》中,虽然没有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直接较量,但是可以借助后殖民主义的视角看到,代表着西方文化的启蒙者掌握了话语权和对被启蒙者的评判权,用启蒙的方式对代表着传统中国文化的被启蒙者进行了压迫。
一、叙事与反叙事——涓生的“看”与“被看”
“在西方人或宗主国的‘看’之下,历史成为‘被看’的叙述景观,并在虚构和变形中构成‘历史的虚假性’。” ②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第一世界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凝视实际上受到自身文化的限制,因此它们看到的结果是失真的景象,它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叙述也是失实的叙述。在这里,从“被看”到“叙述”之间,存在着双重偏差:“被看”与“看”之间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必然存在理解上的差异,从而被动地产生了偏差;而“看”与“叙述”之间又因为叙述者利益的取舍而主动地产生了偏差。
“看”与“被看”是鲁迅小说一个极富特色的叙事结构。在《孔乙己》中,孔乙己被众人所围观、取笑,众人又为小伙计所观看;《祝福》中,祥林嫂被鲁镇的居民所看,而“我”又看着这一切;《示众》中,犯人在被人群围观,围观的人群又被彼此所观看……而在这一切“看”的背后,还藏着叙述者的冷眼,这隐于幕后的悲悯的“看”在嘲讽着前景中热闹的“看”,这“看”与“被看”间形成了反讽的张力。在鲁迅的“看”与“被看”结构下,其实是深层叙述声音与人物声音的矛盾,读者在这样的矛盾中可以拼凑出一个与表层人物叙述不同的故事。
涓生所讲述的故事是一个他所看到、所经历的故事,这个故事由于他自身的限制产生了第一重的偏差,就是他所看到的与真相之间的偏差;又因为他对真相的主动掩饰,在叙述时产生了第二重偏差,就是他所看到的与他所叙述的故事之间的偏差。双重偏差导致了叙述中的矛盾和模糊,也解构了涓生的叙述。涓生的叙述显然只是他的一面之词,但是在这个故事中,他的叙述显示了一重权威的支持,这重权威来自他的启蒙者身份。在同居前,涓生对子君谈的是新思想,新文化,而子君用“稚气的好奇的”眼光仰视着他,温顺地听着他的谈话。当涓生将雪莱的半身像指给她看,她的不好意思被涓生评价为“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当涓生说起“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的时候,子君“领会地点点头”,表明了她对这种观点的认同,也是再次对涓生的权威的认可。涓生以启蒙者的身份面对子君,而子君也乐意将文化的优先权交给涓生。由于背靠着强势的西方文化,掌握了话语权,就有了价值评判标准的制定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涓生就有了对子君的评价权,子君的思想、品质和行为需要涓生的认可才有意义。在这种前提下,涓生对子君的“叙述”、对子君的“看”与子君的真实之间的偏差就失去了意义,涓生的“叙述”就成了真实。要打破涓生对子君的“霸权”,就需要借助叙述者的声音,对涓生的叙事进行解构,来重建整个故事的真相。
在《伤逝》中,涓生与子君也构成了一个“看”与“被看”的结构;但涓生看到的子君,只是他能看到的部分。全文作为涓生的回忆录,是由涓生来叙述他与子君的故事,当然也是以他的视角来看自己和子君。在同居之前,他眼中的子君有“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她来时有皮鞋底的“清响”,“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她的到来“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子君的美丽和浪漫气质使涓生心动,打破了他寂寞的生活。在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的时候,“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她沉静而温柔,却可以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震聋发聩的声音,使涓生从她身上看到中国女性辉煌的未来。然而在同居之后,她“终日汗流满面”,两手粗糙起来;在涓生被辞退后,“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不再幽静,不再体贴;吃了油鸡、丢了阿随后,更是“加上冰冷的分子了”。在涓生对子君的“看”中,子君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使涓生的心渐渐远离她。但是,涓生对子君的“看”与子君本身之间还是有距离的,因为受了涓生视角本身的限制,无法真正达到真相。子君从前的美丽是“为悦己者容”,从前的安靜是因为爱涓生而乐意听他侃侃而谈,从前勇敢与家庭决裂、无视旁人的眼光是因为爱涓生而不惜与世俗为敌;而同居之后的子君其实仍然是为了爱情而甘愿守在贫穷的小家庭里,但此时她表达爱情的方式不再有轰轰烈烈的与世俗对抗,只剩下一日三餐饮食起居的琐事。他只能看到子君从美丽变得粗糙,从浪漫变得庸俗,从体贴变得任性,从勇敢变得懦弱,但看不到子君变化背后地对他不变的爱与甘心的付出和牺牲。
《伤逝》是涓生对二人爱情悲剧故事的叙述;涓生所叙述的故事,只是他想叙述的部分。“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涓生的叙述中,把二人的分手解释为爱情的消逝;因此他对子君说“我已经不爱你了”,是因为“人是不该虚伪的”。但是他对子君说出他的意见和主张:“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了是免得一同灭亡”的时候,却表明他并不是为了爱情的消亡而分手,而是为了利益而分手。他想“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这里的“新的生路”是他的,而不是子君的。“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涓生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分离意味着他的新的生路和子君的死路,但是他却在对子君说出“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的时候,他怎么能是不虚伪的呢?
当建立了新的叙事,由涓生自己所叙述的故事就不再是权威,而他的“启蒙”迷信也就被打破了。
二、伪装与揭露——涓生的说辞与意图
涓生和子君在同居前一同对抗外界环境,此时的二人是同一阵线的战友;而一旦二人克服压力走到一起,二人就由同盟关系变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在这个启蒙与被启蒙的二元结构中,子君成了涓生的“他者”。在面对利益冲突时,主体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牺牲他者的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名誉而掩盖对他者的压迫。
搬到吉兆胡同后,子君养了油鸡和狗。涓生在叙述中指出子君并不爱花,没有养花的浪漫情怀和雅致的生活态度,也不体谅和尊重自己爱花的心;爱动物,也不是出于爱心与善良,是为了“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在涓生自己的叙述中,他此时并未因此产生怨言,反而理解、包容子君,甚至为她而有了换个好居所的想法。然而从前文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和后文的“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来看,涓生自己对这个居所本就是不满意的;但自己的不满意,只能“怨我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而如果是因子君而想要换住所,似乎就有了爱的大义在其中。而涓生对油鸡和狗的真实态度,也可从涓生多次对油鸡的抱怨、油鸡被吃掉的结局和狗被推在坑里的事中略见一二。在二人的生活继续艰难下去时,涓生想:“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但在子君离开甚至去世之后,涓生“一切请托和书信,都是一无反响”;不得已访问久不问候的世交時,“一登门便很遭门房的白眼。好容易才想见,也还相识,但是很冷落”,可见涓生之前叙述中的“生路宽广”其实并不怎样宽广;而他受生活压迫的苦痛,也不只是为子君的缘故,因为即使在他与子君同居之前,也不过居住在“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里。涓生在叙述中的不诚实显然是要遮掩什么。他时时将自己处境的艰难归咎于他者,并将这种观点向对方输出,“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也想不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不断地对对方造成伤害,并且进行伪装。涓生在生活陷入窘境后,就一直将子君视为自己的负担,并且认为子君是让自己陷入困境的源头。他这样推卸责任并不断将这种观点传递给子君,其实是对子君的精神暴力。
他爱子君是因为可以“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涓生对子君的描述里形象是很苍白的,如他自己所说,他们之间有许多隔膜。然而涓生还是期待着子君的到来;当子君来了,“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在子君这里,他由物质性的存在提升到精神层面的存在,他由一个贫穷卑微的小职员成了伟大智慧的启蒙者,他的社会性的失败都在子君这里得到翻转,他在子君这里得到了完全的肯定和胜利。因此,她的胞叔当面的责骂、鲇鱼须的老东西的窥视、涂加厚雪花膏的小东西的打探,都成为涓生胜利的标志。子君的到来,是将他从寂静的失败的人生中解救出来,让他可以享受一次胜利的骄傲。因此,涓生可以骄傲地说“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他享受被子君所爱,却对自己向子君示爱感到可笑甚至于可鄙。他对子君的爱是很可怀疑的,他享受的是成为一个启蒙者,成为一个在思想上占领高地的支配者,他热爱的是那份权力和被仰望的感觉。
三、失语与存在——子君的沉默与问题的症结
在整个故事中,子君是处于失语的状态。因为这是涓生的手记,子君的态度和处境是被忽略的,她只能被涓生所叙述。而涓生的叙述对子君又形成了一种压迫。
涓生一再地强调子君后期的改变,从踏着皮鞋带着槐树的新叶子而来的细瘦苍白的少女成为短发粘额的粗糙女人,是指责子君不知“爱情必须要时时更新”;从敢于抗争不畏议论到“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是指责子君并没有真正地觉醒,“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涓生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表面看来是子君不懂得独立,过于依附涓生,二人被经济压力所击垮,但子君的不独立是离不开她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如果因为子君的不独立、不觉醒来质疑和责难她,就是用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来要求第三世界女性,这不仅不会对她们带来帮助,只会增加她们的负担。“五四”的女性好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局面,但《浮出历史地表》一书指出,“五四”新女性被赋予的唯一一次如同传统男性角色那样行动的权力就是走出父家,但在走出父亲的家之后,女性唯一的去处就是丈夫的家,“五四”时期的新女性最大的可能性只是在两扇门之间没有出路的间隙里挣扎。一旦女性到达丈夫的家,她的“新”就被否定了;子君的勇敢和觉醒在她退居于与涓生的小家之后,就被涓生否定了。在这里,子君不仅受到环境的压迫,还受到来自涓生的压迫。
当涓生被辞退、对未来感到恐慌的时候,试图从子君那里得到肯定与信任,但是子君只能回给他一个怯懦的眼光;涓生说:“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当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他只能一再地否定子君,以些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当涓生吃掉油鸡、丢掉阿随,子君大概已经认定他是一个忍心的人,他“拣了一个机会,将这些道理暗示她”,她却没有懂或者是并不相信,涓生便从此逃进了图书馆。当他与子君的利益产生冲突,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并不尊重子君的需求;当子君拒绝接受他的观点,他便通过冷战和逃避的方式来对子君进行惩罚。
四、结语
《伤逝》是启蒙者涓生对被启蒙者子君的“看”,启蒙者涓生为了保持自己精神上的优势、从对子君死亡的责任中逃脱,利用自己占据话语权的优势不断涂抹被启蒙者的形象,但在这样显然存在不真实的叙述中反而暴露出自己的自私和虚伪。后殖民主义理论提示我们,在“被看”的被启蒙者子君的沉默中,可以摆脱启蒙者的叙述阴影,抵达另一种真相。
注释:
①②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补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6页,第424页。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补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哈迎飞.论鲁迅小说中的“他者”与“自我”——以《伤逝》研究为中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6(02):108-113.
[3]谭君强.叙述者可靠与不可靠性的可逆性:以鲁迅小说《伤逝》为例[J].名作欣赏,2006,(15):26-31.
[4]谢菊.《伤逝》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01,(11):
56-61.
[5]贾振勇.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J].鲁迅研究月刊,2001,(03):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