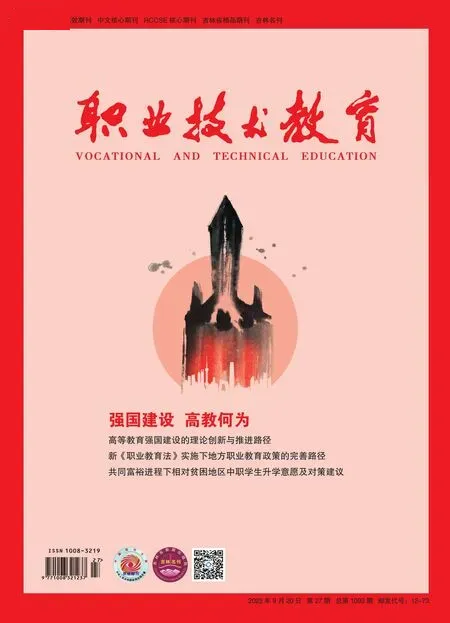邬大光:教育强国视域下的大学治理能力与高质量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邬大光指出,高等教育强国作为一个政策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末的学术讨论中,2010年正式被写入国家政策文件,本世纪中叶被预设为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一个时间节点。高等教育强国最基本的内涵是服务高质量发展,涵盖了教学质量、科研质量以及社会服务质量,涉及优化教育资源、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调整学科结构等各个层面。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一项特定的改革实践,是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跨越式发展为现实基础,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时代任务,核心是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发挥人才驱动作用,助力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规划。为此,需要重新认识大学治理,建构新的治理体系,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一、重新认识大学使命
邬大光强调,大学应该是有民族使命和时代使命的组织。纵观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从“教育救国”到“教育兴国”再到“教育强国”,话语的转变,标志着我国与世界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教育始终扮演着“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尤其是高等教育。知识经济是站在大学肩膀上的。当前,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更应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以“科技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在时代使命方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高等教育需要回应时代的呼唤,肩负时代的使命,在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引领时代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实现大学的科学治理
邬大光强调,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大学治理能力。大学管理者对大学的理解水平,决定了学校的办学水平。大学管理者对大学组织的理解决定了他会建设什么样的大学组织;大学管理者对学科的理解水平决定了学科建设的举措和思路;大学管理者对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理解水平决定了推进三位一体的举措和思路。现在,我国大学管理的基本情况包括三种:一是经验管理,在教学、科研、财务、人事、研究生院等部门的管理中都存在墨守成规的管理方式,亟须跳出经验去真正管理大学;二是制度管理,制度是形式,当一个大学制度越多、越严谨的时候,制度就会给大学带来溢出效应;三是文化管理,文化是根基,我们要反思大学的文化管理。因此,在新时代教育强国的语境下,我们要重新认识大学活动、重新认识大学职能、重新认识大学学科、重新认识大学专业、重新认识大学课程,实现大学的科学管理。
第一,基于“卡脖子”技术的治理体系:从“供给侧”到“需求侧”。大学的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发展、面向实际问题、面向需求、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从“服务社会”到“引领社会”,引领作用是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的新内涵。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高等教育在人才强国、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第二,大学三大职能分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超越学科专业式的人才。在科学研究方面,认清科学研究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服务方面,要面向社会需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有组织的人才培养、有组织的科学研究、有组织的社会服务。
第三,发挥大学的“引领”作用。从大学发展史来看,大学在社会中的引领作用曾经是全方位、全覆盖的,始终处于知识创造的顶端和前沿。但随着知识的“下嫁”和“外溢”,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现代企业迸发出的科技创新驱动力开始强于高校,其科技创新意识和能力与高校并驾齐驱,并有逐渐超过高校之势。在科技创新领域,大学面临着引领的“尴尬”。面对社会和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对大学的“挤压”,解决之方就是回归大学之本——人才培养。大学应该清楚自己的“主业”就是培养人才,自己的“优势”也在于培养人才。
第四,基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治理体系。目前我们是在为“学科”培养人才,而不是为“创新”培养人才。学科分立建制,导致知识过分“割裂”,过分强调专业的细分化,使专门人才的知识构成相对单一,缺乏从比较广阔的视角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知识基础和创新能力。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忽视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培养出的专门人才成为“单向度的人”,难以适应社会问题复杂化、知识应用综合化以及促进知识创新等新情况。学科专业式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转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交叉学科、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等人才培养模式,超越学科专业的边界。
最后,要重新认识大学治理体系,从“就教育谈教育”转向“跳出教育看教育”。知识开放的时代,大学的命运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大学的改革发展不再是象牙塔内部的“自娱自乐”,而是要立足时代发展、面向社会需要,打开大学的大门,实现社会与高等教育的联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