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你时天空放晴
文/ 斩华浓 图/松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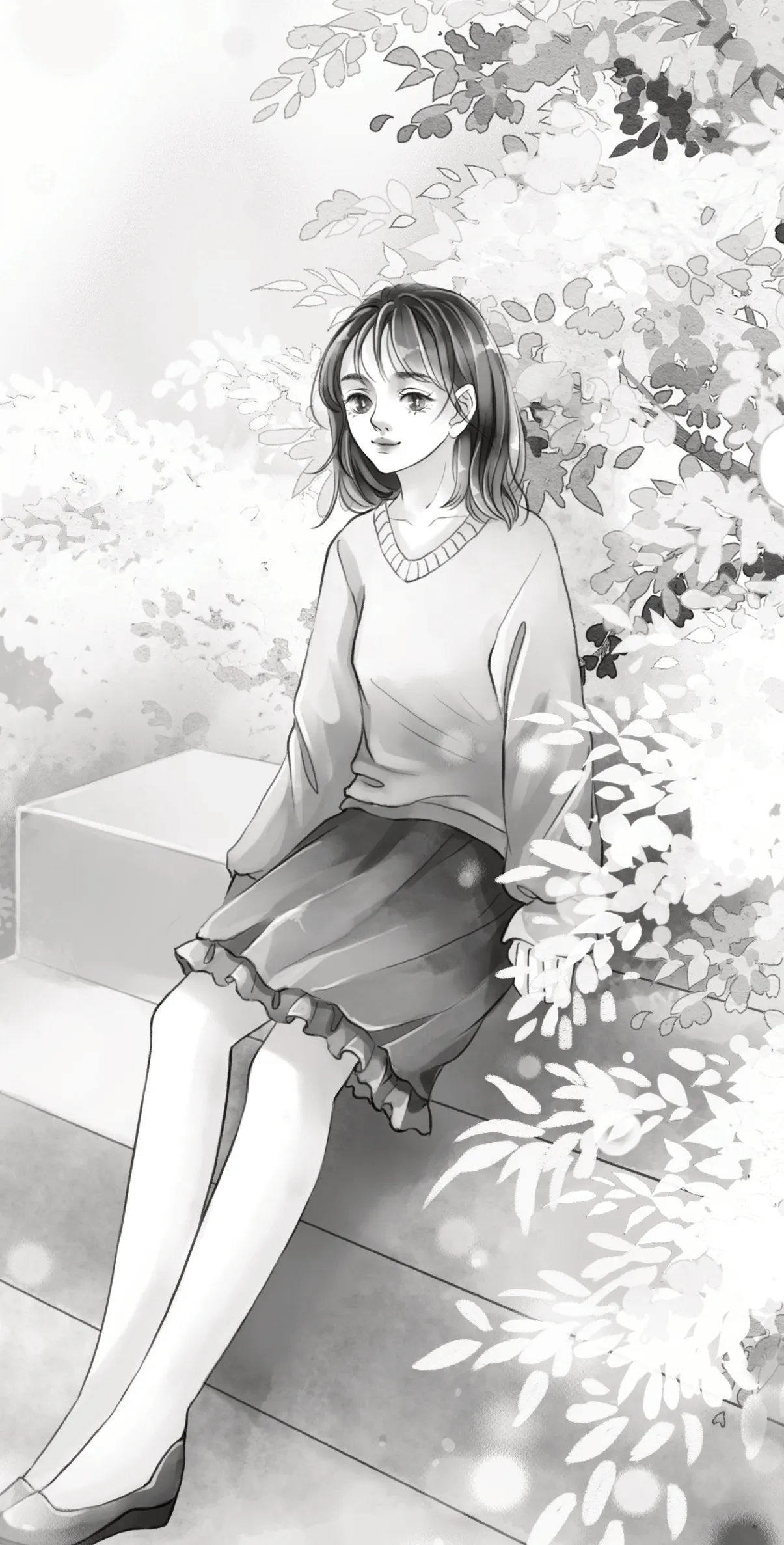
还好一切未迟,她有了他,就像有了整个世界。
一
郑友谅拖着一个拉杆箱无辜地站在土楼门口,汗水还在不断往下滴。
他坐了两小时火车,走了半小时山路才抵达这里,为的是拜年画非遗传承者薛晴为师。没想到薛晴竟是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女生,只听了他的来由就闭门谢客。
郑友谅不服气,他可是在导师面前立下誓言要把这门手艺学来的,怎么第一步就失败了。他择了个石凳坐下,面对着一条小溪,拆开一盒方便面泡了吃,犒劳一下肚子再战。
这里是闽南,正值金秋,远处群山耸立,近处秋叶摇曳,倒是很美。
把最后一口面条吞下肚,他准备到附近逛逛,找个住处再战。可刚走出几步,他便听见头顶一个清脆的女声:“你别走了,上来吧,我答应了。刚刚只是为考验一下你的恒心。”
郑友谅抬头看,女孩打开土楼高处一扇窗,冲他俏皮一笑。
美景配美人,她扎着蓬松的马尾辫,穿着桃粉色长裙。他看着,只觉心已抢先一步飘到了楼上。
二
“你是我收的第五十六个徒弟了,你看看,这是之前他们做的年画,如果你根本不会画画,那就自觉离开吧。”
薛晴带郑友谅进了她的房间,指了指窗旁贴的几十张年画,无不拙劣。他立刻拍胸保证:“我是美术专业,一定会比他们做得好。”
“我也觉得你挺顺眼的。”她眨着一双清澈的眼端详他,看得郑友谅轻咳一声,下意识看向别处,发现其他几面墙上都贴了许多精致年画,心里有底了。
“你家人呢?”
他想薛晴父母是不是有事出去了,可刚问完就见她收敛表情,只是轻轻摇头,脸上更添了忧伤。
他立刻想打住这个话题,而薛晴已拿了一张年画成品塞给了他。
“这地方没旅馆啥的,你要不住我隔壁,有个空房间。还有,明天把这年画的线稿画好交给我。”
她一秒变作严师,语气生硬,然后不由分说把他轰出门。
郑友谅被拒门外,他只得推开隔壁未锁的门。那是个放了张床和桌子的小房间,他打开小窗,让吹进来的秋风驱散杂念,然后准备给导师打个电话,发现这里居然没信号。
他瞥了一眼手机左上角,刚积攒的好心情顿时消失干净。
没有电子设备的干扰,郑友谅只花了一个中午就画好了线稿。
手上这幅年画明显是薛晴画的,色调明亮,粉红嫩黄和青绿颜色大胆组合在一起,少女心十足。看着上面上色均匀的图案,他爱不释手,拍了张照做纪念,接着敲了敲薛晴的门,顺便把一盒桂花糕送给她。
薛晴小脸上充满惊讶,她接过糕,迅速拆开盒子递给他一块:“那个,你别以为我会感动啊,你住我的土楼,也要付房租的哦。”
什么房租?郑友谅忽然发现自己中了她的圈套,而薛晴看着他一副呆滞的模样,忍俊不禁。
“行了别害怕,你帮我做点事,就不用交了。”
薛晴抹掉唇角的糕点屑,撩了下刘海,拿了个竹筐:“你要不和我一起去摘点菊花吧。”
走至溪边,她发现男生犹豫着不知怎么过去,忽觉好笑,果断挽起郑友谅的手,带他从缓流处趟过。他这么多年第一次有被异性牵手的经历,当女孩柔软清凉的手指触到他手心时,脑子竟如宕机一般成了木头人。
于是走过溪水时,他的运动鞋和长裤下端全浸了水,在草地上拖出一条湿漉漉的印记。
“你是不是傻?”薛晴回过头,非常不客气地问他,语气却并没有笑他的意思。
郑友谅沉默了,最终他挤出一个笑,试图转移话题:“薛晴,你几岁了?我都二十多了,一个人是可以过河的,只是今天第一次过……”
“我十九了。带你过河,只是怕你脚一滑摔了,摔出脑震荡就不好了。”
薛晴脸上有睫毛罩下,生出些许脆弱感,兴许是触动了往事,她接下来一段路都没说话。
于是郑友谅决定帮她采菊花,在走到大片菊花前时,他果断出击,电闪一般摘下好几朵,然后放进筐里。一不小心,居然被某根枝叶上的小刺扎破了手,他疼得倒抽一口气。
再看薛晴,她正饶有趣味地看向他的伤口,然后毫不留情地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三
摘完半筐菊花原路返回土楼时,郑友谅长了教训,卷起裤管脱了鞋扔到对岸,踩着溪中石穿过溪水。
薛晴将菊花去叶去蕊,拿了根木棒把它们捣碎倒入缸中加了点水,说要做颜料。
他才知道她年画印染所用的各色染料都是天然提取的,不禁肃然起敬。
“我身上这裙子也是用花染的呢。”
薛晴说完,天井处忽地传来一声吆喝:”开饭啦!”
这土楼是薛晴祖家因战乱南迁至闽南建的,现在唯一的继承人便是她。因为空闲,她把几间房出租给别人,每天中饭和晚饭都在天井吃,一派其乐融融。
“小晴前几年母亲就死了,你作为她的徒弟,要对她好些。”
做饭的大妈如是说,郑友谅颇为同情,他偏头看见薛晴正帮着摆碗筷,忙帮着拿了一摞碗分发。
就这样,十个人热闹地开始吃晚饭。郑友谅初来乍到,倒也不忌口,每样菜都尝了,顺便帮她夹了几回菜。
吃完后薛晴才小声对他说了句谢谢,反手又给他拿了几张年画,还有一把刻刀。
“你先试着把上面的图案切下来,注意小心划伤手。”她指着他手上尖刺扎出的红点笑道。
郑友谅拿着年画回屋时,看见薛晴悠闲地站在门口栏杆前看天。土楼顶上的夜空中散布着许多星星,时不时闪烁如眨眼,带有未散暑气的晚风刮动她如瀑的长发,那桃粉色的裙摆飘逸,像一朵花。
她凭栏站着不说话,侧脸却似带有无限伤感,眼角缓缓滑下晶莹的泪滴。
四
半个月一晃过去,郑友谅已经会用刻刀了,同时天天帮着薛晴干事。
她说他送的桂花糕不纯正,太甜了,于是特地打了些桂花亲手做了桂花糕,一不小心做多了,于是挨家挨户分享。
“春天我教你做鲜花饼!”她一边吃着糖桂花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薛晴虽然瘦,脸上却有些肉,此时如一只小松鼠一样飞快咀嚼着。郑友谅笑了:“你教,我就一定会学。”
土楼内通了水电,他晚上或是写论文或向她请教问题,时不时拍她使用刻刀刻木板的视频,直到她困了为止。
暮秋一天,采完最后一块地上的菊花,离开饭还有很长时间。阳光正好,秋韵更甚,地上铺了一小层红叶,踩在上面软软的,时不时发出沙沙的絮语。
薛晴今天穿了长衣长裤,一身淡蓝。她抱着竹筐趟到对岸,坐在太阳晒暖的石头上,脱了鞋子把脚放进水里。
“你也来呀。”她一边玩水,一边灿烂地笑,天真烂漫如小女孩。
薛晴纤足白嫩小巧,在溪水里搅动波纹,她的腿瘦而长,随意挽起的裤腿上也沾湿一片。郑友谅看呆了,直到她侧头招呼他也来试试,忙扔了运动鞋和她一起泡脚。
溪水清凉透亮,从脚面缱绻流淌而过。薛晴身上带有淡淡花香,她一侧头,却见一旁的男生正用余光瞟她,幽深的眸中满是温柔,心漏跳半拍。
为掩饰脸红,她从溪里掬了一捧水就招呼过去。郑友谅伸手去挡,但还是被淋湿了头发,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打起水仗。
直到天边出现灿烂霞光,薛晴才“啊”了一声,扯了扯身上湿透的衣服。她胸口的曲线因衣服打湿凸显出,兴许郑友谅的眼神太直接,她别过头去,抱着竹筐就跑了。
晚上郑友谅照常敲她的门想领任务,薛晴小脸微白,说今天让他休息,别熬夜了。
“友谅,你挺好的,不像我之前那些徒弟,整天好吃懒做,学了个皮毛就溜了。所以今天让你休息吧,早点睡。”
她声音软糯轻盈,道完晚安冲他挥挥手就关门熄灯了。郑友谅心中一暖,他回房又码了些论文,临睡前点开他拍的那些视频逐个看了看,结果他就梦到了薛晴那双白嫩如小葱且毫无赘肉的手。
第二天薛晴恢复了精神,带了鸡饲料去喂刚出壳的小鸡,郑友谅也跟着去了。
小鸡们毛茸茸的像小绒球,十分可爱。她放下饲料,它们便欢喜地挤过去围成一团抢着吃。
两人刚想走时,薛晴眼尖,看见有只小鸡突破围栏的限制,已摇摇摆摆地走了几米。
她忙快跑两步蹲下身去抓,保全鸡安全后,捂住了小腹,脸上一下褪去了血色。
“我先回去一下。”薛晴皱着眉,上楼前歉意地望了他一眼。看见她疼得脑门出冷汗,郑友谅隐隐猜到了情况,他回房冲了杯红糖水,然后端到薛晴桌上;“这是红糖水,你喝了会好受点。”
薛晴听话地喝完,脸色好看许多。她笑时,脸上红云分外羞涩;“你对我真好。”
郑友谅的心被她的笑靥击中了,女孩的眼神湿漉漉,如雨后初霁的天空,她声音分明一如以前,却更加好听,引得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保护欲。
“我这儿还有点红糖,都送给你吧。”
五
从那天开始,两人的交谈愈发多了,薛晴送了他几块梨木板,教他木刻。一个月过去,郑友谅终于能够雕刻出一整张年画图案了。
此时正是月初,她一天去收房祖,带上他一起,挨家挨户敲门。
房租不贵,每个月五百,可薛晴走到最后一间时,敲门动作明显迟疑了。郑友谅站在一旁,听她好声好气地催:“都三个月了,你再不交房租,我真的会把你赶出去。”
“你把我赶出去?小小年纪对待老人这么不讲理,我倒是要看看——”
薛晴被老赖气得握紧拳头,她咬住下唇思考对策,同时旁边多了道声音。
“你这样是违法的。”郑友谅挡在她身前,语气沉稳,“不怕我拨电话报警吗?”
“报警?”老赖不置可否,后退几步,作势关门。
郑友谅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他知道这里没信号,但还是装作在打电话,把手机靠在耳边。
“你你你,好,我交!”
见他动真格,老赖的嚣张气焰瞬间没了,他吓得立刻回屋数了一千五给薛晴。
郑友谅见目的达成,牵着她的手就走,语重心长告诉她:“你性子太软了,会受欺负的。”
他很难想象薛晴失去双亲后那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她肩上不应该扛下这么多。可不论怎么想,“我会陪你”这四个字都始终说不出口。
“那我……该怎么做才不被欺负?”在他思考未来时,薛晴停下脚步问他。
“像我刚才一样,你说要报警,吓住他。”
“嗯,下次试试。”
因为收齐房租,薛晴心情很好,那天没给他留作业。第二天喂完鸡,她忽然问:“你会爬树吗?”
郑友谅眼睛一亮,这可是他的专长。于是他应了她的邀请,走到远处山坡,一棵枝叶茂密的榕树赫然在目。
树很好爬,腰部有一个可落脚的树杈,郑友谅腿长,很轻松爬了上来,而薛晴更熟练,两人几乎是同时到达树杈上坐下。
远处青色山峦连绵,暖暖的阳光照在其上,让人的心都敞亮起来。
远望薛晴那座土楼,明黄的外墙,深棕的瓦,阳光将其镀上一层金色,榕树枝叶摇曳,竟让人产生它会说话的错觉。
“在这儿许的愿,都会兑现哦。”
薛晴手撑树杈看向远方,她今天梳了双马尾,有发丝拂到他脸上,痒丝丝的,却在他心中泛起无限柔情。
郑友谅也许了愿,希望他能永远当薛晴的徒弟,让她天天都笑。
最近天越发冷,一周都没下雨。爬完树薛晴就跑到天井去,细心给一盆葱绿的植物浇水。
“这是我的幸运草,不过很怕雨水,下雨得把它放在屋里。”薛晴弹了弹它的叶片笑道。
那草的叶片顿时收缩了,郑友谅想了想纠正她:“这是含羞草。”
“总之,它都是我的宝贝。”薛晴不管,又挠了挠它,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过了不久就是元旦,作为她的徒弟,郑友谅自然要有所表示,因为还没有学印染年画,他只能送一张她的素描画给她。薛晴很开心,立刻把画裱了挂在墙上,在元旦这天晚上还喝了好几杯果酒。
酒是用野果酿的,度数不高,但她还是醉了,一双美目似倒映着整个星空。郑友谅扶她回房,见她穿得单薄,脸色还发红,有点担心地探了探她的脑门,微微发烫,应该是喝醉导致的。
“我没醉!”当他掖好她身上盖的被子时,薛晴睁开眼,有气无力地抱怨,“我不困!”
“乖,睡一觉就好了。”
郑友谅耐心地又连续掖了几次被子,薛晴终究没敌过困意,手揪着被子睡着了。
在帮她关窗时,他路过她放了刻刀和画的桌子,看见一本吹翻页的本子。
本子被风吹到某一页,上面写有一句话:今天跟傻徒弟去爬姻缘树啦,我许了个愿,希望他能记住我。
薛晴只有初中学历,那个“姻”字涂改了几次还没写对,无奈用了拼音。郑友谅看着那行小字,心中莫名难过,他又翻了一页,发现她昨天也写了一小篇日记。
“我挺羡慕傻徒弟的,他能考上大学,知道含羞草的名字,还送我红糖。”
“不知为什么,我不想让他走,所以现在这没教他印染,但是春节之前一定要教完。”
“嗯,我这一生,应该只能在这儿度过了。”
看见她最后一句话,郑友谅的心小小地抽痛起来。他望向热得又蹬开被子但睡得正香的女孩,冲动地走过去在她光洁的额头上印下一吻,同时听见楼外传来阵阵热烈的鞭炮声。
这几个月他们天天相见,他也想过之后离开她将会多怀念,但从未从她的角度考虑。
守着土楼,每天简单却孤独地活着,这生活真的很好吗?他不知道。
六
尽管郑友谅没有催她,薛晴还是在元旦过后的第三天开始教他印染。她拿出各色染料,戴上手套,这让他联想起做实验。
想到学完印染即为师成,他更是不舍,便想假装自己还是没学会。
薛晴第四遍示范完,却见徒弟在发呆,一时有些生气,把染料推给他:“你来做一遍!”
郑友凉一愣,再看她,女孩眼圈发红,轻咬下唇,委屈得快哭起来。他明白她不想让他走的小心思,这几日薛晴在一点烛灯下细心染画的一幕幕,他都记得。
他用小刷给梨木板上色,拿长卷纸印染,用工具压实,即出现一张色彩鲜艳的年画。
这是郑友谅第一次完成年画,他的心情却前所未有的沉重,只是讪讪一笑:“嗯,我现在已经会了。”
再看那年画,上面是一个少女的侧脸,青丝垂在肩头,珠唇轻启。虽看不出少女是谁,薛晴还是惊了,她一把抓过画:“你这幅作品,就送给我当分别礼吧!”
她说着虽欢脱,可眼帘还是无声垂了下去,像在伤心。
郑友谅心中一柔,上前抱住了她,薛晴短暂挣扎了一下,接着在他怀里耸动双肩,声音染了哭腔,他顿时慌了。
“你别哭,我想等春节再走,顺便也带上你。你还没坐过火车吧?”
他一下下抚着她的背,像在哄孩子。薛晴很快就不再小声抽泣,冲他伸出小指,破涕为笑道:“好呀,拉勾!
“我听说火车开得非常快,像风一样呢。”
郑友谅看着女孩脸上露出向往的神色,笑道:“那就这样定了,带你体验风一般的感觉。”
接着他还画了张火车图片给薛晴看,她眨着眼问了许多问题,早就忘记哭了。
今年过年很早,他们打算除夕前一天中午走,薛晴把长得有原来一倍大小的鸡都卖了,又将那株含羞草浇了些水,放在走廊里,拿着几卷年画作为行李,和郑友谅沿着他的来路走向邻镇火车站。
同时,他们发现村口有人在修建信号塔,似是要接上移动网络,于是他带她下火车后,先去了手机店。
薛晴穿了他的一件棉袄,正新鲜地点着试用机的屏幕,最后选了一部小巧简约的手机,郑友谅帮她结完账后又办了张手机卡,接着赶去地铁站。
到达学校后他去交论文,嘱咐她在楼下等一会,但郑友谅和导师聊完天下楼,却没找见薛睛,开始着急。
想起刚才在人潮汹涌的地铁上被挤得左右摇晃的她,郑友谅更加紧张,他忙向路人询问。
“我朋友走丢了,她穿一件白色棉袄,看上去挺可爱……”
他如复读机一样边走边问,愈发焦灼。
“是你女朋友吗?刚刚她在那边卖东两呢。”
得到路人指路后,郑友谅看见前边围了一圈的人,急忙拔腿冲过去。
果然,薛晴正在卖年画,她的手指在冷风中冻得发红,旁边围着的人甚至开始为最后一卷画归谁而争执,她夹在中间不知所措,想拿刻刀出来把画一分为二,奈何太冷,根本握不住刀。
“薛晴!”
郑友谅一边喊一边从远处飞跑过来,惊得她手一抖,刀险些掉在地上。
“你放着,让我来。”
郑友谅的举动让薛晴一阵感动,乘巧地答应了。
他把那卷年画分或两半,卖给争执不下的两个人,接着看着散去的人群,缓缓牵起她的手。
“手机号给我,这样,我们就不会走散了。”他柔声道。
薛晴抓着他的手不放,两人一起看向西边玫瑰色的晚霞,郑友谅希望,之后每一个晚霞都能与她共度。
七
第二天便是除夕,他们玩到下午,街上就快没人了。郑友谅打通家里电话,和薛晴一起回了家。
他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平时忙得顾不上他,见他带了个清秀的女孩子回来很是惊喜,在他坦白她的身份后一致催他赶紧表白,免得错过这么好的姑娘。
郑友凉倒没想过他父母这么喜欢薛晴,她碗中的菜堆得很满,相比之下他这边冷冷清清。
年夜饭吃完后薛晴坐在小院里看风景,看刚贴好的几幅年画,困得睡着时脸上带着笑,最后还是郑友谅抱她回客房安顿好。
这两天薛晴跟着他到处跑,原本有肉的小脸都变尖了,他有点心疼。
郑友谅回卧室后果断开始搜索:第一次告白怎么说才能让女孩子答应。
但第二天他还没开始行动,薛晴就想回去了。她说看到一则新闻,闽南下大雨,怕含羞草被淹。
他们乘着最早一班火车赶回土楼时,天上乌云已散,阳光朦胧,洼地里积满了水。
那个除夕夜的雨又多又突然,淹了半层楼,那盆含羞草根系泡得腐烂,叶片浸在积水里,捞起来的时候已经病恹恹了。
薛晴红了眼圈,抱着含羞草趟过积水躲进房间不再出来,郑友谅站在一旁愣愣看着,直到鞋子又被打湿。
正是三九时期,他只感觉脚心向上不断冒看寒气,生怕她感冒,拿了暖手贴去敲她的门,却无人应答。
土楼里的人大都去别的地方过年,中午也没人做饭,郑友谅去一楼还能用的厨房里做了一顿蛋炒饭,放了一碗在她门口,然后又不死心地敲她的门。
细听门内传出低低的抽泣,这是他第一次听见薛晴哭得这么可怜,心都软了。
“薛晴,我炒了点饭,就放在外面,你饿了记得吃。”
郑友谅刚说完就听见她自哽咽中爆发出的一句话:“友谅,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徒弟,给我离开这里!”
她嗓子哑了,如此绝情的一句话也让郑友谅呆在原地,半晌才低声说:“薛晴,要不之后我再给你买一盆——”
“那也不是它了啊!”门唰地开了,薛晴双目通红,一旁桌上只剩那奄奄一息的含羞草。她嘶哑着嗓子吼着,接着又砰地一声摔上门,震得土楼内部阵阵回音。
郑友谅只觉难受,他收拾好住了几个月的房间,最终决定离开土楼。回首只见浸水的运动鞋在地上留下的水痕,门前溪水还在流,就像能流到永远。
他再次抬头看向薛晴那扇窗,却没有机会看见它再次开启了。
八
薛晴还记得初中毕业那天,她早早从邻村放学回家,想给母亲报喜。她等了一会儿,天开始变得黑沉,暴雨突然而至,引发山洪,母亲再没回来,人们在她的尸体旁找到了一盆保护得很好的“幸运草”。
如果她不求母亲买一盆“幸运草”作为毕业礼物,一切都不会发生。
十年前她父亲因肺炎病死,十年后薛晴成了孤儿,她放弃考取的镇上高中,靠出租土楼为生,平时也有人远道而来求教年画,但都是三分钟热度。冬去春来,她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若不是郑友谅打破她一成不变的生活,薛晴觉得自己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他踏金秋而来,出身美术专业,用半天时间做完别人一天的工作量,画的稿子甚至胜于她。
薛晴有记日记的习惯,她咬着笔想了想,恶作剧地给郑友谅起了个绰号:傻徒弟。
确实很傻,他摘花还能扎破手,平时看上去也莫名呆萌,但声音很好听。
不过,她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
兴许是那天互泼水玩的时候,他身上的白衬衫湿成透明。兴许是每次开饭他都会帮忙分发碗筷,他们的手不知觉地相触。
而当他们爬到姻缘树上时,瞧见郑友谅认真许愿的侧脸,薛晴的心就不受控制地乱跳,是先前从来有过的。
他学得快,元旦后就得教最后一个步骤了。有句话叫借酒浇愁,于是薛晴在元旦多喝了几杯,迷糊中竟是他拥她入怀,整个人都飘飘然了,当然更多的还是害羞。
但是那天后来的事她都忘了,之后她愈发觉得必须坦露心思,却又不敢。
郑友谅频繁出现在薛晴梦里,可每次都触不可及。她在梦里踌躇满志准备把他拿下,醒来后一开门,对上他干净的眼眸,勇气又烟消云散了。
因为他,她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知道外面世界如此广阔。
薛晴睁开眼看了看日历,这是郑友谅送的。她已不记得这是第几个离开他的日子,那天发完火她就后悔了。可如今,还能去找他道个歉吗?
或者,直接向他告白吧。
薛晴忽然想到她还有一部手机,打开一看,2 月14 日。她不知这个日期有什么特殊之处,但看见日历上说,今天是情人节。
郑友谅的脸似在眼前晃动,她呆呆地望着屏幕看,回忆他们的初见,回忆他在灯下雕刻的认真细致,直到眼圈变红,泣不成声。
那盆草虽珍贵,但她也舍不得他。
那场雨太突然,他其实也没做错什么,只是她唤起对母亲的回忆,触发了内心最深处的痛。
心结解除,薛晴买了张火车票到了他大学那座城市,她看着窗外风景往后退,心越来越急切。
她要向他道个歉。
直到下车后她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冲动。城里人流如织,一对对情侣在火车站出口拥抱,空气中也飘着浓烈的爱意。
薛晴不认识路,逛到广场,看见中间有块大屏幕,上面播放的视频令她脚步一顿——那是年画的制作过程,那双操作刻刀的手就是她的手。
不用想,一定是郑友谅做的事。薛晴挣扎了一下,站到人群里,看向屏幕。
广场一条横幅上写着“非遗——年画展览”,此时活动已至尾声,一旁年画铺已被扫荡一空,还有不少人在试刻。
郑友谅正在回答记者的问题,他今天穿了件很衬他肤色的黑色羽绒服,笑起来很是自信,晃得薛晴又呆了呆。
“教我年画的,是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小姑娘,她很细心也很可爱。我今天举办活动的目的,一是为了传承年画,二是为了坦白我的心意——我喜欢她。”
郑友谅说完,略遗憾地想起薛晴,可惜他人生中第一次表白如此轰轰烈烈,她却不在现场。
他准备结束活动再回土楼看她,毕竟对于那次不欢而散他心怀愧疚。
记者问完后郑友谅就去了后场,他蹲下来抱起一来滚着露水的玫瑰刚起身,就发现眼前多了一个人。她长发飘摇,乌黑的眸子望向他,然后猝不及防地笑了。
“友谅,”薛晴伸出手在看呆的郑友谅面前晃了晃,“你想对我说什么?”
后者愣住,接着把玫瑰塞到女孩怀里。欢喜来得太突然,他以为自己在做梦。
“我喜欢你。薛晴,做我女朋友,让我陪着你,好吗?”
薛晴惊得小脸泛红,她咬着下唇不知所措,眸子忽闪,其中氤氲着水雾。
“我也……喜欢你。”
话音未落,郑友谅已把她圈进怀里,他们在玫瑰色的浪漫晚霞下接吻,像大千世界最普通的一对情侣。
尾声
一年初夏,春花未败,开得炽烈又明艳。
毕业半个月的郑友谅牵着薛晴的手去爬姻缘树,女孩懒懒地把头搁在男友肩上,嗔怒道:“你当初居然偷看我日记!早知道我就弄个锁了。”
“不看的话,我怎么知道你叫我傻徒弟呢。”郑友谅刚说完,便被她轻轻捶了一拳。
“你之前很傻,现在也傻,但……我喜欢。”
“所以,你什么时候教我做鲜花饼?你去年说过的。”
“不拖了,就现在吧。”
薛晴又一次和郑友谅摘起花来,融融春色正好,耳畔风捎来夏日前奏。她忆起那天从楼上往下看,他后知后觉抬起头,眼中是胜似星辰的笑意。
还好一切未迟,她有了他,就像有了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