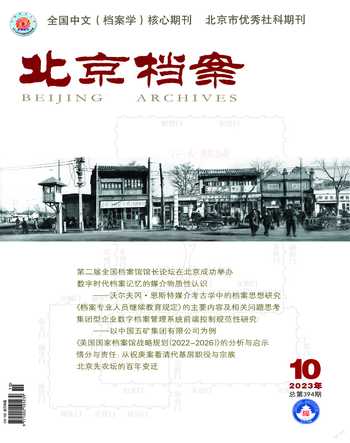情分与责任:从祝庚案看清代基层职役与宗族
王晓斐
摘要:雍正、乾隆年间,婺源县民祝多屡次利用总催这一基层职役身份侵吞钱粮,却在事发后无力偿还,祝庚作为房长不得不为之偿债。后双方爆发冲突,祝庚失手将祝多推水溺毙。乡保见双方私下和解,未去县衙报案。案发后,房长祝庚和乡保均被判罚。这一案件表明,乡约、保甲等基层职役与地方宗族社会有着较为密切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网络,有时会囿于情分而违背法律。清代宗族常以轮充形式选派族人充任各类基层职役,也在官府面前做出担保;一旦其犯罪,且无力偿还赔费,族房可能会承担连带责任。
关键词:清代基层职役 宗族 祝庚案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Yongzheng and Qian? long of the Qing Dynasty, a citizen in Wuyuan county named Zhu Duo repeatedly exploited his authority as grassroot managerial staff to embezzle money and grain, but was unable to repay. Zhu Geng as the head a branch of the local clan had to repay the debt.That stimulated a conflict between Zhu Duo and Zhu Geng who accidentally pushed Zhu Duo into the river and let him drowned and dead. Since the two parties settled the case privately, the grassroot managerial staff did not go to the county government to report the case. However, the crime was discoverd, and both Zhu Geng and rural grassroot officials were sentenced to penalties. This case shows that the grassroot manage? rial staff have close geographical and blood relation? ship with the local clan, and thus they tend to violate the law because of the bond. In the Qing Dynasty clans often chose their members to serve in various types of grassroot managerial positions. They also made commitment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that they would be held jointly liable once their chosen mem? bers committed crimes and were unable to pay back the compensation fee.
Keywords: Qing dynasty; The grassroot manageri? al staff; The clan; The case of Zhu Geng
乡约、保甲等基层职役作为清朝官府和基层民众沟通的纽带,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王朝统治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却也经常游离于法律之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乡保各类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常建华利用刑科题本的研究表明,福建、安徽、浙江等地方社会职役呈现出从乡保到地保发展的变化趋势。[1]戴炎辉针对清代台湾地区,介绍了当地地保的投充、组织、性质。[2]较其他地區而言,有关徽州地域的研究成果较多。廖华生根据清代婺源资料,认为乡保是指代乡约、保甲的专有名词。[3]刘道胜指出乾隆以后的徽州地区,地保是由于里甲制度嬗变所带来的职役变化而普遍出现的。[4]陈瑞认为部分徽商会出钱雇人代替自己充当保甲,宗族内部会给担任保甲的人一定补贴。[5]已有研究虽对清代基层职役与宗族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讨论,但有关犯罪职役与其宗族之间的关系仍有讨论空间。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刑科题本《婺源县民祝庚溺毙祝多案》[6]为例,结合社会史和法律史的分析视角,揭示该案对深入理解清代基层犯罪职役与宗族两者关系的普遍意义。
一、祝庚案概况
祝庚和祝多均为徽州婺源县民。祝庚是祝多同支共祖的小功堂伯,同时也是该房房长,见祝多母亲去世,三岁的祝多孤苦无依,便将其抚养长大。祝多曾在雍正年间担任总催,由于在李知县任内罔顾法纪,侵蚀图内花户钱粮,负累祝庚弃产赔纳白银五十二两。后又在吴知县任内,侵吞钱粮,连累祝庚再次赔付白银六十三两。后于乾隆元年(1736)和二年(1737)因家里贫穷,将族内土名“松林下”等处祀田盗卖给吴大樑等名下为业,并将所得价银五十两花费,后被族人发现,不得已出逃在外,于苏州木行做工,数年未归。族人问责祝多未果,只得再次责令房长祝庚递年揭债替祝多赔偿租籽,以作历年祭祀之用。
乾隆七年(1742)十一月十三日,祝庚听闻祝多潜回归家,便于次日清晨携子祝三十前往祝多家索银赎田还祠。祝多安卧不答,甚至出言不逊,祝庚不满祝多的态度,于是上前殴打祝多脸颊、肋臂,并拉拽祝多,要将其送往宗祠投族问责。祝多因曾在祠堂受责,坚持不肯随祝庚前往,在路上不断地进行反抗并伴有言语顶撞。祝庚见状,先是拾取柴棒殴打祝多臀膝,用绳子拴套祝多颈部,并喝令祝三十在后推走;后一怒之下趁祝多不备,将其推入河中,自己也跳下水。祝三十仓皇之下,下意识先下河救父,无暇顾及祝多,致使祝多沉入深流淹毙。另一边,祝多妻子倪氏见祝庚将祝多拖往宗祠,忙去乡佑祝义家求助,不想祝义病重,根本无法起身。倪氏无法,只得转去央求族人祝佛前去劝解。待祝佛走至村外时,就见祝庚和祝三十湿衣站在河岸,而祝多已尸沉水底,只得先与祝三十一同将祝多尸身捞起。
而后,倪氏和乡保祝周、祝节欲将此事投报县衙。祝庚闻之,赶忙与其子祝三十前往县城拦住三人,并许诺为倪氏养老,替其偿还债务。而作为交换,倪氏就不能继续前去报官。倪氏因孤身一人,且是女流,便听从了祝庚的建议。而后祝庚又恳求两位乡保将此事隐匿。两位乡保见双方已达成私下和解,也不愿多生事端,便没有继续到县衙报案。祝庚随即准备了棺殓等丧葬事务,将祝多掩埋。后来,祝多儿子祝松生闻信归家,在知晓前因后果后,于乾隆七年(1742)十二月十三日,赴婺源县衙控告祝庚,他宣称自己父亲祝多时垂运舛,因债务未清,一直在苏州打工。不料此次回家惨遭族恶祝庚同子祝三十无故拥门殴打,复用绳托赴河中淹死。
官员在接到报案后,分别对原被告双方、仵作、乡保等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在调查清楚事情缘由经过后,祝庚最终拟被依照尊长故杀小功堂侄律,处以绞监候;祝三十虽未同谋,但听从父亲帮推祝多行走,不加劝导,以致祝多溺毙,被依照不应重律,拟罚杖八十,先行折责发落;祝周和祝节两位乡保虽无受贿之事,但知情不报,拟罚杖八十,先行折责发落,革役。祝庚案由此落下帷幕。
二、从乡保隐匿不报看清代基层职役
乡保作为清代最基层的半官职人员,是国家权力和乡村共同体之间重要的交界点,[7]主要负责征收钱粮、承办官差、协办案件等事务,在各类案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乡保大多由当地民众选任,他们与民众之间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很容易成为其办公的双刃剑。
(一)得天独厚:乡保办公的天然优势
通常,乡保的选任主要由地方头面人物或百姓以推举或轮充的方式选出,如“乡约、地方等役,类由本乡、本里之民保送佥充”[8],“地保,每图一人,由该图耆老业户选充”[9]。这种选拔方式选拔出来的乡保大多为当地民众,与其他民众有着千丝万缕的各类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就使得乡保在办公时较官员拥有更天然的地缘和血缘优势。
虽然清律规定乡保无权直接处理地方纠纷,地方官员也不得擅将案件以一定理由交给下属处理,[10]但实际情况是,繁重的官府事务令官员很难对所有案件都进行面面俱到的处理,官员不得不依赖乡保等基层职役,同意或默许其处理部分地方事务。乡保与民众之间的这种地缘和血缘关系很自然地就成为其顺利开展工作的一个便利条件。民众如果有案件想要上报,需先向乡保鸣告,方可诉诸官府。待官府受理后,乡保会陪同来员进行案件勘察。例如,康熙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1709—1710)婺源十一都坑洪汪互控案中,洪槐口发现其父丧命于荒坦,却不知何人为之,当即投鸣乡保,叫乡约汪家义、汪叙保等人前往看验。[11]嘉庆二十三年(1818),婺源程、仉两姓互殴案中,乡约程林报、程远报在案发后,速将仉大别等人逃亡等情况汇报给官府。[12]一旦地方发生盗案、命案等恶劣案件,乡保需立刻就近集人,速行拿获犯人将其送案。若不知犯者何人,乡保也需立即报明官府。[13]
此外,这种较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从另一种形式上逐渐将乡保的职能扩大化,部分族规、家训、合约中为乡保赋予了调解纠纷等职责,如“保护乡里,为人排难解纷、劝止争讼”[14],“农田、水利、森林等事暨乡邻睚眦之争,亦当公平处理”[15],“须照理公言,排解消除弥合,原系保内安居乐业无讼为贵”[16]。而在职能扩大的同时,乡保反过来在实际办公中也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关系。如乾隆三十年(1765)十二月,许公兴、黄升茂等人在乡保方寅政、方茂五的见证下签订合约,以和平方式化解有关祖坟的纠纷。[17]康熙五十六年(1717),保长朱公上劝说窃贼詹国旺改过自新,并立下甘约。[18]这种地缘与血缘关系显然有助于乡保拉近与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距离,便于乡保从事调节工作。同时,半官役的身份也使得乡保在进行调解时具有一定官方色彩,更具权威和公正,有利于更顺利地化解矛盾,将案件消解于民间。
(二)瑜不掩瑕:乡保办公的无形障碍
当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世故与律例规定的法理相互冲突,部分乡保有时也会囿于这一关系,违背工作原則,选择徇情隐匿,试图将案件消弭于官府之外,掩盖既有犯罪事实。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亲亲相隐”所强调的观念在此行为中便体现得淋漓尽致,即极力试图去追求一个稳定的、内敛的社会秩序。此时,这种血缘和地缘关系就会成为乡保正常工作的阻碍。
在本案中,祝周和祝节身为乡保,有遇案投报的责任,本应主动向知县投报祝庚溺毙祝多一案。但因祝庚与尸妻倪氏达成和解共识,便未到案具报。两位乡保的问题主要在于虽至县衙,但并未完成报官流程,虽死者家属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是从结果上看掩盖了祝庚犯罪的事实,直到祝多之子祝松生投告官府后,祝庚才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故在裁决时,知县张厚载认为祝周、祝节虽无受贿情事,但亦属不合,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先行折责发落,革役。
与本案类似,嘉庆十九年(1814),地保熊甫既查知张七宝偷砍伊主坟树,并不禀官究治,反而得受钱文,隐忍寝息,被依殴役诈赃一两至五两例,拟以枷杖罪名。[19]道光七年(1827),地保王魁听从病人家属嘱托,故意隐瞒孙斗疯病状况,致使孙斗因疯砍伤伊父孙克用,照不应重律杖八十。[20]光绪六年(1880),梁遇士诬认平民为贼并致毙人命之案中,乡约梁怀有因病重未报案,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革役。[21]诚然,在此类隐匿案情行为中,部分乡保是因为收受钱财,但同样还有很多乡保如本案中的祝周、祝节一样并未受贿,而更多的是以一种息事宁人的中庸态度去平息纠纷。他们这种行为是清代“不兴讼事”社会导向的真实写照,试图在原被告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在不诉诸官府的前提下解决争端,保全彼此情分和宗族颜面。
英国生物学家汉密尔顿认为,亲缘关系越近的家族成员越倾向于做出有利于自己亲属行为的事情。[22]毕竟同为一乡人,甚至是同族中人,乡约和地保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下,很难一味追求案件的正义性,完全不顾彼此的情面,强行将罪犯与受害者及其家属之间的地缘或亲缘关系割裂开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必须看到,同宗之亲的血缘关系会使得乡保在工作时给当事人双方带来亲和力,拉近彼此距离,但同样可能会给乡保工作带来不便,有时容易使他们带上亲情的枷锁,困于人情世故的泥潭中,无法做出正确的抉择。
此外,乡保将犯人犯罪行為进行掩盖和隐藏的行为虽然是在价值和人性等多方面权衡之后做出的决定,其目的有时并不是为了获取经济收益,而是为了维护所辖地域人群的地缘、亲缘关系的稳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不需要付出代价,无论何时,小部分人的私利必须服从于国家和社会多数人的合法权益。与上述徇情隐匿案件对比可知,在判决乡保隐匿类案件时,是否受贿钱文是决定乡保受罚轻重的重要依据。若乡保得受钱文,则惩罚更重,多以“诈赃”“证佐不言实情,致罪有出入”等具体罪名进行惩罚,惩罚方式多为杖刑一百及枷刑等其他刑法。而若未收受钱财,官员则常用“究属不合”一句描述乡保罪行,多笼统地按照不应重律,以“杖八十,革役”进行处罚。“究属不合”也反映出清代法律的弹性,以一种概括笼统的说法承认乡约行为的错误性,进而对此类群体的其他人员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同时,此举也可令官员能够通过对于案情严重程度的判断、对于律法的理解、自身经验、对案件的感受和情感考量来适时做出最合适的判决,使得辖域内的情理关系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和谐顺畅。
三、从总催侵占花户钱粮看清代基层职役与宗族
保甲制作为清代治理基层社会的一项基本方略,在雍正朝以后迅速推广并颇有成效。在保甲选拔的实际过程中,保甲与其所在宗族构成了一种紧密联系。除对保甲进行一定经济补贴外,宗族在代替官府分配保甲名额、选拔人员的同时,也承担起部分基于其选择的连带责任。
(一)扶助救济:保甲选拔与宗族补贴
清代多倾向于选择家境殷实之人充任保甲。官府在选拔保长、甲长等基层管理人员后,往往在记载保甲信息的材料中注有该人“家世殷实”等字样。例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祁门要求保甲长“均要殷实老诚”[23];《卢乡公牍》中也有“应否当甲约,本县亦知其家道不殷实,不甚可靠也”[24]之语。可见,较为富裕的经济状况是官府心目中能够充当保甲的重要条件。
但由于保长常被归入贱役阶层,经常受到大众的鄙夷,部分族规家法中也告诫子孙不得充当地保,违者斥逐出族,许多乡绅或富商有时并不愿充任,甚至有“钱粮为身家之累,人人畏避”之说。这种畏避充任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在征收钱粮时,保甲等人总需对需征钱粮先行垫付,这使得保甲往往需承担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图内小户银漕押令垫完。倘完垫稍迟,即借惰催之名按限血比”。[25]即使对于家境殷实者,要每年按时完成需要垫付的费用也并非易事。因而,在实际充任时,为保证保甲之位无空缺,保甲常由保内人员以轮流充役制共同承充。宗族也常会以保甲银等名义给予充任保甲者一定的经济补偿。光绪五年(1879),祁门汪家坦黄氏文书记载当地六姓因为保甲推诿,而公议补贴保甲,以办公食之资。[26]民国时期婺源会记也载:“若委坐于轮役,则轮役苦累难支”。[27]“其费用俱系照灶出办朋贴,不得独累有名出身之人”。[28]
而现实情况是,即使有宗族对保甲进行一定补贴,却依旧存在许多保甲家境贫寒,入不敷出,不得不典卖部分财物度日的情况。乾隆二十四年(1759),巴县保长梁凤羽就称自己“家贫业卖”“搬壁佃耕”[29]。本案中,祝多两任总催却在革役时无力偿还贪污钱粮,他的妻子倪氏也表示家下贫穷,以致不得已将小儿子过继给德邑董姓。而祝多将祀田私卖,也是出于生计所迫的不得已之举。可见,保甲这类基层群体的社会处境并非一定会因其所担任的官方角色而得到显著性改变,或生活水平一定优越于他人。
(二)共担风险:宗族为保甲办公承担连带责任
传统社会常用信任将个人捆绑于宗族、乡村等社会亚域内,通过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问题蔓延至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进而构成一种信用网络。成员间的血缘关系使家族成为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雍正时期,觉罗满保建议若房长教化不力,不能约束其族人,出现族人为非作恶的情况,那房长就应该一并受到处罚。[30]湖南仙阳文氏族规规定,如果有不遵守规定以至于酿成阋墙之祸者,除本人会受到重惩以外,还会以不善循诱之罪连坐本房房长或本家户长。统治者希望通过连坐制度强化基于利益关系层面宗族成员之间的约束力,强调一人犯罪,官员在其基础上按照法律规定,对相关人员进行加罪处罚。
与上述情况不同,在本案中,官员要求祝庚代祝多弃产赔纳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祝多身为总催侵占钱粮,在事发后因为贫穷无力支付赔款。也就是说,若祝多作为基层职役,在犯罪后有能力支付赔款,祝庚就无须替祝多赔付。在法律层面上,祝庚并未因祝多犯罪而受到连罪,其赔付行为更多类似于一种担保失败而承担的连带赔偿。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担保制度和担保律条,但有关钱债、典卖的律例中存在有类似含义的律条,多是针对保人、中人等明确的担保对象,并对其担保行为进行一定的约束。与现代法律不同,清廷设置此类律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而并非协调处理私人间的经济纠纷。我们常能看到案例中官员会对双方进行多次调解,部分案件结果甚至是有损于原告及其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
催征钱粮是保甲和里甲等基层组织人员的重要职责之一。为保证征收钱粮按时上缴,官府有时还会要求甲长缔结保证向乡保缴纳钱粮的保状。本案受害者祝多在雍正年间两次经由里长排年轮值担任总催,主要负责向花户催征钱粮。但他并不安分守己,忠于职守,反而屡屡侵蚀图内花户钱粮。由于家贫,祝多在案发后无力赔纳银两,最后是由祝庚来替他承担了还款。为此祝庚不得不变卖家产,两次累计替祝多赔纳白银115两。就两者的亲缘关系来看,祝庚身为祝多一支的房长,其实和祝多的亲缘关系并不亲密,仅与祝多的父亲是同祖的兄弟,他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上的亲缘义务为祝多承担债务。因此,祝庚替祝多偿还银两,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身为房长,对族人行为未尽到约束管理之责而做出的补偿。在官府看来,推选祝多充任总催职役不仅仅是出于祝多的主观意愿,也是整个祝氏宗族商议轮排人员名单后的决定。从保甲、总催这类职役人员名单选定的那一刻起,宗族便在无形之中向官府担保其所选的职役能够满足家境殷实且人品无瑕的任职要求。正因如此,在祝多犯罪的时候,身为房长的祝庚需要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这种责任并非来源于某项法律所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而更多的是出于道德方面的惯例、要求等非正式规则。
综上,祝多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究地方职役与宗族关系的新视角,即清代基层职役与地方宗族社会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网络,且并非仅局限于宗族族规家法对于职役行为的约束。特别是在宗族色彩浓厚的徽州,由于基层职役多由本地人甚至本族人担当,其所处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身的行为。为了保证保甲制的顺利推行,宗族常会以轮流充役制来决定基层职役的人选,并以宗族名义为其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助。这些基层职役虽会因宗族的救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却并不代表其生活水平可以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职役掣襟露肘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当宗族确定职役人选以后,也在无形中为其在官府面前做出担保,一旦其犯罪且无力偿还赔费,本人所在的族房可能会需要为其承担连带责任。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参见清乾嘉时期的福建地方社会职役——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明清论丛,2018(1):193-209;常建华.清乾嘉时期的安徽地方社会职役——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徽学,2019(1): 1—16;清乾嘉时期的浙江地方社会职役——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中国区域文化研究,2019(1):176-194。
[2]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3]廖华生.清代蚺城的乡保[J].安徽史学,2006(5):91-97.
[4]参见刘道胜.明清时期徽州的都保与保甲——以文书资料为中心.历史地理,2008(1):152-160;刘道胜.清代基层社会的地保.中国农史,2009(2):89-100。
[5]陈瑞.徽商与明清徽州保甲差役的承充[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3):40-44.
[6]题为审理婺源县民祝庚因其盗卖公共祭田累其赔偿等启衅致祝多身死案依律定拟事,乾隆九年五月十七日,档号:02-01-07-04653-001;题为审理婺源县民祝庚因员累代赔钱粮溺毙祝多案依律拟绞监候等请旨事,乾隆九年五月十七日,档号: 02-02-07-04641-00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
[7]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236.
[8]清朝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330.
[9]民国太仓州志[M]//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江苏省:第2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5.
[10]黄宗智.民事审判和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11.
[11]刘伯山.徽州文书:第2辑第3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15.
[12]杜家骥.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第2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736.
[13]汤肇熙.出山草谱[M]//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668.
[14]卞利.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宗族规约卷[M].合肥:黄山书社,2014:54.
[15][27]卞利.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村规民约卷[M].合肥:黄山书社,2014:54.
[16]安徽省博物馆.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74.
[17]刘伯山.徽州文书:第4辑第1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19.
[18]刘伯山.徽州文书:第3辑第4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41.
[19][20][21]祝庆祺,等.刑案汇览[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4:451-452,1616-1617,627-628.
[22]刘鹤玲.亲缘选择理论:生物有机体的亲缘利他行为及其基因机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114-118.
[23]王钰欣,周绍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166.
[24]庄纶裔.盧乡公牍[M]//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9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635.
[25]华湛恩.锡金志外[Z].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
[26]刘伯山:徽州文书:第4辑3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9.
[28]祁门十三都康氏文书[Z].合肥: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藏室.
[29]四川省档案馆.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196-197.
[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402-403.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