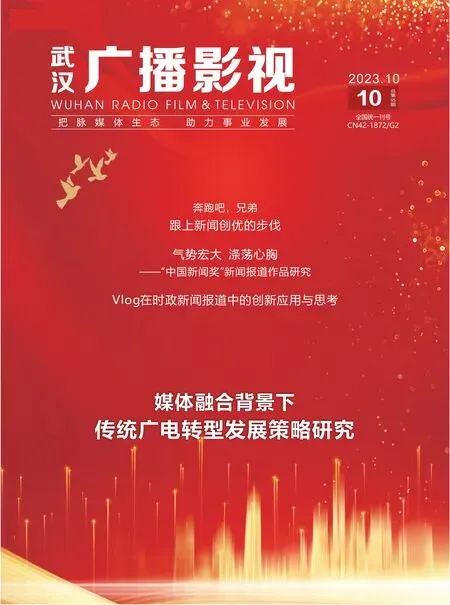围裙网红:短视频平台上家庭主妇职业化的“赋能”与“负能”
任睿睿
据2022《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发布大会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全国网络视听用户达到10.40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12亿,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超过2.5小时。短视频逐步成为用户记录日常生活的重要工具,也催生了大量“职业网红”,也给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提供了展演日常生活和职业技能可见性的可能,“三百六十行”的职业内容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量涌现[1]。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涌现一批以家庭生活为场景,以做饭、打扫卫生为主要行动的短视频博主,她们大多为家庭主妇,通过日常生活的记录与分享收获了一批粉丝。例如在抖音上拥有700多万粉丝的87年广东全职宝妈“王蓉·三娃妈”,以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贵州农村家庭主妇“群姐”。笔者依据该群体的身份符号、内容呈现、价值表达将其定义为“围裙网红”。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崛起,以及衍生出的生活化、大众化特征,家庭主妇得以通过短视频平台提高自身劳动的可见性,实现自我形象构建,密切与外部社会的交流,并以围裙网红的身份,实现经济创收。借助短视频平台,家庭主妇也呈现职业化趋势,成为短视频平台下的新兴“自由职业者”之一。本文以短视频平台的围裙网红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短视频平台在哪些方面为家庭主妇赋能,以及这一展演行为对个体、群体与社会性别观念产生了何种影响,以期能够增益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
一、围裙网红的双重结构特征
家庭主妇在通过短视频平台成为围裙网红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具体表现为双重空间的重叠、双重身份的重叠以及双重关系的重叠。
1.双重空间的重叠
传播学者梅罗维茨在英尼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及戈夫曼的拟剧论基础上,提出了“场景”概念,场景叙事也成为职业网红短视频创作的一个重要维度。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职业身份与职业技能记录与展演的创作者为数众多,例如似“飞行员思齐”、“卡车女司机皮皮慧”、“农民工妹妹聪聪”等,这些职业类创作者的短视频作品中呈现清晰的两重空间划分:工作场景与生活场景。通过不同场景的转换与对比,突出创作者的多样性与专业性。然而在围裙网红的作品中,这双重空间却处于重叠的状态。厨房、灶台、客厅是围裙网红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主要工作空间,通过在该空间内的劳动,填充视频作品内容,这些场景又与该群体的主要生活场景相重叠。双重空间的重叠,对这类短视频的受众而言,因为家庭环境天然带有舒适放松的符号意义,故能够拉近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对于围裙网红而言,双重空间的重叠一方面为其在家工作提供了可能,消解了家庭主妇外出工作的距离问题,另一方面也异化了家庭环境对于围裙网红本人的意义,家庭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休憩场所。

2.双重身份的重叠
“母职”一词原指女性怀孕、生育的生物性母职与育儿的社会性母职两个阶段[2],但对于围裙网红而言,该词可以拆解为“母”与“职”,分别对应在家庭关系中的家庭身份与短视频创作中的职业身份。在成为围裙网红之前,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着妻子、母亲、女儿、媳妇的角色,并进行着相应的劳动。当这些过程与关系被以视频图像形式记录下来,上传至短视频平台时,在家庭主妇的身份之外,她们在互联网中又被赋予了第二重身份:自媒体创作者,即职业身份。在围裙网红的创作及内容的呈现中,实现了家庭角色与职业角色的重叠。
在职业展演的时候,围裙网红与其它女性叙事的可视化作品有所不同。在综艺作品方面,以《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例,该作品中所呈现的女性主义具有形象导向、身材标准化、妇女年轻化、美容整形化的特征,趋于“华丽女性主义”叙事[3]。在短视频方面,变装、美妆类的视频作品主要以身体展演为主要形式,以唤醒女性在身体与形象上的“理想自我”的想象。而围裙网红的视频作品以行动叙事为主,所呈现的是其劳动过程与价值,及对家庭的付出,更偏向于“技能女性主义”叙事。
3.双重关系的重叠
围裙博主的短视频作品中看似缺乏事业部分,但是家庭生活的拍摄与发布也能够成为她们实现经济创收的途径:做饭、做家务、夫妻相处、子女教育,这些全景式的展演也构成围裙网红事业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家庭成员如丈夫、子女、公婆,既是其现实生活的亲人关系,又是其视频作品中的素材,视频作品由这些亲人共同展演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其关系又表现为“同事”。既是家人,又是同事,双重关系的重叠突破了传统的亲密关系框架与共事成员的认知。
二、短视频平台对围裙网红的正向赋能
与大众媒介时代相比,短视频平台为以围裙网红为代表的家庭主妇,提供了自我发声的渠道,能够得以与外部世界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该群体在家庭与社会中的结构地位,实现正向赋能。
1.可见性提高下掌握自我形象构建权
作为一种知识隐喻和社会过程, 社会意义上的 “可见性” 是一种承认, 体现了媒介空间中的权力关系再造[4]。大众媒体时代,由于传媒内部人员性别不平衡及机制的结构性原因,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的构建大多都不掌握在女性自身手中,更不用提及范围更小的家庭主妇形象,以致于公众对家庭主妇的具体劳动及价值模糊不清,其工作的职业性与付出被隐匿,呈现不可见或低可见性,甚至打上“轻松、容易”的标签,造成家庭主妇形象的扭曲传播。
新媒体时代,短视频空间的宽松以及较低的门槛,使家庭主妇这一群体中的每一个体都可以主动走到摄像头面前,选择自己的“出场”方式,记录并上传日常生活及劳动过程,成为围裙网红,以具体的、可视化的形式向大众展现家庭主妇的劳动价值。通过短视频平台,围裙网红能够展示长久以来被遮蔽和被压抑的女性经验,使得家庭主妇原本被忽视的琐碎的家务劳动或情感劳动,从幕后走向前台,显著地提高了家庭主妇劳动及价值的可见性。而可见性的提高能够给予家庭主妇更多可见背后的能动权力,因为“增加可见性是获得更多机会、公平和权力的关键”[5]。与此同时,自主制作并上传短视频,也使得家庭主妇的形象构建权从他者转移到了这一群体的自我手中,实现了形象的自我构建。
2.情感满足下建立与社会的联结
传统的家庭主妇的活动及社交通常都是以家庭生活及家庭关系为轴心展开,其辐射范围较小,与外部世界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因此常有家庭主妇在离开家庭,重返职场后的“掉队”“脱轨”现象,不少家庭主妇为此而感到焦虑。
短视频不仅为家庭主妇提供记录生活的平台,更是通过作品的评论、点赞等互动形式,扩大了家庭主妇的交流沟通范围,获得了与外部世界相联结的渠道。一方面,短视频为围裙网红提供了情感抒发的途径,满足她们对于自我情绪表达的诉求,成为她们在数字空间内自主选择的进行自我表达的替代性场所[6]。另一方面,围裙网红通过女性经验的分享,不用进行物理空间的移动,就能与其他主体产生联系,并且获得社会认同。同时,视频内容的对标性能够使分散化的妇女个体实现在网络空间的集结,以互动的方式实现共情赋权,给予围裙网红更大的可见性。
3.价值创造下实现内外部关系的平衡
围裙网红在创作短视频作品并收获粉丝的过程中,能够一定程度地平衡内外部关系。就内部关系而言,围裙网红在视频创作上收获的认可与成就感,能够构成家庭主妇在新媒体时代自我实现的一部分,平衡其因照顾家庭无法工作实现自我价值的矛盾。就外部关系而言,一方面,在家庭关系中,围裙网红在视频作品播放量和粉丝量不断增多的过程中,能够通过直播、电商和广告合作实现经济创收,从而实现由依附到独立的突围,平衡其家庭地位,以及获取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在社会关系中,围裙网红的作品通过传播,其能够收获网民通过点赞、评论、收藏等方式获得的正向反馈,反映其工作及付出在社会上认同与接受度的提高。同时,围裙网红在短视频中不断争取“出圈”,实现突破圈层的传播,也能够平衡以围裙网红为代表的家庭主妇在社会话语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三、短视频平台对围裙网红的反向负能
短视频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围裙网红为代表的家庭主妇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带来了经济收益。但与此同时,围裙网红短视频作品的持续创作与传播,也会为个人与该群体带来反向的“负能”。
1.内容重复下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加深
中国社会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父权制观念下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与社会结构分工,同时赋予了男性与女性不同的性别期待与性别分工。在这一结构中,女性往往被排斥在社会环境中实现价值创造,而是被置于家庭环境中,承担着生育后代、相夫教子、做家务等工作。
在新媒体时代,围裙网红因家庭劳动的视频而得到流量与关注,并实现经济创收。然而,数据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中,商业数字网络中的用户的内容生产最终都会走向商品化与增值化,被商品化的围裙网红的视频也难逃商业逻辑[7]。在流量、资本等驱使下,按照新媒体平台发展特性,围裙网红会聚焦同一主题来进行同类型视频创作,囿于一屋之内,不断地重复做家务、照看家庭等劳动。在场景固定、关系固定、行为固定的自我重复与外界反馈相互促进下,不断促进围裙网红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观念与分工在无意识中内化,其广为传播后,也会进一步强化现有社会性别分工与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在这一行为过程中,性别权力关系呈现隐匿性特征,难以察觉,最终导致围裙网红在看似自我拓展的空间内,强化了自我捆绑与束缚。
2.内容展演下个体情感与行为的割裂
美国学者唐·舒尔茨(Schulz)将媒介化具体为四个阶段:扩展(extension)、替代(substitution)、融合(a m a l g a m a t i o n)和适应(accommodation)。扩展即媒介技术延伸了人类沟通和传播的界限,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替代即媒介部分或完全取代了既往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制度,从而改变了它们的性质;融合即媒介使用被编织到日常生活的结构中,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适应即各类主体必须适应媒介逻辑。从微观视角来看,围裙网红的产生及爆红也遵循着这一媒介化的过程。原为家庭主妇的围裙网红,通过短视频技术延伸了其传播与沟通的限制,建立了与外部世界的勾连。其次,短视频的技术的介入,也改变了围裙网红做家务的性质,使其从家庭责任转向为个人事业。最后,短视频融入进围裙网红的日常生活,并驱使着她们迁就媒介逻辑,以实现效果最大化。
短视频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围裙网红的娱乐工具,更是生存工具,这要求围裙网红维持长期的内容生产以获得商业回报。在此情况下,短视频的创作不再是“记录”与客观的自我呈现,而倾向于进行迎合大众期待的自我展演,使得真实日常的记录向着模式化的“表演”转变。当这一逻辑渗透到围裙网红的日常生活中,会异化她们对现实场景与空间的真实感受与思考,代替而来的是思考如何在短视频画面中构建与展示,个体感知被带有极强目的性的思维方式所替代,从而割裂个体行为与个体情感。
3.内容传播下群体压迫的增强
短视频创作为围裙网红提供了“自由”与“弹性”的工作,赋予了她们在家庭与职业中的双重角色。然而,围裙网红的特殊定位并没有打破传统性别观念对“女主内”的性别期待,而是给她们带来了更多“碎片化”的责任与期待。在家庭中,围裙网红既要承载照顾家庭的期待,又要承载创造经济收入的期待,从单方面发展为双方面,这要求围裙网红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以实现两者的平衡。看似弹性的工作,实则表现为更彻底的剥削。在社会范围内,当内容传播之后,围裙网红则在社会中树立了一个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做自媒体的“超人形象”,人们对家庭主妇群体也就抱有更多的期待并且实行更强的压迫。
当家庭角色与职业角色都被安置在围裙网红身上时,工作与家庭间的责任便相互溢出。短视频创作的困难与不愉快会进入家庭交往,家庭内部的矛盾也会干扰围裙网红的创作。任何一方面的消极情绪都会对另一方面产生影响,围裙网红作为“责任主体”与中间人,更是担负了两者兼顾的责任,因此她们承担了更多的压力。短视频一方面为家庭主妇平衡家庭事务与经济创造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又成为了压迫的工具,让她们面临更加精致的压迫。
结语
短视频助力了围裙网红的诞生,并赋予了她们新的身份,改变了她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呈现着与其它职业网红所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的双重空间的重叠、家庭身份与职业身份的双重身份的重叠、以及家庭成员既是家人又是同事的双重关系的重叠。短视频平台一方面为围裙网红提供正向赋能,帮助她们提高了其劳动与价值的可见性,自主掌握着形象的构建权;为其提供了情感表达与沟通的渠道,建立了与社会的联结;围裙网红还能通过短视频实现经济创收,从而平衡其家庭关系、社会话语权力,以及实现自我认同。然而,围裙网红短视频内容的创作与传播,也为个体与该群体带来了反向负能,这表现在其视频中做家务等内容的不断重复下,易加深社会对该群体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当围裙网红的视频内容趋向于展演后,也会割裂个体的情感与行为;内容广为传播后,伴随着双重身份重叠而来的,是双重的责任与期待,最终会为个体与群体带来更强烈的压迫。
围裙网红的短视频实践已经体现了该群体的智慧与突破,其目前的困境主要在于父权制下社会对性别分工与性别刻板印象的结构性问题,使得围裙网红的短视频实践无法冲破藩篱,甚至在强化这一框架。如何打破这一传统框架,或许才是将“负能”转化为“赋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