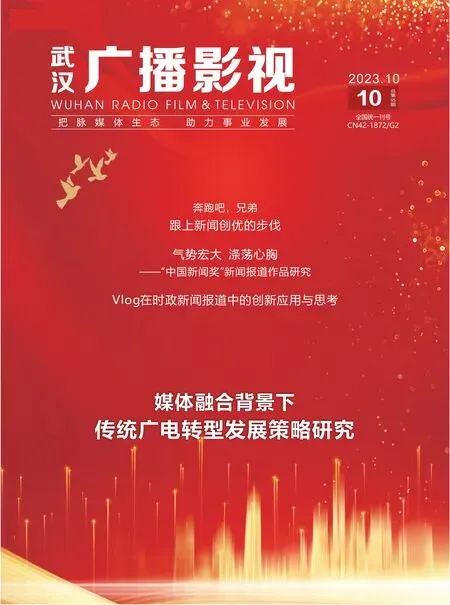使用与满足视域下,中国脱口秀类节目的创新模式及创新趋势研究
——以《脱口秀大会》第五季为例
张超灵
1960年,麦奎尔等人对20世纪40年代由贝雷尔森与赫佐格的广播“使用与满足”的研究重新进行了价值肯定,电视节目赋予受众的四种“满足点”可归纳为心绪转换、人际关系、自我认同与环境监测。《脱口秀大会》第五季结合时事热点,从生活百态中挖掘喜剧点,用轻喜剧的方式消弭生活中的苦与辣,一度成为饱受观众喜爱的节目类型。节目将幕后花絮、拍摄进程、拍摄片段等进行精准投放,符合受众使用与满足的各项需求。
脱口秀这类语言类节目起初源于美国,它的火热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满足美国受众在经济飞速增长时期对于发泄情绪、体悟反讽日常、寻找价值共鸣等使用需求的暴增。美国单口节目内容对于政客丑闻与日常事的花式捕捉,引发思想碰撞,直击内心。该类脱口秀一贯以话题深刻和言辞犀利著称,脱胎于其的中国《脱口秀大会》也通过轻松吐槽满足受众心绪转换需求;大谈交际窘境,带高带响话题热度,提供受众充分的日常谈资;演员不断袒露自我内心,呈现“日光之下再无新鲜事”的自我认同与圈际回归需求,且受众通过找到亚文化圈子,对外进行环境监测与判断,以达到自我安全的确定的使用需求。
一、《脱口秀大会》第五季——新媒体传播路径中的使用与满足
《脱口秀大会》作为网络综艺,在腾讯视频平台播出。首季由央视主持人、中传博导张绍刚担任主持人,统领节目流程,节目共十二期。当季还请到华裔脱口秀先锋黄西,所请嘉宾也集中在娱乐圈,如社会性争议较大的柳岩、名嘴华少、主持人杜海涛等;《中国有嘻哈》《中国好歌声》等热度节目的冠军或评委等。第一季前八期节目由三强PK赛和两队明星PK赛两个环节组成,后两期第二环节改为不快不吐。第二季起取消主持人的角色。五季节目紧紧追踪中国本土化特色,节目环节与模式不断推陈出新,建构受众对该类媒介的接触与印象。新媒体时代,受众在网络媒介的使用过程中不单单只是接受媒体传递的信息,如《脱口秀大会》第五季部分环节,设置加更、脱口秀小会等,更好揭露表演者的性格并方便受众进行人物性格分析统计。受众由此拥有了更多的空间对网络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重组,形成一种交互性的双向传播模式,更好地利用该节目满足人际交往需求。
第五季节目的脱口秀人员的组成也更为多元,不同兴趣的受众可通过信息检索等媒体技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建立多重亚文化圈层,提升自我认同感。脱口秀的内容多是针砭时弊,追赶潮流。对疫情的个体化观察,对就业、升学、考公,内卷等日常生活的观察使受众借助大众媒介获取夹杂各类真实感受的各种信息,一是满足了消除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等发展与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有种找到“嘴替”的情绪抒发感。
二、使用与满足理论在《脱口秀大会》创新发展过程中的运用
相对于线下脱口秀,互联网自制线上脱口秀话题框定得较死,这对演员的考量要求更高。在使用与满足视域下,受众积极地参与到各种可能参与的交流平台上,自主地寻求某种媒体满足自己;媒介也巧用受众的需求,承接“媒介—受众—媒体—传播者”的链环式发展。
1.社交需求:价值观的表述与人际间的沟通
《脱口秀大会》选择了在腾讯视频这个大的网络平台播出,拥有大批网民用户的同时,弹幕的高度互动性使得全季节目都在被高热度地讨论,另设微博超话来进行话题预热与余温既存。
节目从第五季开始变为十期,每一期还分为两小期,中间的环节更多展现了脱口秀演员的后台行为:如创作灵感的寻找。不论是嘉宾的邀请,还是脱口秀演员的学历层次都在提高。请来的嘉宾包括文学作家刘震云,演员中呼兰的金融背景、建国的历史背景、鸟鸟的北大背景、985研究生徐志胜、上交大庞博、吉大赵晓慧等。正向价值观的输出,给受众人际关系带来了更多可讨论的话题。节目相对于其他语言类节目更加大胆,更具突破性。主讲人结合其婚姻经验、性格品质、外形经济条件等打造个人特色,讲属于自己的段子,如:睡在上下铺的夫妻、脱口秀界鹿晗——绝美徐志胜。节目收获了自己独特的受众群体,并充分满足了受众的社交需求。
2.娱乐需求:本土化发展,为受众的心绪转换提供可能
节目最初是借鉴美国的脱口秀常用设备——连线麦,后演员可根据自我需求进行配置,如较多掺杂非语言技巧,采用戏拟化的表演而增添喜剧效果的豆豆,通常使用的都是挂耳麦,有效解放双手的同时,也体现脱口秀中国化特色。在《脱口秀大会》第五季中,不难发现相对于美国脱口秀惯用的中镜头,经本土化改良的脱口秀经常会出现镜头的跳转与直接摆摄,演员、观众的个人特写镜头较多。
虽然相较于美国脱口秀节目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国脱口秀的话题要收敛很多,但相对于国内其他流程固定、以主持人带嘉宾之类的纯游戏纯娱乐类节目,《脱口秀大会》第五季体现的社会面更广,更加注重深挖底层人民的心声;涉及的话题轻松,较易形成感情链接,引人发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过气作者李诞,没上大学的9 5后青年池子,历史科普王建国等等。这种略带标签化的人物特征强化了个人形象,加深了嘉宾的可辨识度。根据《中国网络新媒体用户研究报告》,新媒体用户分为五类:乐观向上的新一代,勇于创新的青年型、追求潮流的小资人群、拥有财富的实力人群、传统的中产阶级。节目在把握“大众化”的基础上体现“分众化”倾向。第五季其中一期节目,“谁都可以上台讲五分钟的脱口秀”和“像个大妈”的说法激励黄大妈上了台,黄大妈五十多岁,她以自己的经验和勇气,大声反驳“大妈打得都比他(男篮)好”,大声喊出:“既然谁都能讲,我就能!”这种轻松欢乐的语言,让各种身份的受众都能从中体味到快乐,放空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心绪得到了很好的转化。
3.精神需求和心理需求:与节目形成情感链接
脱口秀往往通过一种冒犯的形式展现,结合时事热点,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引发深思。演员庞博用一句“柴米油盐酱醋茶,但凡凑齐三样,我都吃上茶叶蛋了。”表达出自己在居家封控时期对物资短缺的担心和忧虑。当时上海处于封控时期,这类吐槽的出现让同在相似社会背景下的受众,能够更好地理解与接纳庞博的话语,在情绪上得到极大的安慰。鸟鸟吐槽自己下厨房如同下地狱,一个29岁处女座社恐独居女的普遍性恐慌,气若游丝地承认自己在生活中没啥存在感,这种表达较易引起观众共鸣,让观众发现原来不只自己这么想,也有其他人这么看,这种安全感让他们在节目中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支持。
4.信息需求:了解娱乐行业,甚至延伸至各行业的生存现状,为后疫情时代就业难问题提供某种解决方案
脱口秀很多演员都不是专职演员,包括一些线下的开放麦也是这样。受众对于脱口秀是不是即兴发挥、如何撰稿、如何成功进行一场演出等都充满了好奇。《脱口秀大会》第五季很好地关注到受众的信息需求,利用技术实现超文本叙事,打破节目完整的内容链,将幕后花絮、拍摄进程、拍摄片段等进行精准投放,并与受众实时互动,利用用户数据反馈,达到使用与满足有效促进方式。通过采纳多方意见,投入到内容创意的研发,形成完备的节目创作系统。巧妙地回应了受众对于脱口秀最终形态形成过程的好奇。脱口秀演员来自于五湖四海,千行各业,坐下来好好“唠”一下,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失爆下受众的焦虑与无措。第五季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嘉宾有邀请刘震云老师,敏感的内心和良好的语言功底是作家独有的,他们来做嘉宾,体现节目新颖性、多面性的同时,也体现了节目内容的抗打性与受欢迎程度之高。刘老师通过文学的角度,对脱口秀演员文本的拆解满足了受众对娱乐喜剧后台工作更深的信息需求。
三、使用与满足视域下,《脱口秀大会》的改进策略
1.不断更新节目形式,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
第五季中老人输给新人,新人成为爆梗王,淘汰选手被复活的现象屡屡出现。通过观看这个节目,观众可以感觉到快乐和放松。吐槽那些令人烦闷却较难改变的人与事,用“说”来排遣压力,用观看娱乐节目这种成本较低的放松方式来调整心绪,应该是节目组可以此为荣的发展使命。“人类社会文化传递的复制因子”脱口秀演员的语言文本,被《自私的基因》书中所提出的迷因理论所论证,他们通过不断地分享和改造自己的话语体系,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探讨和拓展他们的梗,从而形成了一种持续性的群体狂欢,使得节目和脱口秀演员都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宇宙的尽头是铁岭”等潮语的热潮激发了网民的多元化改造和传播,“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宇宙的尽头是直播带货”等论述得以窥见。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复制因子变得更加普遍,它们像空气一样弥漫在媒体传播环境中,让更多的观众沉浸其中,使得节目热度持续升温。
2.巧用“病毒式”传播,互动性增强,更好满足受众的社交需求
有效增加节目在“微平台”的影响力,网络平台与传统平台的联动,也进一步把节目推向火热。常上春晚的大张伟携脱口秀大王王勉上春晚,一时引起了较高的网络热度;第五季节目与台下观众的互动增多,如肉食动物扔兔子;故事类型掺杂的个人事件或个人回应更多,如徐志胜讲述自己看到微博下面的评论都是帅、绝美,难掩好奇,去看其他男明星微博下的评论之后的个人感受;杨笠戏谑自己都被夸得以为自己美若天仙了等。
《脱口秀大会》第五季加入脱口秀小会这一环节,演员与观众的距离进一步拉近。该环节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使得受众在这里体验到比弹幕互动更加真实有效的情感交流体验,这也是节目持续受到欢迎的一大重要原因。演员们聚集在一起,就本期节目内容和演员表现展开激烈的讨论,并积极回应观众的提问。
通过内容的区隔性,有效的持续用户的长效性,构成成功的仪式。柯林斯指出,一个成功的仪式不仅能够让参与者更好地理解彼此,还能够促进沟通的流畅,从而更好地实现信息的及时、精准发布。第四季中,庞博的最后一场演出以“自我介绍”为主题,将自己四季节目以来的演出文本连接起来;周奇墨也用模仿的艺术,将整季节目参赛选手的表演加以融合,通过其高超的模仿技巧和对表演者细心的研究,让老观众们轻轻松松解密,会心一笑,提高对节目的忠诚度。
3.勇担传播社会正能量的责任与义务,巧妙满足受众自我确认及环境监测的需求
李雪琴的《抑郁——不被看到的阴霾》,杨笠的《女权——不急,还未矫枉过正》,颜怡颜悦的《审美——锁骨放硬币的意义》,呼兰的《中年危机》,王勉的《追星少女之歌》以及张博洋的《键盘侠》等,这些短小精悍的故事,深刻地揭示社会问题,充满深刻的现实感,但也存在部分小众文化难以引起大众共鸣的问题,容易挑起性别对立。
4.内容创新化、分众化,满足信息需求
新晋脱口秀演员鸟鸟一反女生就该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惯常视角,她把下地狱和下厨房紧密结合,以“下”为动词,以“别人都会一些拿手菜,而我只会烫手菜和切手菜”为段子,激发出观众的强烈反响,从而满足了观众表达自己观点以及获取信息的双重需求。颜怡颜悦的“锁骨放硬币挑战”以其持女性主义观点的言论,揭示了女性的容貌焦虑现象,这些具有分众化、个人化的段子,让许多受众感觉自己被认可。
结语
笑点密、互动强、信息足、定位准等特点成就了“中国年轻态喜剧开拓者”《脱口秀大会》的第五季节目。一个节目的成功也离不开成功的营销策略,脱口秀演员将其中的赞助广告随着“包袱”一个个抖出来,也是节目新颖之处,观众被逗笑之余,更好地理解广告内容,变相地满足了受众心绪转换的需求。节目组对使用与满足的巧用一定程度上给受众赋权,这种媒介使用具有某种“能动性”,强调了受众需求对传播效果的制约性,由此看来,对受众娱乐、信息、情感和精神层面等需求的持续满足,不断变换节目设计、内容形式和广告投放等各类形式,才是文化语言节目取得长足进步的永久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