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恋我曾两度任职的《世纪风采》
陶炳才
我曾两度供职在《世纪风采》杂志社,那些往事至今让人难以释怀。
我第一次在《世纪风采》任职副主编,是1998 年3 月至2003年9 月,共5 年半时间。我是由省委宣传部调入党史办进杂志社的。正赶上世纪之交,中共百年历史的探秘与追寻成了热门话题,而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词的《世纪风采》杂志则正大放光彩!
一进杂志社正赶上第一次改革,只剩下3 个半人,在编的一个执行主编、一个副主编、一个编务,一个美工编辑是外聘的。杂志社是人少而精,在省委党史工办机关上上下下支持和帮助下,创造了最辉煌的业绩,成为全国知名党史刊物,它的文章被各大报大刊转载,发行也推广至国内外(有港台等地定价)。
翻开往期杂志,最先让我感到骄傲的是,一开始有许多期杂志每篇文章的最后“责任编辑”一栏,都是我的大名。当然,这得益于我和执行主编结伴到北京中直机关去约稿组稿。晚上11 点多钟由南京乘66 次卧铺火车,第二天下午二三点钟进北京站,然后直接去中南海机关。那时中直机关许多处长局长们手中有独家党史资料,他们也期望与我们合作。返程车票比较难买,但中直机关的同志都能设法帮助解决,也很方便。1998 年第8、9 期合刊,我们独家首先公开发表了江泽民的回忆文章《忆厉恩虞同志》,后被新华社转发,过后我们还给江泽民办公室汇去了几百元的稿费。这是很骄傲的事情。
世纪之交的《世纪风采》,它的品牌栏目“伟人剪影”“名人春秋”“纪 实 之 窗”“铁 马 金 戈”“世 纪回眸”“警世钟”等,刊登了许多名人名篇,均被《作家文摘》《周末》等大量转载。

《世纪风采》创刊新闻发布会
杂志的发行是自办发行,加上极少数量的邮局代发,到催款要账时就困难了。往往每年底至年关,我便又前往苏北发行欠款大户催款要账。一开始是个人乘长途车到县市,再乘小三轮或平板车到客户单位;后来杂志社配有小车了,便与驾驶员开车前往。寒冬腊月的,遇上风雪交加也是常有的事情,好在客户单位多是县市区的党史部门同志,他们总能设法凑集些钱给我,少则几百几千元,多则上万元。每当我怀揣着收到的款项,坐在颠簸的长途车上时,心境也是收获满满的。
那时机关也实行自创福利,党史办机关没有什么好创收的,杂志的邮寄分发便组织全机关同志集体劳动创收。每月初是杂志邮寄分发的日子,那一天全体同志集中在印刷厂车间里,工办领导也亲自参加其中,装信封的,贴标签的,打包的,核对检查的,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中午食堂送来了盒饭,大家在谈笑中结束了这样的集体劳动。好让人留恋!
杂志的广告是外包给公司的,我们负责把关稿件的内容与质量。有时也协助广告发行员前往客户拉赞助。第一年底杂志社就有了赢余,发行数量也逐年增加到近4 万份,名列全国党史期刊前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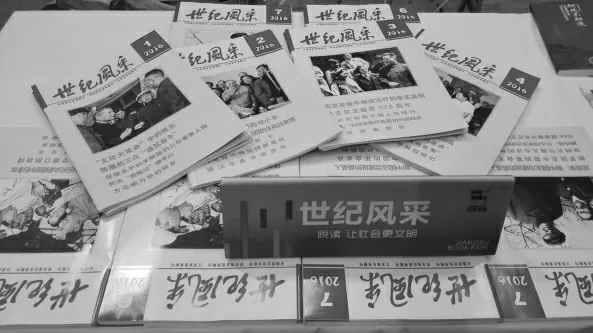
《世纪风采》参加江苏省第六届扬州书展
在跨世纪之交的那些年份,《世纪风采》被全国党史系统多次评选为优秀期刊,还在会议上作经验介绍;也被华东六省市党史系统及本省新闻系统多次评为优秀期刊。
我又回到《世纪风采》杂志社工作是2011 年9 月至2015 年4月,也有3 年半时间,任执行社长、执行主编(同时我还仍然担任着资料信息处处长一职)。我是来救急的,杂志社面临着管办分开、企业化管理的深化改革。
杂志社是差额拨款的事业编制,财政每年20 万的补贴,根本不够杂志的编、印、发及人员开支等。好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杂志社扭亏为赢了,账面上也有了一二百万的结余。这仍是一个好的基础。
我接手杂志社,编辑、发行、广告等都要管,而且主持工作,比之前的责任更重更大了。也好在我熟门熟路,联络各方专家学者,拉上关系,很快就恢复了杂志社的正常运转。
先说编辑这一块。一本期刊的优与劣、好与坏,关键是主编的思路与眼界,能否抓住热点、难点、亮点组稿编稿。我围绕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契合历史人物的生平纪念节庆,组织专题、专栏或连载,受到读者欢迎;特别是文章强调首发、独家,效果极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的推荐文章,有时几乎是本刊一出刊,那边就全部推介,甚至连本刊的“警示钟”栏目的文章,也罗列在其中。这一切又让我更加信心百倍。
当然,理顺杂志社内部的运作制度和调动人员的积极性,也是必须要加强的。三校三审制度、编前会制度、岗位责任制度等等进一步得到确立和强调。也恢复了杂志社的一个好传统:终校前外聘一位专家参与审稿,抓住“临门一脚”前的守护,在刊物质量把关上加了一道“保险”,保证了不出政治事故,差错率也严格控制在万分之一以下。这个经验曾被省新闻出版局期刊处表扬和推介。
千禧之年已过,世纪的话题也淡了下来,历史的兴趣也转移了许多,期刊更面临着网络新媒体的冲击,组稿编稿及发行、广告都困难重重。加上杂志社还在转移主办单位的联络之中,人心浮动。
我是在和会计一同前往属地税务局办理完发行征订税票据的手续后,回到办公室,被通知参加讨论杂志社去留的主任办公会议的。在那个会议上,我提出了辞去杂志社工作的要求。这样,我又离开了世纪风采杂志社,这个让我终生流连忘返、难以忘怀的职场。我离开杂志的那一年,仍然为杂志社特别撰写了纪念刘少奇的专稿《刘少奇与新中国国家机构的创建》和《刘少奇与“三反”“五反”运动》,后被人民网“党史频道”转载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