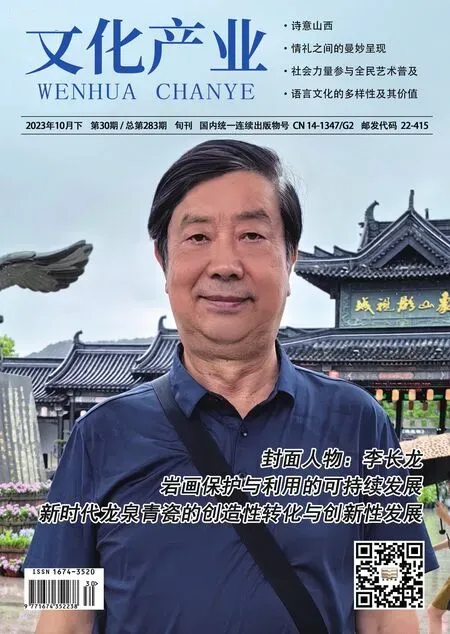南北朝碑额志盖的书法风格流变
◎夏祖晗
■南北朝碑额志盖的发展
已发现的秦代碑石中尚未有带额的例子,所以目前学界认为碑额从汉代开始出现,在东汉时期走向成熟。汉代盛行厚葬,而于墓前立碑是厚葬的基本制式之一。在耗费巨大的财力与人力的情况下,汉代碑刻的制作技艺愈加精湛,碑额装饰雕刻精美,碑文规整有序。而后,碑刻除了作为墓碑之外,也开始有歌功颂德的功德碑出现。至曹魏时期,战乱不断,社会动荡频繁,自汉代沿袭的厚葬风气被魏武帝所终止。《宋书·礼志二》:“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由于严格的禁碑令,氏族豪强都不敢立碑,只得把墓碑做得很小,下部空两三字的位置不刻,以便采用如碑直立的方式,放在墓室内。此时墓志的形制较接近立碑,仍带有尖首、圆首、螭首等类似构造,是地面立碑的缩影。两晋时期受禁碑影响较大,这种仿照碑所造的墓志在两晋时期仍然十分常见。
至南朝时期,墓志已经逐渐演变为水平放置的方形结构。到了元魏时期,墓志基本以方形为主,水平放在墓内;形制也由碑额碑身一体变为完全分离的两部分——志石和志盖。志盖扣在志石之上,上刻有文字或图案花纹,其作用一是保护碑文,南朝时期有志盖的墓志较少,志石多为石灰岩质地,经过长时间的侵蚀,志文剥落严重;二是类似于碑额,起到指明墓志主人身份的作用。至此,墓志发展基本成熟,碑额志盖制式也基本定型。
■南北朝碑志通用文字与书体发展
南朝碑志文字
南朝禁碑十分严格,所以中原地区的南朝碑刻少之又少,后世没有对其进行保护,也没有进行拓印留下资料。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疆地区受禁碑影响较弱,尚存在私立碑志的情况,所以目前可见的少量南朝碑刻多位于西北诸省区。
南朝碑刻文字受东晋影响,多以八分书、楷书为主。东晋时期,楷书已经成为日常用字,但是楷书墓志并不多;到了南朝,碑刻用字大多开始用楷书,所以碑志文字由隶书向楷书转变的成熟阶段应该是在南朝时期。
北朝碑志文字
北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进入中原后开始了漫长的汉化过程,其中,接受并使用汉字是十分重要的一项活动。
北魏时期通行的识字书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急就章》。《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从少至老”表明了《急就章》学习者的年龄段跨度大,学习人数多,由此可见,《急就章》应是北魏时期传播度最广的识字课本。
北魏灭亡后,向南朝学习的风气渐渐消失,东魏、西魏没有沿袭北魏碑志雄强的书风,而是发扬了北魏楷书中的平正之风。如东魏《张瑾墓志》、西魏《和照墓志》。东魏书风区别于北魏,篆隶重新兴盛起来,这一点极大地影响了北齐的石刻碑志,北齐碑志逐渐表现出复古的倾向,隶书在北齐恢复了碑刻字体的主体地位。
北齐统治者信奉佛教,佛教活动频繁,北齐石刻书法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佛经刻石上。如《迦叶经碑》,笔画丰腴,波挑分明,结构平整;《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为大字摩崖刻经,笔画饱满圆浑,体势颇有张力,隐藏了隶书的波磔,体态凝重,有着雍容大度的气势。北齐的楷书也与隶书一样结体宽博大气,如安阳宝山《三十五佛名经》石刻。
■影响碑额志盖书法风格流变的宗教因素
宗教文化对中国书法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其拥有了新的书写文本和新的书写面貌,同时也将书法进行了另一个层面的精神升华。书法本身的传承性和实用性使其在宗教文化背景下找到了新的价值,促进了新的书写风格和审美观形成。
佛教起源于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大部分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建都平城时期开凿了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开凿了龙门石窟,有大批外国僧人来到中国弘法,也有很多中国信徒去印度游学,南北朝时期佛教得以迅速发展。
南北朝时期,佛学文化广泛传播,书法文化自然而然地也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书法的功能性为佛教典籍提供了新的传播途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书体类型。南北朝佛教通过书法传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墨迹,也就是写经;二为石刻,包括摩崖刻经、造像记等。
南北朝时期写经墨迹较多,主要原因是在当时佛教盛行的背景下,从帝王官员到平民百姓都需要阅读和供奉经文,而在印刷术尚未发明之前,手抄是最为快速、便捷的方式,于是各大寺院和受佛教精神感染的信徒便开始抄写经书。因为抄写经书在佛教精神中被认为是一件虔诚的、功德无量的事,所以后来抄写经书的佛教徒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很多文化水平不高、以抄写经书为生的抄手。这种广泛的、群体性的行为使书法与佛教的关系更加密切,参与佛教书法活动的群体十分活跃。
同时期的书法风格对写经书法风格也有一定影响。因为需要手抄的经书数量极大,所以寺院培养了一批专门抄写经书的僧人。在敦煌发现的南北朝写经中,就有多件由同一个僧人所写的写经作品。这些僧人在正式进行经书抄写前,需要临摹当朝或前人的经典作品进行书写练习,所以南北朝时期的写经书法技法精熟、体态稳健、细腻灵动,具有极高的艺术性。
佛教石刻也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南北朝时期以北齐最盛,北齐开国皇帝高洋便是十分虔诚的佛教徒,他以都城邺城为中心开展了众多佛教刻石活动。
造像记在南北朝时期发展迅速,数量也相当惊人,大量雕刻佛教造像体现出了信徒对佛教的虔诚与热情。造像记的题铭风格多样,具有代表性的有洛阳龙门石窟《龙门二十品》(十九品在古阳洞,一品在慈香窟),造像者多为贵族官员或高僧,出于虔诚的祈福修德心理,造像与题记的刻写较为精致,其字体为北魏盛行的“洛阳体”,右上方倾斜的趋势明显,带有波磔,方入方出,有很强的刀刻感,此阶段的楷书尚保留了一些隶书的用笔和结体习惯,整体结构茂密。《龙门二十品》造像记是十分典型的北魏“魏碑”体,虽然多有二十品,但是并不是千人一面,其在“魏碑”笔法的约束之下各有特点。同时期的碑额志盖楷书也体现出这一特点,虽然面貌不同,但是通过观察其笔法与刀法,仍可大致判断出其年代。
刻经摩崖也是南北朝佛教刻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北齐摩崖比较有代表性。北齐的摩崖刻经者多为僧尼,其出发点和手写抄经是相同的,多出自对佛教的虔诚。将经籍刻写于石壁之上永久留存,在积累功德的同时,辛苦的刻石劳动也是一种身体上的修行和磨炼。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以北齐僧人为主力进行的大量造像刻经活动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除了北齐官方对佛教的支持外,北朝的两次灭佛事件也是促使北齐大量刻石的原因之一。
两次灭佛事件的发生均是因为政治与思想文化产生了冲突。北魏真君五年(444),魏太武帝推行政策限制佛教,勒令王公贵族至平民庶人一律禁止私养沙门。后魏太武帝出兵亲征镇压杏城(今陕西黄陵)起义,在一处寺院中发现兵器,于是下诏大规模进行灭佛。后文成帝即位,恢复了佛教的地位。北周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令灭佛,《北史·周本纪》记载了开展“灭佛”活动的诏书:“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周武帝的灭佛手段相当强硬,佛教几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近遭建德周武灭时,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圣教灵迹,削地靡遗。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凡经十年,不识三宝。当此之时,即是法末。”由此可以看出北周在经历了一系列毁佛运动之后,佛教圣地化为民宅,佛教圣物荡然无存,僧侣被迫还俗或远走他方。这一消息传播到北齐后引起了佛教信徒的不安,北齐武平三年(572)刻写的《唐邕写经碑》中写明了北齐大量刻经的原因:“眷言法宝,是所归依,以为,缣湘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北周灭佛运动使北齐僧人感受到了威胁,其便采用刻经的方式保护佛教典籍免受焚毁之灾。
北齐摩崖刻经大多以平正的结体为主,笔画挺拔有力,结字松散,多取横势。风格质朴天然,受北齐复古思想的影响。刻经所选用的书体大多为隶书,小字刻经大小在方寸左右,风格承接魏晋,大字则堪称是隶书史上最为壮观的铭刻书迹。山东泰安《泰山经石峪金刚经》(见下图)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佛经摩崖,面积达2064平方米,单字字径约为50厘米,其字体态卓然实相,气魄宏大,体势开张,有古佛端坐质感。

图 北齐《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实景(图片来源于网络)
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与书法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就碑额志盖的文字发展来说,佛教写经影响了其楷书额盖和隶书额盖的书体风格变化。楷书志盖多集中在北魏与东西魏时期,这一阶段的石刻皆受到“写经体”“洛阳体”的影响,反映于志盖之上的便是“斜划紧结”的“魏碑”体。隶书碑额多出现于北齐北周时期,隶书摩崖大气宽博的风格也直接影响了隶书碑额的刻写。
南北朝道教在东汉道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成为官方承认的正统宗教,道教通过各种途径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如音乐、书画、文学作品等,同时也发展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
在道教文化中,与书法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道符文化。道符是道教十分重要的信仰工具,其面貌与书法有一定相似之处。陶弘景《真诰·卷一》:“云篆明光之章,今所见神灵符书之字是也。”此处所说的“神灵符书之字”所使用的是一种叫作“云篆”的文字,此云篆“以为顺形梵书……乃为六十四种之书也。遂播之于三十六天十方上下也”。云篆有“六十四种”,这与南朝杂体的多变性有相似之处。
唐代韦续《墨薮·五十六种书》:“因卿云作云书,黄帝时也。”将“云书”列为第四,包括在杂体中。
道教符字与杂体书法的相似之处在于其都来源于自然物象,虽然在造型上极为相似,但是其并不属于同一种类型。道教画符包括多种符字和多个图案,按照一定程式进行组合,需要按照顺序准确、连续书写,最终各种道教元素有机组合在一起形成一道符。从符字的功能与属性来看,应将其理解为具有特定意义的道教图像。在非道教人士看来,符字并无多大价值。而杂体则依托文字造型将物象的标志性图案作为装饰,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不仅仅是道教,文字在诸多宗教文化中都具有特别的力量。古代人非常相信文字、图像所具有的魔力,也就是说,凡是可以写出、绘出的事物,在宗教仪式的转化之下,都可以成为真实存在或另一个世界中的事物。在道教中兴的南北朝时期,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王公贵族的丧葬思想,他们向往在死后可以进入超自然的神仙世界,相信某种道教的符字可以作为他们灵魂的指引。志文使用楷书不仅是为了记功宣德,还是北朝一直以来的习惯,故不使用符字;而志盖多用篆书,篆书富有象性意味,与符字较为相似,可以起到代替符字的作用。但是因为志盖的根本功能是辩名,所以不能直接使用符字,故志盖之上使用的是与道家符字相似的南朝杂体。道教符字在从“天书”到“俗字”的变化过程中,与其形态最为接近的就是篆书。篆书由于年代久远,被认为是更接近神圣远古时代的文字,道教符字的生产和书写也大多以篆书为蓝本。墓志盖作为墓志文化的一部分,与道家符字一样,是与另一个世界沟通的工具,因此志盖篆书的写法不可避免地受到道教符字的影响,以保证其形式上的神圣性。
通过对南北朝碑额志盖书法的研究,可以发现书法在依附于碑额志盖所刻写的文字上时带有微妙的象征意义,并且具有一定的符号功能,这与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功能相合。文字在创造初期便带有一定的宗教意蕴,南北朝碑额志盖选择使用古老的文字进行刻写,既照顾到了实用功能,又在时代审美风尚的影响下赋予了书法装饰性与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