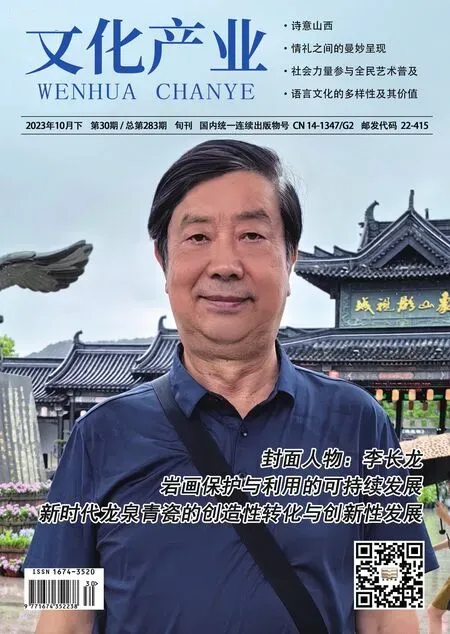情礼之间的曼妙呈现
◎白 杰

森田芳光的《其后》和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在风格与内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可归为文学改编行列,前者改编自夏目漱石的同名小说,后者的灵感来源为刘以鬯的小说《对倒》。一般来说,以对原著的忠实程度为划分依据,电影改编大概分为忠实改编、无修饰改编、松散改编三种。森田芳光对夏目漱石的小说改编忠于原著,王家卫对《对倒》的改编则是借用刘以鬯原作结构进行新的故事拓展。不过,他们都抓住了小说的精髓,将其灵魂融于影像之中,使电影因为有文学气质的支撑而韵味悠长。
■忠于原著,悠长的《其后》
《其后》是夏目漱石的作品,与《三四郎》和《门》共同组成“三部曲”。在这部小说中,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以隽永克制的文笔讲述了一个典型的日式爱情故事。1985年,森田芳光将这部创作于1909年的小说以影像的方式重新呈现出来,以现代的目光重新诠释了这个发生在明治时代的故事。该电影可以说是忠于原著进行改编,不过它把重点更多地放在了代助、三千代和平冈的情感纠葛,以及代助本人作为高等游民的落寞矛盾上,将小说中明治时代的社会动态和氛围放在了相对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简化使故事更像是在呈现一个人在自我道德和听从自然之间的抉择。
小说中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将主人公代助对社会的不满、对友情的执着、对爱情的执念,以及自我矛盾和忏悔等情绪以生动的文字描写了出来。当需要以影像的方式将这些心理活动表现出来时,不太高明的做法是加入旁白;关于此,森田芳光通过意识流的回忆影像,演员们的身姿、眼神,他们交流时的语言碰撞,以及特写、长镜头等镜头语言,使人物之间潜在的心灵沟通具象化。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电车镜头是对原著中情绪与心理活动的展现,它们出现时往往采用了超现实手法:电车中每个人都手持烟花,坐在其中的代助则不为所动;偌大的电车中除了司机之外,只有代助一位乘客,前方是橘黄色的夕阳;敞篷式电车上,一群和代助身着同样服装的男人望向天空,观赏巨大的月亮,代助依然坐在那里想着心事。这几个镜头表现了主人公孤独疏离、与世不相融的状态。
电影中的三千代与小说中的形象相比更加坚定和主动。在小说中,三千代的手上戴着两枚戒指,分别是平冈所赠的婚戒以及代助送给她的贺礼;而在电影中,三千代只戴了代助送的那枚珍珠戒指,表明她内心对自己的爱情归属有清楚的认知。在电影中,代助去看望三千代时,沉默的两人听着风铃声,情感在静默中越发强烈,此时两人都开始猛喝水;而风铃和喝水的情节并没有在原著中出现。在这一幕中,对着瓶口猛喝水的三千代不再像表面看上去那般柔弱、怯懦。另外,对结局的处理,电影和原著都给人留下了“未完待续”的感觉。在原著中,代助和家人摊牌后愤怒出走,打算去找一份工作;电影片尾则留下了代助站在风中落寞的身影,至于他未来何去何从,并未交待。笔者认为这种处理反而更能保持意境美。小说中的代助终于要走出房门,为了现实去面对那个他厌恶的世界,因此平添了一种追寻所爱的坚定决绝,同时也带着些许残酷感;电影则将远离现实的代助出世孤独的形象保持到最后,至于未来则是未知的,眼下他已融入那眼前的风景中。
■形式的借鉴,对倒的《花样年华》
关于《对倒》和《花样年华》,很多人在读过刘以鬯的《对倒》后,不免疑惑在电影中为何丝毫找不到周慕云和苏丽珍的身影。《对倒》和《花样年华》的确是两个毫不相关的故事,然而《花样年华》中有三处字幕摘自《对倒》,影片结尾更是特别感谢了刘以鬯先生,显然他对王家卫的影响非常大,当然这层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电影的结构形式和讲述方式上。王家卫形容《花样年华》和《对倒》的关系时曾说:对倒甚至可以是时间的交错,一本1972年发表的小说,一部2000年上映的电影,交错成一个1960年的故事。时间在此同样是个值得玩味的东西。
在刘以鬯的作品《酒徒》中,主人公就曾写过电影剧本,而《对倒》中男女主人公真正接触也是因为同看一场电影。在文学上,刘以鬯不仅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还受到了鲁迅、张爱玲、穆时英等人的启发。这使得刘以鬯在写小说时,常常给人一种电影感,所写的风景也像电影般淡入淡出。《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编剧罗伯-格里耶也曾影响过他,罗伯-格里耶认为电影与文学具有不同的属性,强调各自表现媒体的本性。例如,罗伯-格里耶认为电影画面的本性具有景框限制与实时性,同时,断续性要由镜头与镜头连接和组合,所以容易产生蒙太奇美学。在小说方面,罗伯-格里耶喜欢强调时间的连续性以及完全静态的动作。从这个方面来看,刘以鬯的小说《对倒》极有可能受到过他的影响,只是在内容主题上加入了香港的本土意识,表达了自己身处都市的所见所感。
《对倒》形式结构的灵感来自一枚对倒邮票,可以说是由视觉产生的意念。它有长篇和短篇两个版本,王家卫借鉴更多的是短篇中的那两条主线。在短篇小说中,主人公一个是颓唐老人淳于白,另一个则是年轻女孩亚杏,两人所处的时间是一致的,在同一段时间各自处在城市的一角,小说的描写就像电影中的蒙太奇一样,交叉剪辑两人的生活。这两个陌生人曾处于同一空间,看见过同一场车祸,遇到过同一个讨厌的男孩,甚至曾坐在彼此身旁看了同一部电影。在同一时空,两人曾擦肩而过,曾肩并肩,最终还是错过。这正像《花样年华》中的周慕云和苏丽珍一般,二人在同一天打听房子,同时搬家,先后路过同一个巷口拐角,有多次交集,两人走到一起,然而又终于错过。电影就像小说一样采取了一正一负的叙事结构。
论者陈智德曾分析刘以鬯的《对倒》,直接将淳于白作为刘以鬯的化身进行分析,并指出:“昔日中国以至东亚最先进的都会上海,现已(在当时而言)被香港盖过,迫使来自上海的淳于白重新思考香港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南来者本认为50年代香港不如内地,到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都市化及其发展已超越内地,南来者这时发觉,他们昔日所居的先进文化都会上海已落后,而本来被他们蔑视的香港已成为超越内地的先进都会,于是一种相对的观念便随故事产生:一种‘对倒’式的本土思考。”在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中,观众依然可以体会到这种对倒的“双城记忆”,潘迪华饰演的邻居太太一口上海话,收音机点唱的是周璇的《花样的年华》,张曼玉身着旗袍的曼妙身姿,那些里巷和石阶比起印象里的香港,更像是张爱玲和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五岁从上海随父母搬到香港的王家卫在电影中呈现了他所难忘的旧时光,这记忆中混合着两个历史命运相似的都市的景象。
■梅林茂音乐的连通性
克劳迪娅·戈尔卜曼曾说:“像语言可给人以充分的想象一样,音乐所设置的调性和调式同样能给观影者以文字和画面的想象。观影者从一部已经完成的电影中所获得的生活体验,比从还处在影片定位、剪辑、灯光、表演……和音乐等未完成状态的电影中所获得的要多得多。”电影配乐在电影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我们偶然听到某个旋律时,那些记忆中的片段会突然在脑海中浮现,这正是音乐与光影联系紧密的表现。梅林茂正是一位能够合理处理光影和声音的配乐大师。
王家卫在拍摄《花样年华》时,主题音乐选择了日本音乐家梅林茂的Yumeji'sTheme,这首曲子并不是原创,曾在铃木清顺的《梦二》中使用过。而梅林茂从摇滚乐队成员转型为配乐家正是从森田芳光的《其后》开始,而《其后》中的主题曲Prologue也被用到了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中作为“Love Theme”,只不过由钢琴弦乐转换为钢琴和大提琴合奏。
在《其后》中,梅林茂的音乐主要是钢琴和弦乐的组合,那如风铃般清脆的琴音,如梦似幻。电影开场时,序曲音乐响起,在一片漆黑中三千代的肖像出现,音乐则如静态的美人一般动人,令人心碎,像一场遥远的梦,这也奠定了整部电影痴迷、惘然、忧郁的基调,同时带着静谧、隐忍的情愫。钢琴独奏《再会》传达出了代助对三千代的愧疚和对爱情的执念。哀怨动人的琴声时时响起,两人之间难言的爱却无法表达出来。在影片中的当下爱情无法实现,所以快乐只能从过去寻找,而在整个电影配乐中,最欢快的便是华尔兹曲《回想》;随着该配乐出现的是充满魔幻感的镜头,其将过去的零星碎片组合起来,并与飘零的樱花相连接,使得影片比其他日式物哀典雅的电影多了些俏皮生动。序曲在片尾又一次响起,在诗意的镜头和音乐中,代助的生命又将去向何方,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花样年华》中由配乐家梅林茂作曲的Yumeji'sTheme则是作为影片的重要线索反复出现。该旋律在影片中共出现9次,每次出现都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第一次出现于麻将桌间,周慕云和苏丽珍辗转在室内外,当时二人只是不太熟悉的邻居,即使在同一空间内也像两条平行线一般,各自坐在爱人的身旁。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出现在狭窄的小巷中,两人逐渐由陌生到熟识,但依然缺乏交流。后来随着相处的逐渐增多,两人越走越近,在同样的旋律中研究武侠小说,各自处在自己空间的两人心事也是相连的。这种音乐结构的使用很显然受到了刘以鬯小说的影响,只有一墙之隔的周慕云和苏丽珍一起听着收音机播放的《花样的年华》,就像小说中不相识的淳于白和亚杏都在听姚苏蓉的歌一样。主旋律音乐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两人坦露心意后不得不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之时。这首曲子就像电影的灵魂如梦般萦绕,充满撩拨和暧昧,却也在不同的场景和情愫下,蕴含着不同的情感指涉,展现了二人之间从陌生人之间的微妙,到感到暗流涌动的爱恋,再到分离时的心痛的情感变化。
《其后》和《花样年华》都使用了梅林茂的音乐,虽然这两部电影的配乐一个以清脆哀怨的钢琴声为主,另一个则是魂牵梦绕、充满情欲的提琴协奏曲,风格上并不相同,但毕竟出自一人之手,气质上也有相连相通之处。比如,我们在看毕赣的《路边野餐》时,当看到陈升骑着摩托车走在凯里的乡间路上时,有时会产生一种在看侯孝贤作品《南国再见,南国》的错觉,想来除了气候和景色相似之外,与两部电影的配乐都由林强完成有关。
■高等游民和武侠写手
不少人会将《其后》中的代助与《花样年华》里的周慕云进行比较,笔者认为,两个人的气质的确有些相似,都带着与世俗不太相容的天真感和文人气。代助是夏目漱石小说中典型的高等游民,高等游民是对日本明治时期至昭和初期大学毕业后未就业学生的称呼,他们以阅读为主要活动。当然要想成为这类人,自然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电影《其后》中有几场戏是代助针对自己不工作以及日本的社会现状与平冈进行讨论,关于此,代助称自己也进入社会,只是与平冈进入的社会不同,他对于不工作的解释是“到了这步田地还以一等国自居,这样受西洋压迫的国民,没有时间去想问题,所以干不出大事来,只知道想自己的事,想自己今天和眼前的事”。
《花样年华》中的周慕云是报馆编辑,和代助相比,他的生活要世俗得多,有工作且已经结婚,只是周慕云这个角色本身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刘以鬯先生的影子,而且又会写武侠小说,伏案写作的身影伴着手边烟雾的升腾,更带着些浪漫的文人气质,举手投足间儒雅、礼貌。周慕云同样也是孤独内敛的人,妻子和邻居出轨,以及在和苏丽珍分别后,内心苦闷却不能同喝酒的友人交谈,只能跑到寺庙在墙洞中将一切吐露出来。王家卫后来将刘以鬯的小说《酒徒》改编为《2046》,其中的男主人公仍由梁朝伟扮演,名字依然是周慕云,讲述他1966年从新加坡回到香港,忘掉过去,在2047房间开始了卖文生涯。被誉为“中国首部意识流长篇小说”的《酒徒》中的主人公也是靠写文为生,在梦与酒之间,从现实到梦幻,对整个社会和文学现状保持着批判的态度。这个角色多少带着些刘以鬯自己的影子,小说主人公的思索和疑惑也是作者的想法投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花样年华》中的周慕云就不再只是简单的公司职员,比起常人来,他的内心中有更多脱离现实的部分,而演员本身的魅力也为角色加分不少。
综上所述,《其后》和《花样年华》都是由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来,都讲述了“情和礼”之间的抉择。不论是共用的梅林茂配乐,还是整个故事走向,两部作品都带着哀伤、无奈的基调。而电影中的两位男主人公——高等游民和武侠小说写手,虽然平凡,却都有超越世俗、纯真浪漫的一面,也同样有电影导演和小说作家现实形象的投射,体现了创作者的自我追寻和定位。这两部电影拍摄于不同年代,且来自不同国家,却有很多相似之处,鉴于此,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寻找二者的共通性,不仅是对比较电影研究的探索,也将成为观众的一大乐趣。这正如戈达尔所说:“在银幕上看到的不是鲜活的,在观众和银幕之间发生的才是鲜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