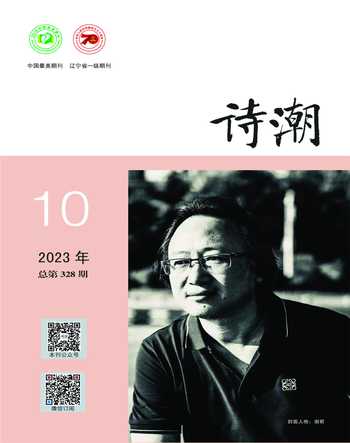AI、稀有金属或终极之诗
杨碧薇
2023年春节后,一夜之间,关于ChatGPT的新闻就霸占了我的微信朋友圈。人们用五味杂陈的口吻谈论着这个陌生的新事物,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此情此景,仿佛一盘散沙的人群中突然响起一阵钟声,人们四顾张望,却不知这声音从何而来,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错愕,感叹,轻松,惊喜,迷茫,失落,恐惧……无数感受交织在一起,在冲撞和推搡里迷途羔羊般慌张地辨认着敌友,千头万绪,竟不知要先抓哪一头。
无论如何,那原本只埋伏在想象中的技术“新怪物”再一次落地了;它用一种“降临”的姿态闯入了人类的生活,不容反驳。面对这名“闯入者”在朋友圈制造的信息霸权,我不禁想到前些年的索菲亚(Sophia)。同样是人工智能(AI),拥有人形外观的索菲亚也激起过不小的讨论,但那阵势与ChatGPT相比,只算是小巫见大巫。至于机器人小冰,那就更不用提了。
如今,堪堪又是数月光景,大量新闻迅速腐朽,湮没于信息的洪流中。但ChatGPT热潮仍未退去——至少,在我的生活里是。直到昨天,我身边还有人主动谈到它;在鲁院课堂上,也总有学员提出关于ChatGPT的问题。我想,之所以这个话题一直“赖”在我周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我从事的文学专业有关:身为文字工作者,我们可以对饭店里的送餐机器人熟视无睹,却无法绕过ChatGPT。这个擅长写作的技术新怪,为文字工作者带来的暴击恐怕还不是一两拳,它随时有可能取代我们的工作,剥夺我们的饭碗,消除我们的身份合法性;从外及内,令我们的存在变得可疑,让我们陷入“里外不是人”的非人境地。
所以,请刹住你的伤感,不必再哀悼人类历史上那些云淡风轻的岁月了——如果真有的话,它们也早都是镜花水月。当ChatGPT势不可挡地临到眼前,我们唯一的选项就是正视它,正视技术暴力笼罩下的生存现实。创作如是,批评亦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代,脱离了科技发展的创作和批评是无效的。这并不是说一定得写科技题材,而是意味着在写作中,科技理应成为我们思维的底盘,因为它不只关涉写作伦理,还关涉人的伦理,乃至全人类的文明。
以科技为镜,纠缠着汉语新诗的一些问题或可厘清。作为一种极富先锋精神的文体,新诗始终坚持探索与实验,因而在其百年历程中,难免伴随这样那样的争议。一个最常见亦最根本的问题即什么是诗。在失去了古典汉诗便利的形式依傍后,自由体给了新诗巨大的发挥空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诗的本质性显现。尤其是在偏向先锋的新诗里,对诗性的指认变得困难,而诗性自身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漂移和裂变。在这样的情形下,李南的诗就尤显珍贵。当人工智能足以替人类完成海量的工作——包括出色的写作时,当新诗的探索花样迭出、新诗现场纷乱而又松散时,李南的诗却具有伫立不变的形象,在众声嘈杂中默默地生长出不可替代性,宛如某类稀有金属,蕴藉着她自身的声音、温度与灵魂。这些诗用灼灼慧眼见证着瞬息万变的时代和我们所寄居的尘世,用明澈慧心翻越现实的山丘,超越词与物的界限,在不懈的精神求索中一路朝向永恒。
稀有金属的特征,首先体现在“常量”上。所谓“常量”,即文学中恒久的品质。人性、情怀、信仰、存在、生命、爱与死……以及与此相连的感动力,由此激发的升华的力量,都属于文学的常量。任形式万变,这些常量始终雄踞于文学的核心;具体到诗歌里,就是诗性。在李南诗中,常量的比重显然大于变量(形式);可以说,她的写作一直更靠近常量而非变量。例如,《想青海》与乡愁有关,又不只是简单的乡愁,还包含着普遍的文学原乡意识;《中年以后》和《生日有感》都是从个人体验出发,谈人生感悟。对常量的坚持,塑造了李南的诗歌面貌,凸显了她的诗人主体形象,更把她的诗与那种技术中心主义写作区分开来。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见证了新诗中的技术演变,却难得地对此保持警惕。当80年代的抒情声调大范围撤退后,新诗的语言转向便以加速度推进,现代汉语的潜力被大大激活,新诗的面貌被进一步改造。在今天,当两首截然不同的诗匿名同台时,通常情况下,有经验的诗歌读者能一眼看出,哪一首是出自60后手下,哪一首又是出自90甚至00后学院诗人笔下。但技术演变也带来一个问题:过度的修辞迷恋与技术迷恋。虽然新诗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实践场域,甚至是第一场域,虽然“诗歌高尚地拯救了语言”,但我们依然要追问:技术在诗里究竟应该占据怎样的位置?是否该取代常量(诗性),成为诗歌的第一性?如果不是,新诗又该如何统筹常量与技术,让二者各得其所,友好相处?
对此,李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很明显,她是技术中心主义的反对者。这个技术的旁观者,在诗里从不使用繁复的修辞,而是力求语言的简洁精准。“走进绵绵山脉,穿越茫茫沙漠/你会渐渐放下复仇的刀斧”(《一个人在镜中》)、“我们活着,结出苔藓/我们爱着,把一天当作一年”(《后疫情时代》),这般语言看似平淡,细赏细嚼,又静水流深,准确贴切,一个字也换不了。再如“我的苍老梦见了我的年轻”(《夜宿三坡镇》)、“我培植屈服的韧性/喂养心中的鹰”(《生日有感》),几乎所有的诗都在说明,李南深知花红柳绿不如洗尽铅华,打扮语言不如打磨语言,她要锻造的,是一种充满内力的语言。不少评论家都注意到李南诗歌的谦卑态度,但更多时候是在诗人主体与诗歌精神的层面上来谈论的。其实这两个层面的谦卑,都分毫无差地落地为语言的谦卑。
语言层面的谦卑极为可贵。扯虎皮拉大旗的语言是故作强悍的,而谦卑的语言才有真正的内力。对于语言,李南的身份定位不妨说是一名使徒,她在《我说汉语,我写汉字》里也表明了这一立场:“这样的命运,我心甘情愿/呵护你的纯正与圣洁——我不遗余力。”使徒身份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语言是高于诗人的存在,诗人必须敬重语言,而不是把自己凌驾于语言之上,做语言的霸主;其二,使徒身负灵魂的使命,面对技术的压迫,又须不卑不亢,而不是充当技术的傀儡。實际上,无论是小冰还是ChatGPT,其写作功能都是以语言的技术性为基石,通过吸收语言、连接语料库、构造语言模型和语言的整合与输出来完成对话与写作任务。而对诗性来说,语言只是一个壳;诗性就是技术无法拆解的那部分,是算法无法抵达的核心,它既神秘莫测,又真实地存在。即使ChatGPT能续写《红楼梦》,也未必能完美复现《红楼梦》那种深情又悲哀、热闹又寂冷的神韵,更难以抓住“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苍凉与虚无。李南的诗之所以可贵,正是因为扣紧了文学的常量,任何时候都坚定地捍卫诗性。在技术暴力下,任何文本都可能在语言/形式层面被AI模仿,甚至被模仿得惟妙惟肖;但剥开语言的外壳,李南的诗仍具有技术无法拆解、模仿的特质:性情、胸怀、灵魂……这样的诗,是诗人在岁月历练中的人格写照,“我有黑丝绸般体面的愤怒/有滴水穿石的耐心。/我有一个善意人/偶尔说谎时的迟疑。/我有悲哀,和它生下的一双儿女/一个叫忧伤,一个叫温暖”(《我有……》);其中有信仰与理想,“活在你的福荫下/我为美工作,不计报酬”(《我说汉语,我写汉字》);有内视与自省,“是因为我每天吃神赐的米和蔬菜/却不如一棵香蜂草更有用”(《羞愧》);有对世间万物的爱,“我只是爱着、战栗着/而说不出一句话来”(《如果我路过春天》)……这些诗铿锵地回答了“什么是诗”或“诗是什么”的问题——无法被技术取代的诗才是诗。
在捍衛常量之余,李南的诗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品质,一是真实性,二是公共性,都可以沿着上文的思路来分析。先说真实性。她的诗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因为其底色是情感真实。“对辜负过的人,犯过的错/说一声‘对不起/感觉是那么好”(《那么好》)……这样的诗句源于自身经验,诗人在写作时投注了真情实感,诗歌感染力自然排闼而至。反观AI写作,就算能批量生产精彩的文本,本质上也只是“仿真”而非“真”。
再来说公共性。与那种极度个人化的表达不同,李南的诗始终具有广阔的公共性背景,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诚恳的理解渠道。这是一种“他者”的视角,更是一种观照他人的能力。在新诗里,个体性与语言技术就像一对冤家,有时互相成就,有时又彼此伤害。前一种情况自然是锦上添花;后一种情况,则让新诗陷入无效的晦涩,沦为能指空转中的小我封闭装置。此谓相爱相杀也。因此,新诗里的个体性要得到真正的释放与张扬,就应该具有反思技术的能力,要将其合理利用,而非被技术绑起来,被技术牵着鼻子走。李南有一首广为称道的《下槐镇的一天》,就是合理利用技术来传达公共性体验的典范。这首诗在外视角的速写中抓住了一些能唤醒共属经验的画面,这,就是公共性的表达。在诗的结尾,诗人并没有进行虚假的总结,没有刻意地拔高声音,也没有矫情地降低声音,而是用平静的语调客观地陈述:“平山下槐镇,坐落在湖泊与矮山之间/对于它/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这一陈述从个人视角出发,经真实性而抵达某种普遍性,同样能唤起人们的共同经验。
正如资本的本质是无尽的逐利,人类对科技的开发也不会停下脚步。随着技术的加速剧变,技术焦虑会成为人类生存的常态。遥想当年,摄影和电影的诞生都给人类带来了技术焦虑。摄影的出现令绘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新浪潮之父”巴赞(André Bazin)就说过:“在达到形似效果方面,绘画只是一种较低级的技巧,一种复制手段的代用品。唯有摄影机镜头拍下的客体影像能够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而当卢米埃尔兄弟(Lumiere brothers)在巴黎咖啡馆的地下室放映《火车进站》时,从未受过电影洗礼的观众们吓得四处奔逃,魂飞魄散,以为下一秒银幕上的火车就要冲到眼前。现在,影像早已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人类又开始应对新一轮技术焦虑的挑战。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技术的演进越来越快,在为人类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焦虑、风险与更加不确定的未来。而诗歌作为人类璀璨星河中的老灵魂,依然负载着永恒价值,寄托着无限理想。没有谁敢打包票,这轮技术演进将把人类带向何方,但或可推想,如果接下来的变化将是翻天覆地的话,那么诗歌极有可能是最后被技术取代的事物之一。同样,在眼花缭乱的新诗文本中,经历了残酷的技术检验与淘汰,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诗,才是人类需要的“终极之诗”。从这个视野来看,李南的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眺望的方向,因而在技术层面谈论她的诗已没有太大意义。毕竟人工智能可以取代大量劳动力,而诗人始终为永恒工作,在能源匮乏的时代做稀有金属的守护者和传承人,正如李南所言,“在浩瀚的文字中留下,哪怕是一小行诗句/沉甸甸的——像金子”(《写诗》)。
2023年5月15日北京
——卡文迪什测定万有引力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