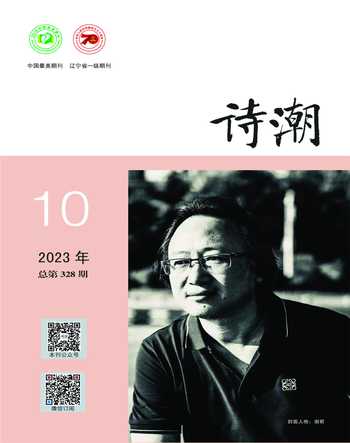穿行于大理石 [十一首]
谢君
折叠梯
记忆比拥有重要。一头鹅会把自己
放到它喜欢的池塘。我曾把
自己放在屋顶,因为砸了
别人家的水缸,当母亲
举着晾衣杆逼近。有助于
上升的事物是美丽的。
今天,当你赤足把自己
放上梯档,缓缓上升,
在空中抬着面孔,我想到了
爬树,少年时的快乐
可以从爬上一棵河边的
柳树开始。而你在寻找什么
我不在意,因为你的名字
已经被我藏在我生命中
最隐秘的柜子,你再也找不到。
浦阳镇
手里举着天线杆子,脖上挂着铁丝
我的父亲正爬往屋顶
修理电视天线。
我的母亲跑在院中拉紧了
从屋顶垂落的导线。
邻居们站着看着,在院外指挥
一会儿喊朝东,一会儿喊朝西。
旭日中,
神的喜悦是江上
运输船的平静行驶。
一只客船驶近小镇,
载来了香蕉菠萝,
码头上的喊声是——
“香蕉,香蕉!”“菠萝,菠萝!”
浦阳江
一条我家乡的河,随时可以
在水面放置三朵水花的河,
用三块石头。
在供销社屋顶下
在拖轮与驳船的震响中
我的父亲在江畔等待
货款像常春藤爬满房子。
而在民国,有条木帆船
在等着我的祖父回来,
并在夜半惶恐地查看
中国地图,用放大镜寻找
军阀们坑坑洼洼的喧闹。
他的兄弟,当张开嘴巴
大喊冲锋时一颗子弹
蹿入嘴巴。他的窗台上
总是停着两三个黄酒瓶子。
韶华宁静就像种一棵树
山峦如云,街市安静
小巷尽头,竹笋摊了一地
抽烟的人唯有抽烟的感觉
小镇唯有小镇的感觉
儿女婚嫁在青石板路上
缝纫机声的柔美时光
在隔壁家的二层阁楼
不知何时你已离去
斜阳下我们也曾漫步
也曾朗读《悲惨世界》
斜阳茫茫不可历数
江河安详,汽笛浪漫
韶华宁静就像种一棵树
诸暨红门
我的母亲不知道我们下错了站。
列车上,母亲问乘务员
到白门什么时候。
对方说马上下,
红门过去是白门。
过了红门,我们下火车,
发现是诸暨站。
站上的人说坐过头了,
红门过去是白门。
那一天中秋,月色宁静,一朵
云彩轻得好像随时准备前去
为《倩女幽魂3》试镜似的。
在往回走的路上,
饿不饿不记得了,
只记得一辆拖拉机
从对面驶来,相遇,车上满载
男女社员和他们摇摇晃晃的罗曼蒂克。
注:红门是浙赣铁路线上的一个火车小站,历史上叫白门,后改名红门。
罐子之家
作为一个物理量,它们在积累,
装满了母亲的房子,
又堆到敞露的后门廊。罐子上
搁着麦草扇,旧报纸,雨伞,
万年历,绿瓶子,以及一本我曾
通宵阅读的小说,关于一个
失踪的人或者说一桩悬而
未决的罪案,一把沉入桥底
淤泥之中的锈蚀匕首,210页。
一個充满罐子的家。罐子里
放了些什么只有罐子知道。
我不清楚,母亲也忘了。我的母亲
孤身一人,臀部广大如俄罗斯,
看她那个样子,艰难而深情地
拖动自己的两条长腿,也是
一个罐子,装满了会唱歌的大黄蜂。
公元五世纪
当我的妻子觉得自己不够漂亮时,我就出门了。
去见颜延之。他在烤鱼,汗流浃背,
手里举着刀刃。
每次去看他都在烤鱼,诵《北使洛》
我吃着烤鱼,吞下一碗酒。
酒不一定能读懂我,我一定可以读懂它。
除了一碗酒,还有什么好东西
能够出于这个时代?何况,
我对权贵又不太友好。就在上周四,
有一个无聊向我走来,
我马上掉头,旋转半圈。
即使给荀雍这样的好友写信,
写完后,下一秒就变得没意思了。
最大的悲剧是,
去年七月,南京朝圣返回,
在长江边的一家旅馆外,
我看到一只雨燕一路摇晃尘埃,
我感觉那就是我。
我迄今所获都是尘埃。
即使夏至清凉
我也懒得去见陶潜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不好。
不,从三十岁开始
就一直不好,不舒服了。
现在,我爱吃自己摘来的猕猴桃。
南朝又換了一个执政官。
它正在变成一个坏疽。
它谀言的制造大于长江流量。
我只有一个人去爬山,
爬到山顶我才能喊出我的悲伤。那些
我一觉醒来就得去死的日子越来越多,越来
越近。
我在萧绍平原上看见云
我的心,就是在那一天创造的
当你写在天上
写在你所去往的地方
你所到达的地方
当你安静地在
我打开房门时突然出现
安静地禀有我的春天
薄雪,农场,新修的马达
这很好,但是
有一天你掉下眼泪
浇在我的小镇,我的屋顶上
青海湖
没有人没有一段恋情,没有一段恋情与湖无关。
看到它的身影,你会想起某一时刻。
来自南方的游客正在和它合影
他们身着连帽衫,不受打扰地牵着手。
同样地,牦牛也在靠近,当青海
把它们轰进青草地,在摇曳的格桑花
和圆穗蓼中。小生命的数量之多
与红黄紫三色印证着它的泽被。
你永远无法将春天驱离高原。
蓝色的天空似乎比我更善于在
空旷中冥想,黄蒿羽状上翘的细枝
已经走近我的镜头,即使漫长的
寒冷也压制不了神奇的向上的推力。
这里是静泊在汉书中的西海,
当斑头雁成为天空的语言,
当一匹马饮水湖边,它似乎
又变成了一首令人联想的唐诗。
如果说,一个孩子最难忘的欢乐
是爬上一棵柿子树,那么现在,
我正为这存在而惊异——
就像一个邮递员或者维修工人
走进了一幢豪华住宅。显然,
我在倾听一个高原的心脏和春天:
由三千米海拔高度所给予的纯净
存在于它的血统中,而细胞中心的
每个球状细胞核都在储存和传递着
它的遗传物质——令人敬畏的辽阔与孤独。
秋季四边形
繁星在我面前静坐,就像地摊文学一样多。
顺着北斗七星的勺口往上,是北极星
和仙后座。左侧,织女、牛郎
与天津四构成三角。右侧,
孤独的五车二,它的后方,猎户座正从
地平线蹦蹦跳跳出来。背后,两颗亮星,
北落师门以及土司空。还有一个组合
在中天,近似正方形,壁宿一、二
和室宿一、二,在巨大、寒冷、混乱的
环境中它们显得特别稳固,闪亮。
好的友谊没有距离,至少距离可以稳固。
深夜,涌出地铁终点站,离开
大街,星空找到了我。星空的感觉
也许是,我们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傻瓜。
橡树叶蝴蝶
我不做梦,世界残酷我跟着。
但有人建议我去找一个梦。
也许她觉得它是一座南非矿山
随时可以射出钻石,
比科幻小说迷人。
她一直在找梦。也许
不是一个,而是两盒。
没有一颗星星
能够分散她的注意力。
我不擅长找东西,如果
使用哲学书中的说法,康德
或者海德格尔冗长的描述,
那是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感觉。
为此她哭了三周,
把化妆品都哭掉了。
在情感不平衡状态需要
足够的空气平衡的情况下
我只好一个人去爬山。
就是这样,我看到一只橡树叶蝴蝶,
它的外观形态异常接近于
一片枯叶——翅膀区域长出了
叶脉图案并且带上了苔藓类斑块。
我知道它可以不再恐惧了。
我看着它有点悲伤,但也不确定有多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