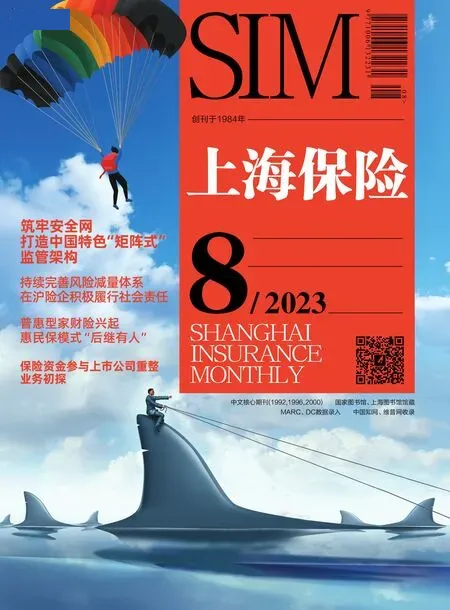重大误解前提下订立的合同应否撤销分析
——以牛某机动车投保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纠纷案为例
朱雨童 南京工业大学法政学院
一、案情概述及简析
2022 年1 月8 日,牛某为其所有的四轮电动车投保了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2022 年11 月17 日,牛某驾驶四轮电动车沿316 国道由东向西行驶,与行人张某发生碰撞,张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022 年11 月29 日,城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委托司法鉴定所对肇事四轮电动车的车辆技术状况、碰撞痕迹、事发时车速、车辆属性进行鉴定,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为该四轮电动车车辆属性为机动车。
2022年12月9日,城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牛某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张某无事故责任。
2023年1月14日,牛某与张某家属达成调解协议,并向张某家属支付赔偿费用。之后,牛某申请理赔,被保险公司拒赔,遂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投保人就涉案车辆向保险公司提出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投保要求,即向保险公司发出了要约。保险公司在作出保险承诺前,有义务对承保车辆的性质与险种是否相符进行审查,对经审查车辆性质与险种不符的,完全可以拒绝承保。本案中,投保人在投保时向保险公司提供了车架号,保险公司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车辆属于超标电动车属性的状况下,认可了超标电动车的非机动车性质,并自愿承保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相应保险责任。即使承保车辆性质与承保险种不符,也是保险公司未尽到审查义务所致,投保人并无过错,保险公司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败诉。
“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案例宣传发布和释法说理,不仅具有法治宣传教育作用,还能起到为避免矛盾以及解决矛盾提供实例参照的作用。本案中,法院虽然处理结果正确,可惜未指出该纠纷的性质,对于保险实务中发现此类错误承保后应如何合理处理所签保险合同没有禆益。
本案性质属于重大误解,应适用重大误解处理规则。重大误解是指表意人为意思表示时对意思表示的内容发生了具有交易上重要性的“认识错误”或者“表示错误”。古罗马法学家认为,此类错误包含标的物同一性错误、相对人同一性错误、数量错误、法律行为类型错误等。近代民法学基本上沿袭了罗马法上的意思表示错误理论。我国民事立法未使用域外民法的“错误”概念,而称之为“误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或者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数量等产生错误认识,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作出相应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误解。”民法意思表示中可撤销的行为,是基于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撤销权而产生的。法定撤销事由包括欺诈、胁迫、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四种。
二、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
(一)表意人存在认识错误
重大误解是在双方当事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中,行为人因为自身过失,对法律行为或事实认识错误,以错误的认识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认识错误可以分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和事实上的认识错误两种。事实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与自己行为有关的事实情况有不正确的理解。若未对相关事实产生误解,行为人不会有实施该行为的意思表示,或者会改变行为的内容。这些相关事实包括:交易的主体、行为动机、标的物的品质、数量价格等。
在一起控制柜采购合同纠纷案[(2021)沪01民终3901号]中,二审法院认为:“双方交易的控制柜价格构成体系透明,乙公司的报价附有控制柜价格构成计算表,控制柜项下物料也列明品名、型号、数量、价格等信息,因此,双方对于订单价格的构成应是清晰的,订单价格也并非打包价,且交易过程中,无论是询价、报价、议价、供货,都明确了物料的计量规格,就系争物料均按照‘PC’执行,而其他物料除‘PC’外,另有以‘PAC’‘M’为计量规格,不存在概念混淆或理解错误的情况。”在“北京成和永信国际文化交流服务有限公司、江西成和永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江西省展览中心、江西省美术馆、程昭金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2021)最高法民申710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般而言,因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合同,系对于合同自身或合同标的物的本质、性质存在误解,直接影响到当事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以及合同目的的实现。从本案合同的签订来看,案涉租赁物的招租公告中已经明确载明案涉租赁物的权属,出租人并未隐瞒。从合同的效力来看,出租人是否系租赁物的所有权人以及对租赁物是否具有管理使用权,并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故案涉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从合同的履行来看,承租人签订案涉租赁合同的目的在于承租案涉租赁物。在该合同签订后,出租人完成了交付租赁物的合同义务,承租人已实际占有、使用该租赁物,且无其他权利人对此提出异议,并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
我国是全球电动自行车生产和销售第一大国,经过多年的发展,电动自行车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短途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社会保有量约2亿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不应大于20km/h。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重量)应不大于40kg。”近年来,不少电动自行车产品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越来越快,部分指标超出了原标准的规定,俗称“超标车”(明慧,2019)。“超标车”部分关键技术指标超出了电动自行车标准的规定,且动力性能明显高于其他非机动车,在司法实践中会被判定为机动车(鲁畅等,2020)。因此,名为“电动自行车”的电动车应分为两种:标准电动自行车和视为机动车的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本案投保人投保时提供了车架号,保险人具有核查保险标的实物的条件,但其未加甄别,仅凭电动自行车产品名称表象就以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和费率承保实为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标的,显属对保险标的事实认识发生错误。
(二)重大误解系由行为人自身过失所致
误解人所作表示行为以错误认识为基础,导致内心真意与客观事实不相符。重大误解是行为人自己的过失所导致,而非对方故意、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也非因第三人的错误而为。相对人故意造成行为人错误认识的,构成欺诈。《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欺诈。”
在“杨某某与武汉百世东晟建材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2021)豫1524 民初4196 号]中,法院认为:“行为人主张在相对人隐瞒合同相关重要事实的情况下,导致行为人产生重大误解。所谓基于重大误解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一方因自己的过错而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等发生重大误解而实施的某种民事法律行为。重大误解是由于本人的过失造成的,而不是相对人的欺诈、误导造成的。”
本案投保人投保时提供了车架号,保险人具有核查保险标的的条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标的究否标准电动自行车,但其怠于勘查保险标的,以非机动车保险条款和费率承保超标电动自行车,具有过错。
(三)重大误解制度中的误解必须是重大的,对行为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产生重大的影响
重大误解制度中的误解必须是重大的,会对行为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产生重大的影响;倘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作出相应意思表示。《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或者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数量等产生错误认识,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作出相应意思表示。《德国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表意人若知悉情事并合理地考虑其情况后即不会作出此项意思表示时,表意人可以撤销该意思表示。”
与前《民法典》时代相比,重大误解的认定不再以造成或者可能造成较大损失为构成要件。例如,卖家混淆买家想购买的纪念品颜色,弄错节日带有特定意义的花束品种,虽未造成重大损失,但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同样可能构成重大误解。在“徐某某与张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2021)浙0281 民初6954 号]中,法院认为:“重大误解制度中的误解,必须是重大的,该误解将会对行为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产生重大的影响。房屋买卖双方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得知过户后产权证上该房屋用途可能会变更,但经法院查证该房屋过户后仍可按原证书记载用途进行登记,故该房屋的原规划审批用途并不会对行为人获取书面权证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行为人的职业为房产中介,购置该房屋亦系用于开办中介门店,故该房屋的原规划审批用途亦不会对该房屋的具体使用产生重大影响。且行为人本人亦从事房产中介职业,具有更审慎的风险辨别能力和更丰富的信息来源渠道。行为人以对房屋性质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该房屋买卖合同,缺乏相应依据。”在“高某某与嘉兴昊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2022)浙02民终2958号]中,二审法院认为:“网店经营者在网络销售平台发布的商品信息系其向不特定的相对人所作出的单方意思表示,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情形应结合合同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交易习惯及诚信原则等因素综合予以认定。网店经营者的工作人员因将商品的数量标注错误导致商品的单价远低于进货价格,更远低于同类商品正常售价,而网店经营者在销售时并未就商品组织超低价优惠活动,且在发现异常后及时予以下架处理,并通过客服与买方沟通解决方案。综合以上情形,网店经营者以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符合法律规定。”
由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风险程度不同,且发生交通事故时所适用的归责原则也存在很大区别,保险实务中,机动车辆保险与非机动车辆保险系两种不同的保险产品系列,保险责任和费率迥异。因此,倘保险人知道保险标的为超标电动自行车就不会以非机动车保险条款和费率承保,或者另以机动车条款和费率承保;倘保险人在错误承保后发现错误,即尚未发生重大损失,亦得以重大误解为由依法行使撤销权以纠正错误。
三、重大误解系得依法撤销的意思表示
(一)重大误解所发出的意思表示在一定条件下依法可予撤销
当事人通过意思表示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私法上的利益关系,由此形成的法律关系是私人之间的法秩序,是意思自治的产物(申智,2022)。通常情况下,即便存在误解,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表意人也不能随意撤销其意思表示。但若当事人在将意思表达于外部的过程中发生错误,导致受领人从表意符号中获取的意义与表意人的意思不一致,则应当赋予表意人一项矫正的权利,即撤销权;否则,表意人将受制于背离其主观意思的表示意义,违背意思自治原则。表意人以重大误解(错误)为由撤销法律行为,乃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根据私法自治原则,权利人可以放弃撤销权,明示或默示皆可。
(二)撤销权须经诉讼或仲裁程序行使
《民法总则》《民法典》与《民法通则》《合同法》相比,一个显著变化是将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后果由“可变更、可撤销”更改为“可撤销”,其理由是:合同的变更在当事人合意的情况下都可以变更;但如果一方主张变更,另一方不同意变更,只能向法院起诉或者到仲裁机构请求仲裁,依《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当事人请求变更的,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此时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作出折中变更的裁断,并非合适的结果,而是使法官和仲裁员的意志代替了当事人的意志,既不切合实际,也违反了意思自治的原则(崔建远,2012)。
重大误解的发生以合同关系为其典型。在合同关系中,误解方以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合同关系,以便从与其意愿相悖的合同关系中解脱,相对方则面临着既已成立的交易关系破裂、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现实困扰。是否允许撤销合同,对于双方的利害得失均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权衡双方的利益冲突,平衡意思自治与信赖保护、正当性与法的确定性(杨代雄,2012),因此,法律将允否撤销合同的权利授予法定的解决纠纷的中立机构(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本案保险人基于认识错误,以非机动车保险条款和费率承保了超标电动自行车,但其未以重大误解为由向人民法院或合同约定的仲裁机构主张解除合同,而是径向投保人发出拒赔通知书,程序和方式不合法。
(三)撤销权为形成权,因除斥期间届满而消灭
形成权,是指权利人依单方意思表示就能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与消灭的权利。形成权唯行使才能产生效力,倘权利人有该权利但不行使,不会影响既存的法律关系。为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法律对形成权规定了除斥期间,即权利存续期间。权利逾期不行使,即为消灭。《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九十日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
与前《民法典》时代的法律规定不同,《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对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分成三种情形。第一,通常情况下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第二,重大误解的除斥期间为九十日。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这是因为,重大误解是由于行为人自己的重大过失引起的,即使行为的后果不公平,也与其他的撤销权不同,除斥期间缩短为九十日,就体现了这种差别(申智,2022)。第三,最长除斥期间五年。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本案投保人于2022年1月8日投保时提供了车架号,保险人此时即可以知道投保电动车有关指标是否超标,其未予查验,错误地认为保险标的为非机动车,进而以非机动车保险条款和费率承保,此项撤销权于2022年4 月7 日因时效届满而消灭,但直至2022年11 月17 日保险标的发生交通事故,保险人仍未主张撤销合同,此合同已不可撤销。
四、结语
保险实务中,由于保险标的品类复杂,难免会发生对标的性质的认识错误。为减少纠纷,维护社会和谐,应当允许当事人对基于重大误解而订立的错误合同依法定程序予以撤销。撤销权唯于除斥期间行使即可,而不必以存在较大损失为前提,更不应以保险标的出险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