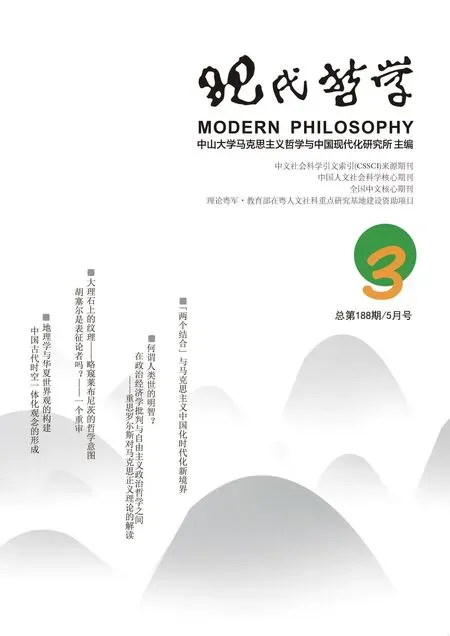从董仲舒“三统说”到刘歆“三统术”
——论西汉“三统”理论的转折
郜 喆
“三统”是汉代《春秋》学中的核心学说,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汉今文经学的框架中讨论其相关问题。(1)关于今文经学中的“三统”研究,近年来有刘禹彤:《从〈春秋繁露〉三统论到〈白虎通〉三皇说》,《衡水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高瑞杰:《汉代三统论之演进——从董仲舒到何休》,《哲学分析》2021年第3期。关于刘歆的《三统历》,参见程苏东:《史学、历学与〈易〉学——刘歆〈春秋〉学的知识体系与方法》,《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第101页。事实上,在西汉时期,“三统”理论经历了从董仲舒“三统说”到刘歆“三统术”的转折。理清这一转折,既可以明晰“三统”的性质与作用,又能够揭示出西汉儒学性质的转变。
一、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三统说”
两汉时期,《春秋》是一部重要的经典。汉人多以《春秋》为孔子所作,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2)[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99页。以下相关引文出自此版本,不再详述。所谓“一王之法”,指的是孔子有德无位,制作《春秋》,为汉制法。由此,《春秋》便成为孔子立法之“作”,是汉代经学的核心。皮锡瑞说:“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3)[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3页。汉初的《春秋》学以“春秋公羊学”为重,《史记·儒林列传》言:“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董仲舒所传“公羊氏”的内容,今已不得其全,幸有《春秋繁露》一书,流传至今。《春秋繁露》多记董子言说《春秋》之理,其解经体例与汉代后的经注不同,如苏舆所谓“说经体”。(4)[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页。今本《繁露》存《三代改制质文》篇,详明“春秋公羊学”中的“三统”之说,或是董子传解《春秋》及《公羊传》的实录: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5)[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4-185页。
董子以为,新王之立,必改制应天,此即《春秋》书“王正月”之意。按,隐公元年《春秋》经文:“元年,春,王正月。”《繁露·玉英》:“谓一元者,大始也……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死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6)同上,第67-68页。“死”原文作“不”,苏舆说:“人以生之始为元,犹王之以即位为元。‘不’,疑当作‘死’。生应春,死应冬。”从苏校。标点有所调整。“元”是万物之本,是天地未起的本初状态。“元”在未展开天地之前是空无的状态,而其有形则为气,造化天地,形成春夏秋冬交替的自然现象,故“元之深正天之端”是为“春”。更重要的是,董子言“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因此《春秋》中的“元年”实则经历了“变一为元”的过程。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董子亦以“孔子作《春秋》”,此处的“圣人”必然是孔子。
“元”的意义在于确立秩序产生的根源,孔子“变一为元”,这是最根本的《春秋》立法。而后“元”产生了天的自然秩序,便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此谓“王正月”。“正月”是历法中一年之始,《三代改制质文》:“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7)同上 ,第185页。董仲舒认为王者皆受命于天,制历法之时,皆需“改正朔”以应天变,改正之法称为“三正”:
然则其略说奈何?曰: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具存二王之后也,亲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统奈何?曰: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具存二王之后也,亲黑统。故日分鸣晨,鸣晨朝正。正赤统奈何?曰:正赤统者,历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具存二王之后也,亲白统。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改正之义,奉元而起。(8)同上 ,第191-195页。标点有所调整。
“元”以阴阳二气的配合,形成四时,四时又以北斗七星之斗柄的指向,细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月。斗柄跟随着阳气的运动轨迹,阳气以建寅之月始出,故而为“孟春”。《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言:“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9)同上,第324页。黑、白、赤三统的正月,与阳气的出入相关联。然而,若以斗建的顺序而言,“三正”以“寅、丑、子”为序,与自然顺序中的“子、丑、寅”正好相反,所谓“逆数三而复”。因此,“三正”之月的确立与自然顺序相反,改正之法必是人为的创制。
从直观上看,“正月”的确立,是记录新王政教时间的开始,即为古典中的历法。并且,新王的历法,需要颁布于诸侯,行于天下。董子云:“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然后布天下,诸侯庙受,以告社稷宗庙山川。”(10)同上,第195页。新王受命改正,此历法需颁布于中国,“以统天下”。由此,新王的改正,既可以确立时间秩序的开端,又可以成为空间秩序的源头。“三统”是为秩序之“始”,“万物皆应而正”,即是“化四方之本”。
董仲舒认为,秩序的开端是“王道之端”,《汉书·董仲舒传》载董子《对册》言:“《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那么,在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核心都落在王者的道德之上。王者道德之正,贯穿着秩序的始终,《对册》云:“《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而王道终矣。”(11)[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1-2503页。《春秋》建构了“元-天-王-人”的秩序结构,“深探其本,反自贵者始”,“王正月”成为这套结构中的逻辑开端,“王道”成为统理“天道”与“人道”的桥梁。
历法在中国历史中有着久远的传统。顾炎武说:“《春秋》时、月并书,于古未之见。”(12)[清]顾炎武撰,[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6页。这说明“元年,春,王正月”正是是孔子创造的《春秋》书法。并且,以《论语》相参,“三统”亦可见于《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13)[梁]皇侃疏、高尚榘点校:《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9页。所谓“行夏之时”,即是“三统”中的“黑统”,以建寅为正月。因此,《春秋》中的“三统”之说,无非是《论语》“行夏之时”的另一种表达。“行夏之时”是孔子回答弟子“问为邦”的答案,“三统”则是孔子通过作《春秋》所塑造的价值理念。不过,若以“行夏之时”对应“三统”中的“黑统”,便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三统”的历法来源于夏代,是否意味着“三统”只是夏商周三代历法的再现与重复?《礼记·礼运》云:“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1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87页。如果《夏时》是历史中实际存在的历法,不经孔子之征,亦不可得。因此,在《三代改制质文》中,夏商周三代的历法进入到“三统”的模型之中,形成“通三统”的制度。
二、“通三统”的制度逻辑与政治实践
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三统”之法可以依次对应于夏商周三代之中:“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15)[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186-189页。标点有所调整。依据“三统”的循环,可以推知“禹受命而王,应天变虞作夏号,时正黑统”。由此,历史中的圣王之治进入“三统”的谱系之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三统”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它让历史中的“夏商周”历法成为《春秋》中的“黑白赤”之统。“三统”的理论在先,历史中的三代需要合于“三统”之法。这意味着《三代改制质文》中的“汤”与“文王”代表的不是历史中的实际人物,而是见于孔子制作中的符号存在。
历史经验进入到“三统”的理论框架后,“三统”就具有了对现实的解释力。《三代改制质文》中的“《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成为现实世界中的《春秋》“为汉制法”,《汉书·律历志》载倪宽答汉武帝《改正朔议》:“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16)[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975页。“夏时”即是“正黑统”,倪宽虽主于今文《尚书》,不习《春秋》,但亦是与董仲舒齐名的“通于事务,明习文法”之儒,又曾为董仲舒弟子褚大的门人。其人所传改正朔之法同于“三正”之说。如此一来,“三统”循环,上通三代,下及汉代,成为解释历史与现实的道理。
“过去-现在-未来”构成一般的时间意识,“三统”之法仅仅覆盖了过去与现在,未来的王朝更替,是否也同样需要遵循此法?换言之,《春秋》“为汉制法”,若汉代灭亡,新王又起,《春秋》的使命是否得到终结?这需要考察由“三统说”产生的“通三统”制度。
“通三统”的制度,即是《三代改制质文》所言“亲”与“故”。具体而言,王者皆受天命而起,由天而言,历史与现实中的王者皆非天下之主,汉代经师谷永言之甚晰:“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17)同上,第3466页。新王受命,应当尊崇前代二王之德,封以土地,存其后人,彰显天下的公共性。董仲舒同样言及“通三统”:“是故周人之王……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18)[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19页。倪宽在劝谏汉武帝改正朔时言:“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唯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19)[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975页。这亦是呼吁汉武帝确定殷周后人,完成“通三统”的制度。其背后,则是“公天下”的政治精神。
推而言之,若有新王再起,汉家亦当存有百里之地,立为旧统。汉昭帝在位时,便有儒者据此进谏。《汉书·睢弘传》载:“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20)同上,第3153页。此石之立,引发了一系列的灾异现象,睢弘推其意,言:“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21)同上,第3154页。断句与标点有所调整。据《汉书·儒林传》,睢弘为董仲舒再传弟子。(22)《汉书·儒林传》:“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孟为符节令,坐说灾异诛,自有传。”(参见[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3616页。)他以彼时灾异为汉家天命当绝之象,在未知新受命之天子的情况下,汉昭帝应当主动退居为“二王后”,如周代的杞国与宋国,再求索新的天子,禅以至尊之位。
睢弘之言可谓千古奇论,学者往往关注此事件中的灾异元素与政治博弈。然而,睢弘以汉家命数当尽的原因,出于“通三统”的制度要求。“汉家尧后”指的是汉帝应当效仿尧舜禅让之事,汉家就如同尧的后人。依据“三统说”的理论模型,汉昭帝禅让后,“正黑统”断绝,新的天子“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白统。绌殷、亲汉、故周”。这说明,《春秋》“为汉制法”并不意味着“三统”理论是汉代之统的文饰。“三统”的循环不仅囊括了历史中的先王与汉代时王,也可规范未来的新王。由此,“三统”不停地循环往复,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历史哲学。同时,眭弘明言其说来源于董仲舒“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的师法。董子此语今已不见,但仍可在《春秋繁露》中找到相关线索: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闻,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23)[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15-19页。
这里的“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即为“通三统”之制,董子将其称为“改制”。《春秋》的特点在于“善复古,讥易常”,维护着普遍的先王之道。于是,“自僻者”问道,既然有普遍的“先王之道”,就应该搭配不变的“先王之制”,何来“改制”之说?对此,董子答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他强调,新王“改制”是为了遵循公天下的原则,彰显天命的转移,避免造成新王之统来源于前王的误解。而“大纲、人伦”等内容,则合于“先王之道”,不必变革。
据此,“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之语,正是眭弘根据“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进行的改编。在眭弘的语境中,新王受命而起,只需要“改制”,不必变更汉家应当遵循的先王之道。汉昭帝废立“继体守文”之君,选择禅让,并不会对天道有何影响,反而符合天命转移之象。并且,董仲舒在《繁露》中,以尧舜禅让为例,说明“有改制”与“无易道”的关系。眭弘同样以“汉家尧后”的方式,明示汉帝禅让。因此,西汉中期的禅让风潮,出于汉初董仲舒“三统说”中的“改制”理论,亦是变更天命的革命说。(24)依据董仲舒的“三统说”,新王改正朔、易服色的目的,正是彰显天命变革。也就是说,“改制”即“革命”。近代以来,多有学者对二者进行区分。典型者如蒙文通,他在《孔子和今文学》中说:“董仲舒却变汤、武‘革命’为三代‘改制’。‘易姓受命’是禅让的学说,但董仲舒何以又要说‘继体守文之君’(即世及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同时又把今文学主张的井田变为限田呢?实际上,儒家最高的理想与专制君主不兼容的精微部分,阿世者流一齐都打了折扣而与君权妥协了,今文学从此也就变质了。董仲舒又何尝不是曲学阿世之流。儒学本为后来所推重,这时经董仲舒、公孙弘之流的修改与曲解之后,这样变了质的儒学,却又是专制帝王汉武帝乐于接受而加以利用的了。”蒙氏以眭弘为今文经学“革命”正统,董仲舒为“改制”异端。他既忽视了眭弘视董子为先师的事实,又没有理解“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一语的革命性质,强行把改制与革命、董仲舒与眭弘分开,实为大误。(参见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蒙文通全集》第1册,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316-317页。)不过,眭弘等儒生并没有成功劝谏汉帝禅让,反而因此丢掉性命,“春秋公羊学”随之逐渐式微。此后,“三统”理论迎来一次转折。
三、刘歆《三统历》中的“三统术”
眭弘之后,刘歆的《三统历》是西汉后期“三统”理论的代表。顾名思义,《三统历》是一部历法,学者多以其中的制历之术为线索,探索刘歆历法的特点。但从《春秋》学的视角来看,《三统历》以“三统”为名,始于刘歆对于“三统说”的重构。《三统历》存于班固的《汉书·律历志》,其中有关三统的内容如下:
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物元也……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楙之于未,令种刚强大,故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六者,所以含阳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内,令刚柔有体也……正月,乾之九三,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为仁;其声,商也,为义。故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戏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也……此三律之谓矣,是为三统。(25)[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961页。
在刘歆的历法建构中,“三统”实为“三律”,是音律与月建配合的产物:十一月建子之月为“天统”,律为黄钟;六月建未之月为“地统”,律为林钟;正月建寅之月为“人统”,律为太族。这显然与董仲舒的“三统说”完全不同。在《春秋繁露》中,“三统”皆出于天道,以“天统气始通化物”“天统气始蜕化物”“天统气始施化物”的反自然顺序推进,故“三统”之正月分别为“寅、丑、子”;而刘歆以“三统”为“天、地、人”之纪,皆出于律数阴阳的自然规律。“天统”以阳气的初生为准,为十一月。“地统”则以阴气始任为据,为六月建未,而非十二月建丑。这是因为,六月之时,“阴气受任”,开始参与万物的造化之中。当然,《律历志》下文云:“其于三正也,黄钟子为天正,林钟未之冲丑为地正,太族寅为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适其始纽于阳东北丑位。《易》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答应之道也。”(26)同上,第962页。刘歆借助《易·坤》卦的彖辞,将六月建未,对应至建丑之月的位置上。天地造化后,“人奉而成之”,为建寅之月代表的“人统”。
在“三统说”中,王者改制应天,以示天命之统,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三统与“地”“人”无关。刘歆将董仲舒的“三统说”构造为天、地、人三统,消解了董子之说中的公天下之义。同时,《易》经的引入,改变了“三统”之为“春秋公羊学”学说的性质:“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27)同上,第983页。刘歆以为,《春秋》中与历法相关的概念可以化约为几个数字,通过简单的乘法,得出《易》经中的“大衍之数”,合于自然世界的运行规律,是制作历法的根源。他借用这些数字,完成了历法的推算,形成《三统历》。可以说,刘歆将“三统说”改易为一套制作历法的“三统术”。那么,刘歆建构“三统术”有何目的?在《律历志》中,刘歆通过“三统”历法引入“五行之道”:
《经》曰:“春,王正月。”《传》曰:“周正月”、“火出,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夏数得天”,得四时之正也。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复于子,地化自丑毕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则三统五星可知也。《易》曰:“参五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28)[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984-985页。
刘歆认为,天、地、人三统的颜色分别为赤、白、黑,与五行的颜色有所对应:天统与五行火德同为赤色,地统与金德同为白色,人统与水德同为黑色。但是,火、金、水的顺序却与五行次序不符。为此,刘歆将地、人二统的月建,拆分为“初”与“半”,再分别加入土德与木德,形成“五行与三统相错”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以“《经》曰”开头,后有两处“《传》曰”。刘歆引用的“《传》”,全为《左传》。按,《汉书·楚元王传》:“歆校祕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29)同上,第1967页。《左氏》本与《春秋》无涉,刘歆以之解经,实为首创。《三统历》中的这段内容或是刘歆引《左传》解《春秋》的实录。
不仅如此,在刘歆的学术中,《易》与《春秋》代表着“天人之道”。《汉书·五行志》:“《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30)同上,第1315页。在刘歆看来,《易·系辞》之言,证明《河图》《雒书》是从天而降的治世法宝,古圣王“则而画之”“法而陈之”,使之为“八卦”与《洪范》。《洪范》中最重要的内容正是“五行”:“‘初一曰五行……’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为《河图》《雒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31)同上,第1316页。《河图》《雒书》象征着天道与人道,殷衰之际,“文王演《周易》”,则八卦,著天道;周衰之际,“孔子述《春秋》”,传《雒书》,效《洪范》,著人道。《春秋》的价值在于承载了《雒书》《洪范》中的五行。显然,刘歆构建“五行与三统相错”的格局,是在用五行替代“春秋公羊学”的三统。此举有何用意?
《汉书·律历志》存有刘歆的《世经》,齐召南说:“统母、五步、统术、纪术、岁术、世经,凡六项,乃历法之标目。”(32)[汉]班固撰、[清]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19页。齐氏以《世经》为《三统历》的一部分,其言甚是。《三统历》的前五项多为具体的律历之术,《世经》则是刘歆依据五行规律构建的历史谱系:
《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传》曰:昭子问少昊氏鸟名何故……太昊帝 《易》曰:“炮牺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炎帝 《易》曰:“炮牺氏没,神农氏作。”……以火承木,故为炎帝。……黄帝 《易》曰:“神农氏没,黄帝氏作。”火生土,故为土德……少昊帝……土生金,故为金德……颛顼帝……金生水,故为水德……帝喾……水生木,故为木德……唐帝 ……木生火,故为火德……虞帝……火生土,故为土德……伯禹……土生金,故为金德……成汤 ……金生水,故为水德……武王……水生木,故为木德……汉高祖皇帝……木生火,故为火德。(33)[汉]班固撰、[清]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第1011-1023页。
本段“《传》曰”仍为《左氏传》。刘歆借助郯子所言古代帝王次序,辅以《易·系辞》中与伏羲、神农、黄帝相关的内容,再用五行相生的规律,排列出从伏羲到汉高祖的历史谱系。前文已述,“三统说”涵盖夏商周三代历法,是容纳百世的历史哲学。《世经》的五行谱系亦可推至无穷,它与“三统说”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首先,最为直观的是,董仲舒以“三统”的方式建构历史王朝的统绪,而在《世经》中,“五行”完全取代了三统的地位。其次,“三统”是一套动态的历史哲学,它的递禅,使得先王的地位也处于改易之中,《三代改制质文》:“故汤受命而王……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文王受命而王……绌虞谓之帝舜,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绌夏。”(34)[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186-189页。先代之“统”的确立,由本代之“统”向前推得。并且,“三统说”规范下的历史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只需确立与本代之“统”的前二代之统,就可以完成“通三统”的制度,示“公天下”之义。而二代之前,则是久远的“帝”与“皇”,其德远于当世,土地也逐渐狭小。每当确立了新王之“统”,就伴随着绌旧“王”为“帝”,绌旧“帝”为“皇”。这意味着,“皇”与“帝”只是更疏远的先王的符号表达,并不存在历史中的首位王者。相反,在《世经》中,“五行”的运行,是以“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为标准来确立的。那么,太昊帝就是王者历史谱系的开端,后代之王便以“五行”的顺序依次排布。所以,《世经》的五行次序,仅是一套历史谱系,而非历史哲学。
《宋书·律历志》如此评价《三统历》:“(刘)歆作《三统历》以说《春秋》,属辞比事,虽尽精巧,非其实也。”(35)[南朝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页。从《三统历》的内容来看,它的确不是一套追求精准性的历法,而是采用《左传》解释《春秋》的文本。简言之,刘歆将“三统”塑造为纯粹的历法技术,并用《左传》中的“五行”历史谱系代替了《公羊》学的“三统”历史哲学。
四、“三统术”与王莽改制
“三统说”引发了西汉中期儒生的革命诉求,“三统术”也对西汉后期的政治事件有所影响。西汉昭、宣二帝以后,眭弘等人依据“三统说”形成的革命诉求仍有影响。西汉末年,汉家国运衰亡一直是无法解决的难题。甚至在汉哀帝时,“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36)[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340页。。夏贺良以谶言的方式,证明汉为“赤精子”,即是火德。汉哀帝若“再受命”,应为土德,故其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如淳注曰:“陈,舜后。王莽,陈之后。谬语以明莽当篡立而不知。”(37)同上,第340页。如淳之注或为附会史事,但《汉书·天文志》记载此事毕,又言“其后卒有王莽篡国之祸”。班固亦以王莽篡汉为汉哀帝再受命的翻版。夏贺良的“赤精子之谶”与刘歆建构《世经》谱系的目的相同,都是将汉代统治的正当性由“三统”转移到“五行”之中。相比于夏贺良卑劣的操作,刘歆的《世经》显得更为精致,在宏大的历史谱系中,确立了汉代的火德。因此,汉平帝时,王莽为“安汉公”,“政自莽出”。他用了五年时间,采取一些手段,使得“天下治平,风俗齐同,百蛮率服”,不仅天下太平,又有“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于是,在王莽掌权期间,刘歆任“羲和官”,二人配合,建立了明堂、辟雍。而刘歆攻击博士之学的一大理由,正是“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可以说,刘歆的理论与王莽的权力,挽救了“大统几绝”的汉代统治,并将其引入到太平盛世。
但是,王莽与刘歆又一同终结了汉家的天命。《汉书·王莽传》:“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38)[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4095页。哀章制匮必为谄媚之行,但其人以王莽代汉为“赤帝传黄帝”,即火德传于土德,这也符合《世经》中的“五行”谱系。王莽即真后亦下书曰:“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旛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39)同上,第4095-4096页。王莽的“改正朔”、“变牺牲”与“易服色”、“殊徽帜”分别采用了两种颜色:他以十二月建丑为正月,从三统中的正白统,故“牺牲应用正白”;服色、旌旗等上黄,合于五行中的土德。可以看到,正白统与土德的搭配,与《三统历》中的地统若合符节。这说明,新莽改制的理论来源正是刘歆的“三统术”。
《三统历》中的《世经》将汉代塑造为火德,光武帝刘秀继承了刘歆的建构,《后汉书·光武帝纪》云:“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40)[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页。光武帝以本朝为火德,否定了新莽土德的存在,回归了《世经》确立的汉代德运。东汉仍为火德,遂与《世经》唐帝相同。此后,东汉古文家从《左传》中找到更为具体的汉与尧同德的证据。贾逵说:“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41)同上,第1237页。《世经》推汉为火德,亦有此意。不过,前文所引眭弘就曾说过“汉家尧后”,为何贾逵仍以“五经家”不能证明刘氏为尧后?眭弘所言,与贾逵截然不同,他意欲汉帝禅让退居二王后以“通三统”,“汉家尧后”是在说汉家就像尧的后人,应当同尧一样,将天下禅让给得天命之人。东汉以火德为运,是在重塑王朝正当性。所以,贾逵强调《左氏》可以证明刘氏在血缘上为尧后,进一步加深政权的历史正当性,并提高《左氏》学的地位。眭弘提出“汉家尧后”的目的是变更汉代的统治,贾逵的“刘氏为尧后”则为了巩固汉代的统治,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推而言之,《世经》中汉与尧同为火德,是贾逵等东汉古文经学家论证“刘氏为尧后”的先声。因此,无论是新莽朝的土德,还是东汉的火德,二者本质皆是在五行的规律中奠定王朝的历史正当性。而刘歆的“三统术”与《世经》正是其历史正当性的来源。
五、总 结
总结而言,西汉的三统理论经历了从董仲舒的“三统说”到刘歆“三统术”的转折:前者是以公天下为精神的历史哲学,导致了西汉中期的革命思潮;后者表现为制作历法的技术,背后则是以五德相生为规律的历史谱系,它帮助新莽与东汉王朝确立了各自的历史正当性。三统理论从革命学说转向王朝正当性论证的过程,也与汉代儒家思想发展的特征一致。盖自西汉末期后,“统治者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种种手段将儒生的精力引导到更好地证明已经存在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非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由此,儒家的‘礼’被简单化为服从而非制约”(42)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9页。。两汉以后,三统理论不具备现实价值,晋代便不再进行“改正朔、易服色”,只采用一种固定的历法。(43)参见杨英:《曹魏“改正朔、易服色”考》,《史学月刊》2015第10期,第58页。相反,刘歆“三统术”中的五德终始说在南北朝时期的正统问题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究其本质,以五德终始为核心的正统论,仍然是一种确立本朝正当性的政治技术,早已与“三统说”最初的精神本质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