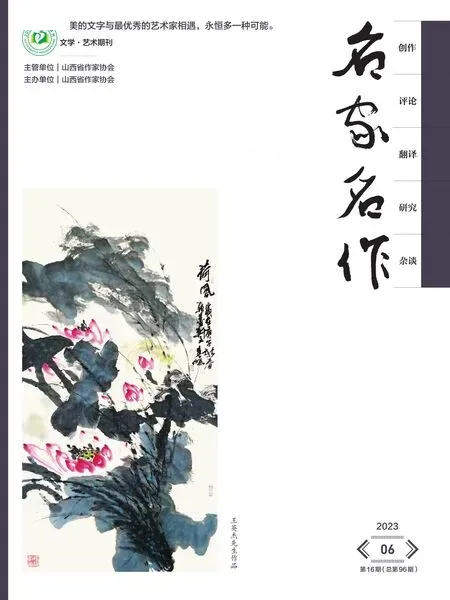《我与地坛》和《目送》的生命意识比较
唐 一
生命意识是当代文艺创作领域的热门话题,因其热门,所以有许多关于它的定义。譬如有学者认为“生命意识是对生命怀有一种强烈的自觉性意识,它表现为对生命自觉地关怀和热爱”[1];还有学者认为“生命意识,也就是人们对生与 死的认识”[2]。这些定义有着各自的合理性,但并不适用于所有场合。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所认可的生命意识是指:人对自我生命及其他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是在此基础上对于生命的价值及意义的探索与思考。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龙应台的《目送》(散文集)是最近文坛在生命意识表达上的佼佼者,两位作家的散文以充沛饱满的情感、平实细腻的语言、严谨认真的哲思,给予了自我生命一个令人信服的答卷,也启迪感染了千万读者。但由于个人际遇、文化背景、观察视角的不同,他们的生命反思呈现出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的特点。
一
中国先哲很早的时候就对生死问题有过思考与解读,儒家说“生死有命”,道家说“生寄死归”,佛家说“生死涅槃”,无论哪种说法,都强调的是我们要看淡死亡,以坦然的胸襟面对死亡。但先哲的思考更多的是体现在形而上的层面,还不能和具体的生命实践结合起来给予人们更真切感人的精神触动。史铁生和龙应台却从自我生命成长的具体实践中,体悟生命的不易,从而以豁达的心胸坦然面对生命的无奈。在生死问题的解读上,他们和先哲殊途同归。
史铁生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龙应台借彼得·席格的歌说出自己对生死的看法:“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目送·什么》)死亡是每个人必然的结果,既然逃不掉,那不如坦然面对好了。
虽说能够超越,但两者超越的方式是不同的。
史铁生在生命最灿烂的年纪突然失去了双腿,是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的,而在其后的很长一段岁月中,他都游走在生死边缘。正如他文中所说:“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即便是和朋友的日常对话,也是关于死亡的:“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活着对于一个健康人而言是一种轻易就可以实现的事,而对于史铁生而言,他要活着,不仅需要克服比常人更多的实际困难,也要克服残疾在心灵烙下的创伤。可史铁生坚韧地活了下来,不仅活着,而且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所以,史铁生的超越方式是渐悟的,而正因为反复地思考死亡问题,他对生命的解读就带有哲学的思辨色彩,试看这样的句子:“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这句话含有宿命论的消极成分,但矛盾对立统一的意味在这句话里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启人深深地思考。
比较史铁生,龙应台人生际遇要顺利得多。很年轻的时候就博士毕业,此后事业发展一路绿灯,做学者、当作家,2010 年登上作家富豪榜。家庭生活中,有一双活泼可爱的孩子。所以,龙应台对生死的感悟不是来自自己的精神危机,而是对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是“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所以,龙应台的反思带有浓厚的抒情意味,是对于生活瞬间的感慨,有顿悟成佛的感觉。比如她在《目送》中非常经典的一段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这是龙应台在目送儿子成长的背影和父亲交往直到火葬场诀别时的几个瞬间里感悟到的。在生命的哲思上没有史铁生深邃,但在情感上比史铁生缠绵。下面的几段话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
我在“金钱”上愈来愈慷慨,在“时间”上愈来愈吝啬。“金钱”可以给过路的陌生人,“时间”却只给温暖心爱的人。(《目送·两本存折》)
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目送·幸福》)
由于超越生死的方式不同,史铁生和龙应台的散文在给人的审美感知上也有所不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体现着“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倔强与挣扎;而龙应台的《目送》体现着“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的温润与平实。
史铁生笔下的“恐慌”就体现着他生命的挣扎:“这一来你中了魔了,整天都在想哪一件事可以写,哪一个人可以让你写成小说。是中了魔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不疯魔,不成活,不疯魔,不成功。可他即便成功后,也依然“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质”。而一系列成串的带有诘难色彩的质问,又表现出精神世界的对抗与不甘: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这些问题很难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体现着人类在苦难面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而龙应台笔下的事物更多了一分生活的平和美好,她读书的学校“外面有野溪,莓果的香甜气息混在空气里”,国语老师“慢悠悠地教诗”(《目送·1964》);和老年痴呆的母亲的对话充满了诗的韵律与节奏。她说:“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对,那就是我。”“喔,雨儿你在哪里?”“我在香港。”“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刚离开你。”(《目送·雨儿》)甚至闺蜜在面对有迫害妄想症的母亲时,会伪造一份“优良职工”的证明(《目送·明白》)……人生不能脱离生老病死的折磨,龙应台用女性特有的温婉坚韧抚平周边人生活的创伤,给我们一个平和的审美境地。
二
人生苦旅,总是难免遇见这样那样的苦难,总是经历人生的种种无常。而个体生命,由于地球只是目前宇宙唯一发现生命的星球,人类的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为应对生命的苦况,我们不得不寻求各种情感去滋养生命的孤寂。于是,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才有了大量对亲情、友情、爱情这种神奇力量的描写,才有了讴歌这些情感力量的文章。
史铁生和龙应台都是智者,在摆脱生命的孤寂时,都没有吝啬笔墨去赞美那些伟大的支持人类前行的种种情感。史铁生更偏重于描写母爱对他的重大影响,而龙应台则以爱的输出的方式来形成自我的生命支柱。与传统情感描写不同的是,由于现代人的情感需要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契合。他们把抒写情感的重点没有放在生活起居的日常照顾上,而是集中写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换位思考。这样,他们的生命意识表达就有了现代性的特色,对当代人生的指引作用会更加强烈。
在《我与地坛》里,史铁生用整整一个章节去阐述母亲的爱,去抒写母亲在儿子失去双腿时的种种忧虑,忧虑儿子的生命,忧虑儿子的前途。但史铁生的母亲是位超越凡俗的女性,为了照顾儿子的情绪,她选择把所有的忧虑独自扛起来,而在儿子面前装得若无其事。“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她总是在儿子常去的地坛默默守候,直到后来儿子才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她就是这样守候着,守候出了一个杰出的作家。而史铁生也给予伟大母爱最大的回报,终其一生,他都是用手中笔真诚地表达生活,不媚俗,不商业炒作,真正做到了“俯仰无愧天地,功业长留人间”。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告诉我们,人都有爱与被爱的需要。获得爱,可以使生命充满力量,而付出爱,同样也会使生命丰盈。龙应台就是以爱的输出方式实现了自我的情感完善。她的文章里写到有父母对她的关爱,但更多抒写的是她对父母的照顾、对孩子的操心 。她的父亲瘫痪了,“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漓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目送·目送》)她看待得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依然是靓丽的风景,“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眼神迷离,时空飘忽。”而龙应台最让人感佩的,是对孩子的教育,因为时代和文化的差异,她和孩子有了隔阂,但她坦然接受,不因为自己是母亲就胡乱行使自己的权威,“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进不去,就不强行进去,体现得是她对儿子的爱和尊重。她不仅对父母亲人竭尽所能地去爱,对于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当他们处于糟糕的不公的对待时,也适时为他们撰文发声,伸张正义。在《目送》不多的篇章里,有六篇是关于残酷战争的:《薄扶林》《四千三百年》《阿拉伯芥》《普通人》《首尔》《莲花》,这里面,有的人为了躲避屠杀而流离失所;有的地方,一场战争埋下的地雷需要四千三百年才可以排除干净;而金门岛上,为了避免军人出事,在糙米里加上黄曲素,抑制人的性冲动,而这一吃就是四十年!种种离奇不可思议的事实,不仅说明了战争的丑陋,也说明了龙应台对生命的关怀和慈悲!
三
史铁生和龙应台两位大家散文的成功当然得益于他们对生命的悲悯情怀,但两位高明的诗意建构的能力和物我齐一的观照方式,也为文本增色不少。
(一)优美清新、意境悠远的语言是诗意的形式外壳
史铁生和龙应台两位大家都非常擅长运用清新优美而富于诗歌韵律的语言来描写景物,给读者以诗情画意的美感。如:
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我与地坛》)
在那一团浓郁的深绿里,藏着一只浓郁深绿的野鹦鹉,正在啄吃一粒绿得发亮的杨桃。我靠近树,仰头仔细看它。野鹦鹉眼睛圆滚滚的,也看着我。我们就在那杨桃树下对看。(《目送·共老》)
不仅在描情写物上有着浓郁的诗意,两位大家还擅长在阐述艰深的哲理时,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使枯燥抽象的哲理变得具有美感。如:
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我与地坛》)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痛,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怎么收拾?(《目送·跌倒》)
(二)物我齐一的观照方式是诗意的精神来源
物我齐一是一种平等地看待世间所有生命的观照方式,并力求融入万事万物中的观照方式。而正是这样的一种观照方式,使两位大家的日常世界那样的生机勃勃。
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我与地坛》)
这里的蜂儿、蚂蚁、瓢虫似乎有着人类的灵性一般,而那些无生命的事物似乎也都有了自己的意识。人们在没有了高于其他生命的偏见后,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更多的生机,而我们的心灵会更加的包容。
涉过浓密的江离,看见水光粼粼的小溪里,隐约有片白色的东西漂浮——是谁不小心落了一件白衬衫?走近看,那白衬衫竟是一只睡着了的白天鹅,脖子蜷在自己的鹅绒被上,旁边一只小鸭独自在玩水的影子。(《目送·十七岁》)
这里,把一只白天鹅看成白衬衫固然可以看作是暗喻的一种修辞手法,可如果没有一种宇宙万物皆有灵性的观照方法,龙应台又怎么能够为我们捕捉到那生机无限的诗意瞬间,充实丰盈我们的审美感知!
四
从三个层面对《我与地坛》和《目送》(散文集)生命体悟的梳爬整理,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两位大家在生命意识这一话题上的经验式感怀。但不止于此,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下,轻视生命的情况层出不穷。而本文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心理纠结的人们摆脱苦闷、唤醒他们去热爱生命面对人生苦难的话,那本文的研究就有着切实的社会意义,不是关在书斋里的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