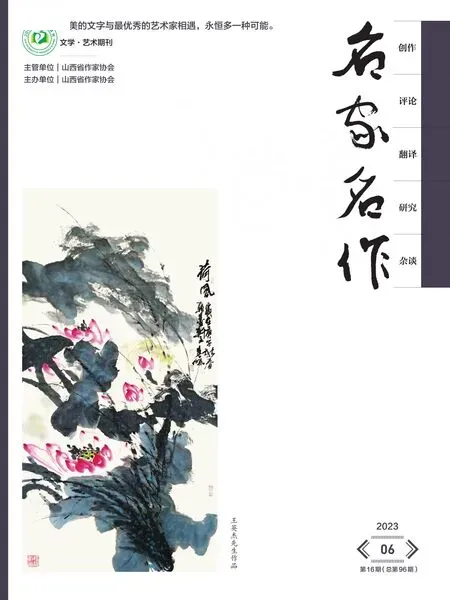《文城》:余华现实主义创作的边界
郝晓寒
余华的《文城》面世后广受关注,而且备受争议。目前,对其议论已溢出了文学批评界的范围,成为媒体谈论的话题。在一阵喧哗之后,我们需要对《文城》进行更耐心的阅读以及更聚焦的讨论,从而有效地理解和评估余华这次写作的意义。较之余华以前的作品,《文城》有哪些新的变化,当然是批评家关注的重点,于是余华的“回归”或“前行”成为众多评论中的关键词。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更多地回到关于作品的阅读感受,感受《文城》带给我们的某种触动,并从这里出发探讨其艺术品格,这是讨论余华此次写作价值的重要路径。无论余华是否被指认为“现实主义作家”,但《文城》所呈现出的现实主义特征是值得重视的。于是,现实主义的理论视野再次向我们敞开,也就是说对余华现实主义创作问题的探讨成为理解《文城》的重要通道。这一点,与《文城》叙事表层显现的“传奇性”形成了某种矛盾,但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余华现实主义创作的边界问题得以凸显,从而使《文城》具有了成为余华某种创作标志的可能性。
一、“寻找”的真实与悲剧的主题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文城》是一部关于“寻找”的小说。黄河北的乡间男人林祥福怀抱不满周岁的女儿,去江南文城去寻找妻子小美,这俨然是一个千里寻妻的传奇故事。因此,读者(或者余华自己)把小说视为传奇叙事就显得理所当然。但是,如果仅从这个角度来看该小说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文城》来说,“传奇性”只能作为一抹色彩,重要的是《文城》书写了现实中的某种“真实”,而非“传奇”意义上的“虚构”。笔者认为,这一点对于理解《文城》至关重要。
追求“真实”是余华这次写作所确立的叙述边界,也就是说小说的叙述并不企图越过现实“真实”的界限。那么,如何理解《文城》中的这种“真实”呢?这种“真实”是指现实主义中的真实观,或者说到底,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摹仿”——这一点似乎不符合读者对余华创作的印象。长期以来,我们或许对“摹仿”有某种误解,认为它更多地带来简单形式的再现。其实,由摹仿带来的真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真实观一直是现实主义的理论本质。这个理论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强调“摹仿”的本质意义,认为“摹仿”并不是肤浅的,“不是反映浮面的现象,而是揭示本质与内在的联系”①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8,第87 页。。奥尔巴赫系统地梳理了西方文学作品与世界的关系,指出正因为“摹仿”,现实主义之路才得以开辟和发展②[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吴麟绶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652-653 页。。在笔者看来,《文城》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摹仿”现实而达到的一种“真实”。我们需要从社会史的视野和对生命体验的想象中讨论《文城》中的“真实”问题。在小说中那个灾害频繁、战乱不断、匪祸泛滥的历史背景中,有无数人背井离乡、外出求生,形成了无数生离死别的历史场景。这一点在社会史视野中并不难发现,也是民族苦难史中的一部分。在逃离故土的历史情形中,从“黄河北”逃难的较为普遍,这几乎成为民间记忆和叙述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这其中,又会发生无数的“寻找”事件,这从社会史和生命体验的想象中是容易理解的。这种历史记忆的苦痛其实并不算久远,它以清晰的代际脉络传递给“50 后”“60 后”甚至“70 后”几代人,这或许是余华此次叙写这种“真实”的渊源。可以说,余华用《文城》为历史中的“逃离者”和“寻找者”立了一块纪念碑,这是小说最触动人心的部分。
《文城》对林祥福寻妻之路的叙述是现实主义基调的。小说对林祥福的塑造不是寓言式的,余华在林祥福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情感,试图穿过遥远的历史去“复活”这个“寻找者”。幼时的林祥福有一个富裕、温暖的家庭,父亲的熏陶、母亲的教育给了他吃苦耐劳、仁厚坚韧的品质。小说叙写了林祥福一路南下的情形,一些细节呈现了经历的艰辛和风险,譬如林祥福怀抱女儿过黄河的描写:“林祥福离开驿站,乘坐羊皮筏子横渡黄河的时候,夜色正在降临。他一手抱紧怀中棉兜里的女儿,一手抓住包袱,在波浪里上下簸荡。艄公跪在前面,挥动木桨划水而行。浪头打上来,淋湿了林祥福的衣服,林祥福的眼睛透过水珠,看到黄河两岸无边无际的土地正在沉入黑夜之中,空旷的天空里一轮弯月正在浮动,女儿嘤嘤的哭声在浪涛里时断时续。”①余华:《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第52 页。还有林祥福在溪镇的冰天雪地里挨家挨户为女儿乞讨奶水的细节,那种神态疲惫、声音沙哑、欲哭无泪的形象形成了一幅生动、鲜活的画面。这些细节大大强化了读者对林祥福寻妻之路的“真实”感受,具有现实主义追求表达“真实”的显著特征。耐人寻味的是,在关于《文城》的讨论中,这种“真实”特征往往被忽视,而《文城》所具有的一种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便容易被遮蔽。
林祥福的“寻找”注定是失败的,这也符合社会史中的“真实”。当林祥福知道文城并不存在但仍然要寻找下去时,小说的悲剧主题便形成了。小说在林祥福的信念和勇敢中展开了悲剧主题的叙写。根据方言辨别,林祥福认定溪镇可能就是小美虚构的文城。在一场雪灾中林祥福折返到溪镇,当时的小美与镇上的人一起在雪地里祭天。小美因心里在为女儿和林祥福祈福,站得太久而被冻死。小美的遗体被人抬走,经过林祥福的身边,这个历经艰辛寻找她的男人竟浑然不知。17 年后,林祥福死去,棺椁被运回老家的路上无意偶停小美坟旁,这个场景令人唏嘘。至此,余华以其卓越的叙事能力完成了这个悲剧主题的表达,形成了《文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文城》中对现实“真实”的书写以及悲剧主题的表达,是余华展现出的自己在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一种边界。无论这种边界的设置是作家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都确定了《文城》之于余华的独特意义。
二、温良与暴力的对峙
《文城》赋予了许多人物以美好的品行,他们朴素、温和、善良、仁义、敦厚、勇敢,集中传递出中国传统伦理中的温良力量。同时,《文城》中也有触目惊心的暴力书写,主要叙写了土匪的凶残、毒辣和暴戾。在温良与暴力的对峙中,余华表现出对温良等传统伦理道德的发掘和凸显,对暴力的一种暴露和批判,从而在审美取向的维度上树立了自己在现实主义创作上的另一个边界。
小说对于温良力量的表达是通过人物塑造来完成的。林祥福集传统美德于一身,具有温良可敬的人格魅力。林祥福身为“少爷”,与佃农一起劳作,勤俭持家,累积家业。善待“仆人”田氏兄弟,田家老爹被冰雹砸死,林祥福亲自做棺安葬。收留落难的小美,并宽恕其偷走金条的行为。因为夫妻一场,更为了自己的女儿,林祥福抛弃一切怀抱女儿南下寻妻。在溪镇与陈永良、顾益民的相处中,林祥福又表现出慷慨、谦恭和勇敢的品行。陈永良全家迁居万亩荡,林祥福赠送两三百亩田地。顾益民被土匪绑票,林祥福前去赎人,与匪首相拼而死。可以说,余华几乎把崇高的美德都集中到林祥福一个人身上。同时,余华也并不吝啬地把这些温良的力量分散给许多人物,形成了一幅温暖、壮美的人物图谱。譬如,林祥福的父亲收留逃荒的田家六口;陈永良安顿刚到溪镇的林祥福,最后智杀匪首为林祥福报仇;顾益民组织民团保卫溪镇,他送别林祥福遗体的场景也让人动容。小美和阿强的身上也闪耀着传统美德的光芒。小美甘愿二次冒险进林家,为林祥福生下女儿;阿强舍弃家庭,带着小美踏上逃亡之路,在雪灾祭天时二人受冻而亡,演绎了一个凄美的爱情传奇。田氏兄弟五人则上演了一场古典式的感恩、忠诚的故事。田大两次来过溪镇,第一次是路上穿烂四双草鞋找到林祥福,送上几年收成兑换的金条;第二次是兄弟五人拉着板车接林祥福回家,田大因病死在路上,兄弟四人拉着装殓林祥福、田大遗体的棺木北上。此外,其他“小人物”也都表现出仁义之举,譬如陈永良的妻子李美莲让自己的儿子替换被土匪绑劫的林百家;“和尚”的母亲善待陈永良的儿子陈耀武;妓女翠萍完成林祥福生前的托付;朱伯崇、徐铁匠、孙凤三等为保卫溪镇壮烈牺牲。这些人物无不展现出中国伦理道德中的一种力量,他们的形象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熠熠生辉,从而形成了《文城》强烈的艺术冲击力。
《文城》中的“暴力”主要是通过场景描写来表现的。暴力主要来自兵匪之乱,尤其是以张一斧为首的土匪杀人越货的暴行。余华是擅长写暴力的,他这次聚焦土匪杀人的情景,描绘了残暴、冷酷、血腥的暴力场景。譬如:“四溅的鲜血让空气里飘满血腥气息,后面的女人看见前面的女人被砍下肩膀、砍下胳膊、砍下脑袋,仍然视而不见地扑向自己的孩子。”①余华:《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第206-207、211 页。土匪还变着花样杀人,方式极为残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描写与余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中的暴力叙事有很大的不同。在《文城》中,余华不再像以前那样努力揭开温情的面纱来表现生命的冷酷本质,用暴力来指向生存的荒谬和残酷,而是让温良与暴力对峙,用后者来映衬前者的温暖和明亮。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余华的叙述态度发生了变化,对温良的渴求以及对暴力的批判已经成为此次写作的重要诉求。
接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余华在《文城》中赋予许多人物如此多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元素?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塑造性格几乎没有变化、没有“缺点”的人物形象显然是冒险的,但林祥福、陈永良等恰恰正是这样的形象。显然,余华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难题。而余华的信心在于他对当下人们精神处境的思考,以及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时代认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余华的复古主义回归,不仅表现在对传统伦理的某种认同,更在于以传统伦理为依傍,重新挖掘出了几乎要被遗忘的壮美情感,以及与之相关的叙事技艺。”②丛治辰:《余华的异变或回归——论〈文城〉的历史思考与文学价值》,《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 年第5 期,第110 页。于是,余华以一种“回归”的创作姿态,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调整现实主义的边界,以挑战的勇气书写历史中的“真实”以及精神世界中闪光的道德元素,并把它们成功安放在当下人们的心灵世界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城》体现出余华小说创作中叙事伦理的变化,也标示出他目前创作的新高度。
三、作为边界的“简约”
简约是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的风格形态。《文城》的简约风格也是其不可忽视的艺术品质。余华似乎并不愿意“抻长”故事,而是以简约作为叙述延展的一种边界,从而形成简约的文本。具体来说,以下三个方面促成了《文城》的简约风格形态。
(一)正文与补记的互文叙事
整个小说分为“文城”和“文城·补”两大部分,我们不妨将之分别称为正文和补记。这两部分各自独立,同时又形成互文,从而有效避免了故事叙述中的枝蔓缠绕,对《文城》简约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小说独特的结构形式。笔者并不认为这两部分的设置是余华故意“创新”而为,而是为了叙述的简洁和顺畅。如果按照当下许多小说的叙事结构安排,余华完全可以把补记拆开插入正文,这样可以使小说因叙事时空交错而显得“复杂”,似乎更具有阐释的空间。但余华不需要这种“技术”,他采用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讲故事。正文部分围绕林祥福展开,家庭背景、偶遇小美、南下寻妻、溪镇生活、客死他乡构成了该部分的主要内容。故事从其童年讲起,至田氏兄弟带其遗体离开溪镇结束,线索连贯、简洁清晰,形成了不延宕、不中断的叙述特征。尽管正文中小美是引发故事发生的人物,但读者与林祥福一样并不知道小美的来历及其来去无踪的缘由,小说并没有变换时空进行插叙处理。小美的故事是在补记中展开的。补记中的故事从小美到溪镇做童养媳开始,通过婆家生活、离家北上、重回溪镇、祭天双亡等事件,叙述了小美一生的命运。补记最后的场景是载有林祥福棺材的板车偶停小美的墓碑旁,田氏兄弟歇脚后继续赶路。从篇幅上看,补记部分不到正文的一半,却补充了林祥福所不知道的关于小美的全部内容。这样一来,正文、补记相互补充,形成互文,大大节约了叙述的笔墨,使《文城》在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内完成了这个复杂故事的叙述。这就涉及长篇小说的“长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批评家指出:“我们检视一个长篇小说时,应该验证一下长度的‘必要性’,验证一下小说的语言、描写、人物等在小说中是否都是必要的。”①吴义勤:《难度·长度·速度·限度——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2 年第4 期,第102 页。在《文城》的创作中,余华的标准更加“苛刻”,似乎在努力“压缩”和“精简”,力求在“必要性”的基础上形成更为简约的风格形态。
(二)小说叙述中的大量“留白”
这些留白主要表现在小说对许多情节的因果关联并不交代,在叙述中留下许多“间隙”。由于大量的留白,使许多读者认为情节设置并不符合逻辑。比如,是什么力量让林祥福放弃家业去千里之外寻找小美?小美在情感上如何能游走在林祥福和阿强之间?再次见到回来的小美,林祥福怎么能容忍她不说明偷金条的原因?在土匪的劫持中,李美莲凭什么能让自己的儿子替换林祥福的女儿?还有其他诸多类似的疑问。显然,余华应该知道读者会有这样的疑惑,但他却执意为之,这自然有其独特的诉求。设想一下,如果余华把这些留白填充丰盈,那就不是现在的《文城》了。毋庸置疑,余华就是想在这些“留白”之处敞开诸多的“不合理”,让有悖常理的情景放置在读者的阅读中。笔者认为,或许我们应该把这些“不合理”放在社会史视野中和发掘传统伦理的诉求中去观照,并结合中国的传统叙事方式理解其合法性。浦安迪认为:“中国的叙事传统习惯于把重点或者是放在事与事的交叠处之上,或者是放在‘事隙’之上,或者是放在‘无事之事’之上。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大多数中国叙事文学的重要作品里,真正含有动作的‘事’,常常是处在‘无事之事’——静态的描写——的重重包围之中。”②[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47 页。余华的这次写作显然故意放大了中国的这种叙事传统——如同凸显中国的传统伦理一样,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城》的简约风格便悄然形成了。
(三)加快的叙事速度
任何一部小说都要求一定的叙事速度,速度的快慢与作家的小说观念、叙事能力等密切相关。与传统小说相比,现代小说的叙事速度相对放慢,“从作家的审美追求来说,在长篇小说表演性、炫技性的艺术趣味里,‘速度’正在沦为一个次要的、过时的美学观念,而从‘速度叙事’走向‘反速度’叙事似乎恰恰成了一种主导性的文体潮流。”③吴义勤:《难度·长度·速度·限度——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2 年第4 期,第102 页。而在《文城》中,我们却看到了叙事的“加速度”。《文城》正文共75 节,补记36 节,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叙事的节奏是紧张的、速度是加快的。在“加速度”的进程中,余华当然不会只在意故事的延展,而是保持着对“叙述”的高度自觉,形成了“加速度”中疏密有致的叙事效果。譬如,小说一开始讲述林祥福的家庭境况、成长经历、父母先后去世、自己几次相亲等,所占篇幅很短,节奏很快。接下来的第3 节小美出场,在这里叙事速度放慢,共用了6 节来叙述小美第一次在林祥福家里生活的状况。接下来小美回来生下孩子又离去的叙述也很简洁,随后小说“加速度”叙述林祥福南下寻妻,即刻又转到了林祥福到溪镇的场景。显然,这种加快的叙事速度成为《文城》形成简约风格形态的重要原因之一 。
可以看出,在书写“真实”的基础上追求简约的叙事形态是余华对文学传统和当下文学观念的一种反思,也是《文城》可以被归属为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证明。综上所述,《文城》所呈现的关于现实“真实”的书写、温良等传统伦理道德的发掘和简约风格形态的追求,都显现了余华这次写作的现实主义表征。其实,在余华自“先锋”转型之后的创作进程中,现实主义的一些元素就一直存在其小说中。正如有的批评家指出:“不论是《活着》,还是与《活着》题材与审美风格不一致的《兄弟》《第七天》,其实都贯穿着对传统的、相对恒定的价值如人、生命、生活、土地、民间、现实、责任等等的演绎与诠释。”④汪政:《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余华长篇小说〈文城〉读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 年第5 期,第86 页。《文城》所呈现的上述艺术特征,可以理解为余华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进行的又一次探索,或者说又一次突破和设置的创作边界,这对于观察余华未来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