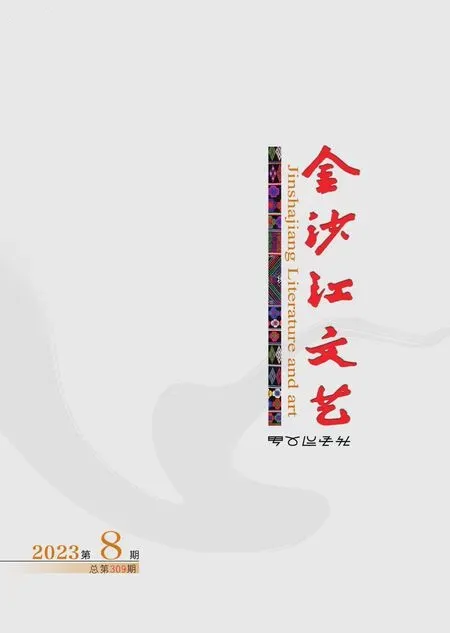艾芜与楚雄
◎ 普显宏 (彝族)
艾芜是云南人民的老朋友,艾芜爱云南,云南爱艾芜;艾芜既是四川人民的骄傲,也是我们云南人民的骄傲。我参加成都艾芜研究学会三年多来,梳理出了两篇艾芜第二次南行的长文和绘制了一张艾芜南行的路线图,知道艾芜三次南行的详情经过,更加懂得中国文坛上不朽的艾芜精神。
艾芜一生三次南行,第一次是1925年,从成都流浪到滇西德宏,后来又漂泊到缅甸、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历时7年,有小说集 《南行记》问世。第二次南行是在1961年9月,也就是在第一次 “南行”后的34年,同行的有老作家沙丁、刘真、林斤澜等,历时6个月,出版了 《南行记续篇》。第三次南行是在1981年2月下旬,在第二次南行20年后,77岁高龄的艾芜应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邀请。这一次与他同行的有老作家高缨、冯永祺等人,又写了 《南行记新篇》。
艾芜第一次南行时徒步经过了楚雄州的禄丰、楚雄、镇南三县;第二次南行时艾芜因患肺结核不能颠簸来回都是坐飞机,从昆明直飞滇西保山,从地理上没有经过我们楚雄州。第三次南行艾芜从昆明坐汽车沿320国道途经禄丰县在楚雄住宿、讲课、开座谈会,到牟定县凤屯公社秧田冲生产队访问。从滇西返回时在南华县吃饭,住宿于楚雄。
艾芜第一次南行时没有写日记,第二次南行留下了部分日记,第三次南行有完整的日记。我从出版的19卷《艾芜全集》中查找,得到艾芜第一次南行时与楚雄州有关的三个细节。
在艾芜散文集 《漂泊杂记》(1935年4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中,有一篇纪实散文——《舍资一夜》,千余字。写1927年仲春,艾芜从昆明流浪到禄丰一平浪舍资驿时,天黑找住宿无着,在点着松明火的街道小酒馆喝酒时遇到一彝族中年男子 (其实是个酒罐)。男子夸下海口 “包住”,艾芜因此还帮男子付了酒钱。结果深夜男子领艾芜回家住宿时,因酒醉连连敲错门,自然闹出了些笑话。最后待男子找到了自己的家时,敲门后老婆也是嫌弃他酗酒臭骂一顿后自然也没有给他开门,结果艾芜和喝醉酒的禄丰彝族男子,就只好无奈在屋檐下睡了一夜。
也是在艾芜散文集 《漂泊杂记》中,艾芜写了一个唱着镇南州 (今南华县)歌谣的中年男人,这篇 《走夷方》的纪实散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1月16日上海 《申报》 “自由谈”栏目上。文章开头作家这样写道:
“男走夷方,女则居孀;生还发疫,死弃道旁。听着暂时聚会的旅伴,拖起漫长的声音,在唱镇南州人唱的歌谣时,轻烟也似的忧郁,便悄悄地绕在我的心上了。跟着他拐下山坡的那一阵,简直是缺乏了走路人应有的力气。”
艾芜在滇缅边境八慕遇到 “走夷方”的镇南州人的时候,年仅23岁,带着好奇心和这个年龄特有的叛逆性格,与镇南人有过一段精彩的对白。
我的旅伴 (一个中年人)说,在清明以前直至去年的九月,这个期间,这里是不缺少晴天的,每天都是好太阳,雨嘛,一滴也瞧不见。现在呢,可就倒霉了,每天总得淋几场雨的。这里的雨,不像汉人地方的雨哪,又毒又可怕 (很容易生病)的。还有那瘴气呵,瘴气!菩萨保佑!
他说到这里,他的周身像突遭袭击一般,简直战栗起来。随即好意地责备我,说是年轻人怎不在腊月间出来,现在来送死么?
我一面听着他的话,一面真见了路上的傣族妇女,多是眉清目秀的,而且有的农家姑娘,竟比汉族女子反要美丽些。便说道,这里的人,不是活得很好么?
这是夷人呀!他大声地驳斥我,随即举出许多汉人在这里中了瘴毒的可怕情形来。我无话可说了,只有用一句话来抵他,即是说,那么,你现在又来夷方做什么呢?
“天哪,这是为了要吃饭,为了要养家哪。”他愁苦地呻吟着。
我因要在言语上战胜他,就微笑地答道: “我不是也同你一样的吗?”
其实,那时我没有家,也不只是为了一己的生活,多半的原因,是由于讨厌现实的环境,才像吉卜赛人似的,到处漂泊去。然而,为了要看看新奇的景物,便来到这么令人丧气的地方,自然心里也不免有些忧郁了。
“那么,你也做我一样的生意吗?”他闪着狡猾的眼睛。
“什么?你做什么生意?”我倒问起他来。
“呃呃?”他不答复了,只是哼着他的镇南州人的歌谣。
后来走到八募原野,经缅甸的便衣巡警搜查时,才晓得他,我的老好的旅伴,是私贩鸦片烟的。倘如早知道,我便要装成他那么一副老成的面容,学他责备我一样,来贡献我的忠告的。但他却由那一次,连同禁物带到牢中去了,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
读着 《走夷方》,我读出了镇南人民在旧社会的心酸和苦难;也读出了镇南人淳朴诚实、吃苦耐劳的性格。
据艾芜第三次南行去牟定访问彝族村寨路过吕合镇时的日记 (1981年2月18日)记载:1927年春天,艾芜流浪到此时曾在吕合街上住过一夜。当时正遇到街上有一家人的女儿结婚办喜事,艾芜怀着好奇的心情参加了这场乡村婚礼,他送给新娘的礼物是一支圆珠笔。我卫校毕业后曾在吕合煤矿职工医院工作28年,经常去赶吕合街,对吕合街的情况非常熟悉。艾芜送新娘圆珠笔,当时应该是非常时尚,算得上是高科技产品。
艾芜第三次南行,于1981年2月17日与高缨、冯永祺同车抵达楚雄,住楚雄州招待所。艾芜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到街上走走。1927年春天曾在此住过一夜,今天已大变了。楚雄现有人口二百五十万,出蚕丝、丝绸缎,出烤烟、香烟,还出盐。”
2月18日一早,艾芜一行到牟定县凤屯公社秧田冲生产队,即现在的凤屯镇飒马场村委会秧田冲彝族村寨访问,彝族是艾芜第三次南行中计划采访的五个少数民族之一,但最后没有写出文学作品。这个秧田冲彝村就靠公路边上,是我当年回牟定老家时的必经之路。前不久我向在牟定凤屯镇工作的文友李登科打探过,艾芜30多年前访问过的彝村秧田冲,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彝族古老民风遗迹。
艾芜第三次南行在楚雄文坛上算得上是大事件,18日下午,楚雄州文联组织城区文艺工作者聆听艾芜和高缨的文学创作讲座。我专门到楚雄州图书馆文献资料室查找过,艾芜和高缨的这次讲课,经整理后发表在1981年的第2期 《金沙江文艺》上,艾芜的约一万八千多字,高缨的一万多字,题目可能是编者加的,艾芜的是《我是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的》,高缨的是 《从艾芜同志的讲话所想到的》,题目的左下方分别印有艾芜和高缨讲课时的照片,但当时的照片印刷质量不好,纸质粗糙,不甚清晰。
18日晚上,据艾芜日记载,州长(应该是我的老乡、已故老州长普联和)和副州长来访,又召开座谈会。艾芜第三次南行有个特点:自称 “威风八面,心情愉悦。”
艾芜第三次南行从滇西返回时,于3月30日一早从大理出发,来到南华县吃午饭。但无从考证在沙桥吃还是在县城吃。按当时习惯,从大理出发到昆明的班车,到南华沙桥刚好是中午12点前后,那时的司机都习惯在沙桥停车吃饭,从昆明到大理的班车也是如此。加之沙桥有享誉滇西的美食 “沙桥三绝”:臭豆腐、酸菜鱼、千张肉,号称小香港。晚上艾芜住楚雄,于3月31日返回到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