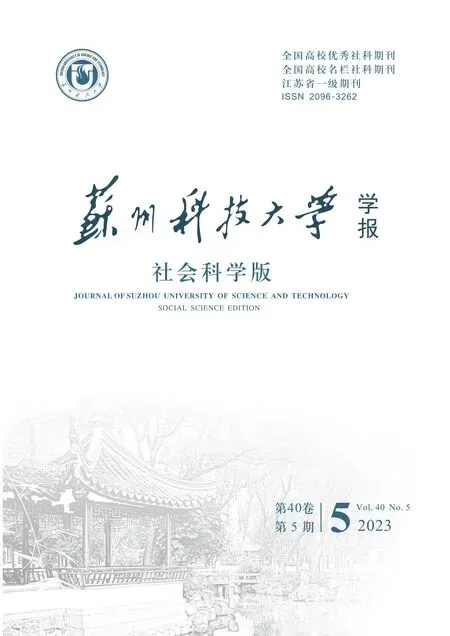景观重建与风雅接续:康熙初期平山堂废兴的文学书写*
袁 鳞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平山堂由欧阳修于庆历八年(1048)创建,并作为扬州重要的文化景观备受世人瞩目。沈括《扬州重修平山堂记》载:“后之人乐慕而来者,不在于堂榭之间,而以其为欧阳公之所为也。”[1]卷38继欧阳修之后,平山堂屡毁屡建,宋代刁约、周淙、赵子濛等人陆续复建,元代平山堂改作司徒庙,明代平山堂再次重建,后经易代之兵燹,至清初仅存故址。平山堂故址“在栖灵寺前,蔓草荒烟,几不可识”[2]。康熙二年,平山堂旧址改建为佛殿。尽管元代已有平山堂改作司徒庙这一先例,但此次废堂为寺的举动引发邓汉仪、宗观、汪懋麟、王仲儒等地方士人的极大不满。康熙十三年,金镇、汪懋麟再度复建平山堂,并建真赏楼用以祭祀欧阳修。平山堂空间变迁带给清初文人迥然不同的地方感受,引发了系列创作活动。那么,何种因素促使平山堂重建活动的展开?平山堂的重建带来了怎样的地方记忆?基于上述问题,我们通过聚焦康熙初期平山堂由废转兴这一个案,探究历史景观与文学书写之间的互动关系,审视后人继轨先贤过程中的创作活动与文化意义。
一、从改堂为寺到建堂增祠
明清易代之初,平山堂虽未复建,但凭借其知名度,依旧吸引文人前来游赏观览。王士禛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的《同诸公访栖灵寺》云:“平山堂外柳如烟,古寺同寻第五泉。”[3]但康熙二年,佛寺扩建则彻底改变其原有形制,“而堂又无复存焉”[1]卷39。与士林精英在清初遭到重创相比,佛教因其独特的宗教空间而迎来发展机遇。“故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皈依者愈众,宗教者人生忧患之伴侣也。”[4]佛教势力不断扩张的同时,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显露。宗观在《修复平山堂记》中大声疾呼:“欧阳文忠公,距今六百余年,中间更废兴者屡矣!而废之久且尽,莫甚今日!寺僧即其址为殿宇,举向之攲楹危槛,参峙于龙蛇漫漶者,湮没无留,而平山堂之名亦亡。”[1]卷39平山堂名实两不存的危机引发士人的忧虑。幸运的是,佛寺侵址尽管带来建筑空间的改易,但未能遮蔽欧阳修所造就的地方记忆。邓汉仪《初冬泛舟游栖灵寺访平山堂旧址二首》其二云:“闻有欧阳迹,风流天下传。少时犹过此,垂老竟茫然。堂址开金像,碑铭坼冷泉。何人轻改作,无乃负前贤。”[5]在感慨之余,邓汉仪将平山堂沦为佛堂的事件告之友人,这也唤起了时人的情感共鸣,如王仲儒《听邓孝威话平山堂遗址》云:“自结维摩室,空传太守名。”[6]251在平山堂沦为佛教场所的十年间,地方士人并非无奈地接受这一现实,而是积极筹划复建活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江都人汪懋麟。
汪懋麟,字季角(1)汪懋麟的字,徐乾学《汪君墓志铭》作“季甪”;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六作“季角”。考其兄兆麟,字公趾;耀麟,字叔定,均源自《诗经·周南·麟之趾》。汪懋麟的字当以“季角”为是,与“甪”字无涉。,号蛟门,又号十二砚斋主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他曾在《平山堂记》中追忆平山堂沦为佛寺的现实:“初堂之废也,余时为诸生,势莫能夺。丁未,释褐。与余兄叔定为文告守令将议复,旋迫于选人去京师五年,而兹堂之兴废未尝一日忘也。”[1]卷39在北京与即将赴任扬州的金镇相遇后,汪懋麟即以重建之事相托:“郡亭形胜枕平山,六一先生政事闲。……但恨林泉僧占取,蜀冈蔓草待君删。”(《送金长真太守之任扬州三首》其二)[7]450不久,因丁忧回乡的汪懋麟亲自参与重建平山堂的活动,他在《同诸子邀金长真太守泛舟游平山因议修复分得堂字》中直言对佛教势力壮大的忧虑:“讵意十年后,浮屠侵我疆。泥佛坐堂上,无复知文忠。致此者谁子?百口罪莫偿。”[7]458在《仲冬平山堂落成太守金公招同诸君燕集即席得五十韵》中,汪懋麟再次重申对佞佛者的鄙夷,凸显其继轨先贤、接续传统的姿态:“此中关典礼,岂独系风雅。……佞佛人情怯,驱僧物议嚣。名山何寂寂,淫祀久滔滔。正气思韩愈,遗书念李翱。”[7]459平山堂的复建承载着汪懋麟排斥异端、复兴礼乐、推尊儒家的政治期待。
除汪懋麟为代表的扬州地方士人的奔走呼吁外,平山堂重建离不开以金镇为代表的官方力量的支持。金镇,字又镳,号长真,崇祯十五年(1642)“举京闱试领解,会鼎革,搜京闱见举者授以官,遂于顺治改元,授山东兖州府曹县知县”[8]。金镇在清初出仕的行为并未影响其声望,时人“以辈刘真长”,赞其“声望大有刘尹之风”[9]4。他与陈维崧、施闰章、毛奇龄、宗元鼎、丁澎、程邃、梅文鼎等知名文人多有交往,且在汝宁太守任上接纳宾客,刊刻何大复诗集,尤其与布衣文人的交往尤为世人称赞。刘中柱《广陵行送金长真太守之任》盛赞道:“元礼之门尽愿登,不嫌座客多衣布。汝宁犹传口碑声,朱幡又指江淮行。”[10]这一好古崇贤的品质为金镇与当世文人的交往打开了局面。他到任扬州后,凭借自身的文艺素养,积极与淮扬地方士人建立联系。孙枝蔚《赴金长真太守宴赋榭》云:“笔墨事寻兵过后,管弦声验岁丰时。终朝未减论文兴,高会还酬贺雨词。”[11]531通过题下注“郡中孝廉文学同宴者十六人”以及诗歌内容,我们既可以感知主宾之间觥筹交错、论文作词的场景与融洽的关系,也可以看到在动荡现实的衬托下,金镇为政之余的文采风流赢得扬州人士的由衷认可。
金镇的循吏风范使他能够应对现实的动荡环境,与生俱来的名士气质又令他在文教事业上用力颇多;因而在积极安抚民众的战争恐慌情绪之后,平山堂的重建也随之提上日程。金镇《重建平山堂记》载:
夫一堂之兴复,微耳!然人情欣欣,若以为事之必不可少者,何也?方今东南不幸多事,吴越之郊,一望战垒。……扬以四达之衢,吾得与二三子保境休息于此,里门晏开,守望不事,四方之结毂而至者指为乐土。此非大幸耶?当此之时,而使前贤之名迹缺焉湮没,至废为梵钟灯火之场而不恤,既非所以称为民父母之意,揆之人情亦必有郁然不乐者也。[6]199
金镇通过扬州平山堂的重建示人以暇,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也积累了顺应民意、重振文教的政治资本。基于平山堂屡建屡废的历史,金镇、汪懋麟并不满足于实体景观的再现,祛除这一景观曾经的宗教色彩,而是尽可能延展景观所具有的儒家教化意义,在平山堂后修筑真赏楼用以祭祀欧阳修等名宦亦出于同样的动机。汪懋麟《平山堂记》载:“(金镇)又嘱余拓堂后地,为楼五楹,名真赏楼,祀欧阳公与宋代诸贤于上,皆昔官此土而有泽于民者。堂下为公讲堂,左钟右鼓,礼乐巍然,所以防后人不得奉佛于斯也。”[1]卷39增设祠堂、祭祀名宦这种仪式化的活动强化了重建行为的文化价值,也为当时以及此后的扬州官员树立了榜样。“已经中断的、仅留下痕迹供人触摸的前历史对于一个后来者的时代说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当这个后来的时代把那个过去当作它自己时代的规定性的基础加以认可的时候。”[12]金镇、汪懋麟借助祭祀欧阳修来彰显扬州名宦传统,并使其与现实政治产生密切联系,平山堂俨然成为接续崇儒重文地方传统的一个重要支点。
相应地,汪懋麟有意回避平山堂作为休闲娱乐之地的旧有印象,将其塑造成欧阳修为政讲学之地。汪懋麟《平山堂记》云:“老、佛之宫充塞四境,日大不止金钱数千万,一呼响应。独一欧公为政讲学之堂,亦为所侵灭,而吾徒莫之救,不甚可惜哉!”[1]卷39关于欧阳修在平山堂为政讲学一事,尚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不过,伴随着平山堂重建,“堂下为讲堂,额其门曰‘欧阳文忠公书院’”[13]379,推广教化、振兴文治的意图据此获得了空间的依托。面对“佞佛人情怯,驱僧物议嚣”的现实,建构欧阳修在此为政讲学的历史记忆,显然有助于强化官方重建活动的神圣性与严肃性。这一点也充分反映在时人笔下,如“鼓钟新俎豆,天地入帘栊”(许承家《金镇太守兴复平山堂落成讠燕集纪事》)[6]230、“星辰垂静院,礼乐示僧寮”(许虬《金镇太守兴复平山堂落成讠燕集纪事》)[6]225,从诗中“俎豆”“天地”“礼乐”之间的呼应关系足见平山堂的出现所赋予地方的崇高感。尽管在后人看来,这样的举动并未获得恒久不变的影响力,佛寺与平山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旧保持了共存关系,但在当时却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在“东南多事,一望战垒”的现实语境之下,战争成为时代的主题,武人较之文人更易在波谲云诡的时代环境下脱颖而出,而这一阶段捐纳制度的开启更加剧了现实矛盾,“会甲寅、乙卯间,滇南用兵饷不给,今得入资补官,于是正途益壅”(邵长蘅《进士王东亭传》)[14]。从平山堂重建的时间节点来看,官方主持平山堂的重建以及雅集活动,寄托着士林精英的道德期待与价值追求,营造出礼乐接续的氛围,有助于消弭战争带来的紧张氛围,实现人文精神的重振。由吴嘉纪的诗句“岂惟山泽荣,士气亦已扬”(《赠金长真郡牧》)[1]卷30可见平山堂重建行为的象征意义。
平山堂的重建为文人展开历史想象提供了重要空间,同时也强化了名宦之于地方的重要意义,因此金镇作为平山堂重建活动的主持者得到后世的高度肯定。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康熙间,土人以王文简公从祀真赏楼。雍正间,以金公及蛟门从祀。”[13]382那么,金镇如何在历史上众多重建者之中脱颖而出,被历史所铭记?作为平山堂雅集活动的接续者,他较之前人又留下哪些文学记忆?下面我们聚焦这一时期与平山堂相关联的作品,回到文学活动的创作现场,分析“文章太守”(2)欧阳修曾以“文章太守”赠扬州太守刘敞;苏轼《西江月·平山堂》之“欲吊文章太守”句,将“文章太守”与欧阳修相联系。此处“文章太守”意指欧阳修。这一历史记忆是如何被唤起,同时又如何将这一记忆与雅集组织者相联系的具体过程。
二、“文章太守”的异代回响
长期以来,欧阳修被视为人臣典范。他不仅在政治层面为世人所认可,其一代文宗的地位也容易为后世官员效法比较。其中,金镇即被视为欧阳修风雅活动的继任者。“国朝康熙癸丑年,山阴金镇来守此土,同郡人议复先贤古迹,仍于寺右建造平山堂,其工落成之时,而江北江南皆称胜概,真数百年风流太守今犹在也。”[15]这一表述虽不无溢美,但一定程度上说明平山堂重建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不过,仅仅通过重建景观、接续祭祀传统来确立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并非易事。始建者欧阳修定义了平山堂的空间意涵,也为后来者带来了无形的压力。我们很容易在众多对前贤的模仿者中找到一些弄巧成拙的例子。对后来者而言,如何处理好自己与前贤之间的关系,显然需要一定的智慧与恰当的机缘。
作为守土官员,金镇对自身所承担的文教角色有着清晰的定位,一方面显示出致敬先贤的态度,“太守师欧公,缔构光遗范”[6]219;另一方面则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地方文坛,明确自身在平山堂历史空间中的文化地位。他在平山堂“勒欧阳公《朝中措》原词,使坐客续其后”,并作《朝中措·平山堂次欧公韵》:“烽烟钟磬总成空,往事夕阳中。重构雕甍画槛,还他明月清风。 庐陵杳邈,千年此地,精爽还钟。留我名山片席,迭教做主人翁。”[1]卷36从“主人翁”“还他明月清风”等语可以看出金镇追溯风雅的自觉意识、以欧阳修继任者自居的强烈信号。
金镇在扬州期间广招宾客,组织雅集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平山堂不仅是欧阳修命名并主持修筑的观览之地,也是其诗酒互动、汇聚嘉宾的重要空间。金镇效法欧阳修,实现了诗酒风雅的接续,而平山堂重建伊始就被寄予厚望。邓汉仪《孟秋陪金长真郡伯游平山堂议复故址分韵得风字》云:“重种我杨柳,重植我芙蓉。重还我山色,延客倾酒筒。庶几复旧观,千古美画熊。”[6]223平山堂竣工更是将文人雅集推向了高潮。汪懋麟《赠扬州知府金公序》云:“取材于官,募役于工,不征一钱,役一民,阅月而堂成。成之日,大召宾客,车马满山谷,远近来观者千余人,咸谓数百年无此事矣。”[7]259据此可见平山堂重建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事实上,上述记载仅仅是众多雅集中知名度较高的一次,金镇于平山堂重建前后主持的雅集活动,明确可考者就有六次之多(见表1)。

表1 平山堂重建前后金镇主持雅集活动情况
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平山堂的重建汇集了不同地域、不同政治身份的文人,其中既有诸如曹溶之类的贰臣,又有以邓汉仪、孙枝蔚、吴祖修为代表的遗民布衣,亦有以汪懋麟、宗观、徐乾学为首的新朝官员。无论是从雅集的规模还是从频率来看,平山堂都俨然成为扬州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据点。金埴“从祖廉使公长真镇,由孝廉康熙癸丑守扬州,时司李王公阮亭方迁官,而公至乃大修平山堂,张淮南诗宴,六七年不怠。南北名士投贽者,多被延接,罔弗各如所欲”[9]3-4。金镇爱才好士的风范使其与周边文人建立起紧密关系,尽管他在扬州任期不满一年,旋即升任江南驿盐道、江南按察使,但平山堂仍旧是其屡屡驻足宴饮的场所。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看,大规模的文人集聚于此,上演了一幕幕同题竞胜的生动画面。周在浚《金长真太守兴复平山堂落成讠燕集纪事》云:“上客词题凤,新声气射蟾。论文矜奥博,索句斗尖严。电扫事无滞,风流政不嫌。”[6]238这些具有不同阅历的文人通过平山堂的重建得以集聚,借助文字打消政治身份的区隔,获得情感交汇的诗性空间。“大型古迹(如长城、故宫或某些古战场)的保存使参观者容易产生置身于历史现场的沉浸感。同时,与小件纪念品不同,它可以集体观看,有利于参观者产生精神的共鸣。”[16]从文学发展的视角来看,平山堂重建前后,一连串的文酒之会激发出诗人呈才献艺的内在渴望。这种对往日的追溯与风雅想象也激发出诗人当下的创作热忱,如龚贤《金长真太守兴复平山堂落成讠燕集纪事》云:“主人贤太守,宾从旧词场。杜许留题咏,欧苏实播扬。”[6]226在平山堂雅集的参与者看来,主宾再现了昔日的风雅景象,实现了文脉的接续。
除复现原有的文学情境外,拥有官方身份的金镇组织雅集难免会被从政治角度予以审视。遗民魏禧、孙枝蔚借助文字参与到平山堂的复建过程中,显示出对官方这一行为的认可。如魏禧《重建平山堂记》云:“公既修举废坠,时与士大夫过宾饮酒赋诗,使夫人耳而目之者,皆欣然有山川文物之慕。家吟而户诵,以文章风雅之道,渐易其钱刀驵侩之气。”[6]201这样的论断固然带有理想化的成分,但精神上的自我澡雪最先在雅集亲历者身上有所呈现。孙枝蔚《观察金长真以丁巳八月十三日祀欧阳子于平山堂招客赋诗予亦与焉诗限体不拘韵》云:“继起惟金公,瓣香何其虔。构堂复筑楼,木主设中间。思齐诚无怠,化俗亦有权。重来摄盐政,俎豆最拳拳。曰闻古名臣,英灵长在天。虽当人代换,魂魄恋山川。胜友况云集,文词总翩翩。迎神神所喜,旷世成周旋。祀毕还觞客,令名各勉旃。”[11]543-544在诗坛同人看来,平山堂的复建不独为诗友云集提供支撑,也再次光大了扬州的名宦传统,诗中“祝毕还觞客,令名各勉旃”的砥砺态度凸显出景观重建背后的教化意义。
除振兴文治之外,一连串突发事件更彰显出金镇的循吏风度。与承平之际欧阳修的闲逸自适相比,金镇在三藩之乱背景下组织的文人雅集被赋予了沉重的时代底色。“然为此于万难倥偬之际,比之前人创建之日,其势尤有不易者,非诸君子之协力交赞,即予亦何能借手以告成哉!”[6]200此时席卷半个中国的战乱与淮扬地区突发的水灾吸引着诗人的目光。周在浚《金长真太守兴复平山堂落成讠燕集纪事》用沉重的文字书写出追步风雅背后时世的艰难:“每叹江南地,民方汤火火寻。流离悲涸鲋,诛责到孤鹣。岂不谋生聚,无如困米盐。维清崇化理,解网罢髡钳。”[6]238其中的感慨亦可与遗民吴祖修的同题之作相对照:
谁知太守乐,孰谓醉翁迂?在昔堪师表,于今复楷模。……高宝冲难筑,黄淮决欲枯。波臣嗟助虐,赤子坐何辜!枉复沉圭璧,空劳掌泽虞。恳蠲渔户税,力缓火田租。目击流民惨,亲为郑侠图。丁男苏转徙,亥老免泥涂。杀气缠滇粤,妖星扫浙吴。索铃朝几撼,羽檄夜还驱。……邮亭抄白饭,传舍饲青刍。顷刻征千骑,咨嗟办百须。六时忘寝食,一昔白头须。[6]242
尽管为宴会应酬之作,但诗人将战乱、水灾等时事融入其中,列举金镇治理地方时在蠲渔户税、缓火田租等方面的具体举措。这些纷乱的时事进入诗人雅集的叙事话语,为宋代开启的以消闲遣兴为底色的平山堂雅集注入了新的时代主题。与欧阳修为政宽简相比,金镇在扬期间鞠躬尽瘁,舒缓民困,这一时期围绕平山堂的书写活动并不全因文人好事的传统及其逸乐需求。文学上的雅人风致与政治上的循吏风范看似矛盾,却共同构成平山堂文学空间的多重精神向度。金镇在文学活动上的投入以及地方治理的成绩,使他不愧于“文章太守”的声誉。
在昔易而今难的时代语境之下,平山堂的复建提高了金镇的文坛声望。吴绮《臬宪金公寿序》称赞金镇:“如一麾于汝水,重新大复篇章;方再莅于平山,更大庐陵堂构。”[17]即便在离任之后,他与扬州文坛依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除仕宦间歇在此组织诗酒唱和之外,一些平山堂雅集的参与者转而成为他为官南京期间的座上宾,如孙枝蔚《赠金长真观察》云:“钟山引领平山近,何幸追随两处同。”[11]592从中不难看出,平山堂的重建已经成为金镇为宦生涯的一个重要事件,而在扬期间诗酒唱酬、爱才好事的风度操守,早已内化成为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并在异地再次上演。施闰章《金长真诗序》云:“公秉节金陵,于官无壅滞,乃从羽檄驿骚之余,嘘枯拾烬,间集贤士名人,文酒谈宴,且侧身与布衣游,酒酣月出,清风洒然,觉王谢声华未歇,亦一盛也。”[18]金镇移官外任后,身在扬州的汪懋麟则自觉延续了这一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平山堂依旧对布衣寒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汪懋麟《人日同诸子游平山堂大雪骤至饮真赏楼走笔得四十韵》云:“接席皆仙客,逃名半隐沦。争先持玉斗,攘臂劈银鳞。势欲倾三峡,欢堪抵一旬。交原垂发好,饮是布衣真。慎勿言通塞,何须辨主宾。”[7]551与金镇的官员身份不同,作为本籍人士的汪懋麟与诸多布衣寒士的交往,更增添了乡邦之间的温情。也正是文人之间的接力,推动了地方文脉的赓续。
总之,金镇通过复现景观、征求文字推动雅集活动,强化了自己与扬州文人集群的联系,提高了平山堂在扬州诸多景观之中的文化地位,扬州地方士人之间的联系亦随之增强。如果考虑到这是政局动荡时期的产物,我们或许更能感知其不易。与历史变迁的偶然性与残酷性相比,文化传承活动则体现出一种别样的韧劲。
三、平山堂重建的文化意义
平山堂的重建获得了士林精英的关注,也就此形成一系列极具向心力的创作活动。人地关系随着景观的复现而调整,暂时的建筑与永恒的诗意并存于平山堂的文学书写之中。这种对前人的步履追随以及风雅相继的竞胜心态,不断赋予着平山堂以纷繁多样的文化意义。
首先,平山堂重建的文学书写见证了明末清初社会由乱到治过渡背景下的诗人心理变迁轨迹。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19]明清之际,平山堂因战争遭到破坏,而诗人对这一景观的书写,也多带有着凝重感伤的时代情绪。龚鼎孳《早春友沂招同孝威园次仙裳定九诸子由天宁寺桥泛舟至平山堂踏草记事五十韵分得虞字》云:
国破迥鸿雁,林昏响鹧鸪。鬼吟清露柝,僧拾绛罗襦。残院鼠行饭,暝烟樵负刍。磷荒丛断碣,雾重隐鍪弧。不唱安公子,能悲宋大夫。萧条双屐在,容易六朝徂。纵饮全关世,伤心欲讳儒。途偏穷鲍谢,命总薄黄虞。[20]
在诗人笔下,平山堂的繁华景象已成为明日黄花,诗中“残院”“断碣”等废墟景观迎合诗人内心的衰飒心境,使诗人的消极情绪有了集中发泄的可能。这些平山堂历史的见证者,并非机械记录平山堂的毁弃,而是通过对空间的文化想象展现出明王朝覆灭带来的创伤体验。
伴随着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清廷的统治愈发稳固,易代之变残存下来的历史痕迹逐渐消散。李国宋《平山堂新成》云:“劫火寒冈三十年,栖灵寺外草芉芊。堂成忽觉诸山近,野阔低看落日悬。青陇马盘高冢路,红桥人醉木兰船。沧桑不改前朝迹,只有扬州第五泉。”[6]244-245平山堂重建行为改变士人观看景观的方式、遮蔽易代记忆的同时,也为诗人提供新的书写语境。盛符升《平山堂中秋燕集奉酬金长真观察二十四韵》将亲密无间的宾主之乐抒发得淋漓尽致:“酬和倾豪俊,文酒留余欢。胜事每遥集,词人乐比肩。千秋此登赏,丽藻尤芊绵。地以高贤重,文缘嘉会传。堂前忆杨柳,风流足后先。”[6]251此地诗酒交融的快慰覆盖了以往肃杀哀怨的时代情绪,表现出风雅相继、比肩古人的内在心理。正如梅尔清所言:“通过诉诸前明精英认同的要素,他们消除了记忆中的灾难,为共享的欢乐和仪式扮演重建了共同的空间。”[21]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前明的留恋与悲情的抒发已不再是文学书写的主流话语,平山堂重建以及雅集传统的接续更新着诗人的地方记忆与情感体验,景观本身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其次,平山堂重建的文学书写体现出先贤人物与后来者之间的文化联系。古迹兴废各不相同,但任何建筑在岁月面前,都不可避免地显示出其脆弱性,况且景观自身也并非不可替代。“平山堂风景固佳,然全国中似此者,要不可以缕指数,终属以人传者耳。”[22]因此,欧阳修无疑是实现古今关联的重要节点。正如汪懋麟《同友人泛舟游平山新堂各赋四首》所云:“堂成群望惬,胜赏众欢同。……五百余年后,依稀六一风。”[7]463通过景观重现、诗酒雅集等行为的效法,实现人文传统的接续。他们的创作难免增加些许传递者自身的色彩,亦无不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这似乎是续写景观过程中常见的一种现象,而正是通过文化的累积与传递,古人与今人的对话得以延续。
不过,继欧阳修之后,莅临平山堂、重现主宾之乐且能够彪炳史册者可谓寥寥,“开辟真难为”的现实似乎消解了后来者比肩乃至超越古人的可能。对于这种面对前贤时的无力感,与金镇共同主持平山堂重建的汪懋麟有切身的体会。其在《六月七日泛舟登平山堂作歌同宗鹤问孙无言豹人穆倩孝威仙裳汝受陶季仔园龙眉家兄叔定》中坦言:“真赏楼中坐六一,俎豆只可眉山并。后贤不敢妄窥觊,揶揄何物空彭亨。诸公大笑急命酒,酒杯落手千忧轻。”[7]485幸运的是,金镇、汪懋麟及其同人并未被历史遗忘,他们重建平山堂、纪念欧阳修的举动引发了时人的关注,也引起后来者的模仿。此后,卢见曾、伊秉绶、李彦章、方濬颐、欧阳正墉等扬州官员在不同时期陆续修筑三贤祠(后增为四贤祠)、六一堂、六一祠等景观,并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续写了类似的纪念活动,实现与古人的对话,扩大自身在地方文坛的影响。从这一现象背后可以看出,扬州社会对于一代文宗欧阳修的崇敬程度,以及后来者在强化自己与欧阳修之间联系所做出的努力。作为有清一代平山堂首次复建的主持者,金镇自然具有独特意义。晚清两淮盐运使方濬颐在其《平山补柳图为僧雪航题》中追溯金镇复建之举云:“吾辈须学金长真,莫使前贤遗址逸。行春台共真赏楼,醵金农隙工先鸠。”[23]建筑的毁灭与重建给予见证者以新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又不断地刺激并推动着后来者创作行为的发生。平山堂所具有的精神资源吸引着来自商界和官方的赞助人,名贤接续、风雅相继的地方传统亦随之接续。
最后,平山堂重建的文学书写折射出文人对不朽话题的再度审视。在扬州留下深刻文学印记的文人中,欧阳修别具代表性。郭振遐《游平山堂诗八首》其四云:“纵眼东南望,芜城压柳阴。朱甍藏锦瑟,碧树弄文禽。歌吹词人梦,繁华帝子心(谓隋炀帝)。何如仿六一,棋酒与书琴。”[24]与昔日徘徊于此的“歌吹词人”“繁华帝子”相比,欧阳修“棋”“酒”“书”“琴”的雅致生活与为政清简的行政作风更为士大夫所接受。与之相比,在政事与文学上皆具争议的隋炀帝自然成为参照对象。孙枝蔚《汪季角舍人与令兄叔定招同程穆倩邓孝威宗鹤问陶季深华龙眉范汝受王仔园家无言泛舟至平山堂登真赏楼,楼有欧阳公木主,与诸子展拜既毕乃饮酒堂上,各赋七言古诗一首,时予初归自豫章幕中,登览唱和之乐二年来所未有也》亦云:“高处忽令怀抱宽,隔江山色青如旧。古人亦赖文章力,盛名不隔往来宙。炀帝何曾有宫殿?欧公俨若在左右。至今真赏迹仍留,坐久何劳笙歌侑。诸君努力争千秋,如欧继韩为时救。”[11]544孙枝蔚亲历了易代之变,对政治的脆弱一面有着切身体会。与隋帝宫殿沦为遗迹相比,欧阳修的平山堂则屡毁屡建,获得了超越时间的可能。尽管欧阳修在此也有过传花饮酒的风流传说,这固然迎合文人追求逸乐的天性,但并非后世文人从平山堂获得价值认同的关键所在。后人对平山堂的阐释是通过对欧阳修一生为政兼为文的整体观照来实现的。欧阳修凭借道德风范与文学修养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他所创建的平山堂成为触发历史记忆的媒介所在,而这种自发形成的历史记忆,恰恰是权势与金钱的掌控者难以企及的。孙枝蔚对隋炀帝与欧阳修一褒一贬的态度背后,未尝不是诗人对“权势与文学何者具有更强生命力”的回答。
孙枝蔚对隋炀帝、欧阳修优劣的评价,既是自身价值取向的体现,也不妨将其视为预言来看待。继隋炀帝到扬州之后,康、乾两帝的南巡同样凝聚了时人的目光,帝王的驻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宫建筑、诗文碑刻,将颂扬盛世的时代风气推向了高潮。时过境迁,帝王在扬州的风流事迹再度成为明日黄花,“天(章)藻被,御座云拱;飏荣竦华,罔敢勿恪。然而土木之陊剥,鸟鼠之穿漏,高台或倾,芳草如积;不能常新榱桷,无损丹臒,亦其势也”[25]。扬州帝王印记的消散再一次显示出政治权势的脆弱。相比之下,即便经历太平天国兵燹,平山堂依旧得以重建,并再度成为扬州诗酒唱和、风雅接续的重要场所。在欧阳修之后,平山堂尽管凝结了不同文人对历史的装点与想象,折射出彼时社会中的文化期待与道德认同,但一以贯之地向世人展示出欧阳修之于这一景观的独特意义,以及受此滋养之后生生不息的文学世界。
四、结 语
康熙初年平山堂的重建,不仅是扬州地标性景观变迁的历史节点,也造就了欧阳修接受史上令人瞩目的文学事件。平山堂的重建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佛教侵址令扬州士林深感失落,具有复振礼乐文化的紧迫感,而金镇的雅人风度又为重建活动提供助力。平山堂重建将欧阳修召唤到清初文坛之上,使得历史记忆与当下情感混同交互,历史得到重新审视,也引发时人的广泛关注与情感共鸣。 当然,景观的价值并非局限于建筑实体之上,还需要通过文学书写的方式实现记忆传递,获得更为广泛而持久的认同。与元、明两朝的冷落相比,平山堂的文酒之会在清代再度兴盛,平山堂成为扬州首屈一指的文人雅集胜地。这一现象的出现与金镇、汪懋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通过重建景观强调自己与古人的联系,通过雅集行为完成风雅故事的再现,以期通过创作获得比肩前贤的不朽声望。在此举行雅集文会促进了扬州祭欧活动的开展,为后来者追寻古人的步履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样本。
平山堂的重建使我们看到扬州外来官员与本土士绅在振兴文教事业上的热忱,这种超越官职品阶与政治立场的交往模式唤起了他们的文学书写热情。在此过程中,欧阳修之于扬州的意义得以唤起,而重建平山堂的推动者与见证者,凭借自身的文化权力为后世认可,同欧阳修一起置身于平山堂这一永恒的文学殿堂。
——兼议古代平山堂由大明寺代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