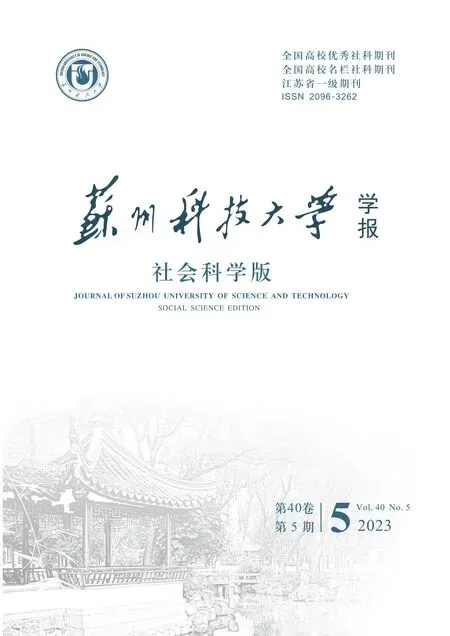风景叙事与澳大利亚早期民族认同的建构*
苏锑平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在读图时代,风景叙事对部分读者的耐性是一种挑战,而在学术界,“风景成为流行的研究主题”[1]。自20世纪70年代风景研究体系建立以来,风景研究基本沿着“心理—象征—(权力)媒介—记忆—身份认同”[2]的方向迂回前进,而风景叙事从一开始就得到借用、引证、阐发。温迪·达比(Wendy Darby)的《风景与认同》(2000)较早提出风景叙事的民族认同功能,她指出浪漫主义风景叙事弥合了英国的认同裂缝,建构了英国的民族认同。[3]84风景叙事通过指涉、隐喻和话语操控[4],可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认同和身份意识,建构民族的共同记忆[5]。风景叙事也能与风景塑造形成互动,重构民族认同。[6]然而,爱班森(R. Ebbatson)在《想象的英格兰》(2005)中却指出,风景叙事不仅是认同的标志,还是差异的标志。[7]譬如,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小说中的风景叙事强化了苏格兰的地方认同,模糊了“英国性”[8]。综而观之,现有研究大多肯定风景叙事的民族认同功能,侧重研究已有民族意识的国家,如英国、爱尔兰、美国等,而对于新兴国家如澳大利亚的研究付之阙如。澳大利亚殖民时期文学被贬称为“游记文学”,风景叙事是其最重要的特色,笔者拟探讨澳大利亚“游记文学”中的风景叙事对其民族认同的建构。
一、领土:作为拓殖者的风景叙事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认同的起源有三个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和权力语言,三者重合使一个新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但它们只是必要条件,想象共同体的生成还需要能将三者黏合起来的媒介,而风景就是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之间进行交换的媒介。通过观察者的凝视或叙事者和读者的文学体验,“用他们熟悉的方式将想看到的,甚至为了自己的需要或目的将几无差别的风景建构为想象的风景,即‘乌托邦表演’”[6]。深谙“乌托邦表演”技巧的英国人从登陆澳大利亚那一天就开始了他们的“表演”,将所看到的和所想象的风景再现纸上,广为流传。
沃特金·坦奇(Watkin Tench)的《植物学湾远征亲历记》(ANarrativeoftheExpeditiontoBotanyBay)就是帝国权力在澳大利亚的首次表演。它被称为第一部向英国读者描写澳大利亚及居民的作品,同时也是澳大利亚第一部国际畅销书。[9]坦奇的著作并非旅行途中有感而发,而是在出发之前就计划好,并且已经联系好了出版商。他的写作也有明确目的,“既想让读者感到愉悦,同时也向读者提供信息”[10]i。坦奇的这种行为深深扎根在英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即“某一时间在某一特定共同体里需要说什么和可以说什么早已被预设”[3]69。
坦奇不厌其烦地记载每一个经过的地方的经纬度,比如他在第十章写道:“在总督的委任状中,这个政权的管辖范围涵盖南纬43°49′到南纬10°37′,这是‘新荷兰’(指澳大利亚)大陆的最南点和最北点。从经度看,它从格林尼治以东135°一直往东包括太平洋上述纬度范围内的所有岛屿。”[10]66他试图客观公正地描绘新殖民地的风景,不仅仅为“满足时下人们的好奇心,更想为将来的冒险者指出这个殖民计划的优点以及在此殖民过程中所伴随的不利情况”[10]i。坦奇在序言中声明,他采用原貌呈现法,以地图学家简笔画的方式真实地勾勒这个新的殖民地。因此他的写作不同于一般游客的观光旅游或本地居民的风景体悟,他对自然风光的描述不多,也很少发表感慨,目的只是要保证其客观公正地呈现原貌,而不附带个人情感。在整本书中,坦奇都保持着克制,只是把他所看到的冷静地记录下来,告诉读者殖民地所发生的一切,让公众去评判谁对谁错。因此,即使当渴望已久的范迪门海岸进入他们的视野,作者也只这样表达:“在这趟非常独特和辛苦的差事中,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憋闷,我们对近在眼前的新鲜景象激动不已,这用不着奇怪。”[10]42叙事者完全没有初到异地的好奇与惊喜,或者说他在刻意压制这种情感,因为作为大英帝国的殖民代表,叙述风景是他的工作。他就像土地测量员一样,做的是纯粹的记录工作,他只是在编撰又一部《末日审判书》(DoomsdayBook),或者说是在跑马圈地。坦奇与其后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一样,“在用文字来参与帝国的自我再现时,显然都采用了一种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态度”[11]。
坦奇对人类活动的记录则采用了二元对立的结构,一方面强调殖民活动对风景的建构性,另一方面则强调土著活动的自然性。比如作者对殖民者与土著的交往、杰克逊港的安营扎寨、地区法庭和公开审判程序的报道、国王生日纪念宴会、公共建筑的建设等等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就像一个熟悉透视法的风景画家,用透视的目光从画面之外或画面之上观察一切,用经受过教育熏陶的手和眼睛建构、接受和诠释殖民者所建构的风景。而对当地环境的描述则强调“大自然的那种单纯自在、毫不修饰的存在”,强调土著活动的自然性,在关于土著的描述中多次强调:“除了防御武器和几种粗笨的石斧,他们的创造才华局限于制作一种小网兜……他们绝对不晓得耕种土地这回事,食物完全依赖于他们收集到的少量果实,在沼泽地上挖出的草根,沿海捡到的以及驾着小划子用标枪费尽心机扎来的鱼。”[10]76-94
直至20世纪末,西方世界都有一个源于洛克的“财产权”的法律原则,即未被占领或未按欧洲法律认可的方式去使用的土地就是无主土地。[12]作者通过对比殖民者的建设性与土著的自然性,按照欧洲法律认可方式宣示对土地的占有。通过这种对立性的表征,叙述者对澳大利亚风景完成视觉、心理和法律意义的占有,把原本中立性质的自然变成具有人文意义的风景。通过对风景的想象和再现,民族文化记忆实现了对风景的文化占有。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游记是纸张上的拓殖,阅读游记则是英国人纸面拓殖的狂欢。坦奇的风景叙事“体现了帝国对征服土地的优越感和控制力。这种帝国的凝视充满了权力的意味”[13]。
风景一旦成为被再现的对象,就具有了主体意志建构的功能。坦奇出色地完成了大英帝国交给他的殖民任务,他在作品中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思维昭然若揭。为了支持和维护世界征服者和文明使者的形象,他充分调用道德、文化和种族优越性等意识形态来支撑其阐释活动,通过贬低澳大利亚的原生风景而自觉不自觉地拔高殖民者的建构风景,从而构建排他的殖民者认同。
二、景点:作为游客的风景叙事
英国有深厚的旅行传统,而异地旅行刺激着人们的表达欲望,这一点明显反映在文学上,从笛福(Daniel Defoe)、菲尔丁(Henry Fielding)、约翰逊(Samuel Johnson)到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司各特(Walter Scott)都是如此,风景叙事是其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早期文学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因为殖民早期创作者不是英国囚犯就是英国移民,陌生的环境并未冲淡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因此,风景叙事就成为澳大利亚殖民时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植物学湾远征亲历记》是其开篇,之后游记、诗歌、小说则是这一特色的延续与细呈。
巴伦·菲尔德(Baron Field, 1786-1848)是第一位描写澳大利亚丛林风光的诗人,其后温特沃斯(William Charles Wentworth)、汤普森(Charles Thompson)等也致力于澳大利亚风光的描绘。罗克罗夫特(Charles Rowcroft)和哈里斯(Alexander Harris)等人的小说对澳大利亚新奇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异国趣闻、安身立命的手段等情有独钟,写景多于叙事,状物多于写人,人物就像司各特小说中的主角一样,只是穿针引线的工具或介绍风光奇闻的导游。
所谓风景,是要经过一种眼界的确认和情感的解释才能叫做风景的。澳大利亚殖民初期作家笔下的风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英国影子,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是英国文学的延续,是英国浪漫主义风格的延伸,“而且在观念、视角、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深受英国传统的影响,对澳大利亚风景的描写更像是对英国风景的复制,无法对澳洲的风土人情进行真实、细致的刻画,更不能做到真正地反映澳洲本土特色”[14]。这个特点体现了这些作家一种典型的游客身份,一种局外人的视角。
早期诗人与小说家几乎都出身于英国上流社会,英国的精英教育造就了他们一双英国式的眼睛。这是一种深度格式化的观看方式,来源于英国传统的风景观看方式。他们将风景的细部整合成一种对世界的观照,用深奥的观念来解释他们的感知。他们对风景的关注不是来自能够传达感官印象的“事实风景”而是“象征风景”(landscape of symbols)。“古典教育形成的文化感知和价值观,最终在具体的风景中得以体现。……教育和旅行相结合强化了18世纪牛津和剑桥精英们根据绘画和文学将风景理智化(intellectualize)。”[3]2718世纪的最后十年间,风景作为文化的表达,无论是通过再现还是旅游,都已经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以及模仿他们的人中间广为流传。随着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借助于多种媒介特别是印刷品的再现方式,这些文化精英赋予风景以文化意义和民族象征,在风景与民族主义的联姻中使风景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风景。
澳大利亚殖民早期的风景叙事就深深植根于这样的文学传统之中。在澳大利亚殖民早期文学中,风景的英国风其实是诗人与小说家这种格式化的观看方式所决定的。风景被他们“理智化”了,他们所看到的是一种“象征风景”而非“事实风景”。他们的诗歌在赞美澳大利亚风景的同时会把他们的感情与英国或“大不列颠”联结在一起,而在讴歌不列颠的同时又拔高了澳大利亚的风景。菲尔德的诗歌《袋鼠》(“The Kangaroo”)就是这样一首得到较高评价的早期诗歌,用英国的颂歌来歌颂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袋鼠,他开篇写道:
袋鼠啊,袋鼠!
澳洲自有的精神!
从原始的荒芜之中,
历经失败而重振。
地球第五大陆的创造,
就此得到验证,
这更像是一种再生……[15]
诗人高度赞扬袋鼠是澳大利亚自有的精神,但全诗并没有诠释何为“澳洲自有的精神”,只是通过比附“斯芬克斯”(Sphynx)、“美人鱼”(mermaid)、“半人马”(centaur)等意象回到欧洲文化传统。他试图抓住澳大利亚新世界的新事物,却又无法表达它的精神,因而只有“回归老传统,把新世界与旧世界联结起来”[16]74。这种模式成为19世纪澳大利亚诗歌的一个流行模式,温特沃斯的《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也非常典型地突出了这个特点。诗人描绘澳大利亚土著的狂欢、法国人探险旅程和悉尼周边的自然风光,流露出对澳大利亚风景的热爱之情,却将其归结为“新不列颠”在另一个世界的成长,赞颂“这种开创精神把大不列颠的研究成果和艺术散布到地球的每个角落”[16]75。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当时的诗歌中,同时也存在于小说中。不管是罗克罗夫特、博尔德伍德(Rolf Boldrewood)还是哈里斯、金斯利(Henry Kingsley),他们都对丛林风光情有独钟,对澳大利亚的丛林生活赞赏有加;但他们最终旨归都是英国。罗克罗夫特叙写丛林激战与迷津、抱怨丛林发家致富的容易;博尔德伍德讲述澳大利亚的神奇风光和离奇故事,目的是吸引英国人;金斯利笔下优美的丛林风光和闲适的牧场生活则是凸显英国人的高贵和本地人的低下。作为澳大利亚的过客和异乡人,他们从未真正进入澳大利亚风景,也难以理解澳大利亚风景的意义结构;他们惊异于澳大利亚风景的奇特,却难以真正表述澳大利亚风景的本质。他们笔下的澳大利亚风景只是表白英国心境的工具。
这是一种典型的游客叙事。他们对风景背后的意义了解不多,也无意深入了解,新版图上的风景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又一个景点而已,在叙事中要么猎奇,要么比附,抓住的是风景的表面特征,却无法真正表征风景的独特性格和气质,因而表面上的澳大利亚风景和深层次的英国情结构成一个撕裂的二元认同结构。这个二元认同结构是对英国本土的国家(大不列颠)—地方认同二元结构的继承与延伸,同时建构了澳大利亚长期存在的英澳情结的博弈。
三、家园:作为居民的风景叙事
澳大利亚殖民早期的风景叙事中,作者大多以局外人的视角取景,站在画外观看,因而会产生某些幻觉或错觉,或美化或妖魔化澳大利亚的风景。他们作为游客前往某一个地方时心里总是抱有某种期待,希望这些风景能够满足他们的期待。他们寻找风景里独有的符号,比如英国的乡村、法国的城堡、意大利的山峰,他人的经历植入了他们的“期待视野”,从而产生一种标准化的观景方式。因此,作家笔下的澳大利亚是片面的、模糊的、程式化的,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观看”根本上是审美性的。
作为居民则不一样,“风景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风景总是同他们的谋生密切相关”[17],风景不是外在于他们的,也不是用来观看的,而是由他们塑造出来的。他们的努力和欲望都在风景中得以体现,形塑着风景的形态与气质。也就是说,人与风景的互动将人地联系起来,最终实现对风景的占有并融为一体,难分彼此。
与早期作家作为游客浮光掠影式的“观看”风景不同,本土作家一生历经磨难,风景真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与风景的关系是体验的、融入的,而不是观看的、审美的,他们对风景有感情,且是细致入微的感情。澳大利亚早期风景的描写习惯于全景式的、抽象的展现,哈珀(Charles Harper)则不同。他的诗歌中不仅有巨幅的画面,还有细微的描绘,并且充满了热爱之情,比如他最有名的诗歌《澳洲森林中一个仲夏的晌午》(“A Midsummer Noon in the Australian Forest”):
空气中没有一丝儿声息,
处处万籁俱寂,
平原,树林,
笼罩着无边的寂静。
鸟儿和昆虫都已躲藏,
在阴凉的树荫酣睡的地方。
甚至连忙碌的蚂蚁,
也在颗粒稀松的土墩上歇息。[18]34-35
诗人通过细致观察寂寥的平原和鸟儿、昆虫等,充分表现了仲夏晌午的炎热与寂静。这是一种典型的澳大利亚风景,与温带海洋性气候所形成的英国风景构成鲜明的对比。他在另一首名诗《四坟河》(“The Creek of the Four Graves”)中写道:
他的目光最后落在
那片灰暗的森林东部的空地上,
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就像天使的剑一样,
在蜿蜒的小溪上闪闪发光,
在拓荒者之间无声地奔跑着,
那些新的亚平宁人奔跑着。[19]
哈珀在诗中展现了原本单调、丑陋大地上的生动多姿,澳大利亚丛林也变得色彩斑斓,富有活力,并充满了诗情画意,也展示了白人拓荒者与土著之间的冲突。他不仅把风景描绘得细致而有个性,而且把人物融入风景,使得原本单调的美景变得鲜活起来。哈珀能把情与景交融在一起,是因为他热爱生活、热爱风景优美的澳大利亚。他不仅仅是一位观景人,同时还是风景的创造者,因此有人称他为“第一个把澳大利亚的景物准确地反映到诗中的人”[18]34。诗人抛弃以前那种崇尚英国风景而羞于描绘澳大利亚风情的忸怩之态,理直气壮地刻画了澳大利亚的地理环境,歌颂新大陆的自然风光并且赋予一种自有精神,即澳大利亚早期开拓者顽强进取的精神和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尽管这一时期哈珀诗歌的艺术特色还不太鲜明,但他已经是具有明确风景意识的本地人,风景已经融入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异己的客体。他明白自己所处之地,亲身融入这个地方,仔细观察这里发生的一切,投入自己的感情,能够体会风景里的精神并且极为精当地表达出来,因而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言人。
风景不仅仅是一目了然的地理现象,还是内含层层叠叠社会文化关系的实体。风景的许多意义就隐匿在当地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当地居民而言也许是不言而喻的,外人却可能捉摸不透,这里的生活远不是这么浪漫、轻松,丛林生活的艰辛在亨利·劳森(Henry Lawson)《什么都不在乎》(“Past Caring”)中得到极为形象的展示:
此刻,在棕黄色的铁路线两旁,
巨大的黑乌鸦在空中盘桓,
而我知道在那山坡的下方,
另一头奶牛奄奄将亡;
地上的庄稼都已经枯萎,
瓷做的水箱底发出了闪光,
但我并没有落泪或者恸哭,
因为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18]65
诗人给我们展示了干旱所带来的萧条景象:乌鸦盘桓、奶牛咽气、庄稼枯萎、水箱露底,这就是真实的丛林生活:艰辛、苦涩。但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丛林人“什么都不在乎”,这是本地居民的无奈,也体现了丛林人坚韧不拔的性格。这是澳大利亚人最核心、最显著的民族性格,也是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内核。[20]
这些小说家和诗人是真正的“实存局中人”(existential insider),即他们不会刻意去反思在这个地方的经历,但这些经历对他们充满了意义。[21]作为当地居民,他们深入体验生活,对所生存的环境产生深刻甚至是完全的认同,有着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他们笔下的风景不再是占有,也不是猎奇或比附,而是具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性格,这种性格既是风景的,也是生活于此的人们的。他们是具有强烈风景意识的本地人,或者是已经“本土化”的外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超越了认知的局限,因而能够在更深广的框架内体验风景、表呈风景。
他们对风景生动的表呈还能造就“感应局中人”(vicarious insider),人未至而心已动[21],让原本对风景没有太多感觉的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丛林风光作为澳大利亚独特的风景,对于早期移民来说是陌生的、惧怕的,甚至是抗拒的;对于逃离不了的本地居民则是适应的、体验的、认同的。叙事者的呈现给外来者提供了“观看”寄居地,给本地居民提供了“凝视”自己家园的机会,通过这样的“观看”和“凝视”,认同也就产生了,“风景显示了强大的凝聚力”[22]。“美国作家华纳斯·斯特纳说过,一个地方在有一个诗人之前,是不能够称其为地方的。”(1)转引自张箭飞《风景感知和视角——论沈从文的湘西风景》,《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16页。同理,一个没有一群诗人的民族,是不能称之为民族的。正是因为有了一群展示民族风景的诗人和小说家,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内核才得以形成。
四、结 语
澳大利亚早期文学被谐称为“文学旅游家”写的“变相的游记”[18]8,原因在于其风景叙事有喧宾夺主之嫌。但随着文学研究的“风景转向”,风景作为体验的过程,其独特意义得以凸显,风景叙事不仅体现叙事者对风景的理解和接受,也反映了叙事者与其背后的文化、社会思潮的双向互动。澳大利亚早期文学的风景叙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坦奇以圈地为特征的拓殖叙事到菲尔德以猎奇为特征的游客叙事,再到哈珀、劳森等人以体验为特征的居民叙事。这种叙事模式的变迁体现了澳大利亚白人作家从大英帝国的殖民者向澳大利亚居民的身份变迁。风景叙事既是这种变迁的表征,同时也是其促成者。通过一代代作家的“理智化”,澳大利亚风景成为民族身份与文化记忆的载体进入人们的心灵,成为其精神依附的大众符号。从作为领土的帝国风景到作为景点的观光风景,再到具有民族意识的家园风景,这既是澳大利亚作家和其他澳大利亚人生活方式转变的结果,也是他们身份认同转变的结果。风景能够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是因为风景总是某一地区的风景,与该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总是被再现或发明出来,作为民族身份、文化记忆建构的手段。需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亚早期文学在建构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将其他族裔排除在外,而这恰是殖民主义抹不去的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