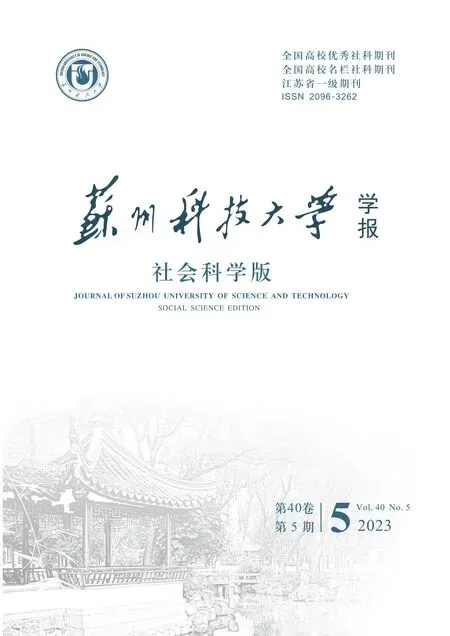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话语*
袁 霞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就一直在为弘扬加拿大民族文学和文化努力耕耘,用自己的作品记录加拿大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然而,关于阿特伍德民族观的研究只是散见于一些文集和期刊中的论文,例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作与主体性》(MargaretAtwood:WritingandSubjectivity, 1994)中的个别论文从后殖民角度出发,讨论了阿特伍德的“加拿大性”(Canadianness)。《多面阿特伍德:对较近的诗歌、短篇故事和小说的评论》(VariousAtwoods:EssaysontheLaterPoems,ShortFiction,andNovels, 1995)中的论文追溯了阿特伍德前后期作品之间在主题方面的联系,其中包括加拿大的民族主义。在《剑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导读》(TheCambridgeCompaniontoMargaretAtwood, 2000/2005)里,有作者指出了阿特伍德文本中“加拿大性”的不同方面,包括她对加拿大社会的态度和对不断变化的民族及身份意识形态的反馈等。这些论文对阿特伍德的民族意识的探讨多集中于其早期作品,如《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1)以下简称《生存》。(Survival:AThematicGuidetoCanadianLiterature, 1972)、《浮现》(Surfacing, 1972)等,且未系统探究阿特伍德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动态演变过程。笔者试从阿特伍德三个时期的部分作品出发,研究其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历程,旨在探讨其中体现的民族和国家理念,尤其是“共同体”思想。
一、寻求民族身份,建立“想象的共同体”话语
民族根植于群体的深层意识,关于民族的想象其实就是塑造民族的群体归属感,因此,民族国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想象的共同体”(2)“想象的共同体”出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之起源和传播的思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91)。。著名思想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曾指出,“想象与文化相关,且扎根于环境”[1],民族身份的建构离不开个体所共有的环境。在阿特伍德看来,这个共有的环境就是她的根——加拿大。阿特伍德的民族国家话语强调的是民族认同理念:民族作为某类人群的共同体,需要其成员具有团结观念、拥有共同文化、发扬民族精神。
20世纪60—70年代是加拿大民族形成的关键阶段,加拿大身份危机作为知识领域的问题被推到了最显著的位置。彼时的加拿大急需一种统一的民族观来摆脱英法的殖民阴影、应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建构强有力的国家话语。70年代初,阿特伍德中断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业回到祖国,在温哥华、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等地大学英语系执教。她的诗集《苏珊娜·穆迪日志》(3)以下简称《日志》。(TheJournalsofSusannaMoodie, 1970)、小说《浮现》和论著《生存》相继出版。《日志》通过苏珊娜·穆迪这位历史人物再现了加拿大早期殖民垦荒史,穆迪实现自我的历程与加拿大人寻找自身位置的过程是一致的。《浮现》描写了女主人公回到故乡找寻过去的经历,象征了加拿大追寻传统的努力。在《生存》中,阿特伍德采用主题研究方法阐述了加拿大文学在情节、主题和想象方面区别于英美文学的主要模式。该书的出版成为加拿大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批评界开始认识到加拿大作为殖民地的身份。《日志》《浮现》《生存》等作品利用独特的叙事手法和写作风格向读者展示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反映了加拿大与宗主国英法两国的关系,以及美国新殖民主义带来的危害,一方面展现了加拿大独特的民族传统及身份问题;另一方面旨在探讨加拿大人的民族国家认同理念和生存策略:寻找传统之根,认清自身位置,正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身份,从而实现自身的完整性,获得民族归属感。
阿特伍德不仅致力于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追寻,还密切关注加拿大社会中的语言问题。语言是透视文化身份的一扇窗户,是决定个体与文化团体归属关系的标志,在文化身份的认同和维护中起着重要作用。阿特伍德曾在访谈中指出,加拿大虽然拥有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但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加拿大语,“这就意味着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文学传统是由另外一个国家创造的”[2]。加拿大人使用的语言表面上看是自己的,但其中隐藏着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殖民经历。对于以阿特伍德为代表的加拿大英语作家来说,他们必须面对英美这两个强势的文化传统,思考如何用与殖民者相同的语言来挖掘民族性。
阿特伍德对帝国语言采取了“去神话化”(demythologization)的策略。“去神话化”一词由加拿大批评家罗伯特·克罗齐(Robert Kroetsch)提出。他认为,帝国在殖民过程中将自认为“标准”的语言强加给殖民地,等于要让自己的语言圣经化、神话化。“去神话化”就是解构那些时刻威胁着要对殖民地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帝国话语体系。[3]在《浮现》中,英国和美国的价值观是衡量文化艺术的权威和标准,女主人公的画作和书稿主要是临摹英美作品,因为加拿大出版商“最喜欢的是那些他们希望能引起英国和美国出版商兴趣的东西”[4]53;美国的文化更是被奉为圭臬,加拿大人正一步步被美国人同化,这不仅体现在行为举止上,也体现在语言方面。乔、大卫和安娜虽然身为加拿大人,却以模仿美国人的风尚和语言为荣。女主人公一行在湖面上遇到一群言语粗鲁的“美国佬”,他们实质上是加拿大人,而这些人也在猜测女主人公一伙是“美国人”,可见加拿大人的美国化程度有多深。这些都是对帝国语言和文化“神话化”的典型例子。随着情节的发展,女主人公越来越感受到英美文化对加拿大人的深刻影响:“如果你的外貌和他们一样,谈话和他们一样,思维与他们一样,那么你就是他们。我是说,你讲他们的语言,语言是你所做的一切。”[4]139她感到了在语言使用方面的“无能为力”,因为“它不是我的语言”。[4]115这种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语言并非自己的经验,它传递的是欧洲或美国的价值观,并且把加拿大人“撕成碎片”[4]158。在小说结尾部分,女主人公揭开了那些“假美国佬”的伪装,她烧掉画作以及打字稿,撕碎了象征着帝国文化崇拜的剪贴簿,独自一人留在了岛上……这一系列看似“疯狂”的行为语言可以说是对英美“普世文化”的反抗,也可以说是对其“去神话化”的过程。
阿特伍德在提倡对帝国语言“去神话化”的同时,努力“寻找第三种语言”[2]。在她看来,加拿大英语毋庸置疑会受到美国英语及英国英语的影响,但同时也具有其独特性,即相似之中又存在着不同,关键就在于如何体现这些不同的特征。这就需要用加拿大English写作,即“挪用”(appropriation)帝国的语言书写真实的加拿大人的生活,从而“对自身文化经历担负起重任”[5]。在《日志》中,空间、位置和语言之间的冲突令人不安。阿特伍德道出了加拿大人作为移民殖民者的困惑:流放的经历促使他们不断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刚踏上的这块土地虽然在他们看来是新的,但它具有自身古老而又确定的意义,于是产生了移民与“新”土地在语言上的冲突。在《双头诗集》(Two-HeadedPoems, 1978)里,阿特伍德希望加拿大语言能建构起一种可以明确表达其相异和变化的表征体系。在该诗集的同名诗中,她这样写道:“要拯救这种语言/我们需要回声,我们需要推掉/其他词语,粗俗的词语/它们如大腿或八哥/到处伸展传播。”[6]65在诗歌的结尾部分,阿特伍德指出了加拿大人的梦想:“然而我们的梦想/是自由,是对/动词的饥渴,是首歌/清澈透明,毫不费力地升起。”[6]75由此可见,加拿大人希望能够自由自在地使用属于自己的语言。阿特伍德创作时所用的语言虽然与英美国家的语言在外形上相似,但意义已经改变,她是在利用殖民者的语言书写加拿大在语言上受殖民的经历,揭示殖民压迫的种种后果。这其实是一种对语言的变形(metamorphosis),即通过语言意义的重新挖掘来达到权力的转换。殖民者的语言在阿特伍德的妙笔之下变成加拿大人控诉殖民统治的工具。
二、建构后殖民身份,创设多元文化共同体话语
加拿大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除土著和两大建国民族(英裔和法裔)之外,还有亚裔、非裔以及许多具有欧洲血统的非英裔或非法裔人口。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造就了不同族裔之间的纠葛与纷争,也强化了各自的文化意识和民族认同。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将国家视作“一个自我命名、自我界定的生活共同体。其公民不断地用共有的象征、价值、传统、记忆、迷思来形塑和再造这个生活共同体”[7]。在加拿大社会中,多元文化主义就是这个“生活共同体”在文化上的具体表现。
在20世纪80—90年代,由于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变化,人口结构也相应改变,这一切带来的是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变。早先的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同质化概念,已不再适应加拿大多元文化的社会潮流。民族结构的复杂性塑造了“马赛克”式的文化杂糅特征,文化和种族差异成了普遍趋势,民族矛盾日益突出。1988年,加拿大政府正式通过并颁布《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法案》,多元文化主义进入制度化轨道。到了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文化遗产部开始主管多元文化政策的各个项目,提出了“认同、公民参与和社会正义”[8]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阿特伍德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几部作品中——如短篇集《荒野警示故事》(WildernessTips, 1991)、小说《强盗新娘》(TheRobberBride, 1993)和《别名格雷斯》(AliasGrace, 1996)——对加拿大历史和民族身份话语进行修正,重新探讨了多元文化时代的“加拿大性”。
《荒野警示故事》对加拿大文学热衷于描写的“荒野”提出了质疑,指出加拿大“荒野”的概念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加拿大民族国家的崛起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对“空旷”景观的殖民和种族灭绝之上的。短篇集收录的同名小说以北安大略的一个小岛为背景,罗兰德四兄妹出生于岛上的瓦库斯塔乡间小屋,他们经常来此度假。罗兰德小时候最爱读乡间小屋里的一本藏书《荒野小贴士》,书中描写的印第安人高贵勇敢、热情好客,罗兰德非常向往他们的生活,甚至想做个印第安人。然而,随着年岁渐长,他发现了现实的残酷:瓦库斯塔乡间度假屋的存在是以牺牲原住民的利益为代价的,《荒野小贴士》中对土著的描述只是早期移民粉饰自己殖民压迫的手段。到了小说发生的年代,更多的移民涌入加拿大(比如罗兰德的姐夫乔治是匈牙利人),他们痴迷于到乡间度假,对印第安人的看法带着猎奇的心态。在罗兰德看来,以乔治为代表的移民“入侵”了加拿大,他和加拿大第一批移民殖民者没有两样,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牺牲他人的权益。阿特伍德通过罗兰德的视角揭示了土著令人悲哀的现状:他们站在路边,穿着毫无民族特色的衣服,试图向开车前往度假屋的城里人兜售浆果。这些原住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民族特性,成为多元文化政策之下被边缘化的他者。
《别名格雷斯》将19世纪的一桩谋杀案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以此探寻加拿大民族话语中被遗忘的历史,修正加拿大民族史神话,探讨加拿大骨子里的“多元民族”事实。阿特伍德通过一位来自底层社会的女性移民格雷斯的视角,展现了一幅19世纪早期的加拿大移民史画卷,有别于早先关于拓荒者在荒野中定居并建立国家的宏大叙事。在格雷斯生活的年代,虽然尚未出现“多元文化主义”概念,但加拿大作为一块移民殖民地,彼时已经成为各个族群的交汇地,其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像座巴别塔”[9]130。以格雷斯为代表的爱尔兰裔移民经历千辛万苦到达加拿大,却饱受歧视。格雷斯是天主教徒,她在劳务市场不受欢迎,因为雇主们觉得“天主教徒迷信,会造反,正在搞垮这个国家”[9]134。在格雷斯涉嫌谋杀被捕后,她的族裔背景成了公众热议的焦点:“保守党人似乎把格雷斯与爱尔兰问题混淆起来,……他们还把谋杀一个保守党绅士的单个事件……与整个种族的暴乱混为一谈。”[9]84格雷斯的谋杀案因此具有了种族冲突的特征,格雷斯个人的经历也与“族裔的、种族的,甚至是国家的过往”[10]联系起来,展现了作者对多元文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考。
《强盗新娘》是一部后现代哥特式小说。它采用传统的哥特式主题,如邪魅的幽灵和肉体的转换等,描写了多元文化社会中加拿大居民族群和民族构成的不断变化,揭示了跨国资本影响之下各族裔的生存状态,再现了加拿大作为民族国家身处的国际大环境,为加拿大身份的界定提供了参考。小说同样以族裔混杂、有着丰富多元文化特色的大都市多伦多为背景,围绕四位女主人公之间长达30年的纠葛,展示加拿大移民问题的真实状况。阿特伍德试图通过“我们”(英裔白人)和“他们”(新移民)的故事反映“英裔加拿大对变化中的民族身份表征的焦虑”[11]。从20世纪60—70年代追求统一的民族文化身份,到20世纪末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困惑,加拿大面临着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民族融合问题:“我们”和“他们”该如何相处。
阿特伍德的民族国家话语既结合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又考虑到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她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不同民族和种族的人们在多元文化下的生活画面,透过普通民众的生存境况展开民族国家叙事,体现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文化内部和自我内部的差异性,从而让人们意识到:加拿大身份并非单一的,而是包含了多种意义、多种话语以及多元阐释的可能性。
三、探寻全球公民身份,关注人类未来命运
在21世纪,阿特伍德的创作视野更加广阔,她不再仅仅关注国家形象和民族身份话题,还开始聚焦于后国家时代(postnational phase)的人类命运主题。这是阿特伍德写作策略的又一次调整,表面上看是在宣扬“去国家”理念,实则是将加拿大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问题置于全球化的大框架之内进行思考,关注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有学者将阿特伍德称作“伟大的加拿大全球公民”[12],认为她并未放弃民族主义,而是秉持着一种“超民族的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 nationalism)”[12],来传播她作为一位全球公民所具有的包容性的星球意识。
阿特伍德在新世纪出版的最著名的作品是“疯癫亚当三部曲”——《羚羊与秧鸡》(OryxandCrake, 2003)、《洪水之年》(TheYearoftheFlood, 2009)和《疯癫亚当》(MaddAddam, 2013)。在“疯癫亚当三部曲”大结局出版之后不久,阿特伍德撰文写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时期:一方面,各种各样的技术——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数字技术——在分秒必争地得到发明和完善,许多曾被认为不可能或神奇的壮举正在上演。另一方面,我们正以惊人的速度摧毁我们的生物家园。[13]
在“疯癫亚当三部曲”中,阿特伍德探讨了生物工程、人工智能和仿生学等前沿技术对人类未来的挑战,质询了人类居住的地球家园所受到的威胁,对后人类时代人类如何与星球上其他生物共存的可能性进行了思考,将人、动物和自然都视作命运休戚相关的星球公民。
过去的20年是全球灾难频发的时代,战争、洪水、飓风、瘟疫、饥荒、人为事故等频繁发生。阿特伍德在“疯癫亚当三部曲”里描写了各种类型的灾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气候灾难。阿特伍德指出,她创作“疯癫亚当三部曲”的动机就是担心气候变化的影响,了解“我们把地球搞得多糟了”。[14]《羚羊与秧鸡》是阿特伍德对北极之行的反思,冰川的融化让她深感忧虑;《洪水之年》的创作与飓风“卡特里娜”对新奥尔良的破坏不无关系;《疯癫亚当》则出版于飓风“桑迪”对美国东北海岸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之后。飓风、雷暴、海啸和龙卷风等“超级物”频频出现,它们并非天灾,而是人类毫无节制地开发引起的恶果。
阿特伍德曾指出,全球变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环境退化,‘自然’灾害,正在加速的物种灭绝——确实不仅是加拿大,而且是整个行星面临的最大问题”[15]。从《羚羊与秧鸡》的描写来看,地球上的很多物种已经消失不见。主人公吉米和秧鸡曾玩过一种叫“大灭绝”的网络游戏。游戏参与者需要知道过去50年里绝迹的生命形式属于“哪个门哪个纲哪个目哪个科哪个属哪个种的,产于何地,最后出现时间,是什么消灭了它”[16]83。那些灭绝物种的名字,“少说也是一份长达两百页用蝇头小字打出的清单,上面尽是些不知名的虫子、藻类和蛙类”[16]83。虽然这只是个游戏,但是它出现在小说中,可以说是作者的匠心独运,短短50年就有如此多的物种灭亡,似乎为后来人类的“大灭绝”埋下了伏笔。
阿特伍德将气候变化称为“万事变化”[17],因为只要气候变化了,其他一切都会受到影响。从物种灭绝到疾病传播,再到社会体制和结构的不稳定,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一切都会产生联动效应。气候变化不仅影响着西方富国的政治稳定,对贫穷国家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女主人公羚羊出生于东南亚国家的某个村庄,那里每家每户都有不少孩子。由于气候变暖,农作物歉收,这些家庭缺吃少穿,便打起孩子的主意。在当地人眼里,女孩们除早早嫁人生下更多孩子之外,没有多大用途,还不如将她们卖掉,换点吃的。因此,女孩中略微长得端正点的就被卖给了一个叫恩叔的人贩子,再由恩叔转卖到西方国家从事皮肉交易。对于这样的人贩子,当地人不仅没有把他当作不法分子,反而对他十分尊敬和友好,视他为“抵挡噩运的护身符”[16]121。当地人越来越频繁地求助于恩叔,“因为天气变得古怪难测——太多的降水或降水太少,太多的风,太多的热量——庄稼备受煎熬”[16]121。这些气候变异的现象在当时已司空见惯。在电视节目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全球变暖导致的社会不安定现象:瘟疫横行,饥荒遍地,洪水泛滥,病毒暴发……而且,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了抢夺资源不断发生冲突争斗,青壮年劳力锐减,不得不征用儿童去打仗。可见,伴随气候变异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些又加速了人类灭亡的脚步。
在后自然时代,人类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该何去何从?“疯癫亚当三部曲”通过描写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危机,反映人类与地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思考人类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的责任、伦理等问题。阿特伍德试图通过文学中的灾难发掘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探寻人们在灾难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思考这种精神对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未来的意义。
四、结 语
阿特伍德的民族国家话语探讨了如何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中实现各民族交流交融、平等共荣的理念;探讨了如何调和种族、地域和语言的差异,寻找共同的历史记忆;探讨了如何在尊重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加强培育对国家的认同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阿特伍德的民族国家话语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是一个不断建构、不断生成的动态历程。从寻求民族身份到建立后殖民身份,再到探寻全球公民身份,该话语经历了由“内省”向“外察”的审视过程。在此过程中,阿特伍德逐渐建构起一种“共同体”理念,反映了她的家、国、天下的理想以及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