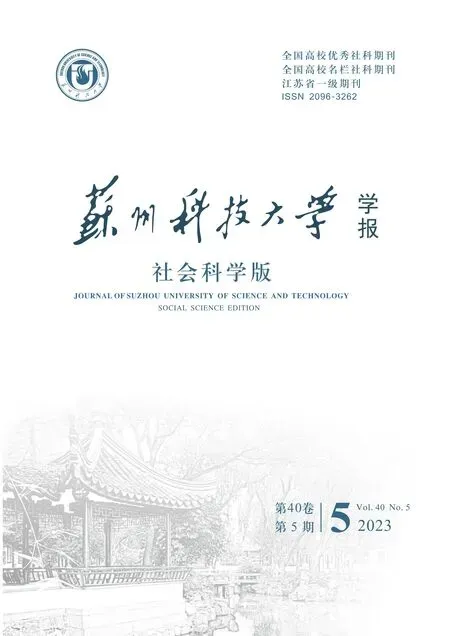儒家“天命”思想与颂体的政治诉求*
杨化坤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不仅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存在,还是能主宰人间万物的造物主,由此形成“天命”思想。不同学派对“天命”内涵的阐释也不尽相同,道家多阐释为宿命、命运,法家认为是指君王意志,儒家则认为是代表上天旨意的意念。这种意念表现为一种非物质状态,通过各种玄妙的媒介为人感知,是人神沟通的重要内容。为了传播“天命”思想,人们不断推衍发展,“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吊民伐罪”等都是这样一种思想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借助“天命”思想实现、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重要学说。颂体源于《诗经》“三颂”,秦汉之后演变为一种颂扬功德的文体形式,其本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自然就成为“天命”思想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媒介。
一、太平之符:“天人感应”的显性表达
“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思想学说,指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达到相互沟通的效果。作为一个完整词汇,“天人感应”最早在司马懿等人《太史丞许芝上符命事议》中出现:“殿下践阼,至德广被,格于上下,天人感应,符瑞并臻,考之旧史,未有若今日之盛。”[1]66但相关的意思早在《尚书·洪范》中就已出现:“曰休征:曰肃,时寒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2]407这段话表明,君主的施政态度与天气直接相关,不同的天气代表上天不同的旨意。这种观念在先秦很多典籍中都有体现,如《春秋公羊传·僖公十五年》载:“季姬归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电击夷伯之庙者也。夷伯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则微者,其称夷伯何?大之也。曷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书?记异也。”[3]这段文字认为“晦,震夷伯之庙”是上天“戒之”旨意的表现。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学的基础上,吸收墨家“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的天惩观点,并继承《公羊传》的灾异说,将“天人感应”思想进一步发展,使之系统化,形成儒家独特的神学观念。
“天人感应”分为两个方面:当君王有德时,天降祥瑞以示嘉奖;君王失德时,天现灾异以示惩罚。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云:“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4]“美祥”代表褒奖,“妖孽”表示惩罚,二者都是天人之间感应的媒介。这种观点早在先秦就已出现,如《尸子·仁意》所说的“尧为善而众美至焉,桀为非而众恶至焉”[5],只不过到了董仲舒才将其发扬光大。不论是尸子还是董仲舒,都是从上天的能动性考虑的。反过来,君王如何能够体现出其政权的合法性以及治理天下的成效呢?最为首要的就是须获得上天的认可。上天作为超乎人世的自然存在,本与人类并无直接的感应关系,但通过统治者的附会,将一些自然现象神化为上天的感应,从而达到“天人感应”的效果。因此,以“美祥”为表达方式的“天人感应”,说到底就是君王试图以上天的名义为自己的政权寻找合适的名分。
符瑞又称“祥瑞”“瑞应”“祯祥”“符应”“嘉瑞”“嘉祥”“休征”等,是古代帝王受命执政、功德卓著的征兆,多为罕见或虚构的动植物及自然现象,与中国古代“天人感应”及“君权神授”的思想均极为密切。符瑞主要包括甘露、河清、嘉禾、醴泉、景云、五星联璧等自然现象,以及各种白色动物、神雀、凤凰、神龙、麒麟等罕见或虚构的动物。《尚书》《春秋》中的异常自然现象便是早期的符瑞。符瑞的出现是文臣借机表现的绝好机会,也是为皇权正名的重要时机。汉代以后,每当符瑞出现时,文臣往往作文褒赞,涉及的文体主要有诗、赋、颂、赞、表等,颂体无论在数量还是出现频率方面都十分显著。文臣作颂颂扬君王功德、树立皇权,也进一步宣扬“天人感应”思想,达到稳固政权的目的。这类作品有些直接以符瑞为名,在题目中标明“瑞颂”,汉代杜笃《众瑞颂》(1)已佚,仅存《文选·雪赋》李善注所引“千里遥思,辗转反侧”。,三国何晏《瑞颂》,唐张说《皇帝在潞州祥瑞颂》、崔禹锡《河渎纪瑞颂》(2)已佚,见《宝刻丛编》卷二十著录。等,以众多符瑞的出现彰显君王之功德,表达天人之间的感召与响应。如何晏《瑞颂》(3)该文目前仅存《艺文类聚》节选的一段。:
若稽古帝魏武,浚哲钦明文思。罄民生之俊德,懿前烈之极休。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聿迪明命,肇启皇基。夫居高听卑,乾之纪也;靡德不酬,坤之理也。故灵符频繁,众瑞仍章。通政辰修,玉烛告祥。和风播烈,景星扬光。应龙游于华泽,凤鸟鸣于高冈。麒麟依于圃籍,甝虎类于坰疆。鹿之麌麌,载素其色。雉之朝雊,亦白其服。交交黄鸟,信我中溜。倏倏嘉苗,吐颖田畴。[6]1696
这篇作品作于曹丕称帝之时,以各种祥瑞的降临来称颂功德。古人认为符瑞的多少与功德的大小密切相关,符瑞越多,功德越大。如黄帝时期“天下既定,圣德光被,群瑞毕臻”[7]760;王莽称帝时,张纯等人皆曰:“圣瑞毕溱,太平已洽。帝者之盛莫隆于唐虞,而陛下任之。”[8]4072这些都是借符瑞“毕臻”来歌颂帝德,体现君王政权的合乎天意。
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群瑞毕臻”的情况毕竟是少数,大多时候符瑞都单独出现,符瑞颂也都有具体的名称。自然现象类如河清、嘉禾、甘露等,动物类如白鹿、白乌、神雀、麒麟等。这些符瑞俱为太平盛世的征兆,需要作颂以宣,如江夏王义恭《嘉禾甘露颂表》称:
臣闻居高听卑,上帝之功;天且弗违,圣王之德。故能影响二仪,甄陶万有。鉴观今古,采验图纬,未有道阙化亏,而祯物著明者也。自皇运受终,辰曜交和,是以卉木表灵,山渊效宝。伏惟陛下体乾统极,休符袭逮。若乃凤仪西郊,龙见东邑,海酋献改缁之羽,河祗开俟清之源。三代象德,不能过也。有幽必阐,无远弗届,重译岁至,休瑞月臻。前者躬藉南亩,嘉谷仍植,神明之应,在斯尤盛。四海既穆,五民乐业,思述汾阳,经始灵囿。兰陵甫树,嘉露频流,板筑初就,祥穟加积。太平之符,于是乎在。[7]830
中国古代向皇帝进文时,需要上表阐明进文意图,通常与所进之文一同呈上。因此,这种表文其实也承担着序文的功能。《嘉禾甘露颂表》一开始就认为,上天的职责在于“居高听卑”,洞察人世,而人间的君王要顺应天意;接着阐述上天与圣王的关系,认为圣王之德可与天地相呼应,化育万物,古今图纬书的记载,均表明圣王有德时,祥瑞方才出现;然后叙述当前各种祥瑞纷纷出现,表明当今天下太平。“嘉谷仍植,神明之应”“兰陵甫树,嘉露频流”,均是自然界的“太平之符”,表明上天对君王的认可。再如何承天《白鸠颂表》:
谨考寻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物以应显。是以玄扈之凤,昭帝轩之鸿烈,酆宫之雀,征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和于地络,烛皇明于天区。故能九服混心,万邦含爱,员神降祥,方祗荐裕,休珍杂沓,景瑞毕臻。[7]849
作者认为,如今天子德合天地,海内一心,因此各种祥瑞纷纷出现。与上文祥瑞的出现昭示帝德隆盛的思维方式相反,该文将祥瑞出现的原因归结为“王德”的感召。二文均是“天人感应”思想的体现,但这篇颂作更加注重颂扬帝德。
《白虎通·封禅》认为,“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9],并列举帝德所及的不同方面,如天、地、文表、草木、鸟兽、山陵、渊泉、八方等,说明符瑞乃天人感应的重要表现。以上两篇表文,或以祥瑞宣示帝德,或为帝德感召祥瑞,均阐述了祥瑞与帝德关系的密切。这也是古代各种符瑞颂创作最常见的两种思维方式。帝德作为一种抽象事物,本为内在的精神品质,只能想象却无法触视,只有通过物化的方式,令其从隐性到显性,从抽象到具体,方可更加直观地体现,让人信服。“太平之符”代表上天的旨意,其意义与其说肯定帝德,不如说体现了上天对皇权的“认可”。符瑞作为“天人感应”的重要媒介,是沟通天人关系的重要手段,而符瑞颂的创作目的,也正是借符瑞之名为皇权寻求名分。
二、受命之符:“君权神授”的神秘暗示
古代帝王继位时,每有“受命于天”之说,认为君王权力是上天赐予,为政权的建立营造绝对的权威。《论语》记载尧禅位于舜时,尧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朱熹注“历数”云:“帝王相继之次第,犹岁时气节之先后也。”[10]193舜因为品德高尚、才能卓著而被选定为继任者,但尧却将之归结于“天之历数”,而非人意,以此为舜的即位树立权威。《庄子·德充符》称:“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郭象注:“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圣人。”[11]这里的“受命于天”与“天之历数在尔躬”一样,均表示帝王的权力为上天赐予。《吕氏春秋·知分》记载禹巡视南方时,曾仰视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养人。”[12]天并非单纯的自然,而是具有意志、可以左右人类命运的主宰者。因此,这里的“天”类似于后世所谓的“神”,“受命于天”类似于西方所谓的“君权神授”,是帝王为了巩固自身地位、确立名分所进行的舆论制造。
“受命于天”又简称“受命”“天命”,《尚书》便保存了不少这方面的史料,如《尚书·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谨天命。”[2]356-357《尚书·召诰》:“有夏服天命。”[2]452“天命”指由上天主宰的命运。一个政权的建立,本依赖于统治者的苦心经营,但古人将其归于客观存在、超乎人类的“天”,既是为现行政权的巩固确立名分,也为夺取、建立政权制造舆论。如《尚书·汤誓》记载汤讨伐夏桀时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2]338,即要借助天命增加征讨夏桀的合理性,以此激发士气,获取胜利。《诗经》中也有不少有关“天命”思想的篇章,尤其以《周颂》最为显著。如《维天之命》郑玄笺:“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13]1258《昊天有成命》郑玄笺:“‘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13]1266《桓》:“天命匪解,桓桓武王。”郑玄笺:“天命为善不解倦者,以为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则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当天意也。”[13]1303-1304《赉》:“时周之命,于绎思。”郑玄笺:“劳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13]1304《尚书》为上古帝王言论的记录,《周颂》则是以文学形式对天命的咏叹,二者俱体现了当时“天命”思想的流行。所受之“命”,其实就是执掌朝政的权力,也即《论语》中尧所说的“历数”,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秩序。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古人以此作为政权之名分,目的是强调政权的合理性。
与“天人感应”一样,“符瑞”也是“君权神授”思想最为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为了彰显“天命”观,这类符瑞往往被称为“受命之符”。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的疑问时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8]2500“受命之符”非人力所能致,君王如果能够爱民如子,积累善行,“受命之符”自然就会出现。董仲舒的这段话是规劝汉武帝施行德政,认为君权来自上天的授予,同时又将“受命之符”的出现归结于君王道德的修行,具有强烈的现世效应。此后,“受命之符”的说法就在各类典籍中广泛出现,如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云:“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14]3052汉哀帝《改元大赦诏》曰:“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8]340《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群臣劝刘秀称帝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15]《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许芝劝曹丕代汉曰:“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1]63上述“受命之符”或用于安抚民心,或用于自我标榜,或用于劝进登基,均是“君权神授”思想具体用途的体现。
颂体中“君权神授”思想的表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直接在作品中展现“君权神授”思想。如史岑《出师颂》云:“茫茫上天,降祚有汉。兆基开业,人神攸赞。”[16]661蔡邕《祖德颂》云:“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祸乱。”[17]高闾《至德颂》云:“乃眷有魏,配天承命。”[18]1197程骏《庆国颂》云:“于皇大魏,则天承祜。”[18]1348从《诗》之“三颂”到后世的颂体,虽然篇体形式和颂扬对象有所不同,但俱为宫廷文学,为统治者政权服务的性质并未改变。上述“君权神授”思想的提出均位于颂作开头,目的就是开篇确立“天命”基调,为下面颂扬的内容提供依据。
另一种方式是经常利用符瑞来宣扬“君权神授”思想。这类“受命之符”简称“符命”,即上天预示帝王受命的符兆。 “符命”在汉代非常兴盛,《汉书》中即有很多记载,如《汉书·扬雄传赞》载:“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8]3584汉代的“符命”还演变为一种述说符瑞以颂扬帝王受命于天的文体,如《汉书·扬雄传赞》引京师之语:“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8]3584这里的“符命”显然是文章的题目。为此,《昭明文选》特列“符命”类,选录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一种文体的确立,须有一定数量的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相同特点的作品,其成型的过程,也体现了“符命”思想的流行。不仅如此,“符命”思想在其他文体之中也经常出现,尤其在颂体作品中表现非常明显。如鲍照《河清颂》云:“素狐玄玉,聿彰符命。”[19]《宋书·符瑞志》记载,大禹梦见自洗于河,以手取水饮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大禹“治水既毕,天赐玄圭,以告成功”[7]763。二者均为帝王受命之征兆。《河清颂》又称:“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应龙之精,俯协河龟之灵。君图帝宝,粲烂瑰英。固以业光曩代,事华前德矣。”[19]《宋书·符瑞志》载:“黄龙者,四龙之长也。不漉池而渔,德至渊泉,则黄龙游于池。”[7]796“灵龟者,神龟也。王者德泽湛清,渔猎山川从时则出。”[7]880“承天命”不能仅仅靠自我标榜,更要以符瑞降临来体现。如陈子昂《大周受命颂》云:“臣闻大人升阶,神物绍至,必有非人力所能存者,上招飞鸟,下动泉鱼。古之元皇,祇承上帝,所以协人祉,匹天休,卓哉神明,昭格上下,莫不以之矣。”[20]新兴政权的建立,往往意味着旧政权的打破,这种新旧轮回,不仅需要用武力解决,还要以符命观念为新政权的确立树立权威,这样才能获得世人认可与支持。
“君权神授”与“天人感应”关系极为密切,二者表现形式相同,都以祥瑞为媒介。《宋书·符瑞志》讨论“符瑞”与“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关系时说:“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7]759神龙的现身预示着圣人出现,既体现了“君权神授”,又是天人之间的感应。颂体作品中,不少都是以符瑞作为载体,同时包含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两种思想。如三国傅嘏在《皇初颂》开篇说道:“寻盛德以降应,著显符于方臻。积嘉祚以待期,储鸿施于真人。昔九代之革命,咸受天之休祥。匪至德其焉昭,匪至仁其焉章。”[6]188该颂作于魏建国之初,亟须证明其合法性。“降应”即天降祥瑞,“革命”指实施变革以应天命。古代认为王者受命于天,改朝换代是天命变更,因称“革命”。傅嘏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君王“盛德”的感召,体现了魏国的建立乃顺应天意、顺应民心,上古时期以来皆是如此。要言之,“符瑞”的意义不在于自身物态与形状,而是代表着上天的旨意,体现了上天对皇权的肯定。在天与人之间,“符瑞”是一种双向的媒介:当君王功德隆盛之时,“符瑞”降临以示上天对君王的肯定,从而体现“天人感应”;当君王希望自己的政权得到世人认可时,也会主动借用符瑞来“传达”上天的意志,体现“君权神授”。前者是“太平之符”,后者为“受命之符”。不论哪一种都值得庆贺,需作文颂扬。颂作为“美盛德之形容”的文体,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三、正义之战:“吊民伐罪”的舆论宣传
“吊民伐罪”即抚慰百姓、讨伐有罪的统治者,最早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出现:“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10]268也有称“伐罪吊民”,如任昉《百辟劝进今上笺》云:“伐罪吊民,一匡靖乱。”[16]571中国是礼仪之邦,两军交战,讲究出师有名,为了让己方占据道德制高点,需要进行舆论宣传。《汉书·高帝纪上》记载新城三老董公说汉王曰:“兵出无名,事故不成。”颜师古注引苏林曰:“名者,伐有罪。”[8]34因此,“吊民伐罪”既是为出师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也是一种舆论攻心战,目的就是要给自己正名。
“吊民伐罪”尤其在易代之际非常普遍。如上文所引《尚书·汤誓》载商汤讨伐夏桀时,打出的旗帜是“吊民伐罪”。《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听闻商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残暴不仁,于是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率领大军“以东伐纣”。从孟津渡河之后,作《太誓》:“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逖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14]121-122《太誓》也作《泰誓》,即出发前的誓师,主要揭示商纣王的罪行。这段文字也蕴含着“天命”思想,“自绝于天”即违背“天命”,“天罚”即替天行道,表明讨伐的行为是“受命于天”,以便收拢人心,团结一致。
儒家向来讲究忠君爱国,而所伐之“罪”有时也会是国君或者诸侯王所犯。当君王昏乱时,是继续尽忠还是勇于声讨?对此,古人早有讨论。《孟子》记载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齐宣王又问:“臣弒其君,可乎?”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0]221孟子认为,破坏仁爱、道义的只能是“一夫”,不再是百姓爱戴的君王。孟子的这段话,合理地化解了“吊民伐罪”与忠君爱国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吊民伐罪”找到合理的解释。正如朱熹所说:“害仁者,凶暴淫虐,灭绝天理,故谓之贼。害义者,颠倒错乱,伤败彝伦,故谓之残。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书》曰:‘独夫纣。’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王勉认为,“惟在下者有汤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纣之暴则可”,不然会背上“篡弑”之罪名。[10]221王勉的解释让我们注意到,“吊民伐罪”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对方是非正义的,己方为正义的,即必须以“有道”伐“无道”。倘若是“无道”伐“有道”,或“无道”伐“无道”,都不能称之为“吊民伐罪”。
人们将“吊民伐罪”的思想在战争前后广泛传播,通过不同的文体反映出来,便是檄文与颂文。檄文主要为战前作准备,主要是“揭露”;颂文作于战后,在颂扬的同时还对战况加以描绘,主要用于战后的民心安抚。二者相互配合,共同体现“吊民伐罪”思想在战争前后的作用。如东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站在朝廷立场讨伐孙权,先以赋笔列举孙权之恶行:“孙权小子,未辨菽麦,要领不足,以膏齐斧,名字不足,以洿简墨,譬犹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陆梁放肆,顾行吠主,谓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灵诛。”然后颂扬汉帝的圣明:“圣朝宽仁覆载,允信允文,大启爵命,以示四方。”通过对比,阐明双方一是无道,一为有道。接下来再写“丞相衔奉国威,为民除害,元恶大憝,必当枭夷”,以揭露对方罪恶壮大自己声威。[16]619-621秦时颂体虽然还未出现,但在秦始皇刻石中,“吊民伐罪”的思想就已体现出来。如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之罘刻石》就说:“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21]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碣石门刻石》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21]秦始皇刻石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颂体,但极大地影响了颂体的创作。后世颂体继承秦始皇刻石的这种写法,既要指出对方的罪恶,还要体现出自己的正义。如西晋张载《平吴颂》:
上哉仁圣,曰惟皇晋。光泽四表,继天垂胤。帝道焕于唐尧,义声邈乎虞舜。蠢尔鲸吴,凭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菁茅阙而不贡,越裳替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号令之旧章。布亘地之长罗,振天网之修纲。制征期于一朝,并箕驱而慕张。尔乃拔丹阳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群丑率从。望会嵇而振铎,临吴地而奋旅。众军竞趣,烽飙具举。挫其轻锐,走其守御。[6]1073
这篇颂作首先树立西晋政权的正义形象,将西晋皇帝描绘为顺应天命的天子;接着将吴国描写为贼匪,作恶多端,为害一方。为了解救百姓,讨伐“群丑”,因而大举征伐。再如北魏高允《北伐颂》:
皇矣上天,降鉴惟德,眷命有魏,照临万国。礼化丕融,王猷允塞,静乱以威,穆民以则。北虏旧隶,禀政在蕃,往因时故(4)“故”字原缺,据《文馆词林》补。详见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1页。,逃命北辕。世袭凶轨,背忠食言,招亡聚盗,丑类实繁。敢率犬羊,图纵猖蹶,乃诏训师,兴戈北伐。[18]1085
《魏书·高允传》记载,高允随显祖北伐大捷而还,至武川镇,上《北伐颂》。与《平吴颂》一样,该颂首先将北魏描述为上天授命的正义王朝,将北方其他政权形容为作恶多端、背信弃义的“丑类”,通过对比,显示出北伐的正义性及必要性,因此获胜归来之后,“六军克合,万邦以协,义著春秋,功铭玉牒,载兴颂声,播之来叶”[18]1085,对北伐作进一步的肯定。上面这两段文字都是颂作的开头,开篇奠定“吊民伐罪”的基调,为战争的正义性寻求名分。
张载《平吴颂》与高允《北伐颂》俱为以战争为题材的征伐颂,是儒家“吊民伐罪”的重要表现方式和传播载体。这类作品有很多,如东汉班固《窦将军北征颂》、傅毅《窦将军北征颂》《西征颂》、崔骃《北征颂》、史岑《出师颂》,西晋张载《平吴颂》、挚虞《太康颂》,唐朝李世民《皇德颂》、李治《大唐纪功颂》、李百药《皇德颂》、张九龄《开元纪功德颂》、杨炎《灵武受命宫颂》《凤翔出师纪圣功颂》《大唐河西平北圣德颂》、于邵《唐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公经武颂》、韩云卿《平蛮颂》、张濛《镇国军节度使李公功德颂》,宋祁《皇帝神武颂》等(5)上述颂作,一类直接以“征伐”为题;还有一类虽然不以征伐为题,但其内容仍然属于“吊民伐罪”的主旨。。明清时期,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征伐颂,还有很多的同题之作,尤以清代为最,如毛奇龄、王鸿绪、孙在丰、徐乾学、尤侗、陈维崧、徐秉义、潘耒等人的《平滇颂》,徐乾学、尤侗、黄与坚、翁叔元、徐钅九、彭孙遹等人的《平蜀颂》。还有标题稍异主题相同者,如方苞《圣主亲征漠北颂》《北征颂》、赵士麟《北征颂》、徐秉义《北征荡平颂》、杜臻《圣驾亲征荡平漠北颂》、熊赐履《北征荡平颂》、张永铨《平北寇颂》、王鸿绪《永清漠北颂》、徐旭旦《平北颂》、陆奎勋《平北颂》等。为了树立正统形象,清初每有征伐,必会出现大量歌功颂德之作。这些颂作和前代一样,都以“吊民伐罪”为旗帜,把清帝描述为“受命于天”的天子,将清军刻画为符合儒家思想的正义之师,认为征伐对象为作恶多端的乱臣贼子,以此为征伐寻求名分。
征伐颂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描绘战争,而是突出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不管怎样,战争都是残酷的,因此需要加以美化,最好的办法就是从道德上凸显战争的正义,消解残酷,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吊民伐罪”与“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思想都基于对“德”的弘扬,是道义的体现。为统治者“正名”,就是寻求政权建立的依据,武力、国力的强盛都是外在的客观条件,“德”才是根本原因,唯有德盛才能服众,也就是儒家倡导的“以德服人”。在创作的过程中,这几种思想往往互有关涉、交合出现,共同营造皇权的正义与权威。如颜师古《圣德颂》开头部分:

《圣德颂》作于唐朝建立之初,有着显著的政治意义。这段文字可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体现了上述几种思想,从开头至“诞受天符”为“君权神授”,至“衔策俱尽”为“吊民伐罪”,至“朔班狼望”为“为政以德”,至“朱草曜芳”为“天人感应”。作品先简要叙述往代的历史沿革,强调唐王朝乃顺应天命而建立,以“君权神授”确立皇权的合法性;再写唐王朝秉承天命,剪灭祸患,拯救黎民,即“吊民伐罪”;政权确立之后,皇帝崇尚“为政以德”,以仁义治天下,百官清廉,人民安康,社会稳定,四海和睦;社会繁盛的局面感动上苍,各种符瑞争相出现,验证了“天人感应”思想。该颂内容丰富,气势恢宏,结构谨严,过渡自然,结合不同方面的描绘,共同展现并赞颂了大唐王朝的功德。通过这篇颂作我们也看到,一个王朝无论是建立之初,还是后来政权的巩固,无时无刻不需要加以正名,上述几种思想的运用就是这种需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