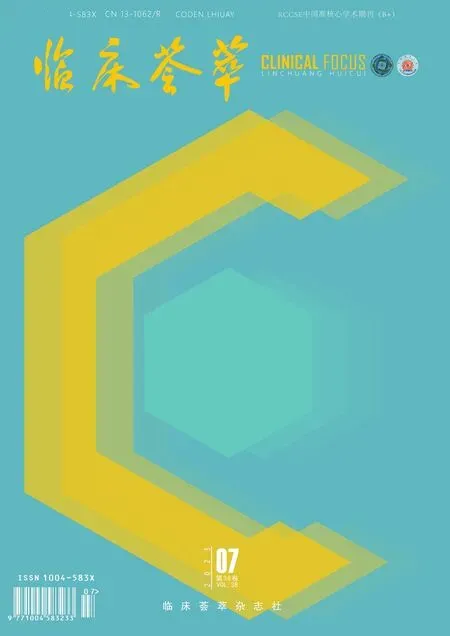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相关研究
----过去与未来
张 会,丁东瑞,金天然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三医院 a.心血管内科;b.感染疾病科,天津 300142)
2019年12月起,武汉市发现不明原因的上呼吸道感染病例[1-2]。2020年1月初,人们确定感染是由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引起的,这种疾病被命名为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 2019)[3-4]。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正式将这种疾病列为疫情大流行[1]。COVID-19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增长,因此了解SARS-CoV-2的致病机制以及有效的治疗途径,显得尤其迫切。
1 病毒学
冠状病毒(coronaviruses)在20世纪60年代被首次发现,当时只知道它们含有“刺突”形蛋白质,且此种蛋白构成的膜结构包围着RNA[5],这些膜表面“刺突”蛋白的冠状外观使病毒家族得名,“corona”在拉丁语中是皇冠的意思[6]。具有这种特殊形状和结构的病毒属于冠状病毒科,根据种系发生可分为α、β、γ及δ冠状病毒[7-8]。只有α和β冠状病毒是人畜共患型,而SARS-CoV-2属于β冠状病毒属[9]。所有冠状病毒由基因组RNA、核衣壳(N)、刺突(S)、包膜(E)和膜(M)结构蛋白组成,此外还有一些非结构蛋白和辅助蛋白[9]。
截至2020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确认了7种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株,它们被归为单链正螺旋RNA病毒[9],基因组包含26000~32000个碱基[10]。
人群中最早发现的冠状病毒是CoV-229E和HCoV-OC43[11],可引起常见的上呼吸道疾病,如普通感冒;此后又发现了HCoV-HKU1和HCoV-NL63[12];其余3种冠状病毒株分别是SARS-CoV、MERS-CoV和SARS-CoV-2,它们可导致严重疾病,甚至死亡。4种非重型毒株全球均有分布,在当地人群中密度很低[9]。另外3种重型毒株,SARS-CoV于2002年出现,导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MERS-CoV于2012年发现,引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而SARS-CoV-2则是一种导致COVID-19全球大流行的病原体。
2 病毒的进化
蝙蝠是冠状病毒的主要动物宿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病毒已变异并适应感染人类,导致动物到人的物种跨越传播[6]。病毒基因组序列分析[13]显示,SARS-CoV-2与蝙蝠冠状病毒的RaTG13基因一致性为96.2%,这表明蝙蝠冠状病毒可能是SARS CoV-2的起源。另外,全基因组[14]表明,穿山甲冠状病毒与SARS-CoV-2相似性为96%,与SARS-CoV、MERS-CoV和蝙蝠冠状病毒的相似性分别为82%、76%和71%,提示穿山甲很可能是蝙蝠与人类间的中间宿主。
3 病毒的传染
基本繁殖数(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s)R0用于描述病原体的传播或传染性[15],SARS-CoV的R0值约为3,MERS-CoV为0.45,SARS-CoV-2为2.2至3.11[16-17]。虽然SARS-CoV和SARS-CoV-2的R0值相似,但COVID-19症状出现前,患者鼻和喉中有更高的病毒载量,这表明SARS-CoV-2可在症状出现前传播,所以更难隔离和控制[18]。
SARS-CoV-2通过“刺突”蛋白锚定人肺部上皮细胞[1,19]。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受体充当了SARS-CoV-2突刺蛋白的“停靠点”,使病毒与细胞膜融合,然后病毒将自身RNA整合到细胞的复制机制中,促进繁殖。这样SARS-CoV-2就能在全身扩散,启动免疫应答,感染人类[20-21]。SARS-CoV-2的刺突(S)蛋白,在感染细胞时分裂成2个亚基,S1亚基包含2个受体结合域(receptor-binding domain,RBD),使病毒与宿主细胞结合;S2亚基对膜融合至关重要[22-23]。与S1亚基结合的宿主细胞ACE2受体是一种跨膜蛋白,位于肺、心脏、肾脏和肠道的上皮细胞[24]。S1亚基与靶细胞ACE2受体结合后,S2亚基的七磷酸重复序列1(heptad repeat 1,HR1)和2(heptad repeat 1,HR2)结构域结合,形成1个六螺旋束芯,使病毒和宿主细胞膜彼此靠近,以便发生融合[25-26]。SARS-CoV-2的传染性、传播性较SARS-CoV高,因为SARS-CoV-2受体结合域(RBD)与ACE2受体的亲和力提高了10~20倍,而这种差异源于SARS-CoV-2 受体结合域(RBD)的氨基酸序列不同[27-28]。
4 流行病学
截至2022年7月,COVID-19已影响全球6.04亿人,引发648万人死亡[29]。SARS-CoV-2的潜伏期长达2周,中位数为5 d,此期间具有传染性[30]。
Hosseini等[31]研究中,80%以上的COVID-19患者表现为轻度发烧、干咳和呼吸短促;重症患者中,44%出现呼吸短促,50%出现组织缺氧,14%出现高热[32-33],死亡率为2%。另外,基础合并症及高龄会增加死亡率[34-36]。有研究显示,依据年龄不同,5~17岁儿童住院率为0.1%,85岁以上老人为17.2%,5%以上的患者处于休克和多器官衰竭等危急状况[32,37]。Onder等[38]研究也显示,COVID-19患者的症状随年龄增长而恶化,19岁以下死亡率为0%~0.1%,75~84岁死亡率4.3%~10.5%,85岁或以上死亡率高达10.4%~27.3%。研究[39]还发现,COVID-19感染男性多于女性,这可能与X染色体和性激素的保护作用有关,它们导致了女性对SARS-CoV-2的免疫反应更强[40]。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甚至不同种族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并不相同[41]。尽管全世界的死亡率为6.9%,但智利和以色列的死亡率为0%~0.1%,而意大利为14%[1],考虑与各国人口密度、医疗体系、检测政策、年龄结构等相关。
5 传播途径
SARS-CoV-2“人传人”的主要形式是飞沫传播,咳嗽和打喷嚏会使其通过空气传播到健康人群[42]。飞沫是人释放病毒的介质,一般不会从源头传播超过2米,但空气动力学研究[1]表明,快速的体育活动会增加飞沫的传播距离,如跑步或骑自行车等。另一项研究[43]发现,SARS-CoV-2实验条件下,在空气中持续存在达3 h。Cai等[44]研究显示,接触SARS-CoV-2的无生命体也可传播,称为接触传播。根据材料不同,传染性从几小时(纸板)到3天(塑料或不锈钢)不等[43]。此外,在粪便中也检测到SARS-CoV-2,这表明其有能力在消化道内增殖,并有可能通过“粪口”途径传播[45-46]。有资料[47]分析,17.6%的患者存在胃肠道症状,当呼吸道样本检测呈阴性时,仍有48.1%的患者在粪便样本检测出病毒RNA阳性。
医院是SARS-CoV-2二次传播的来源之一,因为它是大量感染者的集中地[48]。Santarpia等[9]从COVID-19患者的病房中收集表面样本并提取病毒RNA,发现常见物品及空气样本中检测到SARS-CoV-2阳性,以空气中病毒浓度最高。
6 临床表现
COVID-19患者的常见症状是干咳、发热和呼吸短促,另外可能伴随喉咙痛、头痛、肌痛、疲劳和腹泻等不适[49-50]。重症COVID-19患者表现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和难治性低氧血症。COVID-19可导致严重的肺部感染、呼吸衰竭,伴随其他器官损伤和功能障碍;若出现呼吸系统以外的功能障碍,如血液系统和消化系统紊乱,则败血症和感染性休克的风险会升高,死亡率大幅上升[31]。虽然大多数病例表现为轻症,但所有患者均有新的肺部征象,如X线胸片半透明毛玻璃样改变;CT可表现为磨玻璃影、浸润影、肺实变等[51],且易侵犯血管引起血管炎[52]。在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患者中,双侧多小叶和亚节段区域实变明显[53-54]。
据报道,在感染阶段有些患者表现为白细胞或淋巴细胞数量减少[55],谷丙转氨酶(alaninetransaminase,ALT)、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creatine kinase-MB,CK-MB)、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和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升高[56]。
7 检测方法
早期诊断是治疗COVID-19最关键的一步[31,57]。SARS-CoV-2特点是在休眠或病毒载量低的一段时间内不易被发现,所以许多疑似患者鼻咽/痰标本检测结果呈阴性。总体说来,SARS-CoV-2检测第一道防线是通过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检测病毒基因组物质[58],然后是放射学、血清学检测、基于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检测方法及病毒培养等[31]。
7.1RT-PCR 这种检测方式在美国、德国、意大利、韩国及中国香港被广泛应用[59-61],需鼻咽拭子收集遗传物质,检测是否携带SARS-CoV-2。首先从样本中分离RNA,然后产生RNA的单链互补DNA (cDNA)[62],最后行PCR扩增cDNA进行分析,操作需数小时[63]。这种测试方法存在假阴性和假阳性的可能,与样品污染、病毒载量低、采样不正确有关[64]。在某些情况下,CT怀疑COVID-19阳性的病例,RT-PCR诊断为阴性[64]。中国已经使用高分辨率CT来补充检测,以防止假阴性情况发生[65]。美国雅培公司(Abbott)和德国博世医疗保健公司(Bosch Healthcare)对PT-PCR检测方法进行了改进,将处理时间缩短至15 min[66]。
SARS-CoV-2的全基因组测序已完成,现已允许分析和选择病毒的特定基因。在此背景下,Chan等[67]开发并优化了RT-PCR检测引物,用于检测SARS-CoV-2特有刺突基因(S基因);Corman等[68]也报道了SARS-CoV-2的其他基因特异性引物,如RNA依赖的RNA聚合酶(RNA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RdRp)基因、E基因、N基因。通过这些新方法,患者的唾液、呼吸道分泌物、粪便、尿液、血清、血浆都可用于分离病毒RNA。
7.2放射学检查 胸部CT显示特异性的磨玻璃影,属于辅助诊断工具[10,67,69]。双侧磨玻璃影及肺实变的出现提示需立即对SARS-CoV-2进行检测。Fang等[70]将胸部CT与RT-PCR结果进行敏感性对比,发现胸部CT能在RT-PCR阴性的患者中检测到异常证据,其在COVID-19患者筛查中敏感性达98%。鉴于胸部CT的准确性,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已被用于辅助SARS-CoV-2检测,目前处于起步阶段。COVID-NET是一种三维学习网络,Li等[9]通过使用此网络提取COVID-19患者胸部CT的视觉特征,目前已被证明可准确区分COVID-19、社区获得性肺炎和其他肺部疾病。
7.3血清学检测 血清学检测是将血清样本用于免疫反应检测,而这些免疫反应通常在特定的感染状态下发生,如重症患者垂死状态下,白介素(interleukin,IL-6、IL-2、IL-7、IL-10)的血浆浓度急剧增加[10,71]。有报道显示,COVID-19危重患者的血清中存在特征性“细胞因子风暴”,即免疫因子高涨,包括白细胞减少,CRP(10 mg/L以上)、血沉及D-二聚体水平升高[71-72]。研究发现,大多数COVID-19住院患者淋巴细胞总数明显下降,提示淋巴细胞,特别是T淋巴细胞可能是SARS-CoV-2的靶点。因此,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减少可作为SARS-CoV-2感染的一个标志,也可用于感染严重程度的评价[49]。
既往研究报道,SARS-CoV和MERS-CoV感染中,升高的IL-1B、IL-6、IL-12、干扰素γ(interferon γ,IFNγ)、趋化因子10 (interferon-inducible protein-10,IP-10)、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MCP1)等促炎因子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IL-15、IL-17等细胞因子,可能激活辅助性T淋巴细胞1(thelper cell,Th1)应答,与肺炎和肺损伤相关[31]。对比SARS-CoV-2感染,病毒颗粒入侵引发Th2和IL-4、IL-10等细胞因子的分泌增强,同时使外周血白细胞和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减少,导致炎症反应增强和免疫系统功能抑制,最终表现为严重肺损伤[54]。可见,与SARS-CoV-2本身的致病性相比,严重且难以控制的炎症反应具有更大的破坏效应。
目前,最常见和最快速的血清学检测是侧流免疫层析法,自患者处提取样本,检测是否含有病毒抗体[73];另一个是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以上这些方法的敏感性较高,会导致假阳性及高估感染率[74]。需指出的是,这些检测并不是为确定目前是否患有COVID-19,而是识别是否有SARS-CoV-2抗体,阳性结果表明个体在过去对病原体产生了免疫反应。由此推断,血清学检测可作为病毒传播范围的指标,而RT-PCR检测可显示目前是否患有这种疾病。
目前,多家公司开发了COVID-19检测试剂盒,通过IgG和IgM分子检测,识别出对SARS-CoV-2有免疫力的人,其可补充RT-PCR和放射检测结果[10]。试剂盒的出现,使重点护理检测成为可能,同时也能对疑似SARS-CoV-2携带者进行即时检测,提高了检测大范围人群的能力,从而有助于疫情控制和精准确定疾病病死率[10]。
7.4基于CRISPR技术的检测方法 CRISPR是规律地聚集在一起的短回文重复序列,它可检测到特定的RNA序列。锁定目标后,与CRISPR协同工作的Cas13和Cas12被激活,分别表现出核糖核酸酶(RNase)和脱氧核糖核酸酶(DNase)活性,分解附近的RNA链或单链DNA。当CRISPR-Cas复合物与一个报告分子结合,酶会分解附近的报告分子,引发反应,通过荧光信号或横向流动条带表现出来,与验孕棒相似[1]。此方法不需复杂的仪器进行测试,可靠、经济、敏感性高、特异性高[75]。美国Mammoth Bioscience公司、Sherlock Biosciences公司以及印度一家研究所正在进行探索[75]。
当CRISPR检测到SARS-CoV-2 RNA序列时,Cas13被激活并开始分解附近的RNA链;当RNA报告分子与CRISPR-Cas13结合,Cas13将其分解并通过荧光或横向流动条带发出信号,此过程称为SHERLOCK[9]。同理,当CRISPR检测到特定DNA序列时,Cas12被激活并开始分解附近的DNA链;当DNA报告分子与CRISPR-Cas12结合,Cas12将其分解并通过荧光或横向流动条带发出信号,此过程称为DETECTR[76]。DETECTR技术比SHERLOCK更快,但两者都在作为未来的测试方法进行研究和尝试。
张锋等[31]最近开发了一种基于CRISPR-Cas13的SHERLOCK系统来诊断COVID-19。该团队使用SARS-CoV-2 RNA的合成片段作为模板设计出2个RNA导链(CRISPR),这些导链能与SARS-CoV-2RNA中其互补序列结合,进而激活Cas13,分解报告分子。该方法用试纸蘸取样品,出现1条线即表示存在SARS-CoV-2。
7.5病毒培养 与其他方法相比,病毒培养更费时,但在其他方法使用前,其在疫情爆发最初阶段发挥巨大作用。此外,病毒培养还可用于体内、外抗病毒治疗和疫苗的评价试验。目前,一般实验室尚不具备条件进行SARS-CoV-2检测[77]。
8 治疗
8.1机械通气 在缺乏长期、可持续治疗方法的情况下,医务人员通过使用机械通气来改善COVID-19患者的严重呼吸道症状,如呼吸困难和缺氧。有研究纳入2634例COVID-19住院患者,约12%需机械通气,而接受此项治疗的患者死亡率高达88%[78]。
8.2抗病毒药物 现有药物在治疗COVID-19症状方面也显示出希望,WHO在报告中概述了治疗COVID-19的4种候选药物,即瑞德西韦、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干扰素β-1a和羟氯喹/氯喹。目前,瑞德西韦最有希望[79]。
瑞德西韦最初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其可阻断RNA复制的关键酶----依赖RNA的RNA聚合酶(RdRp),进而阻止病毒繁殖,能有效防止SARS-CoV和MERS-CoV扩散[80-81]。有研究[80]将瑞德西韦用于感染SARS-CoV、MERSCoV和SARS-CoV-2的小鼠细胞,结果表明,其能抑制SARS-CoV-2病毒传播。目前,几项关于瑞德西韦的Ⅱ、Ⅲ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美国一项大样本量研究现实,与安慰剂相比,瑞德西韦康复时间快31%,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紧急授权使用该药物[1]。目前,中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也在进行相关测试来确定其功效。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结合后被称为Kaletra,主要用于治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属于神经氨酸酶抑制剂。Kaletra在中国和南韩初步报告[82]成功后,科学家们开始关注其治疗COVID-19的效果。然而,当Kaletra单药治疗住院COVID-19患者时,并未显示出明显的益处或改善,这表明其对SARS-CoV-2的蛋白酶抑制作用与对HIV不同,因此停止对该药物的未来测试[82-83]。
干扰素β-1a用于多发性硬化症的治疗。干扰素是免疫系统的天然组成部分,能激活人体自身抗病毒机制,达到抑制病毒复制、增加免疫应答的效果[84]。早期研究[85]显示,注射干扰素可使人类上皮细胞的病毒载量降低,且喷洒干扰素可降低感染率,以上均支持干扰素疗法。近期研究发现[85],干扰素β-1a对SARS-CoV-2最有效,因其能上调肺部抗炎细胞,但此药仍需进一步研究。
羟氯喹和氯喹是两种安全、廉价的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疟疾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也被发现有抗病毒活性[1]。病毒通常通过内吞作用进入人体并感染细胞,所谓内吞作用即将病毒包裹并由核内体带入细胞。然而羟氯喹/氯喹增加了核内体的pH值,使其过于碱性而不利于病毒生存和复制[86]。鉴于其疏水结构,这种药物可在血液中循环,其作用可扩散到包括肺在内的全身组织,使其成为治疗COVID-19的候选药物[86]。在中国和法国,羟氯喹/氯喹的抗COVID-19作用已被临床试验[87]所证实,但样本量较小。由于该药物的已知不良反应最小,FDA已授权紧急使用。然而,也有研究[1]表明,羟氯喹/氯喹对COVID-19无作用或作用有限,甚至不良反应严重,所以有些医院停止使用。
法匹拉韦与瑞德西韦类似,通过阻止依赖RNA的RNA聚合酶(RdRp)与ATP结合,选择性地抑制RdRp,使其失去功能[88]。法匹拉韦疗效很好,服药后发烧、咳嗽等症状快速消退,中国科技部称其是一种“有效且高度安全的治疗方法”。目前,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89]。
EIDD-2801口服给药,通过在病毒中积累有害突变来抑制依赖RNA聚合酶(RdRp)活性,最终诱导病毒致死性突变,但存在很多脱靶效应。在小鼠实验中,预防性服用EIDD-2801可降低SARS-CoV-2及其他冠状病毒(SARS-CoV和MER-CoV)的浓度。2020年4月,FDA已批准负责EIDD-2801的公司进行人体试验[1]。
奥司他韦属于神经氨酸酶抑制剂。COVID-19出现在流感季节,抗菌药物联合奥司他韦成为COVID-19的试验性治疗方法。然而,并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奥司他韦是治疗COVID-19的有效药物[90]。
格里菲思作用于刺突蛋白表面的低聚糖,已进入治疗HIV和SARS-CoV的I期试验,但对于SARS-CoV-2的疗效应重新评估。刺突(S)蛋白在病毒-细胞受体相互作用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也是开发抗病毒药物的有前途的靶点[31]。
糖皮质激素治疗仅在医生诊断为重症COVID-19肺炎时才联合应用。系统性糖皮质激素治疗(甲基强的松龙40~120 mg/d)通过降低SARS-CoV-2诱导大量细胞因子减少肺损伤。但既往在SARS-CoV、MERS-CoV中证据[31]认为,接受皮质类固醇治疗不能预防感染患者的死亡,而是延迟病毒的清除。
一些非抗病毒药物,如二甲双胍、格列酮类、贝特类、沙坦类及营养补充剂,可通过增强免疫功能、预防或限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影响,进而减少感染引起的免疫病理损伤,改善病情[91]。
8.3基于CRISPR技术的治疗方法 基于SHERLOCK病毒检测技术,PACMAN(prophylactic antiviral CRISPR in huMAN cells)利用具有RNA酶(RNase)活性的Cas13,精确地摧毁病毒,也可敲除RNA依赖的RNA聚合酶(RdRps)基因,最终消灭SARS-CoV-2[92-93]。这项技术的给药途径尚在研究中,目前已建立了脂质体给药途径[92]。上述治疗方法仍需进一步测试,但使用CRISPR技术靶向病毒和消除症状,以及使用PACMAN预防未来病毒大流行,这方面的研究前景非常乐观。
8.4抗体治疗 To等[94]在一项23例COVID-19康复患者的研究中发现,血液中抗体浓度与抗SARS-CoV-2活性相关,因此将静脉输入恢复期血浆作为可行的治疗方法。Wang等[95]用恢复期血浆治疗5例危重患者,其中4例体温恢复正常且病毒载量降低,这表明抗体具有抗病毒活性。
有研究[95]利用ELISA发现一种能阻断SARS-CoV-2感染的人单克隆抗体——47D11,与恢复期血浆中发现的抗体类似。47D11能降低病毒活性,且可在实验室中合成。最近有证据表明,47D11在细胞中有效,制药公司正加紧生产单克隆抗体,以投入到新的研究中。
托珠单抗是一种重组单克隆抗体,与IL-6的亲和力很高,从而减少IL-6与原始受体结合并控制炎症反应。Xu等[96]研究显示,托珠单抗在改善症状方面效果显著,75%的患者能减少通气依赖。Guaraldi等[97]也观察到,接受托珠单抗治疗的COVID-19严重肺炎患者,有创机械通气和死亡的风险较对照组均降低。
8.5疫苗治疗 疫苗开发需数年时间才能获得全面批准并批量生产。试验通常分为:评估安全性,选取少数健康志愿者注射;评估疗效,选取上百名志愿者进行测试,其中包括高危人群;评估疫苗不良反应,在上千例患者中进行测试。
减毒活疫苗是将其引入接种者体内,引发免疫应答。这些减毒活疫苗是最接近自然感染的,在产生免疫应答方面非常有效[98],但儿童和免疫缺陷人群禁忌。
灭活疫苗是将死病毒或灭活病毒引入接种者体内,无需担心病毒恢复致病性引起疾病,但引发的免疫反应较小,为获得持续保护作用,需加强注射[99]。
亚单位疫苗只含有病毒结构的部分或亚单位[100],如针对SARS-CoV2的亚单位疫苗可能只包含S蛋白或S蛋白的一部分。亚单位疫苗不良反应较少,需加强注射,且昂贵。
核酸疫苗是将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NA,mRNA)直接注射到体内,然后mRNA编码病毒蛋白,引发免疫反应,接种者再次接触病毒时提供保护作用[1]。尽管这种技术已约30年,但核酸疫苗还未获批,因为需要有效的给药途径才能使其与活疫苗的功效相匹配[1]。
病毒载体疫苗是将编码病毒抗原的特定序列设计成非致病性病毒,即病毒载体。这种疫苗可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101],若接种者已对病毒载体存在免疫力,则无效。
9 新的病毒变异体
2021年11月,南非发现了第1例奥密克戎(SARS-CoV-2 Omicron)病例。这种新型谱系(B.1.1.529)与原始野生型菌株(wild type,WT)相比整个基因组共60个突变,被WHO归为SARS-CoV-2第5个病毒属。截至目前,突变的Omicron已进化成5个不同亚系,标准的Omicron亚系命名为BA.1,其他4个亚系称为BA.2、BA.3、BA.4、BA.5[32]。Omicron BA.1的受体结合区域部分共积累了15个突变,这有助于病毒与宿主ACE2的结合,增强了病毒传染性,且降低了疫苗及自然感染诱导的体液免疫保护作用[102-103]。有资料[104-105]显示,Omicron的基本繁殖数R0是δ冠状病毒的2.5倍,有效繁殖数Re比δ冠状病毒高2.7~3.8倍。
2022年1月,天津首次确诊本地传播Omicron BA.1病例,并达到社区传播阶段[29]。同年2月,Omicron BA.2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中国大陆,并升级为国内流行病。此后,各亚系Omicron病例接踵而来,且病毒携带者为疫苗接种后的完全免疫个体,这提示新型病毒存在严重免疫逃逸现象,之前的疫苗接种并未保持对Omicron的高水平保护[32]。虽然Omicron的传染率有所增加,但住院率和死亡率呈下降趋势。Menni等[106]的研究纳入63002例SARS-CoV-2 Omicron阳性患者,结果显示,与δ冠状病毒相比,Omicron患者在发病期间嗅觉丧失的发生率更低,喉咙痛的发生率更高,住院率更低。
此外,人们对于保护性疫苗的研究也从未停止,它是预防未来SARS-CoV-2变体的重要工具[107]。一项关于加强剂有效性的荟萃分析[108]报告显示,与未接种强化疫苗者相比,接受强化疫苗者Omicron感染率减少了71%。以色列另一项研究[109]也表明,第3剂疫苗接种能有效预防与Omicron相关的住院(93%)、重症疾病(92%)和死亡(81%)。而添加第4剂mRNA COVID-19疫苗,能在年老虚弱的个体中,减少各种原因导致的过早死亡[110]。因此,每年定期普及加强疫苗接种仍是预防SARS-CoV-2感染的有效策略,尤其是异种加强剂推荐用于顺序接种,其可诱导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有效的“交叉免疫记忆”或“互补免疫记忆”,以最大限度地防止COVID-19严重疾病和死亡[32]。
目前,WHO正在追踪许多亚型,如新出现的BA.5亚型BA.5.2.1.7(BF.7)正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并可能成为下一个主要变体。下一个SARS-CoV-2 VOC(variants of concern,VOC)也可能以SARS-CoV-2重组体的形式出现[111]。通过深度探索解码SARS-CoV-2的进化规律,有望预测新的变异毒株、获得更精确的数据、预测未来的大流行并及时预防。
10 小结与展望
对SARS-CoV-2结构及感染分子机制的深入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临床检验的进步可提高检测速度和特异性;而药物治疗的进步同样意义非凡。目前,SARS-CoV-2处于不断进化中,其危害性仍不可小觑,尤其是合并基础疾病、肺部结构性损伤的患者。另外,孕妇、健康状况欠佳者及免疫系统受损者属于临床试验的排除人群,但同时也是需保护的群体,应予特殊关注。
SARS-CoV-2导致了COVID-19持续大流行,还引发了急性期后后遗症,被称为“Long COVID”,即多系统负面影响,其与病毒直接损伤、全身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状态、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异常及社会心理压力直接相关[112],如何消除或减少这些负面影响也需格外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