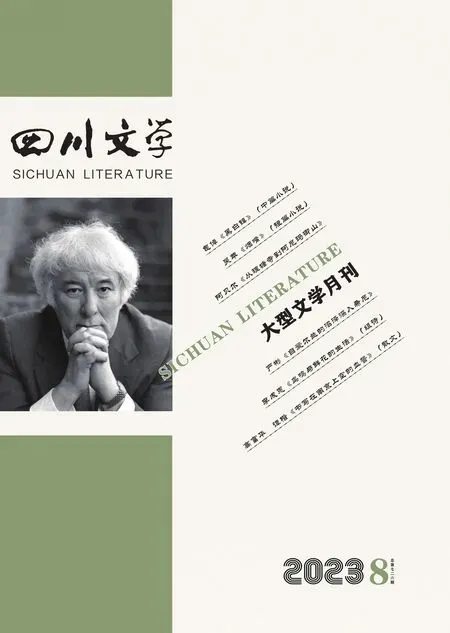从理塘寺到阿尼玛卿山
□文/阿贝尔
理塘寺:引导内心
每一天都是走向未知。但不是黑夜和死亡的未知,有线索(一点点)有想象。318国道不是线索,是导引,带他渐进地进入未知,不断地修正着想象变成实景(想象总是嫁接了脑壳里固有的印象)。
车过剪子湾山隧道,他平生又上了一个新高度:尼玛贡神山,海拔4668米。溪流般的兴奋对付着轻微的缺氧,脚步恍惚,视野却是平静而真实的。佛塔形的经幡层层叠叠没有超出想象,“高反”也没超出想象,超乎想象的是展现在眼前的史诗般的大景——原谅他找不到比喻,那是毗连着二郎山、折多山和贡嘎山的群山,以及群山间的山谷沟壑。葱茏,充满生机,苍翠,甚至铺展着新绿。用想象褪去它植物的衣裳,那便是洪荒,弥散着刺鼻的硫黄味道。这衣裳,它穿了亿万年,看似花团锦簇,其实是偌大的有颜色的时间。他首先着迷的是山脉呈现的线条,葱绿和翠绿的线条,高低远近,像海浪,又像乐谱,叫人去想象神的眼波,想象大地女神的胸乳肌肤……如果说远山淡影有那么一点形而上的话,那么路坎下的花草则是具象的。奇花异草,叫不出名,但却生爱、生占有欲,想即刻定格在镜头。
尼玛贡神山。除了代表敬神的经幡和玛尼堆,他并未感觉神的存在。因为八月,因为草长花开,他更觉得是伊甸园。神住在砾石山,神住在荒凉处,神住在雪冬天。
如果说理塘事先朝他发射有什么暗物质,那便是一幅阿来在毛垭草原匍匐拍花的照片。还有他对那个八月的理塘之夜的想象:篝火、锅庄、辩经、诗朗诵……这些只是背景,包括欢歌笑语,主角是孤独(一个诗人的孤独,以及虫鸣般的寂寞和酒)。
他想象中的理塘在靠近天边的草原。不是高原的尽头,是人间烟火的尽头,牛羊和野狼出没,人类活动的痕迹止于玛尼堆。
街道、树荫、房屋、规整后的溪流是人间的,国旗、横标和广告词是人间的。太阳则是洪荒,还有抬头可见的白云,以及白云和白云之间深邃的蓝天(一点看不出空洞,像是倒悬的海)。
时间,一种无法把握的反物质,像双面胶,将理塘的现实与虚无粘连在一起,也将他同那些之前、随后来到长青春科尔寺的人粘连在一起。换句话说,无论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都置身同一条河。
长青春科尔寺。他就在寺院门外墙根的阴影里。一辆手推车停在广场上(一个现代物件),一辆马车停在草径上(下来两个喇嘛),一只狗飞快地从停车场跑过(阿弥陀佛)……长青春科尔寺就在眼前,但对于他仍是个谜,随着他略显胆怯的脚步渐渐展开——却并无信心。
一座寺庙的功课无外乎三要素:创立时间、创立者和教宗教旨。知道了三者又怎样?他想要的是做30分钟的喇嘛(若30钟不行,就3分钟)。他想要的是一次反省、一次洗心革面,或者说一次融化。
寺院的阳光里真的有暗物质。不是天下第一高城的紫外线,是寺里隐隐的诵经声(像来自很远的潮声),是让他心跳加剧的神秘气氛。僧房、寺院、经幡、云朵、日夜不息地诵经的溪流、偶尔从院墙的转角走向广场的静默慵懒的喇嘛……静默是一种暗物质,僧衣的绛红也是暗物质,还有他们投在蒲公英和格桑花上的长影。
在经堂门槛外脱鞋的一瞬,他恍然意识到他是带了罪来理塘、来长青春科尔寺的。他的罪是焦虑、贪婪、怯懦和缺乏爱心。淤泥和污水长出的东西是不适应清澈的溪流和纯净的土壤的。他在这浊世生活了多年,身心充塞不少污垢,而今步入寺院,自然有种不适之感。它是身体对精神羞惭的反应,也是对洗涤的抵抗。习惯了喧嚣,习惯了随波逐流,习惯了在红尘飘然昏聩,心已经无法面对真相与善念。谁敢把真相讲出来?谁敢将善念领回心、变成行动?这里的谁不是你、不是他(她);这里的谁是“我”,一个个“我”,怯懦的“我”、贪心的“我”、世故的“我”、不安以及昏聩的“我”……走进经堂的时候,他们一个都没缺席,他们齐扑扑躲在他的衣服下、身体里,像一群幽灵。
他是在“我”的主导下,也可以说是在某种神秘的暗物质的主导下走进经堂大殿的。现在,这种暗物质变得清晰了一点,它不是道德或理性,而是一种审美,但这审美不只是感官的,不只是视觉的和听觉的,也包括直觉,包括一种来自雪溪和山泉的冲刷。
大殿很大,有一个大剧院那么大,是他念念不忘的林波寺经堂的好几倍。他站在门口,或依照转经的方向转到左侧,所见正在大殿中央位置诵经的僧人都显得邈远,听到的诵经声也像是隔了河的喧哗。大殿装饰华贵,流光溢彩,金碧辉煌(原谅我找不到别的词语),每一物件都巧夺天工。空气也流光溢彩。每一物件皆神器,每一柱子(贴了金箔和唐卡)皆神柱,每一喇嘛(正在大殿中央上课)皆神仙。
置身大殿,他感觉到某种胆怯和羞惭,暗中拿自己同殿中喇嘛相比有种无地可容之感。他羞惭的不是他为一俗人,而是他身上那份剔除不了的追求功名的执著(就像长进了肉的陈年污垢)。然而很快,他便摆脱了这样的自省,被大殿的神位和喇嘛的经课引发的好奇心牵引。他不再是一个戴罪之人,不再是一个忏悔者,他转眼变成了一位摄影师、一个纪录者(不舍执念,希望记录下神圣——僧人的日常)。
连拍几张照片后,他有了一种收获感。不是喜悦,是侥幸和满足,就像他拥有了另一个长青春科尔寺,就像他成了长青春科尔寺的特殊一员。拍下华贵,仿佛自己也拥有了华贵;拍下唐卡,仿佛也拥有了唐卡;拍下佛像(阿弥陀佛),仿佛佛可以带走;拍下僧人的上午课,仿佛自己也成了一个僧人,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拍照还不能满足,他又开始拍视频(做贼心虚),希望占有寺院生活的美好瞬间——僧人美好的人生片段。远远地拍,躲在柱子背后拍,将镜头拉近了拍,左右移动着镜头拍……120秒,他心满意足地收起手机,揣起长青春科尔寺2022年8月7日午前上百僧人的日常片段,继续转经堂。
舍弃执念、妄念,诚心体验,他感觉他在一步步走向天堂。他不知寺院任何的来历、传说和故事,不知1580年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也不知“长青春科尔寺”要断句念作“长青—春科尔寺”,意为“弥勒佛(未来佛)”和“法伦”;然而,他感觉到了颇有来头的神秘与神圣潜伏寺院的每一物件中,潜伏在空气中。他停下脚步,闭上眼,呆愣在一根神柱后面,像在溪水中感受鱼儿的亲吻与碰触一样感受着佛的关注。有一会儿,他感觉他像个泥人遇上了大雨,周身都有东西剥落。那是一种异域的外部力量,理塘乃至康藏的力量,进入了他的内里,做一次意外的清理。或许这力量来得更远,般若来得更远,基因来得更远,吸纳了藏地多种元素。看大神坛供奉的释迦牟尼和观音的五官就晓得了,那是南亚佛、印度佛、尼泊尔佛在康藏尚保留着原貌的样子。它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异域的美,是信众的生死观与日常生活的外化。
泥身脱落,浊气消散,他只剩“我”,肉身护卫着骨头,骨头护卫着心,心安放着莲花……有一种崇拜,有一种慈爱,不用五体投地,只需用心感应,好比同频电波彼此发收。
转到大经堂左侧,他数了数竖排的床榻一般的经席,从左至右一共有十五列。他突发奇想,若能将这一场景移至他未完成的小说岂不绝好!小说中的喇嘛寺遭遇乱世,大喇嘛所能做的只能是救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经堂传出的声音对于生者永远是一种治愈。
这么想,他的执着与妄念又回来了,即刻还俗。
澜沧江:美丽的错觉
澜沧江。他第一眼看见便驻车奔向她——奔向国道外侧高悬的崖岸,凝视她。她深潜谷底,咆哮奔腾,弓形的血色样子像一条偾张的动脉。浩荡的江水,荒凉的峡谷,他感觉到的不是澜沧江的壮丽,而是自己的渺小。然而,渺小的他也有按捺不住的兴奋,也有突发的眩晕,不敢想象跌下去的后果。如果跌下去可以化作澜沧江的一滴水、横断山的一粒沙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是去西藏,想必是逆流而上,澜沧江迎面从觉巴山流来——他感觉也是这样,殊不知他错了,且将错觉保留了数日,直到查看地图后才得以纠正。
他对于澜沧江的错觉远不止于此。“澜沧”是汉字,但不是一个汉语词(作为县名除外),只有“澜沧江”才是一个汉语词。不看不知道,“澜沧江”来自傣语“南(咪)兰章”的音译。“南咪”是“江”,“兰章”就是“澜沧”,意为众多大象生息的地方。
他很好奇第一个把这条发源于唐古拉山的河流书写为“澜沧江”的人——未必是语言学家,但一定是个诗人。于是,在他的想象中便有一条鱼,先是带着傣语“南(咪)兰章”,后来便是带着汉语“澜沧江”,从哀牢山中的热带雨林一路向北,游过横断山,游过昌都高原,直到在唐古拉山下与带着藏语“扎曲”的鱼相遇。在他的直觉与认知中,一个事物的命名,一种语义的确立犹如通电,在照亮语义所指的同时也确立了语义。一条下游有大象上游有牦牛的河流,最终在命名学上只彰显了大象的地位。
澜沧江流出云南后叫湄公河。“湄公河”也是泰语,母亲河的意思,意为“大河”,高棉人自己的河。
所有河流的命名都源于生息在河畔的人的自认,源于一种爱和交付。澜沧江还有一个别名,叫东方多瑙河,意为流经多国的国际河流(一条河首先是地质、地理学意义上的,然后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很晚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但它给予了河流命名。国家意义上的就更晚了)。
三天之后,在昌都,他又见到了澜沧江。年少的它有那么一点轻狂,有那么一点浑蛋,晚上华灯初上,又显得周武郑王。
怒江:内米诺夫斯基
由邦达镇西行转南行,攀升至业拉山垭口,沿途好几处都是回望玉曲河和邦达草原的好角度。接近垭口的位置最佳,不只看得见异域风情的邦达镇,还能看见邦达草原绵延天边的肉身和玉曲河亮晶晶的S形灵魂。
他再一次被眼前的高原大地震撼,灵感发现地驻车,从背包取出旅途携带的书籍,以邦达草原和玉曲河为背景,拍下几帧书影。首帧是曼德尔斯塔姆《时代的喧嚣》,次帧是伊莱娜·内米诺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以及他的《飞地》。
带内米诺夫斯基到西藏是他多年的梦想。她在被逮捕转运至奥斯威辛前几日仍在安静地写作《法兰西组曲》。她坐在火车站附近废弃的铁轨上用铅笔写作的样子让他浮想联翩。她早有预感,但仍未绝望,现实塌陷了,甚至个体生命也将陨灭,但并不妨碍她创造自己的世界。鉴于她创作的执着与勇敢,他带她来到西藏。
至于曼德尔斯塔姆,带他来西藏是一种复活。他的精神有着玛尼堆一般的坚强,他的审美有着怒江的深度与冲击力。
从业拉山垭口下怒江七十二拐,海拔直降1500米,怒江隐现于山涧谷底,像一条手术未尽暴露在外的大血管。
驻车怒江大桥,在傍晚变暗的光线里看见的怒江果真是一条大血管,桥头孤立的小石山、两岸风化崩塌的岩层就像手术中尚未清除的血块息肉。怒江在流动。坐在岸上,同它在一起,听它的鼻息,感觉如同和一条安静下来的巨龙在一起,与它合影也便是与巨龙合影。到了怒江,看见怒江,是一辈子的福缘。身到心到,才能完成审美。
暮色降临。互不相识的人聚集在怒江峡谷,准确地说是聚集在318国道怒江大桥一侧,赏景拍照,谈论怒江和怒江大桥。峡谷的空气里有种怪怪的氛围,怒江是个庞然怪物,新旧怒江大桥也像是庞然怪物。
怒江时间曾经也是地壳般洪荒原始的,只能用泥盆纪、白垩纪和侏罗纪标记。因为有了人,因为人的抵达才得以启蒙开化,第一管炸药引爆,第一辆汽车通过,硝铵和汽油的味道改变了怒江时间的成分。
怒江有它的史诗,从那曲一路向东、向南,千回百转,纵贯横断山,构建了独特的多语种的不仅有地质意义同时也有美学与人类学意义的语言。怒江不语,其存在就是一首史诗。我们的旅人在这个八月的傍晚读到的只是它的一个词语,一个让他惊叹的句点。
返回时在怒江又做了停留。这一次,他的兴趣不再在怒江身上,也不在拍摄72拐全景,而是在他恒久暗恋的三位作家身上——除了曼德尔斯塔姆和内米洛夫斯基,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娜杰日达也加入了进来。他隆重地将她介绍给了怒江,让她感受横断山最深处的脉动,请求怒江、横断山和西藏爱她。他有一种预感,她会爱,会与怒江一见钟情,而怒江也会像接纳它的孩子、接纳朝圣者一样接纳她。
在他的感觉和理解中,曼德尔斯塔姆对真理和美的捍卫有着业拉山的分明与不可动摇;做了他19年妻子却做了41年遗孀的娜杰日达有着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一样真实的母性。母性之水如同怒江水,或清澈或浑沌,内含神性,她的两本回忆录(《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足以与南迦巴瓦峰媲美,让怒江呜咽。
把他们的书取出、打开,任风翻阅,分享与怒江。书中的语言、思想、情感、画面犹如群鸟放飞怒江峡谷。相信她们的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
帕隆藏布:祖先之地
过安久拉山垭口,进入江那曲,他并未意识到他离开了怒江流域进到了雅鲁藏布江流域。
过然乌湖急下坡、长下坡,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迥异于冷曲河谷的大峡谷。
一个陌生刺激的峡谷,山随水转,山不转水也转,刺激来自急转直下的柳暗花明。陌生里有几分熟悉,不是之前来过或前世来过,而是这峡谷和他熟悉的岷山峡谷有几分相像。特别像夺补河峡谷,陡峭壁立的山势相像,石灰岩花岗石的岩体相像,山脚的森林和山顶的裸岩相像;更为相像的是湍急的水流、山体崩塌滚落激流的石头(制造出激流和轰鸣声)以及两岸被山洪冲刷见根并未倒伏的树木。
最为相像的是河流的灵魂,没有时间感的空谷弥散的气味——如果你驻车下到水边,避开不多的一点汽油味和急下坡刹车片产生的铁焦味。不只是大脑有记忆,身体也有记忆,急下坡的前倾和急转弯的重心偏移都能唤起他对夺补河的记忆。什么时候发现的,那种在视线很少被遮挡的急下坡所看见的景象——不是驾车行驶在某个国道某条河谷,而是行驶在一朵雪莲花瓣的缘口(不是雪莲花也是莲花白)?想到的不是“天路”,而是“天梯”——车行天梯。
帕隆藏布大峡谷。当他知道与他伴行的这条江和峡谷的名字时,当他意识到他身在何处时,他有些按捺不住的兴奋,有种幸福地被静电闪击的感觉。
帕隆藏布!他首先想到的是雅鲁藏布江。这里的江不再叫“曲”了,而叫“藏布”——叫“曲”也蛮好,雪曲、绒曲、格曲、阿总曲、玉曲、橙曲、瓦曲、桑曲、日曲……叫“藏布”更好,就像汉字里的“江”“河”,两个发音一个意思,一个意思两种意味儿。“曲”是乳名,叫“藏布”是学名,有种正式的南方气息。江那曲、巴曲、日隆曲流进然乌湖再流出来,就变成了帕隆藏布,感觉如同一个牧童进了学堂,老师给取了学名。
从然乌湖到米美村,37公里无人区,我们的旅人有种错觉一直在南行,下陡坡强大的惯性和身体持续的前倾也是朝南的。看地图才发现,318国道在然乌镇完成了近乎九十度的右转,向西的同时尚有大于三十度的北折(河床的面貌及其走向改变的精度,叫他无法不想起阿来故乡的梭摩河)。有时候,错觉并没有错,那是一种超乎知识的直觉,错的是拿知识作比直觉。
帕隆藏布同样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雪线后退,冰川融化,山洪泛滥。然乌湖一天不澄净,帕隆藏布一天不清澈。
如果说爱帕隆藏布,米美村之前是爱她的激流和大峡谷,爱那种夺补河复活的感觉,那么过了米美村爱的便是两岸的村庄、田野和树木了。那种既有人间烟火气又不失灵魂的村庄,可以看作每个旅人的故乡。
玉普乡至扎木镇(波密县城)一段,有种进入“江南”的感觉。当然不是苏杭水乡那种甜腻的感觉,而是河谷开阔、水流淙淙、森林茂密、生机盎然的感觉。雪山触手可及,气候明显呈垂直分布,空气湿度和氧气密度完全不同于八宿。他倏然意会这或许就是林芝的气息(植物太过旺盛分泌的气息,一种特殊的南方气息),或者说印度洋的气息。
接近扎木镇,村庄越来越多,多在帕隆藏布右岸的国道旁。路牌一晃而过,所能记住的名字都是最美的——尼根、仲美、纳玉、东若……每一个名字都有不同的释义,不同的释义是村庄不同的根、不同的历史与故事。
车过龙亚村,他被路边的青稞雪山吸引,驻车观景。栅栏外一直到帕隆藏布都是大片青稞。江边有白杨,闻到的是已经收浆青稞的麦香。对岸的雪山只是布景。“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他不经意念出了歌德的诗句。
龙亚村到波密都是林荫道,一种车行林区的感觉,行道树背后葱茏的灌木加深了这种感觉,舒适的路况和充足的氧气让他松弛而懈怠。
村庄一个接一个,且不再是他在冷曲和玉曲看见的相对原生态的藏村,而是重建不久或刚刚做过风貌改造的新村,一种超乎烟火味的时代气息与雪域江南的自然气息交织在一起,给了他的审美一种轻度的剥离感。
波密,藏语意为“祖先”意思。在玉美村和龙亚村停留的时候,他没有问那里的人他们的祖先是谁、从哪里来(既然是“祖先”之地,祖先都留下了哪些建树)。他没有问,想必问了也不能作答。人是很难内视自我的,更别说内视自己的遗传链了。不用问,也不用查阅经文史迹,唯一能寻觅到他们“祖先”的是他们保留下来的饮食、呼吸、语言和劳作的方式。
这么想,不知不觉到了波密县城。马路宽绰,街道整洁,饥肠辘辘但仍觉神清气爽。他感觉林芝的因子通过呼吸正在注入他身体。不是自作多情,西藏之旅到了林芝,想必理当如此——想想都兴奋,满怀憧憬,前面就是雅鲁藏布江、就是林芝,前面就是布达拉宫。
浪拉山垭口:发现伊甸园
214国道上的浪拉山垭口。旅途中又一让他震撼的风景(震撼指数不低于姊妹湖和觉巴山)。人们在观景台看风景、拍风景,他下到观景台下方的草坡,只想把“伊甸园”看个够。一片雪花落在溪谷,融化变成了村庄。你怎么想都可以,村子里的人不是从邦达草原下来的,也不是从外面的学曲、色曲进来的,他们不是女娲原地用泥土捏的就是由花神树精化成的。
站在海拔4572米、坡度超过70度的浪拉山垭口,我们的旅人有种冲下山谷去到“伊甸园”的冲动。去了未必住下,住下未必长住,只是去到,走进村子,走过那些泥木屋,掬一捧溪水或采几枝野花,听村里人说几句藏话(听不懂没关系),然后离开,就像那一次去与九寨沟一山之隔的中查。
他克制住冲动(让冲动化入想象),上到停车场。浪拉山垭口、德玛雪山、扎巴觉巴、雪瓦村……这些名字都是他后来知道的,包括《格萨尔王传》中十二座神山聚集的拉岭德玛觉尼。
车启动又停下。一片瀑布般向下跌落的草地吸引了他,其坡度、弧度以及静态中透出的流动感让他想到了当年的冰川。上车时他恋恋不舍,在一丛矮灌下捡了几块滑腻的赤石——裂痕里透出冰川的气息。
昌都:天路上的站台
昌都是一个站台,一个超出想象的二等站台(拉萨是一等)。澜沧江从站台一侧的大桥下流过,带来天国的冰洁与寂寞,带走昌都的灯红酒绿。一条大河流经都市,被水泥钢筋归顺、被流光溢彩照耀、被声色犬马感染的样子,会让人忘了她在源头的冰洁与纤弱,以及流经无人区、特别是流经某段尚未为人命名的大峡谷时的完美孤独。
夜晚走过马草坝大桥,获得命名不足500米的澜沧江被流光虚饰,在人工修筑的河道里发泄着某种克制不住的怨气。
一个与内地隔着千山万水的高原城市,昌都的繁荣超出了他的预判。这繁荣不是高楼、广场、霓虹灯和灯箱广告,不是肯德基、星巴克和书亦烧仙草,而是遮盖、剔除了酥油味的空气和市声。
回到现实,他不得不去做现实中的事:给汽车加油、入住酒店、做核酸、洗换下的衣裳、借酒店的签字笔手写一份授权书、与一位在昌都当过五年老师的熟人通电话……好在“列车”是他们自己的,自己驾驶,昌都站也是租借。虽然天国的绳子(比如汇流于昌都的昂曲和扎曲)牵引他们,奥密克戎追逐着他们,但还是不用太急,给汽车加满油是必须的,喘息和思考是必须的,重温人间的温情是必须的。
康。客木。都是昌都所指,都是一个意思:水汇合处。水为昂曲、扎曲。
昌都成为吐蕃地之前为西羌地,称东女国。可惜他不能像鹰飞起来,飞起来看“昌都”,就像在卫星地图上看见的那样:昂曲从西北来,扎曲从东北来;西边是亚贡玛和觉肖瓦,东边是果布卡和达客卡;214国道在俄洛镇离开昂曲,移情别恋色曲——若曲;317国道跟扎曲的关系稍好,维持到嘎日村才分道扬镳;澜沧江像一位南来的母亲认领了这两个孩子,并将她们领出横断山,带去了中南半岛。
玉树:在水一方
玉树有种天外之感。天外,又在人间。一个迥异于内地的人间,看上去很接近康巴的人间,或者说就是康巴延伸到天外的一个国度。
各曲流经的巴塘草原有天国的景象与气氛。不是荒野,是异域他乡,是时间遗落在昆仑山、巴颜喀拉山与唐古拉山之间的一片青稞。祥和安宁,有着不受外界纷扰的繁衍生息。
“玉树”是藏语“遗址”的意思,与他初见的直觉相符。早先是遗址,后来苏醒萌芽了,长出了一棵“玉树”。萌芽生长的遗址,多么像一个老树蔸,树砍了,根还在,深扎在大江大河的源头,从泥土和岩层吮吸力量,像一条条龙一张张嘴。各曲、扎曲、当曲、沱沱河、通天河都是它的根,每一棵草根、树根也是它的根,每一个部族、每一页藏经、每一块玛尼石也是它的根……玉树,激发他的首先是汉语的想象:一棵白玉、蓝玉、黛玉之树,酷似一棵冰树,开的花也是冰花,结的果也是玛瑙,长的叶也是玉叶;之后才有“玉树临风”“玉树芝兰”“玉树琼枝”“玉树银花”。
玉树是一个圣洁之地,可以疗愈不洁的悔过之心。
玉树在天边,但并非在荒漠旷野,也不在戈壁。在水一方。
结古寺下,玉树一夜。没有感觉到天国的抬升,灵魂还是深锁于肉体,且一如既往地被忽略。
他想得最多的不是格萨尔王,不是文成公主,也不是唐蕃古道上的那些化身贝雅特丽齐的大小曲河,而是教科书上的通天河。与其说格萨尔王住在玉树,不如说住在传说中——玉树也是一个传说。
玉树已在天国,通天河还要通哪一重天?
上午九时。文成公主庙香火淡淡,清寂而阴沉。庙门外的道路空寂,路下小溪自流,一位红衣女子远道而来,七步三叩。他确信贝纳沟裁取了一片唐蕃时间,就像庙中壁龛保存下来的唐卡。
进庙看见酥油灯,他不敢相信已静静地燃了1300年。正堂的如来佛,佛像上方岩壁雕刻的九尊佛像,也都供奉1300年了。
文成公主庙供奉的不是文成公主,而是文成公主选定的如来佛。其实,就算佛像不是她选、寺庙不是她建,传达的也是她的意思——她对贝纳沟、对贝纳沟人的感情。
勒巴沟。“勒巴”是藏语“美丽”的意思。文成公主汉藏和亲,“勒巴沟”藏汉合词。或许因为路况很差,注意力都在驾车上,他一点没觉得勒巴沟有多“勒巴”,怎么也无法与他见过的益洼沟(扎尕那)、玉瓦沟(九寨沟)、多儿沟(多儿洋布)、绒曲沟(如美村)、学曲沟(雪瓦村)相比。
如果说勒巴沟是真美,那一定是我错过了,比如1300年前凿刻在岩壁上的白塔和佛像,比如古往今来人们凿刻在溪口的玛尼石——浸润、流淌的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关于灵魂的信仰。
通天河出现的一瞬,他在没有获得确认的情况下叫出了“通天河”。微浊的河水,宽广的河面,高耸的崖岸,流动缓慢但不失整体的能量。通天河超出了他的想象,有他熟悉的蜀中河流的范儿。
通天河让他心安。沿通天河右岸去三江源纪念碑,他有种从一棵树上落地的感觉。不是一棵寻常的树,而是一棵玉树。车行肋巴村,跌落感特别明显,粗糙的树皮、坚硬的雾凇蹭到了肉。
玉树是一棵扎根通天河的树。一棵冬天结满雾凇的树——雾凇是它的玉佩。远在天边,与世隔绝,因为通天河又与外面世界相连。
通天河不是通横断山的天、金沙江的天,更不是通川江、汉江和黄浦江的天,而是逆流向西,通沱沱河、当曲的天,通唐古拉山的天。
通天河所通之天围拥起来,便构成了玉树的天界。
阿尼玛卿山:洛克之路
他是从洛克的日记中知道阿尼玛卿山的。它不是一座真实的山,是一个梦——于洛克是梦,于自己更是一个梦,一个不时唤起绝望之人希望的虚无,好比死神。
阿尼玛卿山作为一个梦之于洛克、之于我们的旅人不是相同的梦:洛克到阿尼玛卿山是要测算它真实的高度(以为会超过当时公认的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成为世界新的最高峰),一鸣惊人;我们旅人的梦要单纯得多,等同于冲着“阿尼玛卿”四个字一个词、冲着这四个字的发音“Ani maqing”;洛克筹划到阿尼玛卿山找角度,测算玛卿岗日的新高度,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论文;我们的旅人走洛克之路,只想来到阿尼玛卿山下,看一眼阿尼玛卿(看过,离开,阿尼玛卿山仍是一个虚无)。
现在,在约瑟夫·洛克的阿尼玛卿山之梦破灭九十七年后,他的机会来了。
上午九时,他出发去阿尼玛卿山,有种试探性地与梦中情人见面的感觉。阿尼玛卿山自己无法发给他位置,导航确认的是阿尼玛卿山所在的雪山乡。
出玛沁县城,过格曲河大桥,随导航沿209省道一路向西北疾驰。直至此刻,阿尼玛卿于他仍是一个虚无,一个被约瑟夫·洛克放逐的破碎之梦(犹如彩色气球破裂后散落的橡胶碎片)。他没有默念她的名字,没有为见面做点准备。除了“阿尼玛卿”这个名字,以及海拔高度远不及珠穆朗玛峰的结果,他对阿尼玛卿一无所知(百度词条所述内容系事后查阅),但阿尼玛卿的神圣早已从洛克的文字传给了他。
有些意外和惊奇的是,出城不久,在卡羊沟某处(具体位置可以通过所拍照片确定),一列雪山如满月般出现在了他视野的左前方,遥远而圆润,在一座略矮的黛色山脉后面绵延逶迤。
“阿尼玛卿!”他禁不住叫出了声。减速慢行,寻得一个停车区。阿尼玛卿,他看见她更多、更清晰。遥而可及,玛卿岗日的线条(弧线与折线)毕现、雪域的肌肤毕现。阿尼玛卿,彼此瞬间的对视便是一生,便是万年。“我数了数,有九座山峰,其中一座呈金字塔状……我不停地眺望,只见一只乌鸦在雪峰前飞过。”洛克见到她是在五月,他见到她在8月:稍显清瘦,轮廓清晰,额挺饱满,呈金字塔状的乳白山峰是最高一座。
阿尼玛卿,他想说他和你不是偶遇。他是追寻,你是他梦与现实的叠合。
接下来,他剩下的旅程——余生,便是去到阿尼玛卿的膝下,请她接受他的膜拜。
德马高速,沿东科河西北行,阿尼玛卿又一次呈现在眼前,金字塔的棱角、轮廓愈加清晰,白雪覆盖的坡面显得性感。导航的目的地是雪山乡,但是,当阿尼玛卿出口的指路牌出现,他临时改了主意,在阿尼玛卿山出口下了高速。
在青藏高原,相较于横断山和唐古拉山,阿尼玛卿是座孤独之山。孤独是阿尼玛卿的气质和精神。孤独而被膜拜,且多了梦的气质。
阿尼玛卿是切木曲和曲什温撑起的一只蚕或一片雪桑。切木曲有两只手,阳柯河和阴柯河(阳靠与阴靠)。阳柯河有四指:苦姆、酿母、年姆和赛当。年姆直接承受着玛卿岗日的冰寒与重量。阴柯河有五指:哈龙、阴靠、亥勒瓦勒、亥勒晓玛和尕尔玛。最长、最为承重的是哈隆和阴靠,阴靠托举着唯格勒当雄冰川,哈龙又一指分五茬,拦腰托举着整座阿尼玛卿。
曲什温又叫吻什曲、曲什安河。曲什温有三只手,青龙、扎青和得勒尼,但真正搂住阿尼玛卿的只有青龙。青龙的四指纤细却刚强,足以承受阿尼玛卿分配于西侧的压力,昂晓曲、切什克贡玛、切克什晓玛、阿玛尼捷赫分工合作,给予阿尼玛卿的爱一点不输给切木曲。
阿尼玛卿是孤独之神。曲什温和切木曲是神的血管与经脉,它们在托起阿尼玛卿的同时也成了神交的一部分。融雪融冰汇成涓涓细流,将神意分派给果洛大地、分派给黄河与炎黄子民。
阳柯河谷的泥碎路凹凸不平,草甸掩不住冰冻与泥石流撕裂的伤口。我们的旅人走走停停、犹豫不前。他不是怀疑阿尼玛卿的神性,也不是对阿尼玛卿的爱有所保留,他只是担心汽车爆胎。
在阳柯河村止步,改线返回走阴柯河。前面就是年姆,阿尼玛卿近在咫尺却不能抵达,这或许是人与神永远的距离。
出阳柯河,重新上德马高速,穿越阴靠峡谷,在雪山乡下高速。雪山乡是阴柯河于切木曲的汇入口,偏狭而隐秘,看不见阿尼玛卿,但空气里有阿尼玛卿的味道。
沿阴柯河谷的泥碎路进山,向西北方绕一个弧形,来到阴靠与哈龙的交汇口,我们的旅人终于又看见了阿尼玛卿。走得近了,换了角度,阿尼玛卿不再是远眺的样子,不再是一列,而是一座,伫立在面前,像一尊大神,人的幻化之神,有着人的模样、神的泰然。哈龙冰川和唯格勒当雄冰川像神袍的两幅前襟反射着太阳的光芒,传达着人们自以为尚可意会的神意。他面朝冰川,没有长跪,只是微闭双眼,双手合十,以自己的方式在心里膜拜。膜拜的同时,没有忘记感谢已故的人类学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的引领。
继续前行,他选择了走靠近德马高速的阴靠,愈加狭窄坎坷的泥碎路考验着他的驾驶技术和他的车胎,也考验着他对阿尼玛卿的虔敬。半程之后,他下车徒步,开始接受体力的考验。当雄冰川看似咫尺,他却走了近两个小时。
阿尼玛卿,请别出声,包括冰川融水汇成的浑浊细流,包括撕扯着经幡的风,包括洛克看见的乌鸦和洛克没有看见的神鹰……让我们的旅人静静地听、静静地感觉,让他调节好呼吸,在感觉自己心跳的同时也感觉你的心跳……
当雄冰川有着二叠纪、三叠纪砂岩的灰暗,冰川融化、刨蚀的截面明显,滴水如钟,传达出悲剧的意味……他长久地膜拜,短暂地迷失……阿尼玛卿,从此往后不求你中有我,但一定是我中有你!
“阿尼”藏语意为“先祖老翁”,兼以“美丽幸福、博大无畏”之意;“玛卿”意为“黄河源头的山”。阿尼玛卿即“祖父大玛神之山”,换句话说就是住着“阿尼玛卿”的山。藏民称它为“博卡瓦间贡”,意为开天辟地九大造化神之一,在藏人信仰的二十一座神山中排名第四。由此,我们的旅人想到了在阳靠和阴靠遇见的朝山者,他们从不结伴,独自一步一叩,朝拜阿尼玛卿山。他不敢说他们的膜拜是最高的审美,但可以说是最高的信仰。
藏民对阿尼玛卿山最虔敬的信仰是转山。与转经筒、转玛尼堆一样,按顺时针方向从阳柯河进山,翻达木乔垭口由前山转到青龙河,再转至西北,翻知亥代垭口转回前山的哈龙沟,再由哈龙沟转到雪山寺和阿尼玛卿白塔。朝圣者跋山涉水,顶风冒雪,风餐露宿,通常要七八天才能绕山转一周、完成膜拜,以达消除罪孽、灵魂升天的目的。
约瑟夫·洛克和我们的旅人在阿尼玛卿山都目睹了磕长头的转山者,他们用身体丈量着朝拜之路。“朝圣者都必须徒步,即使宗教地位最高的转世喇嘛也不能骑马转山。”朝圣者磕长头绕山一周,需要花数月的时间。这是洛克时代人们对神山圣境的真心。今天这样的朝圣者已寥寥无几,大多数人都是骑马驾车,怀着一种神已远去的功利心态。
离开阿尼玛卿山后,我们的旅人会时不时神游阿尼玛卿山。他的神游算不上是信仰,只是对美与神秘的迷恋、对现实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