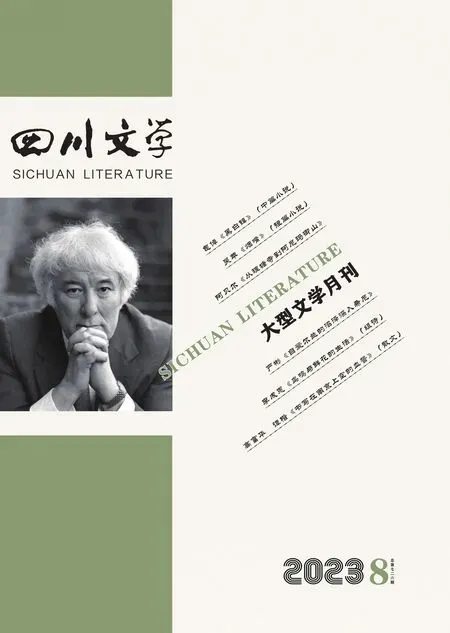一次失败的采访(短篇小说)
□文/刘庆邦
从1978年春天,到2001年秋天,我做过23年新闻工作,连续当过20多年编辑和记者。我写小说的时间更长一些,是从1972年开始的,至今还在写,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也就是说,我在做新闻工作的同时,从没有中断和放弃文学创作。不是我对新闻工作不重视,有证书为证,我得过三四次好新闻奖呢。只是相比较而言,我对文学创作更感兴趣一些。在我看来,新闻作品就是用来闻的,写出一条新闻,闻一鼻子就过去了。而文学作品是用来存的,每一篇小说、散文都可以长期保存下来。从数量上说,我所写的新闻稿子,要比文学作品多得多,可我连一本新闻作品集都没出过,而长篇小说却出了十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也出了好几十本。
我的体会,新闻和文学虽分工不同,各有使命,二者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不但有联系,而且有时候还可以做到相辅相成。新闻在于新,在于鲜活,在于和时代保持同步;文学可以不断从新闻中得到素材,启发灵感,汲取营养。同样,出色的新闻工作者也善于从文学作品中学习叙事的生动、语言的精准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反正从事文学创作几十年,我的不少写作素材都是从新闻采访中得来的。比如,我的一篇影响比较广泛的中篇小说《神木》,生发的基础就源于一篇案例性的通讯。
新闻之余变成小说,这并不意味着小说所使用的是新闻的边角料或剩余价值,不是的,在我看来,小说使用的是最动感情的部分,也可以说是新闻材料中的核心部分。新闻的特点之一,是要求客观、冷静,板板正正,不能过多地带有感情色彩。小说恰恰是诉诸感情的,情感之美才是小说的审美核心。一篇新闻稿件写完了,我觉得情犹未尽、意犹未尽,欲罢不能,通过进一步想象和虚构,就写成了小说。
所有动情动心的采访,是不是随后都可以写成小说呢?那不见得。年轻的时候,我曾有过一次大动感情的采访,三十九年过去了,我迟迟没有把那次采访得到的材料变成小说。我在一篇创作谈里谈过,我们在某件事情里付出了感情,并老也不能忘怀,其中包含的可能就有小说的因素,或许可以写成一篇小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我每年都会想起那次采访,一想起来就会在心里掂量好一会儿。可掂量来掂量去,好像找不到短篇小说应有的生长点,掂掂就放下了,我始终难以将其写成小说。冥冥之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不是很有能耐吗?不是能把一点点小事就可以写成小说吗?那次采访,我就是不让你写成小说。好,好,我服,我无能,行了吧。就算写不成小说,我退一步,只如实记述一下那次采访的过程,总该可以吧?我把那次采访,定义为一次失败的采访。
1978年春节过后,我从河南的煤矿调到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从事编辑工作。先是编煤炭工业综合性杂志《他们特别能战斗》,接着编《煤矿工人》杂志。杂志改成《中国煤炭报》之后,我被分配到报社的副刊部当编辑和记者。报社的说法是编采合一,编辑记者不分家。坐在编辑部里编稿子是编辑,外出采访就是记者。当时当编辑没有编辑证,外出采访却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记者证。我那时年轻,喜欢到全国各地走动。我一直渴望当记者,当记者让我感到荣耀,感到兴奋。不管是乘车,还是采访,我愿意亮出自己的记者证,多少有点显摆的意思。我还得承认我有私心,我的私心就是文学创作。文学创作的动力大都是源自私心。我走得越远,视野和胸襟就越开阔。我看的地方越多,心里装的东西就越多,写小说可供挑选材料的余地就大。于是乎,过一段时间,我就以采访的名义,到外地走一走。
这年秋天,我一个人来到牛店煤矿采访。出发前,报社领导没有给我布置任何采访任务,采什么,访什么,完全由我自己做主。我之所以选择去牛店矿,因为这个矿的王矿长是我的老领导:我在矿务局宣传部当通讯员时,他是宣传部副部长;我调到煤炭部工作之后,他被选拔到牛店矿当了矿长。那时全国煤矿实行矿长负责制,矿上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由矿长一个人说了算。说来王矿长对我有过知遇之恩,当年就是他不顾别人的反对和阻挠,执意把我从下面的基层单位调进矿务局宣传部。我去牛店矿,是感恩看望老领导的意思,也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宣传一下牛店矿的工作,以表示对王矿长工作的支持。矿上的宣传科,新分去了一个退伍军人小史,小史给我写过几篇不错的稿子,我都给他编发了,他也很希望我到牛店矿住上几天。
说起来,我对牛店矿是熟悉的,也是有感情的,因为我曾在牛店矿的井下抛洒过青春的汗水,甚至遭遇过冒顶的危险。那是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上级要求矿务局干部转变作风,跟矿工们一块儿下井参加劳动。矿务局的机关干部坐办公室坐惯了,都不愿意下井劳动。他们嘴上不敢反对下井,心里却嘀咕着,躲避着,把下井视为畏途。然而,我不怕下井。从农村被招工出来参加工作时,我并没有被分到井下,而是分到了水泥支架厂当工人。我的想法是,在矿务局宣传部做宣传工作,如果不熟悉井下的劳动环境和采矿过程,搞起宣传来就没有底气。我那时还没有真正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但我隐隐约约知道,要写哪方面的故事,得熟悉哪方面的生活才行。再说了,我当年二十三岁,在宣传部的所有干事中,除了一个不能下井的女同志,数我最年轻,我不去下井,让谁去下井呢?宣传部一动员下井,我就当仁不让似的举手,说我去。
那个时候的干部下井,不是走形式,摆样子,是铁打实凿,真干真拼。矿务局下到牛店矿的三十多名机关干部,被单独组成了一个掘进队,负责打一条煤巷。掘进队白天黑夜三班倒,每个班都必须完成一定的掘进进尺任务。我们穿上矿上发的劳动布工作服,戴上柳条编成的安全帽,去灯房领了矿灯,每天按时和矿工一起下井、升井。矿务局财务处去的一位老会计,兼任我们干部掘进队的记工员。我们每下井干一个班,他就在考勤簿上我们的名字后面画一个圈儿。我们的工资由矿务局发,矿上不再给我们发工资。记工的用处在于,我们每下一个班井,矿上会发给我们两角钱下井费,轮到上夜班,下井费是四角钱。我那时工资很低,每个月才三十元多一点,平均下来每天只合一元钱。我给自己定的生活费,是每个月九元钱,平均每天才三角钱。挣钱不易,我对角角分分都很重视。记得在牛店矿下井干活儿的四个多月时间里,大月我上三十一个班,小月我上三十个班,月月出满勤,一个班都不落。
兼任我们干部掘进队队长的是矿务局革命委员会的吴主任。作为全局的一把手,吴主任除了坐着小轿车回矿务局开会,或到市里和省里开会,一有时间,他就下井跟我们一块儿搞掘进。他本来就是一名矿工,因“革命”有功平步青云,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在我的印象里,他潇洒地把矿灯往安全帽上一卡,灯盒往腰间一披挂,不管是打眼放炮,还是架棚护顶,都干得十分卖力和娴熟,有时嘴里还说着粗话,一点儿都不摆谱。
在吃的方面,我们拿自己的钱和粮票,去食堂的会计那里买了饭票,然后就拿着饭票,到矿上的大食堂,跟工人一起在窗口外面排队买饭。工人买馒头,我们也买馒头。工人打稀饭,我们也打稀饭。打完了饭,我们就在大餐厅里跟工人一块儿吃。我们真正做到了和工人同吃。可在住的方面,我们没有做到和工人同住。相比之下,我们的住宿条件和工人差多了。工人都住在单身职工宿舍楼里,每个人至少都有一张床,而我们是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打地铺,硬地上铺的是从附近农村买来的谷草。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枕头,或者什么都不枕,或者枕一块砖头,砖头上垫上自己的衣服。每天下班后,我们哪儿都不去,除了坐在地铺上参加必须的政治学习,就是呼呼睡大觉。
忽一日,妻子到矿上看我。说是妻子,那时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起,她仍然住在她爸爸妈妈家里,我还一个人住在矿务局的单身职工宿舍里,家的概念还很模糊。说不是妻子吧,我们已经办了结婚登记手续,成了合法的夫妻。在牛店矿下井期间,我每天都在想她。可那时候没有移动电话,我无法和她联系。这天是个星期天,妻子骑着她爸爸的男式自行车,上上下下骑了几十里山路,竟然到矿上看我来了,这让我有些欣喜,甚至有些感动。这天赶上我上夜班,早上升井,半夜才下井,正好有时间和妻子说话。我马上带妻子去矿上的招待所,要求招待所的管理人员给我们安排一个房间。管理人员是一位在井下受伤调上来的老师傅,我之前到矿上采访住招待所时认识他,他也知道我是矿务局宣传部的新闻干事。不料他只同意让我妻子住招待所,却拒绝让我住招待所,更不要说我们两个住一个房间了。我跟他解释说,我们两个已经领了结婚证,住在一起是合法的。他很警惕地看看我,又看看我妻子,说那也不行。他给我妻子开了一个房间,我们在房间里刚说了一会儿话,他好像对我不放心似的,突然推门进来,催我离开。真可气,真让人扫兴!遇见这样古板的老师傅,让人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无奈之下,我只好带妻子到山里走了走,摘了一些成熟得像玛瑙珠子一样的酸枣。我们还到附近水库边的浅水处,以手绢当网,捕捉了一些小青虾。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回忆在牛店矿的那段经历,是想表明,那段青春岁月的经历,的确让人难以忘怀,并让人禁不住想旧地重游,重温旧梦。
老领导王矿长当然很欢迎我,他把一些在矿务局宣传部工作过的老同志也召集到了牛店矿,我们一块儿吃了一大盆子刚从水库里捕捞上来的野生鱼,你敬我、我敬你地喝了不少酒,高兴得不亦乐乎。
闲话少叙,该回到正题,集中记述一下那次采访了。在喝酒的时候,王矿长提到,矿上生产科有一位叫乔海东的工程师,那位工程师在牛店矿的矿井改造和生产潜力挖掘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值得宣传。牛店矿是一座老矿井,资源即将枯竭,矿井面临关闭。是在乔工程师的建议下,牛店矿延伸开采,开辟了新的采区,使老矿重获新生,原煤产量比以前提高一倍还多。乔工作为矿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做好规划、晒出蓝图就可以了,不必天天下井,到一线指挥。可乔工几乎天天下井,每月下井的次数,比采煤队采煤工的平均次数还要多。凭着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敏感,我一听就意识到,这位乔工程师的事迹值得采访,值得写成一篇人物通讯。在整整十年“文革”期间,工业战线动不动就批判“唯生产力论”“生产挂帅”和“技术第一”等,工程技术人员被说成是“臭老九”,普遍受到压抑,积极性和创造力很难得到发挥。春雷一声震天响,粉碎“四人帮”之后,知识分子受到重视,他们的报国之志和聪明才智被重新激发出来,又积极投身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谱写出了新的篇章。而我们的报纸,受以前长期形成的新闻宣传习惯影响,还是宣传不识字的、苦干型的劳模多一些,很少出现工程技术人员的先进事迹。这一次,我要解放一下思想,把报道对象对准一位矿上的工程师,写一写矿山知识分子的事迹。我之所以打算写成一篇人物通讯,而不是写成一篇消息,因为消息一般是综合性的,需要采访好几位工程技术人员,才能形成一篇消息。人物通讯是典型性的,只和一个人谈深谈透就可以了。还有,人物通讯里必须有人物,这与对小说的要求比较接近。就算人物通讯里的人物不一定会变成小说中的人物,但脑子里多储备一些人物,终归不是什么坏事。对人物通讯的写法,我也有了初步构思,我的构思是,写一个人物,不能为这个人物所局限,要通过人物前后境遇变化的对比,写出命运之变、时代之变。
这天上午,小史陪我去乔海东家中采访。小史已经提前跟乔海东联系好了,乔海东上午不去下井了,在家里等我们。乔海东高高的个子,显得有些瘦削。但他大大的眼睛、浓密的眉毛,有着堂堂的仪表。他说话声大气粗,像是一个采煤队队长的风格。他家住在职工家属区两间窑洞式的平房里,门口一侧开有一个小菜园,用木条钉成的兔子笼里,养有两只半大的白兔儿。我们在房子里的木头椅子上坐定,我说他住的房子还可以,我们的聊天就从住房聊起。乔海东说,这两间房子是他当上工程师之后,矿上为了照顾他,去年才分给他们家的。在此之前,他们一家常年借住在附近一户农民家的一间柴草屋里。他从矿业学院大学毕业和妻子结婚后,因妻子身体不好,需要他照顾,他就把妻子带到了矿上。他妻子没有城镇户口,矿上不能按双职工分给他们公房,他们只好到农村借房住。好在他天天为房东家挑水,并打扫院子,房东没有让他交房费。
我说:等于你天天为房东打工,房东不给你发工资,就免除了你的房费。
乔海东笑了,说是的,这样说也可以。又说:房东老两口岁数大了,去矿上挑一趟水不容易,我为他们挑水是应该的。
我问:柴草屋是不是很小,很简陋?
是很小,大约六七平方米吧。小屋是用石头片子干打垒垒起来的,不少石头片子之间都有缝隙,四面透风,八面漏气。小屋原来没有门,我去矿上拣加工坑木扔掉的板皮,才钉了一个门。门上也有缝隙,冬天下雪时,雪花儿从门缝里钻进来,每条门缝下面的积雪都有一小堆。后来我从矿上找来一些废弃的风筒布,在木门外面又钉了一层风筒布,才把风雪挡住了。
作为一位大学毕业生,你的居住条件是够差的。
那时候不讲什么大学不大学,好像谁上的学越多,谁的问题就越多,不受批判就算是好的(当时的说法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都有些灰溜溜的)。亏得我的家庭成分是贫农,政治上才没有受到过多歧视。当时我们家所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我每月的工资太低,粮食标准也太低,解决不了全家人最起码的吃饭问题。我的工资是每个月四十三块钱,一进矿就拿这么多钱,干了十多年,一分钱都没涨。我的口粮供应标准是每月三十八斤,一半粗粮,一半细粮。问题是,我们头一胎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儿后,又接连生了三个孩子,从两口人变成了七口人,多一口人就多一张嘴,每张嘴都要吃饭,不吃饭就不能活。可是呢,我的工资和粮票还是那么多,平均下来,每个人头每月摊到伙食费才六块钱,摊到的粮食才五斤多一点。
我说:那是太少了。一般社会上的人都认为,在煤矿工作的人收入高。像你们家这样低的生活水平,连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的农民都不如啊!
是不如农民。所以我就把两个大一点的孩子送回农村老家去了,让孩子的爷爷奶奶帮着养。牛店矿周围也都是农村,家里的粮食不够吃,我和妻子年年都带着孩子去周边的土里刨食。妻子去地里挖野菜,我是带着我们家的三小子,去农村收过玉米的地里溜玉米,或到收过红薯的地里刨红薯。到了秋后,地上都落了一层白霜,我们仍然去地里刨红薯,能刨到一块是一块,能刨到半块是半块。有时候,我们把土地刨开一大片,都刨不出一块红薯,只能刨出一两根细细的红薯行条。刨到红薯行条,我们也拿回家去。我们家的三小子学习特别好,也特别懂事,有时到点了,我急着去上班,他一个人还留在地里刨红薯,下起了小雪还不走。说到这里,乔海东停顿下来,眼里顿时有了泪光。他摇了摇头才说:不好意思,我不能提起三小子,一提起三小子我就有些难过。
我猜三小子可能有过什么不好的遭遇,刚要问三小子怎么了,乔海东却把话岔开了,说:我天天下井,并不是我多么喜欢下井,也不能说明我多么有敬业精神。当然了,井下天天都有变化,我作为采煤技术员,随时掌握变化情况是必要的。不可否认的是,我下井也是为了能多挣一点下井补助费,补贴家里的日常生活。话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不怕记者笑话,天天下井,我也是为了能挣到一份班中餐。班中餐是一只牛舌烧饼,大约有三两重,由矿上免费供应。每次领到烧饼,我都只吃一半,留一半悄悄揣进怀里,留给家里人吃。有一位老师傅,说一只烧饼他吃不完,也是只把烧饼吃一半,另一半塞给了我。我心里明白,老师傅知道我们家的困难情况,同情我们,就省下一半烧饼给我。我把烧饼拿回家,妻子把烧饼切成细条,兑上水,掺上野菜,放进锅里一熬,够全家人吃一顿的。
当记者的对采访对象的理解,离不开对自己的理解。只有把对自己的理解,与对采访对象的理解结合起来,才能加深对采访对象的理解。对乔海东所讲的家庭困难情况,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当时的艰难处境,要比乔海东家的严重得多。乔海东所讲的老师傅给他留一半烧饼的细节,虽然一带而过,但我一听就记住了。我心里一明,心说,这是小说的细节,老师傅的善良,正是一篇短篇小说的心啊!但我没有再多问老师傅的情况,只是问了一句他家的三小子现在怎么样了?肖海东在前面说,他不能提起三小子,一提起来就有些难过。这样的欲说还休对我构成了一种悬念,我还是想把悬念放下来。过后回想起来,我的刨根问底,对乔海东来说可能有些残忍。那次采访之所以成为失败的采访,也是我自找的。
听到我的提问,乔海东像是愣了一下,低一会儿眉,才说:三小子不在了,他遇到了车祸。
我心里疼了一下,不敢再问什么。屋子里一时静默下来。
停了一会儿,乔海东才接着说:孩子为了给家里省钱,连一支带笔杆的圆珠笔都舍不得买,只买一根带有蓝色墨油的笔芯儿,在笔芯儿下面缠上胶布,手指捏着缠胶布的地方写作业。一个星期天,笔芯里面的墨油用完了,他想搭乘矿上拉煤的卡车,去镇上买一根新的笔芯儿。他抓住车门外边的把手,已登上了车门下面的脚踏板,司机还是把他推了下去。结果孩子就倒在了车轮下面……乔海东说不下去,两行泪热漉漉地流了下来。
太惨了!孩子太可怜了!!怎么能这样呢?真让人难以接受。这样说着,我听到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有些哽咽,好像有一种东西已不可抑制,欲奔涌而出。我说:不行,不行,我受不了,受不了。接着,让我自己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我竟然哭了起来,并哭出了声。每个人的哭,都有一个自我引爆、自我推动的过程,听不到自己的哭声还好些,一听到自己的哭声,如同河水打开了闸门,我就有些管不住自己,哭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我像是忘记了自己的记者身份,也忘记了自己所担负的采访任务,表现得非常失态,甚至有些丢丑。我没见过乔海东的三儿子,谈不上对他的三儿子有多么深的感情。我之所以如此痛彻心扉,大哭不止,都是因为我联想起了我的小弟弟。小弟弟生在困难时期,因极度营养不良,造成了身体残疾,六七岁就病死了。小弟弟死时,我没能最后见小弟弟一面,在我中午放学回到家之前,母亲已着人做了一个小木头匣子,把小弟弟埋掉了。那天恰逢端午节,中午放学回家,我见母亲和姐姐、妹妹、弟弟哭成一团,我忍了忍没忍住,也哭了起来。在此之前,我不知道自己这样能哭,不了解自己痛哭的能力如此之强,我一哭就哭得翻江倒海,浩浩荡荡,以致浑身抽搐,手脚冰凉,差点儿昏死过去。自从那次为夭折的小弟弟痛哭之后,我这是第二次哭得这样厉害。哭着哭着,我头晕眼黑,手脚发凉,出现了与哭我小弟弟同样的症状。
我的痛哭把乔海东吓坏了,他站在我身边,手足无措,一再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陪同我采访的小史更是吃惊不小,他端起一杯水,让我喝口水。
我拒绝喝水,仍在挤着眼哭。
小史抱住了我的一只胳膊,把我往起拉,说刘老师,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一个人失去了理智,采访不得不中断。
小史带我来到矿上的医院,医生说我是精神受到刺激,导致神经紊乱。医生给我打了一针,我的情绪才逐渐缓解。
一次失败的采访,就这样结束了。
失败总是比成功更让人难忘。
尽管采访没有完成,回到北京后,我还是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人物通讯,题目叫《乔海东今昔》。我把稿子交到总编室后,总编室的老主任没有马上签发。他认为,今昔的昔字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特指,指的是旧社会,而我所写的昔,并不是旧社会,是乔海东“文革”期间的困难经历。这样使用昔字,容易造成概念上的误解。别看老主任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的老知识分子,我还是不同意他对昔字的意识形态化理解,辩解说:昔是指以往、过去、从前,是一个泛指,不是一个特指。把“文革”的日子说成昔日,没什么不可以。老主任摇头说,字字千斤,用字还是要谨慎。他还说,这篇稿子除了题目需要斟酌,今天的变化写得也不够充分,说服力不强,补充一些内容才好。
我心有不悦。在整个报社,我是比较年轻一些,但我是这家产业报的创办者之一,部长关于要把报纸办成什么样风格的署名文章就是我代为起草的。以前我所写的稿子,都是发得又快又好,从来没有被拖延过,更没有被“拍死”过。这次老主任不但认为标题不妥,还要我修改补充,岂有此理!我的犟脾气上来了,标题我不改,内容也不再补充,稿子爱发就发,不发拉倒。我和老主任僵持不下,稿子就被拖了下来,以致成了明日黄花。
这样一来,不但我的那次采访是失败的采访,所写的稿子也成了失败的稿子。
几十年过去了,我每每想起那次无果的采访,都觉得有些对不起乔海东。但落花流水春去也,我也无可奈何。
如今,我把那次采访写成了一篇小说,谁知道这篇小说是不是也是一篇失败的小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