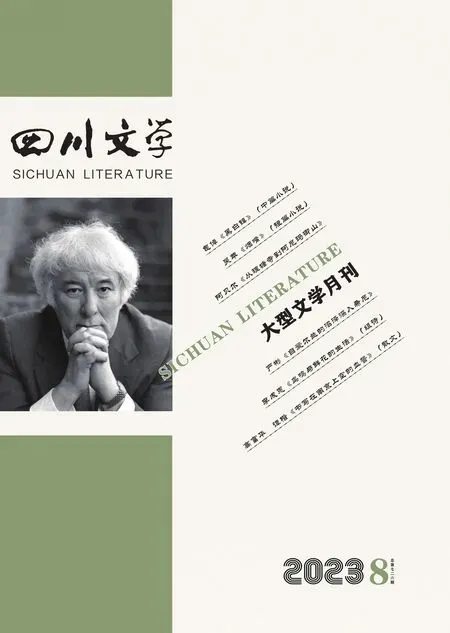暗战
□文/王建潮
李大成从商场对面的树荫下走出来,穿过马路。他见那对夫妻已经铺好摊,无非是两张粗糙的木凳子上搁一块两米多长一米多宽的木板。男的戴顶线帽,缩着脖子,女的一只大口罩遮住大半张脸。正是腊月,风刮到脸上生痛。李大成走向男人,说道:“昨天发酒疯了?”男人青了脸,说道:“想打架?”女人忙摘下口罩,露出谦卑的笑,一边道歉一边解释。听到女人的话后,李大成就会缓下脸色,说几句硬话,阐明立场,“不允许这样的事再发生!”铿锵有力地甩下这句话后,事儿也就翻篇了。
这是最可能发生的事,也是李大成乐见其成的。还会有另一种状况,一语未毕,男人即黑脸相向,伸出鸡爪似的五指叉将过来。但无论如何,必须去面对,否则,老婆那儿,周边经营户那儿,自己的心里,都,过——不——去。
李大成性格偏软,何况过了一夜,气消了不少。妻忙于生意,神情也舒张了些。近午边,李大成又出去了几趟,都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如此几回,再激不起勇气,仇恨的波涛也缓了下来。没想到到了下午,妻忽然说,不对,我的头仰不起来了。妻正做着一件睡衣生意,睡衣挂得高高的,需仰头用叉子叉下来。他忙接过来。忙完生意,妻说,我以为是落枕,看来是被他弄伤了。
李大成摸了摸她左边的脖颈,用力按了按,她疼得叫起来。是这里,肯定是伤筋了。
“贴个膏药。”李大成说。
“老毛病来了,不好贴的。”妻说。
“那休息一下。”
“明天总会好的。”
每到中午,李大成总要睡一会儿,今天他却对妻说,“你去睡一会儿。”店里的货架后面有一块木板搭的床,刚好够一个人平躺。
妻说,这么冷,还是不去了。你也不要睡,坐一歇。
一有空李大成就会坐到电脑前,看看新闻,玩点小游戏。那根凳子窄窄的,只能坐一只屁股,妻很少有时间坐。两只屁股一起坐,另一只只能坐半瓣。妻很少来挤,她一天到晚没有坐的时候,吃饭时也站着。柜台内除了电脑桌前有点空地,就是窄窄一溜,两人走路都要挺直身子,尽量往一边靠才能交会通过。
李大成让妻坐在里面。这样生意来了,他可以站起来做,让妻好好休息,这是他目前唯一能为妻子做的事。但妻是劳碌命,生意来了,还是抢着做。
晚上到家,李大成拿出红花油准备帮妻涂。妻摇头说气味太猛。李大成说白天怕影响人,晚上管什么?妻说你晚上要睡不好。李大成不管,涂了许多到她脖子上,又用食指上下刮。妻啊呀啊呀叫起来,李大成更加用力地刮起来。“痛,说明有效果。”李大成说。
当时报个案就好了。妻说。
李大成的心又一次沉下去。心里说,狗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狗屎!嘴里却说起别的事。妻叹了口气。
垃圾。李大成心里说。
“你有没有说给姐妹听?”妻问。
“没有。”李大成说。
“你呢?”
“没有。”
李大成想抱抱她,又觉得不妥。“明天你休息半天好了。”李大成说。
“不要。”
李大成拍了拍妻的肩,转过了身。
李大成不想让更多人知道,他想尽快平复心里的屈辱,可一闭上眼,屈辱感又充斥脑海。那婆娘冲到柜台前,指着妻大声吼的样子;男人冲上来一把扼住妻的脖颈的样子,甚至——有人说在推搡的时候,看见那男人的左手还捏了把他妻的乳房。凡有血性的人是不是应该以更强横的手段去报复?!比如冲上去,拔出尖刀,剁下他肮脏的手。
不声不响算什么,他们会怎样看你?周边的人会怎样看你?你不想扩大事态,也许会被他们视为懦弱。
但李大成还是决定息事宁人,只希望妻尽早走出阴影。他辗转反侧,妻也翻来覆去,直到晨曦初现,两人才蒙眬睡去。醒来时,已七点半。李大成说,你再睡会儿。妻说好。过了会儿,她说还是起来好。
到店,李大成坐在电脑桌前,不走出柜台一步,妻也如此。
李大成夫妻从商场开业就入驻,二十多年来,与来店的顾客和周围的商户从来没有红过脸。但自从那对夫妻来后,情况变了。李大成经营的是小百货,这么多年下来,积累了许多老顾客。那对夫妻是前年受让了老周的摊位进来的,因为与李大成的摊位相邻,李大成还曾为他们出谋划策。他们开始做玩具,刚有点起色,改行做服装,那婆娘矮矮胖胖,什么衣服穿到身上都不上相。男的比婆娘高不了多少,尖嘴猴腮,眼睛常年湿溻溻,初看可怜兮兮,处久了才发现自尊心强着呢。妻第一次见到他,说他长得像狐猴。李大成听了大笑,确实神似,他们刚看过动物世界的纪录片。李大成说,不好叫出来的。妻说,晓得。“狐猴”难得抬头看人,瞄你一眼,却让人想起鼠和狼的神情,胆怯里带着狠意。他们来商场半年多的时候,“狐猴”的女儿生了场大病,住院费也缴不上,李大成让妻拿了笔钱过去帮助周转。那婆娘当时感谢得几乎要跪下来。后来那婆娘逢人便说,“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真有这样的好人,我没有向他们开口,他们先送钱上门,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人啊!”
每次听那婆娘这么说道,李大成说,“不要再提这事,又不是什么大事。”
那婆娘便说,“对我们是大事。我会记住一辈子。”
李大成说,“你真要改改脾气,说话不要这么响好不好。”
那婆娘说,“啥,做生意的人,声音能不响。”
李大成说,“生意好坏与声音高低无关。”
那婆娘哈哈大笑,说,“你们城里人就是不一样。”
那婆娘的女儿四年级,婆娘晓得李大成读过大学有文化,便让他指导一下他女儿的作业。女孩继承了父母不好的基因,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粗鲁地把作业本一递,说,“喏,我妈说给你看看。”
李大成倒不觉得什么,妻却生气了。李大成还想好好教教女孩,包括为人处事。但来往了几次,李大成放弃了,就像妻说的,基因生好的,你也没有义务。
从骨子里李大成看不起他们,不是生活条件、衣着打扮,而是他们的做派。小心眼,猜忌,这方面,男的尤甚。“狐猴”很少与人打交道,一说话就能逼你到绝境。
去年他们也做起小百货,相近的摊位做同类商品,是大忌。一开始婆娘来叹苦,说没什么好做,饭都没得吃,只能弄点小东西卖卖。小百货品种多,婆娘起初还节制,尽量进与李大成不同的商品,渐渐地就不管不顾,后来更是见李大成哪样好销就进哪样。矛盾便产生了。
妻摆出脸色,又在李大成耳边嘀咕。商场没有明文规定,相邻的商铺不能买同类商品,但有行规啊。李大成刚进商场那会儿,相邻的商户都自觉地避开了售卖同类商品。
妻好几次想去讨说法,被李大成劝住。李大成说时代变了,老人跌地上都没人扶,你看看南门的老三,明目张胆卖假品牌,还炫耀。你看看朱胖子,人家摸了下商品,问了下价格就说商品给弄脏了,一定要人家买走。你看学民,介绍表妹来商场做生意结果成为竞争对手,整天闹得不愉快。你还以为是我们刚开店的时候?李大成总是这样劝妻。
那婆娘是真吃得了苦。她在商场外支出个摊。每天九点城管巡视结束,就搬出钢丝床,摆出应时商品。天刚冷,就在靠墙处支一横档,挂上各色各样的丝巾。再冷一些的时候,则摆上电热水袋,然后是棉手套电瓶车挡风罩。下午两点左右,城管巡视前,他就把商品搬进来。三点半城管走了,就又大张旗鼓地撑开帐篷,支起两块门板,像样儿地做起生意。天暗下来的时候,从商场里拉出电灯,一直要做到商场关门。进入冬季,风像刮肉的刀,那婆娘总是穿着宽大的羽绒服,戴顶线帽,大口罩遮住大半张脸在哪里做生意。
但她的生意是真的好,顾客进商场前就看到他们的摊,特別是路过的,以为摊上的东西便宜。这一来对李大成的生意影响很大,妻也想去大门口支个摊,被李大成拦住了。李大成说,你看看那胖婆的脸,那种罪你也要受?摆一天,刚做的面膜白弄了。李大成一说,妻的心理就平衡了。
李大成夫妻都是城里人,正经的商业类中专生,以前是百货公司的正式工。公司改制后,他们继续老行当,只不过自己做老板。夫妻俩的兄弟姐妹不是公务员、老师,就是电力公司的经理、电信公司的老总……那时候生意好做,他们的收入一点不比亲戚们差。
生意人看见同行生意好,心理总不平衡。“胖婆又进了三箱货。”妻说。那几天冷空气突降,那婆娘一天能销一箱电暖宝。每次李大成去公厕回来,总能看到顾客在那婆娘的摊位上挑选,而商场里却很少有顾客光顾。
妻向李大成说,“一个顾客买了她十只。”
李大成说,“不要去管人家,那么冷,你吃得消?”
妻说,“谁吃不消?”
李大成说,“想想人家,还租屋住,还过着你十多年前的日子。”
妻笑笑说,“也对。”
说归说,李大成的心里也是不平衡的。如果那婆娘不在外面摆摊,大半生意都是他们的。
相邻两个摊成陌路,但还没有撕破脸。圣诞节临近,李大成不准备做这个生意,因为电视上老早在呼吁不过洋节,学校里还明文规定。李大成把去年剩下的商品摆出来,贴上“处理”的标签。那婆娘还像去年一样大肆进货,一时间圣诞树就摆满了摊位前的走廊。这次那婆娘生意出奇的淡,到平安夜那天货还有一大半没有销掉。李大成看那婆娘惶急的样子,颇有点幸灾乐祸。晚上李大成去参加个饭局。大约七点左右,他接到妻的电话,说与那婆娘吵了一架。李大成说,怎么了?妻说,也没什么,过去了。李大成说,跟你说过,与他们吵最没意思,垃圾人。
虽这么说,李大成还是提前退席赶到了店里,见那边已经盖好布帘回家了。妻坐着发呆。便问道:“怎么回事?”
“有人问彩带,我说没有。”那人又问哪里有?我把手指到了东门,谁想那婆娘就对着空气骂起来。
妻开始还没听清那婆娘在骂什么,总算弄清了,但妻不擅长骂人,只会说一句,搞搞清楚,人家问的是彩带。
那婆娘跑到通道上说,骗谁呢,顾客刚刚在我这里问了圣诞树——你自己没有,乱指什么?
妻说,什么叫乱指,手生在我身上,你管得着。
这时候隔壁的晖晖说,我作证,顾客问的真不是圣诞树。
那婆娘说,我早就晓得你的心思了。
妻说,不要脸。
就见那狐猴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单手叉到妻的脖子上。这一叉用了狠劲,又显得滑稽。妻比狐猴高半个头,一时竟反应不过来,几乎要窒息。妻双手乱抓,双脚乱踢。边上几个人赶紧上来拉开了。
妻说,他也便宜不到哪儿去,脸上被我抓了几把。但看妻的形状,显然吃了大亏。李大成又去问了晖晖情况,问到关键点晖晖就支支吾吾。卖棉被的阿凤明确告诉他妻的胸部被侵犯了。李大成气得浑身发抖。可那边已经提前回家,灯也熄掉了,有力也使不上。
这是难熬的一夜。
他想时间会冲淡一切。可事情过去了一周,依然没有平复。李大成要忘却,“狐猴”那张青皮瓜脸就浮现在脑中,它冲出脑门,伸出青筋暴突的手,一下子扼住了妻的脖子,屈辱感就像洪水汹涌而来,淹没了他。
李大成不再去看他们一眼,再不经过他们的摊位,于他而言,那个区域就像一座坟墓。
一天,大约十点光景,那婆娘又在外面支了摊,突然从转角处出来五六个城管,搬了东西就走,那婆娘哇哇叫着一屁股坐到地上抱住了城管的脚。
看见这一幕,李大成像吃了块蜜。
那边开始骂起来,指桑骂槐。李大成当作没听见,妻也当作没听见。
第二天上班,妻刚进摊位,突然叫起来。李大成跑过来,看见地上躺着一只老鼠头,丑陋,血迹犹存,两只细眼,狰狞地盯着他。李大成解决了它。妻蹲在一旁干呕。妻说,肯定是他们。李大成说,不要瞎猜,他们哪有机会?可能是野猫吃剩下的。
李大成想,应该是我们送他们一只老鼠头才对。李大成确实想过许多招数,他甚至想把一个定时燃烧的机器,趁下班人少的时候丢到他们的摊位,把时间定在半夜。李大成知道一烧起来,自己的店也要受影响,但他不管这些,他就是要惩罚他们,最好让他们倾家荡产。但这些都是想想而已,本质上李大成还是一个善良的人。
这天,商场办公室老张叫李大成去一趟。老张说,大成,远亲不如近邻。
李大成说,什么意思?
老张说,我都晓得了,包括昨天城管来的事。
李大成说,你是说有人举报?
老张说,倒没有。
李大成说,没什么意思?真是垃圾人啊。
老张说,大家都赚点辛苦钱。
李大成听了,气得转身就走。
那婆娘依然把商品摆到外面,她难道不晓得卫生城市验收开始了?上次搬去的东西被她拿回来,她在吹嘘,说她走到城管大院,看见东西还在车斗上。
有人说,你不怕?
她说,他们搬东西也没有留下凭据。
下午城管直接找上门,说胆子不小嘛,这是犯罪。
那婆娘吓死了,因为她拿回来的东西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摊位前。
城管撕下一张处罚单,说,念你初犯,看你也不容易,否则……
那婆娘低声下气地说着谢谢谢谢。
城管一走,婆娘泼天泼地骂起来。她认定这事又是谁举报的,因为城管的院子里没收的东西堆成了小山,谁会注意她这点东西。凡熟悉的人都晓得她骂谁。
李大成恨不得杀了他们。
那天下班,李大成发现停在店门口充电的电瓶车的充电器烧掉了,充电器的上面还有一摊水。这是自己的店门口,为了安全,他还在充电器下垫了一块砖。李大成怒火中烧。
可这样的事防不胜防,还无计可施。
第二天晚上,李大成停在公园边的轿车轮胎被人扎了个洞,下手真狠,如果把钉扎进去,车子还可以开一段,他直接把轮胎弄出个洞,也不晓得用了什么工具,洞像一只可怕的蛇头嘲讽着他。
这里没有监控,报案也没用,一种无力感让他站不住脚。
他走到办公室,把事情讲给老张听。老张说,我说过,各退一步嘛。
李大成说,我没有做错什么。
老张说,与这样的人闹没意思,降低身份。
李大成说,我真没有做过什么。
老张说,我晓得,你不会做那些龌龊事。可人家会啊,你犯得着?
李大成说,没有王法了,没有道理可讲了?
老张说,世上哪来这么多道理。
李大成噎住了。
老张打了个电话,让那婆娘来。
老张特别说了句,让她一个人来。
老张说,你看看,我做事情总是想过又想的。
李大成说,你的意思是我怕他们。
老张说,这样说也可以,你这么好的形象毁掉多可惜。
李大成说,形象是给好人看的,对恶人要什么形象?那天要是我在,非打残他不可。
老张说,打残他,你不要坐牢?
李大成说,是他冲到我们店里来,就像一个强盗冲到你家,你任他肆意妄为,难道正当防卫也错了?
老张说,说你不懂,就是不懂,你以为是美国,人家冲到家里可以拔枪。我们不是这样的,你一动手,性质就变了,就是互殴,都要捉进去,还要留案底。
李大成说,胡扯。
老张说,到最后还是以调解结束,警察会劝你,冤冤相报何时了。
李大成说归说,心里真不想与他们正面冲突。对那婆娘,倒没有多少恨意,她的一些做派恶心可还在生意竞争范畴。
这么想着,婆娘阴沉着脸进来了。李大成瞥了她一眼,似乎还微微地给了个和善的脸色。
老张说,你说说,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那婆娘说,我们不像人家,玩阴的。
李大成耐下心,喝着老张泡的苦滋滋的老叶茶,听老张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轮到他了,他轻轻地叫了声婆娘的名字,他确实想了好久才记起她的名字,他看见婆娘的身子轻微地抖了下,然后他说起事情的前因后果,甚至还说了妻的一些不是,比如看见人家生意好心里会不痛快之类,没想到婆娘的脸瞬间乌云腾起,李大成不晓得哪一句触动了她的神经。那婆娘喋喋不休地数落起李大成的不是,好像李大成欠了他们多少人情。
原来如此啊!对他们的好变成了施舍,借他们钱是看不起他们,侮辱了他们,他们倒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李大成再也忍不下去,说,像你们这样的人家真是天下少有。
你才是最阴险的人,人模狗样,心最黑了。婆娘说。
李大成一股气直冲脑门,他用力拍了下桌子,准备离开。谁也不晓得“狐猴”是什么时候进来的,“狐猴”也用力拍了下桌子,把桌上的一次性杯子都震倒了。狐猴狠
狠地说,早看不惯你了,假正经。
李大成说,垃圾人。
老张说,一边说谁让你来的,一边收拾起桌上的茶水。就在这时,“狐猴”冲过来,伸出手,似乎直朝李大成的喉部而来。这一幕无数次地出现在李大成的脑际,在狐猴的手掌将要叉到脖子的时候,李大成拿起老张的保暖杯,用了全力,那几乎是动了杀人的恨意劈过去,只听咔嗒一声,像什么被摧毁一样,只听一声惨叫,“狐猴”跌到地上。那婆娘疯了似的扑过来,李大成拎起椅子,咬紧牙关,那是一种比疯更疯狂的神情。那婆娘哇一声改了方向,扑向男人。
警察来的时候,李大成早跑了。他不晓得“狐猴”的手伤得怎样?也许他们会砸他的店,也许他们会报复妻子,也许……李大成从来没有与人动过手,想不到动手即下狠手,这都是那只伸过来的手,那是只叉住过妻的脖颈侵犯过妻的手。
妻说,你不用管我,出去避避风头,反正报过警,就让警察来解决。
李大成关掉了手机。
李大成想,也许自己会进拘留所,也许会留下案底,但无论如何终于狠狠地收拾了“狐猴”,心里的恶气倒消了大半。该来的就让它来吧。
到了晚上他开了手机,果然有许多未接电话。妻说,警察说你一定得去派出所一趟,不过已经通过关系说好了。他们去过医院,给了些钱,调解成功了,你过两天就可回来。
这么简单?
李大成是在第三天晚上快打烊的时候到店里的,这是他想过又想的时间。毕竟这事已经在商场里传开了,他是要面子的人。这会儿大家忙着收摊,看见李大成都点头致意,有的还说,回来了,仿佛他去旅游回来一样,但他还是发现人们的眼光里有了别样的东西。李大成之前一直是温和的“好人”,这是大家公认的形象。
妻说那边这些天都很早收摊。李大成想过许多结局,也做了许多准备,看来比预想的好。
妻说,在派出所,他们很乖的。警察看了妻之前脖子受伤的照片,弄清了事情的原委。那家伙畏缩了。老张也说了经过,他只叫女人来,没有叫别人来。所以两次事件都由对方挑起。
花点钱值。妻说。
第二天李大成就正常上班了。他瞄了那边一眼,男人的手上还缠着绷带,呆呆地坐在走廊上。李大成倒有点同情他,可脑子里又出现那双伸向妻的手,叉向自己脖颈的手,他的怒火又一次涌上心头,他想,为什么办公桌上没有一把刀。
活了大半辈子,李大成还没有遇到过这么难以消除的怒火。
李大成的摊位在北门主通道边,整个墙面都是钢化玻璃,他在玻璃上贴了个广告,画了些毛巾、脸盆、整理箱上去,中间是美术体“大成百货”。与他相邻的便是那婆娘的摊位,那边也有一扇门,不过是小门。那婆娘把与李大成相邻铺面的三分之一租给了晖晖,晖晖做的是玩具。晖晖的店成为缓冲地带,就像两个敌对国中间有了个中立国。这当然缘于那婆娘的精打细算,房东给她的租金是每年六万,那婆娘租给晖晖三万,租金上就赚了许多。
商场里贴隔壁的摊位,要么成为好友,吃饭时你来我处夹一筷菜,我来你处倒杯酒。要么成为仇敌,各自站在柜台上相骂,一般不会走出自己的领地,否则性质就变了。抬头不见低头见,最重要的是大家都靠这里吃饭,真闹翻,谁也承受不了后果。“狐猴”不同,他冲出领地,跨过一家摊位,侵入到你的地盘,就像一个国家侵入到别国的领土,能不反击?
“狐猴”很少与人说话,整天没有笑脸,难得聊天,几句就能把你逼入绝境。刚来商场那会儿,老张让李大成传话缴管理费。“狐猴”说,为什么要你来说,这不是办公室的事么?李大成说,是办公室的事,我就传个话。“狐猴”说,为什么要你来说?李大成说,就传个话,谁传都一样。“狐猴”说,要缴,也要办公室人来——谁晓得里面有没有猫腻。
李大成据此分析此人可能曾经被人欺侮过,所以总是一副警戒的神情。后来知道,他们到城里来寻活路,果真在村里待不下去了。
两家人从此形同陌路,好几年了李大成再没有经过那边的摊位。有时候去公厕回来,突下急雨,如果走小门可以少淋点雨,李大成还是冒着大雨多跑十多米路。当然,仇恨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慢慢减弱,但没有从心里根除。同一个商场,抬头可见的位置,那婆娘过分的笑声,夸张地喊老公的声音都能让他反胃。
但他们在改变。他们舍得花钱了,小小的摊位搭建得像蜂窝一样。门口的摊位越来越像样,玻璃墙上方装上可以称得上巨大的雨棚,临时摊位上的支架木板都是可收缩的,看上去精致又漂亮。那婆娘似乎与城管达成了某种默契,只要他们不过分占道,城管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李大成好几次看到婆娘与城管眉来眼去。这样一来,临时摊位变成长期摊,晚上下班也不收摊,只用一块雨篷四面一围,夹上铁夹,反正到处是监控,不担心被偷窃。第二天婆娘总是很早来到商场,掀开雨篷就可以做生意,早起的买菜者锻炼者路过就会顺带点小东西回家。等李大成上班,那婆娘已经忙过一阵。
当然可以学样,但不是所有样都可以学,让李大成学他们的样,也让他面子上过不去。所以即便有一百个不舒服,李大成能做的也只是避开与那婆娘类似的商品,还得找理由寻个安慰。不得不承认就几年工夫,李大成的生意已经不如他们,这是李大成最不愿承认,又不得不承认的。
李大成只有一个女儿,在市中心有三套房子,对生意倒真没有多少追求,但生意人竞争的心理还是在的。那婆娘的性格一直没变,大声地说话,夸张的言词,对此李大成也麻木了。去年十二月晖晖的铺面到期不做了,那婆娘竟然把摊位租给了卖佛宝的人,在正规的商场里卖这样的商品简直不可思议,但没有人管。显然那婆娘事先说了李大成的坏话,新来的摊主对李大成爱理不理,很快便在李大成的对面挂出了一些花里胡哨的挂联纸,一串串金色银色的元宝。这些东西整天飘在眼前,李大成的心情再也没有好过,初一十五更是整天唱着阿弥陀佛。李大成觉得这是那婆娘有意为之,因为晖晖决定不做的时候,曾经有个卖挂件的人看上了这个位置。
正月里,李大成去一个姨父家吃饭。也不晓得怎么说起的,姨父说,你们商场有个叫XX的吗?李大成说有,怎么了?
姨父说,江边不是大拆迁吗,那些握手房里都住着些什么人,真是三教九流泼皮无赖的世界。
李大成说,也可以说是贫民窟。
姨父说,这下翻身了。政府给了最好的政策,可有些人还变着花样讹钱。这个人最奇怪,在车库里贴了张营业执照,就狮子大开口,至今也治不了他。
李大成心里抽了下。商场里营业执照批不出,发票就领不出,这意味着稍大点的生意就做不了。李大成是有些单位生意的,要发票只能去批发商处或者去别的商场里托人开。这是额外的麻烦,想不到这婆娘竟然想出这样的法子,怪不得生意越做越好。被李大成看不起的人原来精明着呢。
李大成说,你们不是有许多办法?
姨父说,问题是他们家族白开水一样,一个公家单位上班的都没有。这次工程,书记说过绝不能用强,现在这钉子落在我身上了。
李大成说,你有多少尺寸?
姨父说,不瞒你说,有点大。
李大成说,抓蛇抓七寸,打人要打到痛处。
姨父说,你倒说说。
李大成想了下,说,生意人,最重要的是生意。
李大成没有再发挥。李大成一点也不想惹事。李大成晓得凡做过的事总有露出来的时候。李大成年纪大了,心态放平和了。李大成想,他们赚得再多也是他们的,与我无关。这话很好笑,但李大成就是这么想的。李大成最关心的是妻的心态,他怕妻没有他这样的心态,躺平也好,想通也好。实际上妻比他还通透,妻甚至打算再过两年把摊位转让掉去农村租个小屋过过美好的乡村生活。
过了元宵,生意慢慢好起来,城管又开始正常巡逻。那婆娘还是采取原来的措施,赔笑、巴结,很听话又屡教不改。城管也给他们好脸色,口头通知,好好劝说,边上还有同伴录着视频,后来城管就没有好声气,真是牛皮糖啊,就撕下一张处罚单。
处罚的金额倒不大,可是烦,得去执法局。处理的姑娘态度蛮好,会拉张椅子给你坐,然后开始问讯,姓名、身份证、营业执照……然后让你对着镜头,姑娘读着一大段文字,你要回答晓得了、是、知道的。那婆娘觉得留下了案底,浑身不自在。罚过了,以后还能不能摆么?她竟然问出这种话。
不摆摊几乎要了“狐猴”的命,而拆迁的事也让他身心俱疲。城管似乎就守在看不见的地方,一摆出来就冒出来,而拆迁办更是不时打电话让他们去协商。李大成当然不晓得这些情况,谁去管与自己无关的事,但“狐猴”他们不能出摊他心里倒高兴。
那天打烊后李大成与朋友去江边喝茶,结束后到商场边的停车场开车,他看见“狐猴”他们又在门口摆摊了。这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光景,路上行人已经不多,李大成就在马路对面的树荫底下站下来。
他是好奇。一辆三轮车上放着一块平板,平板上放着商品,雨棚上挂得密密麻麻,寒风不时把那些围巾啊袜子啊吹得东倒西歪。李大成看了二十分钟,平均三分钟有个顾客,买的商品都是便宜的日常用品。当然生意不能这么算,谁也不晓得啥时候来个大一点的生意,还有,鬼知道他们几点开始出摊的。
九点半光景,那婆娘开始慢慢地收摊,李大成估算,整个摊收好总需半个来时辰,李大成决定回家。就在这时,对面吵起来,“狐猴”把那婆娘正收到箱子里的商品夺下来,重新摆到摊位上。那婆娘不理会,继续收摊。就这样,一个收一个摆,看来顶上了,显然“狐猴”还想摆一会,而那婆娘坚决要收摊。忽地,至少在李大成看来是毫无预兆的,狐猴伸出他瘦小的手就叉向婆娘的脖子。奇怪的是,婆娘没有反抗,反而把脖子挺了过去。那神情可不是怄气,而是迎合。狐猴就轻松地叉住了婆娘的脖子,婆娘并不反抗,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那婆娘的脸色渐渐变了,接着干呕起来。就在这时,又是没有预兆的,“狐猴”转身就蹲到地上号哭起来。隔了条马路,李大成还听得真切,那是类似于受了伤的动物的悲鸣。在空旷的马路上,在寂静的人行道上,那带点憋屈的哭声把城市的树叶也惊得纷纷飘落。李大成的心里一颤,转身就走。
那天是个下雪天,大约晚上八点半光景,商场早打烊了,所以几乎没有商场里的经营户看到事情的经过。商场门口突然开来一辆执法车,忽地跳下四五个协管。许多行人都看到了当时的场景,那婆娘在赔好话,“狐猴”在与为首的议论,然后推搡,谁也没有看清细节,因为那天的雪后来转成了雨夹雪,湿漉漉地落到身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而路灯也被雨雪打湿了,整个场景便处在朦胧中,好像梦里的样子。看热闹的人都站得远远的,后来人们统一的说法是确实看到了“狐猴”的手叉到了为首城管的脖子上。接着便是混乱的状况,有人说听见一个人恐怖地叫了一声。“狐猴”撒开腿奔跑在湿溻溻的人行道上,被水老鼠喷得满身污水,只有一个人在追。躺在地上的是一个年轻协管,血与污水混在一起。
有那么一刻,李大成热血沸腾。似乎奔跑着的是他,躺着的是“狐猴”。
此事过后,那婆娘的摊位一直盖着布幔。商场里足足热闹了好几个月。那婆娘在“狐猴”判刑后处理了商品,摊位便转到了卖佛宝的手里,买佛宝的把那些东西搬到小门边,原来的地方租给了卖挂件的人。小门的上空便整天飘扬着挂联纸,似乎商场里正在办着丧事。
于李大成来说,一切都了了。但卖挂件的经营半年后生意清淡,也卖起小百货,毕竟小百货是最简单的生意。
绕了这么多,李大成又要直面竞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