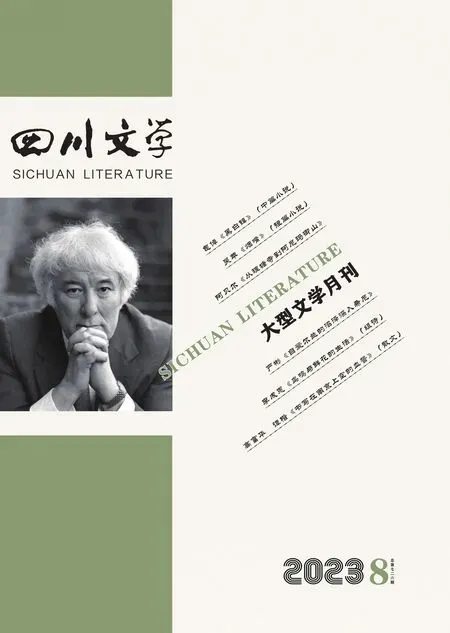自爱尔兰的沼泽深入希尼
□文/严彬
1
1995年10月的一天,希尼和他的家人在异国他乡,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度假,住在离皮洛斯港口不远处的一家小旅馆,在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的“所有欧洲人的故乡”。诗人希尼从他和他家人生活的地点,他出生的北爱尔兰,他反复往来漂泊讲课的美国,回到了欧洲人的精神源头希腊。
伯罗奔尼撒古老的风吹动希尼的满头银发,诗人在翻阅他已经翻译了五年的索福克勒斯;那首有关那场发生在三千多年前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和特洛伊人的著名战争之诗篇《迈锡尼守望者》已经完成,后来收录在他1996年出版的诗集《酒精水准仪》中。
电话打来了。已经成为和他父亲同行的语言教师的克里斯托弗接到电话,并将那个传言数年而终于成真的消息转达给了他的父亲:
“爸爸,我们为你感到骄傲。……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希尼在突兀的消息中回过神来。他告诉克里斯托弗:
“你最好告诉一下你妈妈。”
很快,整个希腊和北爱尔兰都知道了希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他们的诗人正在希腊的消息。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打电话,试图和家里的人、和散布在各地的朋友联系,爱尔兰的和美国的。”希尼对后来的采访者奥德里斯科尔说,“我满身大汗。”
获得至高文学荣誉的希尼自希腊返回北爱尔兰。总理在机场等他,礼宾车送他直抵总统府,而第一个播出获奖后接受采访画面的是爱尔兰广播电视台……作为诗人的希尼几乎享有了诗人能收获的所有荣耀,那荣耀照亮他的爱尔兰家乡德里郡和成长的摩斯巴恩农场,照亮了世代耕种劳作的希尼家族。此时距他出版第一本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1966年,费伯出版公司)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
2
我读希尼已经很晚,大约在2017年写那首以《挖土》为题回忆父亲的诗之前不久。
《挖土》是受希尼1966年(作者时年27岁)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吴德安等译本)第一首诗《挖掘》启发创作的一首诗,名称和对象几乎也相同。作为同样来自乡村的诗人,我从希尼《挖掘》中领悟到的是一种对乡村经验和情感的朴素书写方式:作者从我们通常不会留意的——不以为具有诗意之处下笔:
我的手指和拇指间
夹着一支矮墩墩的笔
偎依着像杆枪。
进而,希尼的笔触落到正在窗外挖土的父亲身上:
窗下,响起清脆刺耳的声音
铁锨正深深切入多石的土地:
我的父亲在挖掘。
在这样一首书写我们亲近土地和传统家庭的人再熟悉不过的题材作品中,希尼用他平静的叙事者的目光和心,将眼前所见父亲的日常劳作转述为诗,并如父亲挖掘的行为所达成的目标——诗歌《挖掘》也像希尼家族的更深处挖掘,从父辈到祖辈,同样的劳作如传统般在作者笔下展开:
我祖父一天挖出的泥炭
比任何在托尼尔挖炭的人都多。
随着作为农夫的父亲和祖父在几乎同一块土地上相同的劳作,由日常经验而深入记忆和印象,日常深入到传统中,希尼家窗前的土地延展到托尼尔的土地——乃至希尼家族根植的爱尔兰土地,在开始处看似平常的一瞥,到一个农夫、一个农民家庭、一个一个北爱尔兰的挖炭人及其家庭必须完成的成为传统的经验——由经验而生发的深沉的情感,诗人希尼借一首诗完成了他的“发掘”,进而将传统引向自身——然而挖掘的工具也由铁锨过渡为笔,一个家族的三代人在此“挖掘”:
……(父亲)我父亲在挖掘。
……这起伏的节奏穿过马铃薯垄
他曾在那儿挖掘。
……(祖父)为得到更好的泥炭
越挖越深。挖掘。
……(“我”)我的食指和拇指间
夹着一支矮墩墩的笔。
我将用它挖掘。
关于《挖掘》,希尼在他的回忆散文《摩斯巴恩》中提到,“《挖掘》是我写的第一首我自己认为把感觉带入文字的诗,或者更准确地说,我认为我的直感进入了文字”。
3
对“挖掘”如一首深情的歌谣般反复吟唱,希尼为同样作为诗人的我和作为读者的我们提供了一种面对日常经验和习俗、面对家庭和家族的观看、领悟与书写方式。
《挖掘》中不见我们通常在有关家庭或乡村的诗歌中常见的——以至于泛滥的——有关情感的直接抒情性词语,比如“爱”“深爱”“劳累”“眼泪”,而是以直接的经验,以反复的自当下向时间和空间深处的叙事,表现了更为亲切、可感、可信赖的乡村诗歌,真诚和深刻的情感正如一条发生的河流,自源头的涓涓细流,缓缓地,在途经万水千山的奔流中扩展和纵深了自己。
感谢希尼赋予我诗人的经验,我以谦卑的心去写那首《挖土——献给我的父亲,并致希尼》,回忆我父亲和我家周围我们一家数代人反复劳作过的土地,我们熟悉的身后蜿蜒的浏阳河,写出了自己理想的——尽管是受到启发甚至于有模仿痕迹的——属于我自己的诗:
我的父亲曾在门前挖土
为了挖出第二口池塘,让我们天天都有鱼吃
作为浏阳河的养子
我们一家五口都生活在这里
在我爷爷死的时候,他给我们传下这把锄头
挖土。一把挖出过老房子和旧陶罐的锄头
就在我家后院,父亲后来用陶锉和磨刀石磨它
这把时常闪着白光的锄头在房前屋后翻来覆去
比我的爷爷还要勤快,像是守着自己的坟和土地
……
谁人没有家乡?
但在某种更宽阔的意义上,有人说,“诗人没有国度”——又或者说,诗歌本身也是一个共和国,诗人和诗歌的读者在其中生活成长。在那样一个诗歌的国度,爱尔兰的谢默斯·希尼和中国的我,此刻或曾经被希尼和他的诗歌照亮的我们,有相似的经验和共通的情感。希尼有他的德里郡家族农场,我有我蜿蜒的浏阳河和浏阳河岸长年吹拂的风。而诗人给读者——所有生活着的人带来的,是一种深入的观看、参与生活的角度,交给我们一把把开掘自我生活的铁锨:
在诗人的引领下,我们拿起自己的铁锨(或笔,或其他),在自我熟悉的家和土地乃至历史中挖掘。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希尼,颁奖词是“由于其作品洋溢着抒情之美,包容着深邃的伦理,批露出日常生活和现实历史的奇迹”(“Seamus Heaney for works of lyrical beauty and ethical depth,which exalt everyday miracles and the living past”),为二十世纪的大诗人希尼作注脚。
4
“那是1940年代初的伦敦德里郡,美国轰炸机咆哮着扑向机场,美国陆军在路边的田野里行进,但所有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没有打扰院子里的节奏。水泵就站在那儿,一个苗条的铁家伙,头戴钢盔,有鼻有嘴,浑身颜色深绿,配有一只长长的手柄,站在石头基座上,标志着另一个世界的中心。五家人在这里抽水日用,妇女们忙忙碌碌,来时空空的搪瓷水桶一片喧哗,去时提着沉甸甸的缄默之水安安静静。”(希尼《摩斯巴恩》,姜涛译)
这就是希尼印象中和笔下的德里郡,他的摩斯巴恩。抽日用水的邻人家庭,忙忙碌碌的熟悉的妇女,跟随马匹回家的男人,在漫长的春天的黄昏,所有的孩子都想蜷缩在他们隐秘的巢穴……希尼的童年蜷缩在那些充满幻想的孩子中,关于童年记忆的诗行自孩子们的玩闹和笑声中浮现:
“你的土豆干了吗
该挖的时候到了吗”
“拿起铲子试一试”
脏脸的麦克古根如是说
作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出生于英属北爱尔兰而始终以心归属爱尔兰的天主教家庭的诗人,日常生活和家乡经验是希尼一生写作的重大主题之一,这些主题诗篇汇集于诗人的早期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1966)、《进入黑暗之门》(1969)、《熬过冬季》(1972)和《北方》(1975)等诗集,并以一首《北方》中的长篇诗歌《演唱学校》,仿佛为这一主题作结。
和大多数诗人一样,在出版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之间,希尼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年轻人,但已经走出他的家乡德里郡,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完成了他的本科学业,不久便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学生时代的1957—1961年,他在女王大学的学生杂志《Q》和《戈尔工》上发表了最初的诗篇,我们已经难寻这些诗歌的下落,并未出现在他后来的第一本诗集中。
作为年轻的二十岁出头的诗人,希尼投入到文学阅读和诗歌写作中,从他生活的经验和爱尔兰的诗歌传统中汲取营养。很自然地,他读到了爱尔兰大诗人保罗·策兰的诗。策兰的影响深入他今后的诗歌写作中,并在1996年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得到了阐释。
希尼青年时代的诗篇陆续出现在1962年的《贝尔法斯特电讯报》、1993年的《爱尔兰时报》《基尔肯尼杂志》上……1964年圣诞节前夕,他的三首诗被知名杂志《新政治家》的文学编辑看中并发表,引导他通向了一条更开阔的文学道路,也帮助他打开了成为女王大学讲师的工作生涯。而后者是希尼半生大学诗歌教授的起点,引导他后来通向大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德里郡和摩斯巴恩将成为回忆。
不久,费伯出版公司向25岁的诗人希尼提出约稿,希望出版他的诗集。
1966年,也就是希尼和玛丽结婚后诞下第一个孩子麦克尔的那年,他的第一本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终于由费伯出版公司出版了。
这是一家有着优良诗歌出版业绩的公司,奥登、艾略特、休斯、拉金、麦克尼斯、斯彭德等赫赫有名的诗人出现在它的出版名录上。“它是一个改变的时刻”。希尼后来在自己和奥德里斯科尔的长篇谈话录中回忆了那段决定性的往事,他将它称为“‘博尔赫斯和我’状态的开始”。一个自传式的诗人开始登上文本的假面舞会,那个舞会中出席的是教科书式的大人物,正如费伯公司出版名录上刊登的那些名字。
5
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希尼第一本诗集已经向爱尔兰和日后的全世界展示了一位大诗人的气象。希尼也许算不上普通意义上那种光彩熠熠的“天才诗人”,他不曾在某一次或某个阶段将诗歌连同自身作凡·高或海子式的彻底燃烧,而是以一位“高水平诗歌选手”的身份登上诗歌舞台。他是高度自觉的诗人,不在创作中放纵语言或个性。他也是一位深情的诗人,甚至记得自己每一首诗歌的写作地点和创作状态:
“《挖掘》就是1964年8月我在伍德的家里写的,在楼上的卧室写的”;
“《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是一个周日的下午在一套公寓里写的,和玛丽及她的同屋一起在她们泰特街的公寓后面躺着晒完太阳之后”;
“《鳟鱼》是在玛丽公寓,写在一个C&A购物纸袋上”;
“在植物大道我坐在我的大众甲壳虫的司机座位上写了那首饥荒诗,《挖土豆》的一部分。我可能在等什么人”……
诗人站在一个诗人的角度回望,那些珍视个人诗歌经验的才会走得更远,因为诗歌技艺并不难于习得,诗歌印象和背后真诚的感性力量则更为可贵。大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也是因为拥有和开启了自己印象中的回忆大门,才向世人铺开了浩瀚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繁复又深邃的人生与社会画卷。
6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眼中,爱尔兰大约更因为它养育的作家而闻名:他们是伟大的诗人王尔德、保罗·策兰,不朽的开意识流先河的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现代派大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穿过二十世纪,谢默斯·希尼又加强了爱尔兰的文学重量。很难想象,这个占据了不到一个海岛、国土面积不如中国重庆的欧洲小国,竟被文学女神如此眷顾。
当我们这些东方人中的某些有幸去到王尔德和乔伊斯的国度,在飞机上俯瞰大西洋的季风和大雨不断洗刷的岛屿时,也许会看到成片的闪光低地,分布在那个历史上饱受战乱与纷争的土地上,它就是爱尔兰沉重、黏稠而能封闭一切沉没者的沼泽地。在那些沼泽地,人们挖掘出了四千年前的“沼泽人”遗骸,他们比大多数古埃及木乃伊都要古老;人们挖掘出两千年前的巨大黄油,黄油经过了漫长的发酵期;挖掘出死难的少女和被处决的士兵……
无尽的历史被爱尔兰自己的沼泽吞没又保存……它们为爱尔兰的儿子——德里郡的诗人希尼带来了独特的“沼泽诗”。
我们无遮拦的国土
是一片沼泽,在太阳落下和升起之间
不断结着硬壳。
他们开掘的每一层
似乎都曾有人住过。
——《沼泽地》
这些诗篇在最初的《挖掘》中,在祖父和父亲挖掘泥炭的劳作记忆中崭露头角,在《沼泽橡》(来自1972年的诗集《熬过冬季》)成为一个马车夫的“战利品”(指沼泽橡,保存在沼泽地泥炭层中的橡木,是爱尔兰居民常用的建筑材料,人们用它们盖自己的茅屋),而终于被诗人升华为沉重历史脚步的爱尔兰诗篇——诗人最重要的诗集之一《北方》中的诗歌《沼泽女王》中爱尔兰母亲的象征。诗人以那位被挖掘出沼泽的沉睡的女性口吻自述,令“沼泽女王”复活:
我躺下等待着
在泥炭表皮与庄园墙之间,
在长满石南的地面
与玻璃齿状的石头之间。
我的身体是盲文
……黎明的太阳在我的头顶上摸索着,
在我脚底下冷却,
透过我的织物和毛皮
冬天的渗透
消化我,
文盲的根
……我的王冠渐渐腐朽,
宝石掉在
泥炭块里
像历史的轴承。
……而我从黑暗中升起,
破碎的骨,陶罐似的头颅,
绺绺磨损的缝线、毛发,
泥堆上的点点微光。
——《沼泽女王》(黄灿然译)
7
作为爱尔兰的和守卫爱尔兰的诗人,自浪漫主义的十九世纪走来的诗人叶芝身上背负的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战栗,在爱尔兰民族战争中诗人走向战场,那些经验都体现在叶芝的诗篇中。
叶芝去世的1939年,希尼恰好诞生。
在希尼的时代,同样是欧洲战乱和爱尔兰的民族冲突,希尼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并成长。正如他所仰慕的“庄重的”东欧诗人们,有幸接受大学教育、成为大学教授、走向爱尔兰和世界精英阶层的希尼更重要的选择,在叶芝那著名的诗句“想到的人的光荣大多数在哪里开始和结束,不能不说我的光荣是我有这样的朋友”的开阔话语的启示下,希尼将目光投向我们反复提及的爱尔兰过去的历史和沉入沼泽中的历史。他在诗篇中将那位在十八世纪的贝尔法斯特沼泽中发现的莫伊拉沼泽女王视为爱尔兰的象征——爱尔兰的母亲,那位伟大母亲的女儿,借助希尼的诗,讲述了她那被蹂躏、被掠夺,有头顶着太阳散发微光的历史,闪烁于爱尔兰的泥堆中。
《沼泽女王》,是一位母亲的深沉的呼唤,在爱尔兰的大地上回荡,点点滴滴,既是历史的诉说,又是爱尔兰的根在发芽。希尼所在意和书写的,是他早已形成的诗的自觉和诗歌美学。他爱亲身经历并书写了二十世纪沧桑的波兰诗人米沃什,也爱遥远的比利时画家“农民的勃鲁盖尔”,爱为美国的林场与树木作见证的“农民诗人弗罗斯特”。关于希尼的美学倾向,他已经言明:
“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从承受着更大压力的环境里诞生出来的,是那种比阿什贝利诗派、梅里尔诗派,有着更复杂解释的起源和更紧密的纹理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希尼倾向于从东欧诗人——如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和米沃什他们身上获得更多启示和归属的原因。“庄重感”是希尼追求的,他不愿走向那些所谓“轻体诗”(如打油诗)的诗歌,那些未能包含多少深刻体验、见证和沉思的、无关重大责任甚至生死攸关的诗。
希尼庄重的使命感使得他在中后期更为关注爱尔兰和爱尔兰人面临的社会、民族和信仰危机,并由这些现实、见证,进而深入到爱尔兰两千多年的历史和传统中,并在他生命长河更为开阔的晚年,退回到了希腊,在希腊那全欧洲人的故乡回望迈锡尼的守望者。
正如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在《阿伽门农》中所言:公牛在我的舌头上。
希尼在1994年前后的《迈锡尼守望者》中留下的诗有这样的诗句:我的哨兵工作是命运,是要回去的家。
这就是为什么希尼不愿成为阿什贝利和布罗茨基那样的纯艺术诗人,没有走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先锋派、颓废派诗歌,而是深入现实社会生活,往回追溯,参与到当下的、追寻回溯的爱尔兰的历史进程中。一般人会认为,基于现实的创作是一种低起点、低艺术性的事业,而希尼以他的追求和作品通向了诗歌大师,这离不开他对血源和传统的认同,对现实与历史的关切,对信仰和意义的追寻。信念和经验贯穿希尼的一生,使得他成为真正的爱尔兰诗人,如同他面对和想象过的“沼泽女王”,为整个爱尔兰的历史和精神传承。他的诺贝尔演说词标题为《归功于诗》:
“我归功于诗歌,它使这空中漫步成为可能。……首先,我要使那种生活的真谛具有一种具体的真实性,最为欣慰的时刻是诗作显得最直接,成为其所参与、所辩护和所反对的世界的一种最前沿的再现的时刻……”
终于,他和爱尔兰互为归属。火、箭头和炮弹曾落到爱尔兰的土地和爱尔兰人民的家园,爱尔兰和希尼的沼泽将它们沉入国家深处,它们和祖父和父亲的挖掘声,窗外爱尔兰夜莺和长脚秧鸡鸣叫声,盖尔语的呢喃和反抗声,甚至四千年前沉没于沼泽的爱尔兰男子重见天日的呼吸声,莫伊拉沼泽女王如泣如诉而又温柔的低语声,和它们一道,成为爱尔兰的历史和希望,诗人的爱和信,被全世界的人听见和想象。
我爱这地面
涌出的泉水,
每条河岸都是绞刑架的下落板,
每个活池塘
都是一个瓮的
拔开塞子的口,一个饮月者,
为肉眼所
难以测探。
——《亲属关系》
一个好诗人追求什么?难道他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如飞絮飘浮在时代上空,只是存在而难以把握、没有根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