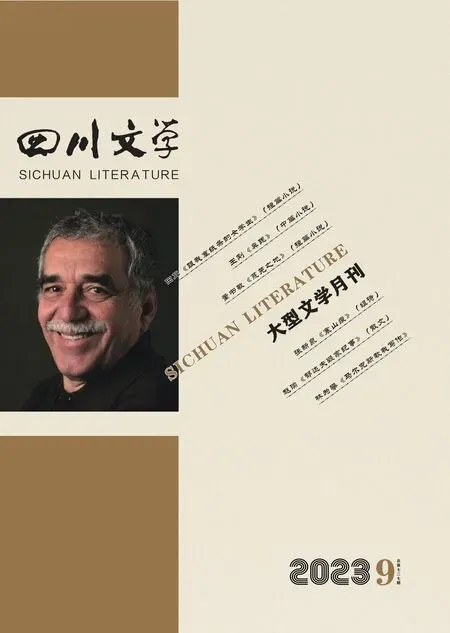异质,新意和多向的可能(评论)
□文/李浩
加主布哈为我们提供的小说文本中,有一种异质性的东西存在,而且吸引,而且强烈。它让我小有意外,进而是欣喜。不得不承认,在时下,我们的写作相对而言同质化倾向越来越重,大家以一种相似的甚至共同的认知、文学理解,相似甚至相同的社会理解和语言方式,勾勒着一种相似的、匮乏新知提供的小说文本,以至于也悄然地耗尽着我们的阅读热情。然而,加主布哈不同。加主布哈为我们提供着异质,虽然这异质恰恰从本质上更接近文字的真正诉求。我说“异质”更接近文字的真正诉求,是因为文学一直是要求新求变的,它始终要求我们的新文本一定要有新的创造性,由此,有批评家才会以片面深刻的语调向我们强调,“所谓文学史本质上应当是文学的可能史。”我想我们也可看到,加主布哈的异质性有着多个向度,也就是说,他在自己的写作刚刚崭露头角的时段,就开始悄然地为“个人的缪斯画下独特的面部表情”。
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异质故事,无论是做出更多强化的《瓦萨从湿地游过来》,还是略略弱化民族意味的《父与子》,它们其实都具有一种异质的不同,这种不同或是体现于对自然、神秘和关系的处理上,或是体现于情感、观念的不同,以及“一种生活”,一种与我们平常经历有诸多不同的那些点上。这些不同的点点滴滴融聚一起,其异质性便强化出来了。必须说,加主布哈在语言上的异质性更鲜明、更强烈,也是最让我“眼前一亮”的部分。说实话,在我看到“加主布哈”这个名字时就开始期待他在语言上的异质提供。我以为,他会借助方言、地方性语言和民族性的语法(包括对汉语的部分生涩)来完成这种差异,然而这并非加主布哈的主要凭借,他的异质性注入是思考的、纯熟的、审慎的、诗意的和强自主性的,是一种有意的自觉。譬如《瓦萨从湿地游过来》中描给瓦尔的斧头:“他沉迷于站在幻想的刃上,舔舐着自己的锋利”“他的斧头已经被他磨得越来越小,也越来越冷静,始终没有落在那个男人头上”。《父与子》中描述“我”的沉默:“凛冽的风把我的嘴巴缝得很严实,没有一句话想跑出来”——加主布哈的语言有着明显的现代诗歌的浸润,加上他对地方性差异的部分纳入,从而使异质性获得了更重的彰显。或许,因由语言上的诗性注入,使得加主布哈“观看”生命、生活的眼光也有了某种异质,譬如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有意点到即止,偶尔还会以一种具有诗意的描写来冲淡它,虽然这种生存之难是刻进骨头里的;他淡然若轻地对待着死亡和死亡议题,有一种麻木式的洒脱,它恰恰与小说的语境以及氛围极度匹配;他能把生活中的锐利、病疼以及粗粝故意用一种“内心之死”的方式、钝感的方式表达至深,这一能力我在威廉·福克纳的小说《沃许》中见到过,而在加主布哈的《父与子》中,我又一次被它所感动、震撼……
两篇小说,两种非常不同的指向。这也是让我对加主布哈、陌生的加主布哈“刮目相看”的地方,我见到了他近乎于显著的驾驭能力。《瓦萨从湿地游过来》侧重的是诗性和神秘,包括民族性的差异,普弥的存在离开这片土地甚至这篇小说都可能不复存在,他是加主布哈的个人之力创造的有标识的“新人”,而在《父与子》中,那场景、那境遇以及那种生活也许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民族、地域和国度中都可遇见的,它更具普通性指向,尽管这一生活未必是我们习惯直面的。在《瓦萨从湿地游过来》的小说中,加主布哈是以外观的但包含着悲悯的笔触来描述的,他对瓦尔以及他儿子普弥始终有一层理解性的悲悯存在,包括普弥身上那些“非常”表现;但在《父与子》中,加主布哈是“冷静进入”,他冷静甚至略显凛冽地进入这个父亲的心里,他不再将自己抽出,而是努力与这个父亲融合在一起——我猜度,加主布哈未必认可这个父亲的行为和选择,未必认可他看世界、看生活的理念,然而他却将自己倾空,却让自己以水的样态进入另一个灵魂里面并按照它的样子塑形——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匈奴人生活的小说,在那里我也试图让自己进入我不认可的人生观、世界观中,并尽力为它辩护——我似乎觉得加主布哈所做的比我要更好一些,它其中的难度是那么巨大。在这两篇(其实是两种类型)很不相同的小说中,加主布哈有意展现了他结构不同故事、使用不同方式来言说的基本能力,也充分展现了他驾驭语言并随类赋形的能力(尽管前面我统一性地谈及了作家的语言异质,然而两篇小说因为故事载体上的不同,他的语言在统一特色的前提下又有调整),这种基于不同而随之调整的设计自觉,让我对加主布哈有了更多期待。
关于加主布哈两篇小说的主题性和对生活的言说部分在这里我不准备过多阐释,之所以这样选择并不是它可言说的部分有所匮乏,也不是说它的表达不够深刻;之所以不做太多阐述,是因为本文随着加主布哈的原文一起刊出,我愿意阅读者能更多地注意于加主布哈的小说,更多地以自己的敏锐、敏感来读出。
如果吹毛求疵,我可能会认为,在《瓦萨从湿地游过来》一文中,前面部分的追光是给瓦尔的,中途让他死亡又将聚光追给普弥,多少有些脱节,不如从一开始就让普弥出场,瓦尔作为背景性人物、相关性人物出现;沙吉寡妇的戏也应更丰满些,因为她连贯了前后,是一个可用的支点。《父与子》,基本完整、自恰,只是“我”的舅子、姆巴在文中出现得过于集中,似乎可以“破”一下,让他们被几次提及,然后在该出现的段落再集中出现,这样,可能就显得连贯性、圆润感更强。
无论怎样说,我都想从我的阅读感受出发做出重申:我,看好很是陌生的加主布哈,期待能读到他更多的更为丰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