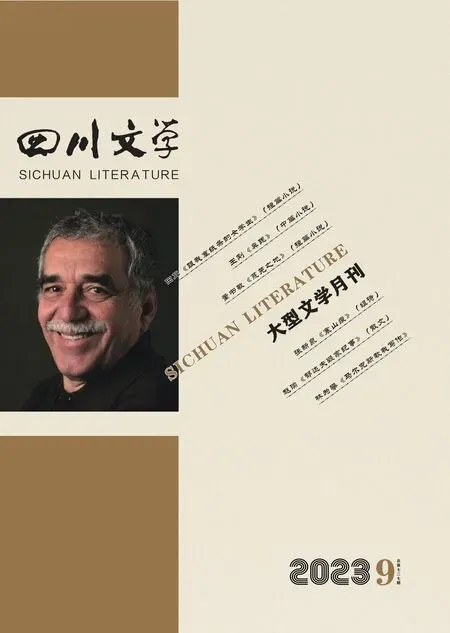瓦萨从湿地游过来(短篇小说)
□文/加主布哈
一
傍晚是一件鲜红色的披毡,穿在群山上,万物正准备着失去彼此间的血缘关系。为缓解心里的恐惧,瓦尔在深山唱歌,他明知道这一带没什么可怕的东西,但他总感觉身后有一双眼睛。他挥动斧头,尽量制造出大的动静,倒下的树木被他从树林背出,像一头野兽从密林走出。他知道是时候了。
“瓦尔死了,瓦尔被他砍倒的松树压死了,快来人啊。来人给他收一下尸。”他站在树林边缘的石头上大声叫喊。
等阿卜村的男人纷纷到来,瓦尔却在石头上捣碾一条蚂蟥,来一个人他就塞一撮旱烟,并佯装愤怒地解释:“哪个不安好心的人又想着我死?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只是这蚂蟥的确吸了我不少血。”
他十八岁的儿子普弥也牵着那匹黑马来给他收尸了,还带来一件白披毡。大家纷纷指责那个希望瓦尔死的人,不安好心的人。瓦尔捣碎的蚂蟥溅出的血染红了那块石头,夕阳也染红了每个人的身体。大家准备下山了,瓦尔一边抱怨那个人,一边说道:“反正你们也是要下山的,就每人顺便帮我拿一块木头下山去吧,冬天还靠它们过呢。”大家意识到了什么,却又不好意思拒绝这个刚死里逃生的人。走在前面的人嘀咕:“他死了也要靠这木柴烧掉的。”然后狠狠将木柴仍在瓦尔家后就走了。瓦尔一边感谢他们,一边咒骂那个人。然后抡起斧头劈开那些木柴,将它们堆在墙角,直到天黑,他吃了一颗土豆就消失在黑夜里,摸进了沙吉寡妇的被窝里。
“你今天怎么不来给我收尸?”
“你这该死的,是不会这么容易死的。”
普弥已经习惯这样的夜晚,自己对抗那些奇奇怪怪的梦,他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无边无际的笼里,怎么也走不出去。最近他的梦里总是出现一片湿地,湿地上长着(或者说是漂浮着)形状相同的灌木,每株灌木上都安坐着一只褐红色的鸟,鸟群会同时发出似孩童哭声的鸣叫,当它们同时起飞,普弥就会惊醒,然后感觉自己头顶着一片下雨的湿地,一切那么熟悉且真实,却无法触及。
普弥把自己的状况告诉父亲,瓦尔却说:“胆子小的人才多梦,你就是走在树林都怕树叶落下被打伤,应该让你的胆子肥起来。”事实上,胆小的人是瓦尔,他害怕在夜晚独行,所以普弥脱口而出:“心里有事的人,胆子才会小。”开始的时候,普弥总是在半夜醒来,独自躺在漆黑的屋子里,他甚至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等他开始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瓦尔也没太在意。
“一只乌鸦在牛身上寻觅虱子,一只耳朵在我身上聆听噩耗,一条河流在我身上倒流。”这是普弥最近在重复说的话,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他自己也不知道。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傻笑,搂着那匹黑马的脖子重复那些不着边际的话。
直到那天晚上,他从那片梦境中的湿地醒来,并且在漆黑中向神龛边摸索并取下那面羊皮鼓,然后重重地敲响了它。羊皮鼓发出了沉闷、厚重又神秘的声音,那声音在普弥的脑海里回响着、徘徊着,让他感觉自己的灵魂被击中了,他觉得异常兴奋、眩晕,四肢便不受控制地抖动,他在漆黑的屋子里摇晃着头脑,舞动着四肢,并且脱口而出:“瓦萨,我的瓦萨,他从湿地游过来了。”
瓦尔家里半夜突然持续的鼓声敲醒了阿卜村的人,他们举着火把闻声赶来,聚集在瓦尔家堂屋里,看着眼前的普弥满头大汗,原地打转,时而敲那面羊皮鼓,时而对着鼓胡言乱语,没有人阻止他,人们面面相觑。瓦尔最后赶来,他从普弥手中抢下羊皮鼓,把普弥抱在怀里,嘴里咆哮出一些普遍的咒语,直到普弥在他怀里沉睡。
几个妇人生了火,沙吉寡妇也在其中,她把自己裹在一件青色的羊毛披毡里,一块红绿相间的布巾盖着她的头发和长颈,只露出那张土黄的瓜子脸,几条皱纹若隐若现。她以为没人注意到她跟瓦尔前后脚踏进来,但还是感觉到每个人的眼光都在看着她,她尽量避免跟别人对视。事实上,有几双眼睛真是在暗处盯着她了,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揭开一切,瓦尔的酒便敬到他们面前,堵住他们的嘴和无端的猜想。
瓦尔打发走了所有人,独自坐在火塘边陷入沉思,他把那面羊皮鼓放在怀里,右脸枕在鼓面上,聆听着从鼓里暗涌出的往事。他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此时,普弥还在喃喃着:“瓦萨,瓦萨……”瓦尔已经很久没有躺在儿子身边了,这一晚他没有合眼,嘴里偶尔飘出一些不痛不痒的咒语,心里做好了随时接受噩耗的准备。
二
又是个阴雨天,屋顶的瓦片上无数精灵在跳舞,滴滴答答的,汇集到一起后从屋檐上跳下来,把地面上的鹅卵石清洗得晶莹。普弥醒来的时候已是正午,他悄悄走出屋子,坐在门槛上望着潮湿的远处发呆,一层浓雾正在阿卜村正南边的乱石坡上慢慢消散,然后听见火车从浓雾背面的阿尔依隧道里驶出,那是他母亲出走的方向,当然,这些都是他的父亲瓦尔告诉他的。这个少年,只要坐下来,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呆,他的眼睛深邃又荒蛮,仿佛所有物体陷进他的眼神后都死在里面,无法反射出一丝光芒。
瓦尔看到儿子似乎又恢复了正常,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在细雨中劈柴,他蓬松的头发上趴伏着透亮的雨滴,每一次斧头落在木头上,他的心里都觉得痛快,仿佛砍在那个男人的头顶,这些年他不知道想了多少次把斧头落在那个男人头上。他沉迷于站在幻想的刃上,舔舐着自己的锋利。直到雨再次大起来,凉意浸透他的遐想,才冷静下来,坐在普弥旁边磨斧头:他的斧头已经被他磨得越来越小,也越来越冷静,始终没有落在那个男人头上。“去搬个凳子吧,坐在门槛上,是不吉利的。”普弥没有听进去,这几天,他们之间的对话很少超过三句,确切地说,一直以来普弥跟人的对话就很少。
晚上瓦尔没有去找沙吉寡妇,怕普弥的病再次发作,早晨他已经将那面羊皮鼓扔到了山洞里,并恶狠狠地对着那个山洞吐了三口痰和几句咒语。他喜欢说咒语,比如去死吧、见鬼吧、让老子的斧头敲碎你的屁股吧等等。但是,他的咒语没有一句是变成现实的;他还喜欢撒谎骗人,他的谎言确实每一次都能骗到大家。普弥在深夜时不停说着梦话,一直重复:“瓦萨,瓦萨……”瓦尔忍不住了,他起身跑进鸡窝里抓出那只黄色的母鸡就在煤油灯下活活掐死了,嘴里诅咒着:“我知道是你回来了,这只鸡打给你,你这负心的女人,找那个瘸子去吧,你不去找他,总有一天我会送他去找你的。”但是他不敢走出去拿柴,他怕在推开门的一瞬间看到她的脸。所以,那只被他掐死的母鸡就躺在锅庄上,几根脱落的羽毛掉进将熄的火堆里,发出臭鸡蛋的味道和噗嗤的声响,据说这种味道能驱赶走内心的恐慌和迷雾。可是普弥仍不见好,他的额头像一颗炭火,烧得厉害,瓦尔没有摸到。他仍然坐在火塘边说着咒语,他的口水都被他吐干了,于是他不停抽烟。他的心里陷入了一种无望的等待,他不知道等什么,也许是等天亮吧。可是他又暗暗发誓着,“天亮了我也不会去求那个瘸子救我的儿子。我要去砍了他,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该死的瘸子。”他的这个誓言阿卜村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除了普弥。大家还知道他不敢,不然那把斧头也不会越磨越小,一些男人看到瓦尔在磨斧头的时候嘲讽他:“再磨,就成针了。瘸子医生那里的针,可比他这尖细得多了。”
三
这件事发生在普弥十二岁那年夏末。
无所事事的瓦尔在村里晃悠,他准备到斯拉河附近找个地方洗一下自己的身子,在玉米地里除草的村民看见他便激将他:“瓦尔,你不是很会骗人吗?今天来给我们编个谎言吧。”
“谁他妈还有空跟你编谎言啊,斯拉河昨晚涨水,今天退潮了,河岸上到处都是渴死的鱼,我忙着去捡呢。”他边说边往斯拉河跑了。
可村民赶到斯拉河边时,瓦尔正趴在河边的石头上仔细寻找着那件白披毡里的虱子。大家指责他,却被他反驳得哑口无言:“是你们让我骗你们的呀。”大家很无奈,只能悻悻离去。这时,一列火车从斯拉河对面驶去,轰隆隆的声响盖过了几个女人对瓦尔的诅咒。
瓦尔心里乐滋滋地走向火车站,好不容易来一趟,他准备去那里打几斤白酒,并且趁天黑之前赶回去。这个快五十岁的男人,身高八尺,胆小如鼠,却喜欢独来独往,他喜欢独自走在路上吹响亮的口哨,他感觉独处是他对抗时间的秘诀。当他吹着口哨走进小卖部时,正巧遇到阿卜村几个男人也在那喝酒,看到瓦尔后他们压低了声音,转移了话题,顺便邀请瓦尔跟他们共饮。瓦尔谎称家里还有事,打了三斤白酒便来到铁轨边的水泥地上自饮起来,他的口哨声引来细细山风,在自己的惬意里越来越醉,但潜意识还是驱使他往回赶。走到乱石坡附近时太阳快落下去了,他已经喝醉,而那几个在小卖部喝酒的男人也赶上来了。他们说的话里酒精含量极高:“瓦尔,你在等婆娘吗?我们又看到她进瘸子的诊所,大半天了。”
瓦尔没有理会,因为他平时对他们撒的谎太多了,所以也觉得这些人在骗自己,出于客气,他还分享了酒。但越来越多的话从他们嘴里溢出来了,他们说你的老婆科莫阿果已经跟瘸子好上了。瓦尔不仅没生气,反而大笑起来,他越不信另外几个人就把事情说得越详细:“你婆娘去瘸子那儿上环,结果自己被瘸子上了。”瓦尔的脸瞬间黑下来,太阳最后的余晖正从他的脸上徐徐落下,他假装镇定,心里却有无数麻绳在打死结。他说不可能,至于为什么不可能他说不出口,羞于启齿。实际上,他和科莫阿果结婚多年,只有普弥一个儿子,再也没能怀上,所以不需要上环。
“不可能。”这几个字从他嘴里飘出来时是颤抖的、无力的。他再也没能忍住内心的镇定,于是狂奔向火车站,他在黄昏下跌跌撞撞跑起来的样子,像一条被打断后腿的狗,扬起了一些尘,但不大。
几个醉汉怀着某种兴奋又忐忑的心理,追了上去,想去看看这把火要燃得多热烈多血腥。当他们赶到时,瓦尔被瘸子家族的几个男人绑着在地上咆哮,嘴里满是些恶毒又伤不到人的咒语。这个从外地搬到阿卜村的吉石家族的男人,他此刻多么需要他的家族给他一点帮助。有人在暗处嘀咕:“真是猴子靠树生存,人靠家族撑腰。”现在,瓦尔的腰被扔在地上,沾了灰尘,像一棵歪下去的朽木,狗想往上屙尿,猪也可以上去打个盹儿。而他的老婆,那个女巫师,惊慌失措中已经爬上一列火车出走了,她没有留下一句话,她的蓝色头帕掉在铁轨上被碾碎。阿卜村的醉汉们酒醒了,也许他们喝得没自己想象的那么醉,他们从中斡旋没一会儿,就把瓦尔的绳子解开,并将他拖着往回走了。整个过程中,瘸子医生吉尔都没有出现。
走到半路的时候,瓦尔慢慢酒醒,天彻底黑下来了,他试图挣脱阻拦,嚷嚷着要去卸掉那个死瘸子的另一条狗腿。但是人们放开他了,他却了。
瓦尔的老婆科莫阿果就那样走了,他没有扔掉家里的关于她的一切,包括那面羊皮鼓。科莫阿果是阿卜村唯一的苏尼,她在的时候村民家里有什么人生病了都会请她占卜,并通过一场仪式来治疗人们的病痛。她走了,好像大家的疾病也减少了,除非迫不得已,谁都不愿意去请另一个村的巫师来到村里治病。有人说她被瘸子偷偷藏在另一个地方,还生了个儿子,有人说她已经死了。瓦尔觉得她死了,有时候又觉得她没死,所以他对儿子普弥说你阿姆出走了,坐在一辆火车上。此后,瓦尔会每天磨斧头,发毒誓,继续说谎话,并且把沙吉寡妇哄得耳朵里都长出了很多甜蜜的毛茸茸的情话。
瓦尔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他说自己在高处得过且过,在更高处,等待着闪电来临。
四
稀薄的雾里,人们在各自的荞麦地里收割着,他们趁太阳出来前把荞麦割下、捆扎、竖立田里,周边还守着几个奇形怪状的草人。如果等到午后,经过太阳晒过的麦子容易掉落,镰刀一过,就会有大把的麦子掉落在土里。瓦尔带着一斤白酒、一颗鸡蛋和儿子普弥的生辰八字来到吉克拉莫家的荞麦地里,他想让吉克拉莫给儿子占卜一下。
吉克拉莫是阿卜村唯一的毕摩,他主持着几十户人家的祈福祛灾仪式,他还在学校里坐过几天,认识几个汉字,是位德高望重且学识渊博的老人。此前他也大概听说了普弥的一些谣言,所以心里已经有答案,他说:“应该是来自后方的瓦萨找上你的儿子普弥了。需要做一场瓦萨附身的仪式,让普弥成为真正的巫师。”他还建议瓦尔带着普弥也去医院看看,但是被瓦尔果断拒绝了,他说我儿子就算死了,也不可能去求那个死瘸子来治疗。
“还是请你选个良日,让瓦萨附普弥的身吧,这也许就是他的命。”瓦尔用瓶盖给吉克拉莫倒了一杯酒,继续说道,“我那死婆娘就是女巫师,应该是她的瓦萨神不要她了,回来选中了普弥。我的儿子最近越来越不正常,他每天尽说些我听不懂的话,昨天晚上他一直反复恳求咒语,我隐约听到他在呼唤瓦萨神。而且他的身体真是越来越虚弱,那眼窝子,都快陷进去了。”
吉克拉莫没有推辞,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于是让瓦尔回去准备一只纯白色的公鸡和一头纯黑色的乳猪,“还有一面羊皮鼓,那是巫师的法器。猴日吧,我来主持。”
瓦尔在回去的路上,顺道在自己家的荞麦地里多编弄了一个草人,他的心也像这麦地,荒草杂乱,雨露闪闪,不知从何下手,于是就让它继续生长。总有个头吧,他想。他在屋后看见普弥正搂着马脖子,嘴角微扬,用自己的脸庞蹭着马的鬣毛,像一个熟睡中的婴儿。
普弥感觉自己掉进了那片梦里的湿地,他感觉不到父亲的情绪,甚至自己的情绪,他只感觉身体里有一头兴奋的公牛,用它那粗钝的角,不停歇地到处乱顶。他偶尔能听见父亲的叹息,却无法感知到父亲的悲伤。他说,“瓦萨,瓦萨……”于是,就在吉克拉莫的主持下,他的瓦萨从湿地游过来了,一寸一寸漫过他身体里的谷地、沟壑。他觉得自己湿漉漉的,又感觉有无数个火堆在身体里燃烧。所以,他敲响了羊皮鼓,在原地起舞,他说:
“我恳求的咒语,我要独自畅饮。”
普弥成为继他母亲科莫阿果之后的巫师,但没有人找他占卜治病,因为大家觉得他道行浅、经验少。可普弥痴迷于这份职业,他像带着心爱的玩具,随身携带着羊皮鼓,有时他把自己倒挂在树上,朝着地面击鼓念咒,每座山谷都会传来咚咚的鼓声,浑厚而沉闷,仿佛是鼓里无数幽魂在倾诉、在哀怨。
深秋,十八岁的少年巫师说出了第一个预言:“一片湖从远方飞来,那座古老的石桥要塌了。”没有人当回事儿。
五
连着一个月的秋雨,让阿卜村陷入了毛茸茸的霉,锄头生锈的黄昏,一切都在失去耐心。
普弥翻过一座土墙,说自己要去追一个人,不觉中跑到铁路边,火车轰隆隆地驰过,他觉得脑袋空白,甚至有些失落,于是抱着双膝痛哭起来。他感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也在做一些多余的事,比如把一个死人的名字倒过来誊写在石头上,比如把一杯水倒进另一杯水。回来的半路上天黑了,始终觉得有什么东西追着他,就加快了脚步。他想象自己是兽,想象时间驯养着他,喂他九分熟的粮食、洗干净的善意,当然,也将逼迫他咽下莫名的恶果。
这天夜晚,一场洪水冲进阿卜村,带走了部分未收割的粮食、几个男人的醉意、沙吉寡妇将倒的墙壁和瓦尔。这个男人在酒精的麻痹下终于走了一回夜雨路,不料刚准备翻越围墙,洪水就如猛兽般,把他卷进去了。人们在斯拉河附近的石桥边找到他,已经是第二天午后,原本瘦如竹竿的身体现在浮肿得像全身被蜜蜂蜇了个遍,最让人难忘的是那对大眼珠,感觉随时要跳出来,怎么也合不上。而那座古老的石桥,从中间断开了。由于村子受了灾,加上瓦尔家里的条件本就艰难,他的葬礼很简单,宰杀了唯一一头母牛接待祭奠的人,大家有一句没一句地唱诵哭丧歌,几乎没有夹着一丝感情,甚至眼泪都像是为另一个人酝酿而流。直到凌晨,沙吉寡妇点着一束火把孤身从不远处走来,她锤着胸口唱着丧歌,声如洪水:
“亲爱的表哥,洪水拦不住,死神劝不住。人说金银贵,金银难买你的命,你离开了人世,好比大山倒塌,羊群没有了牧场;河流干涸,鱼儿无处游,从此以后啊,青稞变不成荞麦,没有人能替代你。在座的亲朋们,好人的葬礼上我们结伴流泪,坏人的葬礼上我们也结伴流泪。瓦尔去了,只有夜晚的风,在徐徐吹呀……”此时,人们才感觉到瓦尔真的死了,他带着满腹的谎言和咒语,去了。
普弥在父亲的葬礼上没有流一滴泪水。他倚靠在瓦尔的遗体上,显得异常冷静,偶尔他还会起身给大家敬酒。他也敬了沙吉寡妇,那一瞬间他有号啕大哭的冲动,但他收回了自己的感情,这是他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想念母亲了。直到天快亮了,人们把父亲的遗体抬出门,仿佛是几束火把将父亲瓦尔托举着,走向火化场,他饮下人生的第一口酒,脱口而出:“一个湖泊,安居了。”
那片湖就在阿卜村的牧场上,面积很小,且浑浊,原本那个位置就是凹下去的,据村里的老人讲,那是神话里的巨人支格阿鲁路过这里休息时,其中一颗睾丸留下的形状,另一颗睾丸的位置,如今长满了松木。牧场上有湖泊形成的事被传开,再加上那座古老的石桥断开,大家才想起普弥的预言,才想起他是个巫师,他们夸奖附在他身上的瓦萨神法力无边,能预知未来。甚至有人笃定,普弥身上的瓦萨是所有瓦萨里最高贵的自然瓦萨神。于是,他们纷纷带着鸡蛋、白酒和其他的食物,排在普弥家门口,请他为自己占卜、预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家庭美满,身体康健。
“今天不是个好日子。”普弥拒绝了他们:“等羊日吧。”他的声音似乎变得雄厚了,披着一件纯白的羊毛披毡,头戴一顶天蓝色的帕子,整个人显得肃穆而端庄。等大家散去了,他露出鬼魅的笑,钻进屋子里,击打着那面羊皮鼓。他的内心狂喜、兴奋,于是匍匐在地上,像一条蛇,从床底咬住犁铧就手舞足蹈起来。他享受这样的感觉,他在这样的感觉里变得模糊、痴狂……
羊日如约而至,由于刚经历一场灾难,阿卜村陷入了无法言表的恐慌,人们的内心需要一个慰藉,这个慰藉最好来自神灵,来自他们不得不信且无法拒绝反驳的神秘领域。于是,结伴来到普弥的屋前。他们依次进到那个狭小漆黑的土屋,谦恭地放下手中的粮食,给普弥端敬一杯酒,普弥用食指蘸酒,挥洒一部分向身后,开始邀请他的瓦萨附身,他嘴里念念有词,手脚开始抖动,然后说出每个人想听的话,最后饮下一口酒,他只是湿润一下自己的嘴唇,便让前来占卜的人将杯中剩下的酒饮尽。每个人走出来都会被问占卜得准不准,每个人都很坚定地回答准准准,很准。他们的内心无法拒绝这样的预言,这使他们心里感觉踏实,即使有的占卜结果并不准确,他们也说很准,他们宁愿被普弥欺骗,宁愿互相欺骗,也要用这预言驱散心里的雾霾。
六
普弥的名声被阿卜村的风吹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响亮。人要是出了名,就非要给他涂抹一些神秘色彩,凸显出他与众不同。关于普弥,只有一句话:“他说的每句话都是预言。”这句话像一朵鲜艳的花,让人们蜂拥而至,但普弥仍然坚持只在羊日接待这些访客,这个举动让大家觉得他更神秘,或者更神圣。他们说瓦萨可不会随叫随到的,瓦萨需要被侍奉,也只会在吉祥的日子降临。所以每逢羊日,普弥那个土房子门口就坐满了人,他们提着粮食、酒,带着虔诚的口吻说:
“我们要帮普弥侍奉着他身上伟大的瓦萨神。”这个瓦萨看见了他们身体里的疾病,揪出了引起疾病的鬼怪,并且通过普弥传达了制服鬼怪的仪式与方法。只要完成了这个仪式,疾病就将退散,他们坚信不疑。
那个冬天,除了羊日,普弥都不说话,因为他觉得话说多了就会失去威信。他会在大雪纷飞的清晨牵着一匹马,走出屋子,来到斯拉河边,或是那片小湖边,升起一堆火,他想:“彝族人的火,不能熄。”有时他会在湖面看到一条鱼怀揣着匕首游过。但是他没有说出来,遇到人,他也只是以微笑招呼。人们会在暗地里把他跟那个满嘴谎话的父亲比较,说瓦尔的一生像狼狈的狗,普弥的一生将如猛虎。然后,普弥就从他们的眼睛里,牵着那匹黑马,在大雪中归来,他十八岁的身躯伟岸如松,怎么看都顺眼。然而,在他们看不见的夜晚,普弥陷入了无止无休的对话。他感觉那些逝去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在夜里聚集在自己身边,包括自己的父亲瓦尔(他背着斧头和木梯子)。他和这些不存在的人无休止地争吵、辩论、谩骂……直到他感觉自己的脑子快要炸裂了,他突然冷静而庄严地说:“在门楣上取走属于你们自己的咒语吧。”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他才清晰地感觉到多么无力,又无法自拔。
最开始发觉普弥不对劲的人是沙吉寡妇,那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出远门的儿子走在山谷时被一块滚石砸死,她惊魂不定,还没忍到公鸡打鸣,就准备去找普弥占卜一下儿子的凶吉。但是她听到普弥在屋子里自言自语,还时不时发出让人惊悚的笑声,她顿时不知所措,慌忙往回跑。半路上他想起瓦尔,于是取下头帕不断挥动,嘴里不停吐出口水和咒语,她的咒语凝固在风雪里,她再次来到普弥的门前,里面却异常安静。她颤抖着问:“普弥,普弥,你没事吧。”普弥打开门,沙吉寡妇的火把照在他清澈的脸上,他用手挡住了,连忙说自己没事,额头上有几滴汗珠。沙吉寡妇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只说一句没事就好便离开了,她悬着的心感觉踏实了许多,又有些不安。
普弥盯着那台已经锈得转不动了的石磨。现在,它躺在那里,不再发出拙劣的声响,不再磨出母亲的叹息和粗劣的粮食,它终于把自己磨成了两块普通的石头。记忆深处,松脂灯下的母亲科莫阿果面容祥和,她推着石磨,石磨推着她,磨出过命运阴险的笑脸。这台石磨是母亲的嫁妆,它推着母亲走了几十年,终于把她推出了这个家,也终于,把自己磨成了两块喜欢安静的石头。普弥流下眼泪,他很想跑出去问问沙吉寡妇来找他做什么,就是这样的夜晚,雪仍在忙着埋屋顶,于是他把自己蜷缩在自己的梦境里。那晚,他看见瓦萨神变成一座山脉,他躺在上面,感觉到了自己连绵起伏的一生。
七
阿卜村的人相信鬼神,并且认为每个鬼都有姓氏名字、家庭背景、姻亲关系;每个鬼对应着某个病、某种危机;所以,只要巫师普弥能找到那个鬼的来历,就能按照对应的仪式制服它。老人说最大的鬼叫孜孜列乍,住在达布洛魔山,她每晚都会变成虫趴在树上“吱吱,吱吱”地叫,所以孩子们听到吱吱的声响,都会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耳朵,乖乖睡觉。胆大的孩子会问还有没有比孜孜列乍更大的鬼,只有智慧的老人回答:“更大的鬼长居人心里,所以,只要有自认为美好的事物出现时,人就会按捺不住内心,想去亲近、去巧取豪夺,去反对自己。”
村里的木噶拉且是公认的见多识广的年轻人,他去县城读过书,据他说还乘着火车去过更远的地方。他在羊日走进普弥的房子,两人一见如故。
“我得了一种叫艾滋的病,你帮我想个办法弄它吧。”他的五官精致,说话的时候一直在抽着烟。
普弥思索了很久才回答:“没有一个叫艾滋的鬼呀,我也没听说过一种叫艾滋的病嘛。”
“那你就造出来一个新鬼嘛,就叫艾滋鬼,再想出一套仪式,制服他,比如牺牲一只公鸡,给它杀一头牛都行啊。”木噶拉且显得很激动,此前他已经在吉克拉莫那里碰了壁,吉克拉莫建议他去找瘸子医生,很坚定地说这个病只有医生能治。
普弥感觉自己秽迹般的内心被吹出了星火。为了造出这个叫艾滋的鬼,他邀请木噶拉且住在自己的家里,一起分析病情,两人同吃同住,甚至普弥提出想得一下艾滋病的念头,但被木噶拉且委婉拒绝了。木噶拉且嗜酒如命,整日待在普弥家里,每天喝得稀里糊涂,同时也拉着普弥一起喝醉。两人在醉后就敲击羊皮鼓,用云里雾里的咒语编排着制服艾滋鬼的仪式。为此,普弥还取消了羊日的占卜,他准备像治疗自己一样,治好木噶拉且的艾滋病。
木噶拉且给普弥讲了很多新鲜的事,讲到女人,普弥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放了一场大火,正在迅猛地燃烧着,他饮下一杯烈酒,对木噶拉且说:“我要一个女人。”木噶拉且哈哈大笑,说:“你治好我了,我带你去。”这是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两个男人像两束熊熊的烈焰在屋子里对饮、念咒、击鼓。第二天,普弥却怎么也叫不醒木噶拉且,他安静地躺在火塘边,枕着一根烧黑的木头,修长的脸被木炭涂抹得像戴着一张面具。普弥的内心崩溃了,但是他哭不出来,他把木噶拉且扶起来,为他擦拭着身体上的脏,梳妆一番后让他躺在草席上。普弥就这样让木噶拉且的尸体陪着自己,他害怕失去朋友,又孤身陷入无边无际的孤独,他开始召唤瓦萨:“来吧,如果你爱我,就要爱我的朋友。你不该总是微笑地看着我失去……”他的瓦萨没有来,于是他饮酒,也给木噶拉且一杯,就这样不知过了几天,木噶拉且的家人找来,抬走了尸体,并恶狠狠地在普弥脸上吐了浓痰。普弥像个被断奶的孩子,大声哭起来,他感到自己与人世的羁绊,正日渐松落,于是他继续饮酒,麻痹自己。
普弥蓬头垢面地出现在木噶拉且的葬礼上,牵着一头纯白的公羊,手提一坛酒,他一句话也没说,把羊拴牢在门前的核桃树上,就转身离去了。他在自己的马圈里看见黑马已经饿死在那里,马蹄里夹着冰沙,马笼头已经陷入它的肉里,想必它挣扎了很久。普弥冷静地找到父亲留下的那把斧头,把黑马卸成块,然后一块一块地往黑石堆方向背,马血从他身上流下,滴落在雪地里,铺成了一条蜿蜒的血路。几只乌鸦盘旋在马肉周围,普弥瘫坐在一旁的石头上,血已经把他染红,几粒肉末凝固在他的头发上,他狠狠饮下一口酒,把大卸成块的马肉又拼接成了马的形状,又饮下一口,然后把酒瓶放在马头边。普弥用手抓起雪,一寸一寸,把马覆盖,直至堆起一座如坟的小雪山,他的手已经冻得失去了触觉。回去的路上,雪突然下大,他走出的血路,也被覆盖。
夜晚,无数张旧人的脸,被火托举着,围坐在普弥的身边,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误解的锦鸟,只能唱诵哀歌,他感觉自己掉进了荨麻地里,铜质的墙壁围困着他,身体里无数狼群在嘶叫、在剥削。他已经很久没有做梦,躺在火堆边,枕着自己的羊皮鼓,努力做一个梦,但是怎么也没法入睡,越来越模糊的意识里,他感觉自己的瓦萨神已经弃他而去。但是他不甘心,又坐起身来开始敲响羊皮鼓,他似乎再次看见了那片湿地,上面躺着困倦之水、暧昧之水、虚妄之水……然后,一群鹞鹰飞起来……他说:
“是时候了。在自己的清晨,河流再次准备清澈一点。”
八
晨曦是单薄的,普弥打着喷嚏,在院子里生了堆大火,然后用细竹鞭打挂在栅栏上的棉被。太阳的光芒照在每片屋顶,像闪电般刺眼。普弥的房子在阿卜村最西北边,地势高,几乎可以望见整个村落被雪埋得密不透风,炊烟从各家的屋顶升起。通往普弥家的路平整无脚印,他时时望向那边,渴望着有个人来拜访他,找他占卜,但无人前来。他拿着竹质的扫帚清扫院子里的雪,把屋子打扫了一遍,归置好所有物品,坐在屋檐下,他穿上了那件纯白色的披毡,戴着青蓝色的头帕,深邃的目光望着远处,他想重新开始,从哪里开始呢?他不知道。
沙吉寡妇走过来,她的噩梦不断,儿子也未归,普弥从一颗鸡蛋里占卜出来:“你儿子的魂灵丢在一棵老树下了,需要给他招魂。”沙吉寡妇想让普弥今晚就去主持这场招魂仪式,可是普弥拒绝了,他还没有主持过任何一场仪式,他说应该找个经验丰富的老巫师,我只会占卜。
“谁都有第一次,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的瓦萨神。”沙吉寡妇的话好像是在她嘴里积的雪融化而成,凌厉又温柔,让人无法拒绝。普弥笑着说当然相信自己的瓦萨神,于是答应了。
招魂仪式在夜里举行,普弥盘坐在锅庄石边,闭上双眼开始召唤他的瓦萨神附身,他在自己的想象里看见他的瓦萨神从一块湿地上游过来,那是一只纯白的鸟,羽翼丰满,他说:“来吧,来到我的身体里聆听噩耗,成为我……”然后他开始抖动四肢,敲响羊皮鼓,他说他看见是一个头戴红色头帕的女鬼,屋子里的人就齐声大喊:“去吧,去吧。”沙吉寡妇拍打着自己的胸脯骂道:“去吧,去你妈的吧,不要阻拦我儿子回来。”然后他们宰杀并吃了那只黑乳猪,打包一只猪腿和部分内脏给普弥,众人便离去了。沙吉寡妇为普弥铺了一块竹席在火塘边,明天还需要祭献一只白色公鸡才能把沙吉寡妇儿子的魂灵招回来。
夜晚的火没有熄灭。普弥枕着自己的羊皮鼓陷入陌生的梦境,今晚他喝了几杯烈酒,没感觉到醉意,因为那是侍奉给瓦萨神的酒,自己并没有真正享用那酒。他在朦胧的睡意里感觉到母亲科莫阿果的胸脯笼罩着自己的脸,他喘息着喊出:“阿姆,阿姆。”他得到了回应,这是这么多年来他得到最温暖的回应,他感觉身体被一层湿热的棉覆盖住了,他任由自己迅速升起到天空,又狠狠掉进谷底。
第二天,普弥的内心得到了不可言说的满足,同时也吹进几缕苦涩的冷风。他召唤自己的瓦萨神附身,然后提高了诵经的声音,他第一次在自己的声音里听到了雄性的力量,他说他看见一个少年正经过森林,众人就齐声大喊:“归来吧,归来吧。”沙吉寡妇走到门槛上,左手倚着门,右手放在额前挡住光,大声喊:“归来吧,阿姆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归来的路上别受诱惑,别害怕。”
阿卜村的雪在不知不觉中融化,从屋顶、旷野、松枝堆……最后只剩下墙角的阴暗,山坡上也会这里躺一撮、那里卧一把,分不清是羊还是雪。沙吉寡妇心心念念的儿子没有归来,她每晚悄悄来到普弥的身边,说一些云里雾里的话,普弥也回答一些云里雾里的话。普弥不再选择羊日占卜,他说要随时端奉出自己,为大家服务,即使是不吉祥的日子,他也愿意。但是相信他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在暗地里说:“先把沙吉寡妇的儿子唤回来吧。”他们悄悄讨论如果沙吉寡妇的儿子回来了会发生什么呢?
不知不觉中,普弥的心口上仿佛长出了一株倒刺,一碰就疼,那是拔不掉的疼,是恐惧的疼。于是他关闭了所有的门,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拒绝所有人,包括沙吉寡妇。在一些夜晚他会悄悄出门,举着火把,来到火车站附近隧道口上方静静坐着,听见火车从自己身下轰隆隆地驰过,仿佛他没有站台的想象里也有无数火车在不停奔驰,最后那些火车撞在一起,于是他的想象变成了废墟,废墟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哭声。很多次,他想过跳进那些装满炭的货车里,他想知道火车能把自己带到哪里,又把她的母亲科莫阿果带去了哪里。但他没有,不是不敢,是不想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
是的,当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刻,普弥想离开了。
他开始出门,背着竹筐钻进松林,收集松针,堆放在院子里、屋顶上;又背着他父亲瓦尔那把斧头在山上砍回来一些树枝,如马桑、索玛、杉木、竹枝等。遇到一个人他就说:“我要邀请我的瓦萨神附我身,去咒停一列火车。”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的瓦萨神是假的,再怎么证明都真不了,牧场上的湖已经枯干。还有人说他跟那个骗子瓦尔一个德行。
这晚他没有睡,点着火把不停往火车轨道边运送那些东西,起夜的孩子看到一束火把正从普弥家方向疾走,吓得跑回屋子里,试图叫醒熟睡中的父亲,却挨了一顿骂。这一晚对普弥来说很漫长,他从家里背着羊皮鼓,穿上白色披毡,牵着一只黑色的山羊,出发了。火把烧到尽头,他已经把树枝排序插在铁轨边的空地上,点燃了松针,火焰照在他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盘坐着,那只黑色山羊在啃路边的干草。熊熊烈火,烧出太阳通红的脸。
普弥饮下最后一口酒,开始召唤他的瓦萨神。他洪亮的声音引来早起的人,早起的人叫醒了晚起的人,他们围在附近的坡上,睁着惺忪的眼,看普弥的仪式,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阻拦。普弥开始在轨道附近起舞,敲响羊皮鼓,嘴里的咒语如星火,黑色的公羊还在啃那棵枯草。
“嘟……”当火车的汽笛声从远方响起,普弥的斧头落在那只山羊头上,它躺在地上四肢抽搐着,普弥站在铁轨中央,大声诵咒:“为了自由、群山、迎接你,尊敬的瓦萨。我用衣袖擦去了姓名。现在我剩下普通的自由,群山护佑和瓦萨孤独的疼爱……停下来吧,火车,或者游过去。”人们方才想起他要咒停这辆火车,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那只黑色的公羊,四肢已经停止了抽搐。
沙吉寡妇没有来看这场热闹,此时她正坐在屋檐下,给怀里刚出生的羔羊喂了几口糖水,然后取走屋檐下的那团麻绳,走进了下葬瓦尔的那片松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