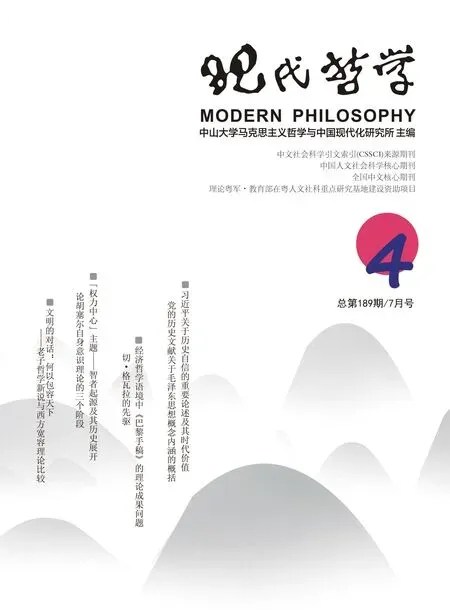何以为家?
——论海德格尔与虚无主义问题
陈 勇

一、非本真性与反讽的本真性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本真性的伦理》一书中将对本真性的追求视为现代性的一大特征。“本真性”概念具有歧义性:一方面,它代表了一种道德理想,要求“原发性(spontaneity)原则”,即每个人都不应该盲目服从外部规范,而应该听从和表达自己内心的声音;另一方面,它面临着滑向个人主义、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危险。(7)[加]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36-38、73-75页。这个观察对于理解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各种本真性伦理思想来说具有启发意义,本真性与虚无主义之间存在着一条隐秘的红线。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人的生存的基本特征规定为自由,用他的话来说,“此在的存在”始终意味着“能在”(Seinskönnen),“此在总是他的可能性”。(8)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S.144,42.非本真性与本真性是对生存方式的进一步区分,它们并不是不自由状态与自由状态的区分,而是两种自由状态的区分。(9)当然,相对本真性而言,非本真性是一种比较不自由的生存方式。虽然自由对于理解人的存在以及存在一般来说是关键性的,但自由问题在《存在与时间》中并没有被展开。在随后的《论真理的本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等文本中,它却成为海德格尔眼中哲学的“基础问题”(Grundfrage)。(10)Martin Heidegger,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Frankfurt a.M.:Vittorio Klostermann,1994,S. 114.《存在与时间》呈现出来的只是海德格尔自由理论的基本轮廓,即将自由区分为非本真的与本真的。(11)关于《存在与时间》中的自由理论,参见陈勇:《〈存在与时间〉中的自由概念》,《现代哲学》2016年第5期。
非本真性是指日常性的“常人”存在方式,尽管这种存在方式被描述为“此在的沉沦”,然而它并不意味着道德上或宗教上的堕落,而是指“迷失在常人的公共性之中”。(12)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S. 175.常人的生活方式是平均化、扁平化与同质化的,正是这些特征带来了现代生活的便利性。“公共性”一词的德语Öffentlichkeit来源于offen(公开的),公共的存在方式是习以为常的,它以天然的正当性面目呈现出来。日常的或者说正常的(normal)存在方式包含种种规范或者标准(norm),以这种存在方式生存意味着遵循规则,因而公共的常人存在方式包含规范性(normativity)。这种规范性不以实践主体的自由选择或反思为前提,被规范的常人的行动是不经意的、自然而然的。海德格尔写到:“常人无所不在,而且它使得自己避免遇到需要做出决定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常人规定了所有的判断和决定,它从此在那里总是把责任心(Verantwortlichkeit)给拿走了。”(13)Ibid.,S. 127.常人遵循规则并且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但常人的行动不以“决心”(Entschlossenheit)为前提,“责任心”或者说“良心”(Gewissen)在常人的存在方式中是缺失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种存在方式是他律的,即非本真的(un-eigentlich)。“迷失在公共性之中”的常人可以说是无面目的,作为常人而存在的“我”并没有发现真我或者说“本真的自身”,而是将“我”理解为“常人自身”。
诚如泰勒所言,对于本真性的追求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同样可以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他对本真性的刻画充满张力:一方面,他强调非本真性与本真性的区分并不涉及道德与价值判断,而只是对于人的两种存在方式的存在论上的区分,并且本真性(“具有罪责”)是“道德上的善与恶的(即道德的)可能性的生存论条件”,本身并不能被规定为善的或者说好的;另一方面,他似乎暗示着本真性是一种比非本真性“更好的”存在方式,因为本真性意味着“此在的成为自由”,对现代人来说自由天然地比不自由更好。(14)Ibid.,S. 286,287.“此在的成为自由”这个表达本身是带有歧义的,非本真性并不等同于不自由,只不过与本真性相比显得不自由。即便在存在论上本真性也比非本真性“更好”,因为只有在本真性之中人的存在以及存在一般的意义才得到揭示。
在近代哲学中尝试为道德进行形而上学奠基的范例是康德哲学。康德认为,道德是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之上的,而作为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的自由意志并不是超然于善恶的,而是绝对善的“善良意志”。此外,意志自由意味着自律:实践法则或者说道德律并不来自自然界或者上帝,而是来源于人的理性本身,人为自身立法。实践法则作为“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作为一种纯粹的形式让人超越了自然因果律的束缚,并认识到自己不仅是自然界的一员,而且是自由王国的一员。简言之,道德以及为之奠基的自由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的形而上学规定,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等同于道德的奠基。(15)Immanuel Kant,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Stuttgart:Reclam,2008,S. 15,42,70-71,80.
康德区分了他律与自律,海德格尔则区分了非本真性与本真性。在本真性中,“良心的呼唤”把人从常人自身中唤回,聆听到或者说理解了呼唤的人意识到常人的存在方式的“虚无”(Nicht)(16)孙筱泠将海德格尔的本真性伦理学解释为一种应答伦理学。这种解读是有道理的,海德格尔对于本真性的分析是从“良心的呼唤”以及对这种呼唤的理解着手的;但他认为良心的呼唤并非来自于他者,而是来自此在自身,对于它的理解意味着“想要有良心”或者“决心”,在这个意义上本真性甚至意味着此在的自律。(孙筱泠:《责任与应答——海德格尔原伦理学初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意识到自己“是有罪责的”(ist schuldig),从而处于“无家状态”(Unheimlichkeit,阴森可怖状态)之中(17)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S. 188.。从根本上说,良心经验与死亡经验是相同的,都是面向虚无而存在。在这两种经验中,人并没有停止存在,而是以不同于常人的存在方式而存在,处于“无家状态”的人意识到另一种生存可能性,即不是作为常人而存在,而是面向虚无而存在。这种生存可能性不再是公共的或者说他律的,而是本己的;人可以选择接受或者逃避它,如果是前者,那么人自己选择了自身,这种选择意味着本真性与真正的自由。在海德格尔这里,本真的自我不是一种实体或者作为“我思”的先验主体,而是自由的生存可能性,作为“真我”而存在;就其摆脱了常人的规定性而言,它不再具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性,而是面向虚无而存在。海德格尔也赋予这种生存方式一种积极意义,即本真性意味着“责任心”或者说“想要有良心”。(18)Ibid.,S. 287-288.在康德哲学中,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任意或者说随心所欲,而是自律,自由的人“出于义务,而不是合乎义务”而行动;在海德格尔这里同样如此,尽管本真的自我没有赋予自身任何一种实践法则,然而却是具有“责任心”或者说“想要有良心的”。(19)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只有本真的自我才是真正的道德主体,海德格尔将义务或者说责任赋予自身,为自身“立法”,而非本真的自我或者说常人则将责任与义务看成是被给予的。
海德格尔的本真性理论常常被指责是唯我论与唯意志论(20)Ernst Tugendhat,Selbstbewusstsein und Selbstbestimmung,Frankfurt a.M.:Suhrkamp,1979,S. 241-243;Dieter Thomä, Die Zeit des Selbst und die Zeit danach:Zur Kritik der Textgeschichte Martin Heideggers,1910-1976,Frankfurt a.M.:Suhrkamp,1990,S. 418f.:本真的自我摆脱了公共世界或者说他人的束缚,成为单独的“向死而存在”“想要有良心”;此外,生存的真理被规定为“决心”(Entschlossenheit)(21)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S. 297.,不受社会规范制约的决心无非是另一种强力意志,正是这种唯意志论使得海德格尔后来滑向纳粹主义。即便不考虑这些,这两种批评也并非没有道理,只不过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任何一种本真性理论都面临这种危险,各种本真性理论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要求原发性原则,即自我规定。
海德格尔也指出,本真性不是对与他人的共在的否定,而是意味着本真的与他人共在:“只有出于决心的本真的自身存在才出现了本真的共处。”(22)Ibid.,S. 298.与他人的共在有两种极端样态:一方面是“越俎代庖”(einspringen),替他人操心,虽然它也是一种关心(Fürsorge),然而在这种共在的样态中他人的自由被否定了,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他人的操心被拿走了,他们成为依附者与被统治者;另一方面是“做出表率”(vorausspringen),作为本真的关心方式它将他人的操心交还给他人。(23)Ibid.,S. 122.换句话说,只有本真的自我才能将他人视为(与自身一样)同等自由的,他人与自我一样生存于世,操心于他们自身的存在;他人不是物,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常人,而是与自我相遇的具体的“人”。如果说本真性意味着无规定的面向虚无而存在,那么本真的自我与他人恰恰是平等的,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自我与他人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是何种常人。可见,本真性理论构成唯我论的对立面,本真性不仅意味着自我的真正自由状态,而且意味着对他人的自由的承认。
此外,自由地、平等地与他人共在从根本上否定了唯意志论,“决心”并不意味着漠视他人、为所欲为,而是对自身“处境”(Situation)的理解。单从《存在与时间》来看,海德格尔的本真性理论带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决心恰恰把自身带到当下在上手者旁的操劳着的存在中,把自身驱入与他人的操心着的共在中……但作为操心的此在是被事实性与沉沦决定的。”(24)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S.298.本真性不是对常人的存在方式的逃离,而是让人带着决心自由地选择这种存在方式,是超人式的热爱命运(amor fati)。走出洞穴的人决定要带着良心与责任心回到洞穴内,但洞穴内并不会因此就变为洞穴外,常人的存在方式依然是公共的、非本真的。本真性理论的宿命论色彩体现为非本真性构成人的存在的必然性规定,本真性的积极意义仅仅在于让人带着良心与责任性去选择、接受它。在海德格尔看来,公共的常人存在方式,即日常生活成为本真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生存的日常性等于非本真性。(25)Ibid.,S. 126.
总地来看,《存在与时间》过分强调本真性的存在论意义,忽视了它的伦理学意义,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基础存在论不是规定存在者本质的形而上学,而是揭示存在的意义的现象学。他甚至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视为一种基础存在论(26)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分析了康德的“道德人格”(personalitas moralis)与“敬重”(Achtung)概念,并由此出发批评了舍勒将康德伦理学视为形式主义伦理学的观点。在《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中,海德格尔分析了为何康德从因果性的角度引申出自由的先验理念,并指出这种形而上学理论径路的局限。(See Martin Heidegger,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Frankfurt a.M.:Vittorio Klostermann,1997,S. 185-198;Martin Heidegger,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S. 139f;蔡文菁:《自由与有限性——对海德格尔〈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的解读》,《哲学分析》2018年第5期。):“‘道德形而上学’,即此在与生存的存在论。”(27)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S. 293.也就是说,基础存在论不等于原初伦理学,但包含了它。在《存在与时间》中,基础存在论的伦理学之维体现为对非本真性与本真性的区分:非本真性呈现为在家状态,在常人的日常生活中周遭事物是熟悉的,作为生存空间的周遭世界的意义与自我的角色(常人自身)是不言自明的,生存于其中则是安之若素的。但在常人存在方式中,人并不是作为真我而存在的,常人的存在方式意味着人的“异化”(Entfremdung);(28)Ibid.,S. 178.相反,本真性呈现为无家状态,无论物、周遭世界还是生存本身都失去了不言自明的意义,世界向人呈现为虚无,真我仅仅是面向虚无而存在这种生存可能性,它是阴森可怖、充满恐惧的。此外,即便本真性意味着找到真我,获得真正的自由,但它只是一个“瞬间”(Augenblick),除了选择接受自己的处境、带着决心与良心去选择常人的存在方式外,真我别无其它选择。(29)回到洞穴与一直处于洞穴当然意味着两种生存状态,但“决心”或者“良心”无法让俗世生活成为本真的,对此我们并不缺乏经验,甚至它们带来的是现代悲剧,正如20世纪历史所展现的那样。
这种发现真我与克服异化的方案很难说是成功的,非本真性固然意味着异化,但本真性却意味着直面虚无与反讽性的无家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中无论物、世界还是人的生存都没有获得坚实可靠的意义。(30)孙向晨认为,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来自“无根的个人主义”,我们要以历史性来克服个体的虚无主义。他的分析与泰勒对于本真性理论的诊断异曲同工,尽管他们抓的药方并不相同。能否通过“寻根”,即把个体放入“家”“世代性”或者“历史性”之中来克服现代虚无主义,这个问题依然有很大的探讨空间。本文将聚焦海德格尔后期抓的药方,但不主张这个药方是唯一有效的或最有效的。(孙向晨:《家——个体与亲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68页。)海德格尔对非本真性与本真性的分析带有强烈的虚无主义色彩,这种虚无主义体现了一战后欧洲的时代精神,家园(Heim,家)在战争结束后残留下来,却失去了作为家园的意义,由汽车、电话、报纸等“物”构建起来的现代世界令人感到厌倦,无家可归的现代人只能带着决心去创造新的世界、构建新的家园。虚无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的关联并不隐秘。(31)斯特劳斯对此的观察是富有洞见的。(参见[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编:《政治哲学史》,第1068-1069页。)《存在与时间》中没有让日常生活世界成为家的思想。
从笛卡尔哲学中的无限的自由意志到康德哲学中的自律,再到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向死而存在”与“想要有良心”,泰勒所说的原发性原则构成近代西方哲学的核心精神之一。现代人要自主地规定自身、自由地做出选择,真正的、本真的自由意味着摆脱一切束缚,由之而来的是直面虚无。直面虚无并不必然是消极的,可能是平等性智与慈悲心,可能是强力意志,也有可能是决心与良心,等等。但人的生存无法停留于虚无之中,走出洞穴的人还是要回到洞穴之中,只有让洞穴成为家,才会产生真正的“积极虚无主义”。但在《存在与时间》中,我们没有发现如何让日常的生活世界成为家。
二、虚无主义必然来源于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思想理解为虚无主义,相反,他将自己视为“欧洲虚无主义”的诊断者。在1936年开始的尼采讲座中,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核心议题。他对尼采与虚无主义的阐释并不是一项哲学史研究,他在《尼采》的前言里指出,这个文本是他从1930年到1937年的思想缩影。(32)Martin Heidegger,Nietzsche, Erster Band,Pfullingen:Neske,1961,S. 10.他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1943)一文中同样指出,他的阐释是对虚无主义的本质的追问。(33)Martin Heidegger,Vorträge und Aufsätze,Frankfurt a.M.:Vittorio Klostermann,2000,S. 193.在他的纳粹政治生涯结束、二战即将爆发之际,这种追问绝不会仅仅是出于学术的兴趣。
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虚无主义表面上看是指最高价值或者意义的丧失,“上帝死了”,但尼采进一步将它的根源追溯到西方形而上学或者说柏拉图主义:对于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区分;不仅如此,在这种区分中,此岸世界或者说感性世界的价值被贬低,最高的价值则安置在超验的彼岸世界或者说理智世界之中;由于这些最高价值是无法在此岸世界中被实现的,最终的结果是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为了克服这种(消极的)虚无主义,尼采发展出“积极虚无主义”,即强力意志肯定自身以及感性世界,否定彼岸世界的存在,并为自身设定或者说创造价值。海德格尔更进一步,将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即强力意志哲学也诊断为一种主体性形而上学,理由是强力意志也是对存在者的本质的形而上学规定。(34)Martin Heidegger,Nietzsche,Erster Band,S. 257f.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并不必然以柏拉图主义的形态出现,而是意味着对存在者本质的规定。与尼采不同,他并不将柏拉图主义理解为虚无主义的根源,而是将它的根源规定为西方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
如果海德格尔的诊断是成立的,那么他的思想就不能被视为虚无主义,因为其关注焦点始终是存在的意义,而不是存在者的本质。但将存在、生存与世界的意义都规定为虚无的基础存在论实际上也是一种虚无主义。即便本真的自我带着决心自由地选择常人的存在方式,日常生活世界也不会成为人所居留的家园(Heim)或者说家乡(Heimat),它始终是异化的。甚至这种异化经验本身是由本真性带来的,始终以非本真的常人方式生存的人不会经验到它,一旦有了本真的虚无经验,那么原本熟悉的日常世界将被经验为异化的。《存在与时间》中带着决心去生活的人与《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35)参见[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都是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性神话,并且与尼采的超人一样体现了热爱命运的英雄主义精神。
海德格尔将现代人的命运规定为无家可归状态,并不仅仅受荷尔德林的启发或者源于对尼采的阐释,而且来自其早期思想中对人的本真的无家状态的思索以及他自己的时代经验。在1933年充满战斗激情的“校长就职演说”中,他呼吁“每一个个体都一道做出决定,即便当他逃避这一决定时,尤其在这个时候”(36)Martin Heidegger, 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weges,Frankfurt a.M.:Vittorio Klostermann,2000,S. 117.,随后的纳粹经历则告诉他这种英雄主义是行不通的。决心或者良心并不能使常人的存在方式成为本真的,1933年的海德格尔遗忘了自己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洞见了么?《人文主义书信》的第一句话“对于行动的本质,我们还远远没有充分明确地加以深思”(37)Martin Heidegger,Wegmarken,S. 313.是他的忏悔么?行动与思考都是在世界中存在的或者说居留的方式,政治上的失败与时代悲剧使得海德格尔更加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人应该如何在世界中存在或者说居留?人与世界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何以克服虚无主义而居留?在《存在与时间》中,“无家状态”(Unheimlichkeit)被规定为生存的本真性;而在《人文主义书信》中,“无家可归状态”(Heimatlosigkeit)(38)Ibid.,S. 341.则被描述为(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与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从中不难发现海德格尔思想光谱的位移。
三、克服虚无与诗意栖居
虽然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不是系统性的,但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在《人文主义书信》中,他明确地与传统人文主义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划清界限,认为这些思想都是遗忘了存在的形而上学思想,但他并没有否认自己的思想也是一种人文主义,“但它同时是人文主义,在它之中不是人,而是从存在的真理而来的人的历史性本质才是关键”(39)Ibid.,S. 343.。虽然存在的真理与天命占据了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核心位置,但人的存在与“历史性本质”也是其后期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并且与前者紧密相关。
人与存在的关系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发生了颠倒,不再是人筹划存在的意义,而是存在的历史规定了人的本质,人只是“存在的牧羊人”。(40)Ibid.,S. 330.强调人的自由与价值的现代人文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尼采、萨特以及海德格尔早期的思想也处于这个框架之内,而他的后期思想则是对于它的批判。虚无主义并不能通过人的自由创造来克服,正如《存在与时间》所揭示的那样,自由的本质是面向虚无而存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任务之一是思考如何让世界成为“家”,如何让人在世界中“诗意地栖居”。他在《人文主义书信》中指出,家乡意味着“存在的亲近”(Nähe des Seins),克服无家可归状态只能通过对于“存在的天命”的倾听或者说“存在的澄明”来实现。(41)Ibid.,S. 337-338.
在《存在与时间》中,常人的存在方式是非本真的,而本真的存在方式是无规定性的,这种截然的对立在其后期思想中不再存在。不仅“思”与“诗”属于“诗意的”居留方式,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甚至农妇的生活也被刻画为“诗意的”:“借助于这种可靠性,农妇通过这个用具而被置入大地的无声召唤之中,借助于用具的可靠性,世界对她才是确定的。世界和大地为她而在此,也为与她相随以她的方式存在的人们而在此,仅仅以这样的方式:在用具中。”(42)Ibid.,S. 19-20.虽然在农妇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真理没有被揭示,在这个意义上她的存在方式并不是原初的或者本真的,但在对于用具(一双旧鞋)的使用中她建立了与世界以及大地的坚实可靠的关联。在海德格尔看来,农妇对于庄稼的照料(pflegen)、诗人的作诗(dichten)与哲人的思索(denken)都是筑居(bauen)与居住(wohnen)的方式。(43)Martin Heidegger,Vorträge und Aufsätze,S. 148-150.他不再把一切日常生活方式规定为非本真的,而是赋予一些日常生活方式以“诗意”。(44)海德格尔并没有说明看报纸、开汽车、挖煤矿等现代生活方式是否也是诗意的。不可否认,海德格尔后期作品中充满了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的怀旧与思乡之情。此外,即便诗与思构成原初的、本真的存在方式,但它们并不是对日常生活方式的扬弃。一副梵高的油画描绘了农妇(或者他自己)的鞋,这幅画作为艺术作品的作品存在并不在于鞋的再现,而是揭示了“用具的用具存在”。(45)Martin Heidegger, Holzwege,Frankfurt a.M.:Vittorio Klostermann,2003,S. 21.它揭示了鞋子的可靠性以及与世界、大地的关联,赋予农妇的居留以诗意。用具也被海德格尔赋予新的意义,在《存在与时间》中作为用具的用具存在是它的“有用性”(Dienlichkeit),每个用具都存在于用具整体之中,并最终服务于人的目的(Umwillen,所为);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则相反,可靠性(Verlässlichkeit)构成用具的规定性,人需要依靠(verlassen)它们,并且只有通过它们才被置入世界之中、生活于大地之上。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用具或者说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本真的、诗意的居留不能是无规定性的或者说虚无的,而是依赖于物所带来的意义。(46)这里,我们可以批判海德格尔忽视了道德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他所谈论的并不是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是人(类)与世界的关系,道德是另外的话题。
对于“物”的追问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存在与时间》中,“物”被划分为作为认知对象的现成者与作为实践对象的用具(上手者),而在后期思想中“物”有了更多的形态,例如《艺术作品的本源》将艺术作品规定为不同于用具与认知对象的物。但海德格尔真正关注的并不是物的分类,而是物的本质,它在《物》一文中被规定为“聚集”(Versammlung):“物成物(dingt)。通过成物,物让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必有一死者逗留;通过逗留,物让相距遥远的四方相互趋近。”(47)Martin Heidegger,Vorträge und Aufsätze,S. 179.物不再是人的认知对象或实践对象,也就是说,人和物之间不再是主客关系,相反,作为必有一死者的人被物聚集起来与天空、大地、神圣者一起构成世界,世界是由它们共同构成的“四方域”(Geviert)。(48)Ibid.,S. 180.《道德经》第25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海德格尔的《物》一文出现在他与萧师毅合译《道德经》之后,“四方域”概念是受《道德经》的启发而产生的一个合理推论。人在世界中存在或者居留意味着与其它三者发生关联,并且这种关联是通过物才发生的,物的聚集(“物成物”)与天地神人的相互趋近(“世界的世界化”)是共同发生的。简言之,居留实际上意味着天、地、神、人、物五者之间的“诗意的”游戏(49)这种游戏是诗意的(poetic)意味着它是创造性的,在古希腊语中,poesis意味着制作、创造。虽然海德格尔没有明确指出,但我们可以认为诗意的游戏是自由的,在其中没有任何一方是统治性的、压迫性的,用他的话说,天地神人处于镜像(Spiegel)关系之中。,只有在这种游戏中,世界才成为人类的家园。

此时的海德格尔还没有放弃将世界理解为生存视域:“农妇却有一个世界,因为她逗留于存在者之敞开领域中……作品存在包含着一个世界的建立。”(51)Ibid.,S. 31-32.农妇的或者古希腊神庙开启的世界并不是物与人构成的整体,这个整体是大地,它是不可名状的一切事物的“隐匿之所”,而农妇的世界或古希腊世界则是“敞开的”意义世界。只有在敞开的世界中,大地才涌现并隐匿,在这个意义上,大地属于世界;(52)“作品把大地本身挪入一个世界的敞开领域中,并使之保存于其中。”(Ibid.,S. 32.)反之,(意义)世界并不可见,只有通过大地,它才得以敞开自身。海德格尔将世界与大地的这种关系形容为一种“争执”(Streit)。(53)“世界建基于大地,大地穿过世界而涌现出来……世界不能容忍任何锁闭,因为它是自行公开的东西。而大地是庇护者,它总是把倾向于把世界摄入它自身并且扣留在它自身之中。世界与大地的对立是一种争执。”(Ibid.,S. 35.)在此,他修正了自己早期思想中的世界概念,作为生存视域的世界必须与大地发生关联,由此它才不是虚无的。(狭义上的)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实际上体现了(广义上的)世界的双重意义:作为生存视域(世界)与作为存在者整体(大地)。
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指出世界是有多个维度的,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是两个维度,在《物》一文中则是“天地神人”四个维度。海德格尔在揭示世界的大地维度时颠倒了人和世界的关系,世界并不等同于人的生存视域,它也是人的生存根基,并且作为必有一死者的人将复归于其中。此外,就作为敞开域而言,世界还包含了天。在《物》一文中,天被描述为“是日月运行,群星闪烁,是周而复始的季节,是昼之光明和隐晦,夜之暗沉和启明,是节日的温寒,是白云的飘忽和天空的湛蓝深远”。(54)Martin Heidegger,Vorträge und Aufsätze,S. 179-180.这个意义上的天似乎只是《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的大地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我们对于“天”与对于“空”的经验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有了敞开域或者说空,才会有在大地之上(包裹着大地)的天,换句话说,天空是没有被大地遮蔽的敞开领域,它使得大地涌现并复归于其自身。《物》一文中的天空与大地的关系来源于《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世界与大地的关系,天空是作为敞开领域的世界,由此大地才更成其为(作为隐匿之所的)大地。值得注意的是,“天地”构成对大自然的崭新规定,这种规定在西方思想史中可谓“开天辟地”,彻底摆脱了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的束缚,赋予我们另一种审视自然的视角。
海德格尔天地神人四方域的思想来自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解读与翻译《老子》的经验,这一思想最著名的应用是《物》一文中对壶的分析,但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天地神人并不是某种诗歌经验或者对于某些特定用具的浪漫想象的产物。通过赋予世界天地神人四重意义,海德格尔重新规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说人的居留,本真的居留不是面向虚无而存在,而是在世界中获得意义,让世界成为“家”,克服虚无。天地神人四方域的思想是一种“家”之思,也许它并不构成普遍性经验(一切形式的伦理学也都不是),但它至少开启了一种本真居留的可能性,在虚无主义时代意味着一种原初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