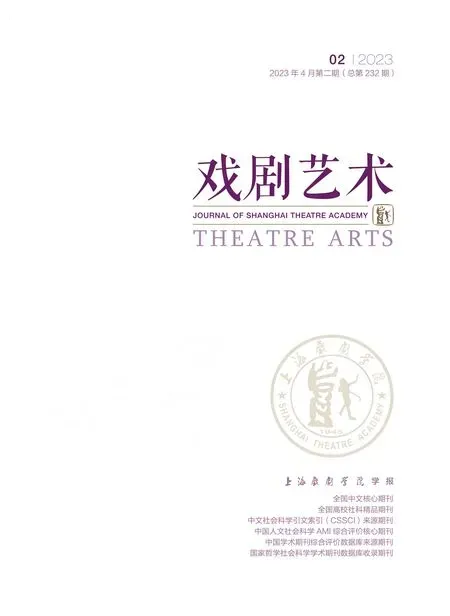如何并置东方与西方: 莎剧歌舞伎的三个案例
胡纹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跨文化戏剧演出引人注目。1986年,上海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带来昆剧《血手记》(《麦克白》)、越剧《第十二夜》等具代表性的莎剧戏曲。同年,台湾的当代传奇剧场也以《欲望城国》(《麦克白》)开启跨文化戏曲的探索。莎士比亚作为带有启蒙色彩的国际文化偶像,为东方戏曲的现代化提示了一条新路径。这条路很诱人,因为它并置了东西方的艺术高峰;这条路也多歧,因为两座高峰无法直接拼接。当“凝固的”舞台艺术引入舶来文本的时候,它容易遭遇形式对文本的制约,或是新内容对旧美学程式的挑衅,在“西方化”与“本土化”之间难以落脚。这使莎剧的戏曲化陷入争议。本文并不试图直接回应此争议,而是期待从邻国的经验中获得提示——日本的歌舞伎与中国戏曲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如程式高度成熟、重视歌舞戏、具有时空虚拟性等。因此,日本的跨文化戏剧面临的困境与我们也是相似的——如何并置东方和西方,如何面对文化差异与文化交融的双重现实。本文将以三部莎剧歌舞伎为例,审视民族戏剧演出跨文化剧本的三种代表性的处理思路——“一半西方,一半日本”“足够西方,又足够日本”“既非西方,又非日本”。
一、 一半西方,一半日本: 《何樱彼樱钱世中》
1885年的歌舞伎作品《何樱彼樱钱世中》是第一部莎剧歌舞伎。在明治初期,为西方文本量体裁衣的“新剧”尚未出现。对歌舞伎等“旧剧”无法兼容新文本的反思催生了新剧。因此,以歌舞伎演出第一部莎士比亚戏剧,是一条被动的路径,也是一次不可避免的实验。
1. 从文本到舞台
《何樱彼樱钱世中》最初以连载小说的形式登载在1885年的《大阪朝日新闻》,作者是知名作家宇田川文海。在此之前,宇田川文海已发表《汝所好》(《皆大欢喜》)、《恶因缘》(《罗密欧与朱丽叶》)、《阪东武者》(《奥赛罗》)等多部改编自莎剧的报刊连载小说。怀着西闻东渐、启发大众文化的目的,明治的许多知识分子投入莎士比亚的译介工作。1872年,政府发布演剧改良方针,要求废止狂言绮语,采取尊重史实的范式,因此当时出现了人生教训等主题的改良倾向剧作,这也体现在文海的写作中。
关于《威尼斯商人》,1877年的《民间杂志》连载了改编小说《胸肉的奇讼》,1883年井上勤的《人肉质入裁判》是对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中相应篇目的翻译。《胸肉的奇讼》《人肉质入裁判》的标题虽然猎奇,却吸引了一定的社会关注。在这两部前文本的基础上,宇田川文海把《何樱彼樱钱世中》送上了戏剧舞台。被称为“大阪剧坛第一人”的胜谚藏(1)服部幸雄,富田鉄之助,広末保.歌舞伎事典.平凡社,1983,p.108.担任该剧的歌舞伎脚本作者。主演中村宗十郎是与“剧圣”九世市川団十郎齐名的歌舞伎明星。
1885年5月16日,《何樱彼樱钱世中》的歌舞伎演出登上大阪“戎座”。《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了数篇评论文章,赞扬法庭一场演员的出色表现力。(2)平辰彦.『ヴェニスの商人』と『何桜彼桜銭世中』: その台本と上演をめぐって.『英学史研究』,1994,995(27),p.167.观看了公演的关根默庵评价这是一部感觉不到是舶来品的、非常巧妙的翻案作品,逻辑通顺且新奇有趣。(3)関根黙庵.芸苑講談.伊吕波書房,1913,p.109.首演一个月后,《何樱彼樱钱世中》又在大阪“朝日座”再次公演,1886年在堀江、纪州、若山等地公演,1893年在大阪的“弁天座”重演。(4)白川宣力.『何桜彼桜銭世中』: もう一つの台本をめぐって.演劇学(早稲田大学演劇学会編),1990,31号,p.158.从商业演出的角度来说,这部作品在当时颇为成功。
2. “翻案”与“折衷”
歌舞伎及莎剧接受史的研究专家河竹登志夫对《何樱彼樱钱世中》有这样的评价:“不过是从表面提取了西洋的新奇素材,然后用旧的歌舞伎手法处理罢了……是过渡性质的现象在初期的一种形态。”(5)河竹登志夫.歌舞伎化された『ベニスの商人』―何桜彼桜銭世中―.シェイクスピア研究(日本演劇学会編),中央公論社,1951,p.91.河竹教授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的暧昧性与妥协性值得关注。而这与“翻案”的改编形式相关。
明治初期,刚刚摆脱锁国状态的日本人对异国文化缺乏常识,也没有翻译的习惯和规则。西洋的人名、风俗过于新奇、陌生,杂糅的信息不便于理解。因此,当时最普遍的译介方式就是“翻案”(6)此处的“翻案”是和式汉字的用法,与中文语境中的“翻案”(意为推翻定论)存在偏差。本文保留日语中的“翻案”说法,下文不再重复解释。——把一个外国故事嫁接在本国的某个历史背景中,风俗、地名、人名都替换为本土内容。同时,这也是舶来文本走向歌舞伎等传统戏剧舞台的通道。
“翻案”常常与“折衷”挂钩。《何樱彼樱钱世中》设置了一个楔子,开门见山地提示折衷背景——书生和田、中村二人在大阪心斋桥的会面。和田买了江户后期名作家柳亭种彦的《正本制》,中村买了脱胎于莎剧的《人肉质入裁判》。两人分别站在拥立传统与推崇西洋的立场。在他们的争论中,友人鸟山登场,表示想要中和西洋文学的精神与日本文学的趣向,撰写一篇新作,也就是后文的正体。
《何樱彼樱钱世中》一例中,作者意在提取日本传统与西方新潮的各自菁华,进行合并。为了兼顾不同立场的观众,该折衷主义试图取一半西方与一半日本的中间点。这是明治实用思维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做法。而笔者认为,此处折衷的双方处在各自的认识域当中,两者并不重合在同一平面,因此无法求得中间点。此处的折衷,是将一方掰碎,融入另一方——经过“翻案”,莎士比亚的浪漫主义几乎消失,改头换面成为“日本式”的人物和精神。此处的“日本”指受武士道传统和程朱理学影响的19世纪末日本,也是资本主义实用观念下的维新日本、一个“半开化”的日本。
3. 严肃的道德正剧
在人物形象上,莎士比亚笔下的浪荡子巴萨尼奥被塑造成了刻苦勤勉的武士青木庄太郎。原文里巴萨尼奥为追求鲍西娅向安东尼奥堂而皇之地借款,导致安东尼奥陷入危情;而青木庄太郎则是有苦难言,隐忍不发,在纪伊国屋伝次郎(安东尼奥)的再三催说下才道出穷状——隐忍是儒生的美德。此外,出于武士尊严,纪伊国屋伝次郎在审判前夕还差点剖腹自尽。
在选匣子的一场,莎剧中狂放的巴萨尼奥在金、银、铅匣子中选择了铅。他放弃价值更高的金银,是因为铅匣子上写着“谁选择了我,就必须准备牺牲他所拥有的一切”,是出于浪漫的、冒险的人生观。而青木庄太郎在金、银、铁中选择了铁,他的理由是铁最具实用性——铁炮、刀枪、锄头、锅釜等是各行各业的工具,外国的铁道、铁舰也都是铁做的。(7)鈴木邦彦.『何桜彼桜銭世中』研究.商学論究,2003,50(3),p.107.宇田川文海笔下流露出实业兴国、富国强兵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世界观,隐去了个人主义价值观。
宇田川文海不能像莎士比亚那样坦荡刻画人物的缺陷和率性。《何樱彼樱钱世中》要求主人公在道德上是严肃、完满的,符合儒学精神的刻苦上进、屈己待人、心怀天下,以及武士精神的绝对坚韧。整出戏的落脚点也在于天道酬勤、扬善除恶的劝世论。法庭一场是最博人眼球的戏份,也是《大阪朝日新闻》上的评论重心。这场高潮戏的支点在于情节的反转: 狡诈阴险的五兵卫(夏洛克)得到惩罚;对朋友鼎力相助的伝次郎(安东尼奥)化险为夷,善有善报;寒窗苦读的青木庄太郎最终抱得美人归。最后该戏在演员全体高喊“善有善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呼声当中落幕。(8)鈴木邦彦.『何桜彼桜銭世中』研究.商学論究,2003,50(3),p.117.原本展现鲍西娅的过人智慧,嘲弄犹太人夏洛克的一出喜剧,在日本化之后成了一部严肃的道德正剧。
此外,在这一宣扬因果报应的演出中,玉荣(鲍西娅)女扮男装出庭宣判的情节被删除。相应地,玉荣被替换为一个新的男性角色“水木平十郎”,他主持正义,将全剧推向高潮——父权意识形态之牢固不言而喻。
4. 边缘化的他者
从演进的历史观来看,歌舞伎《何樱彼樱钱世中》是一次不彻底的文化译介,具有过渡性。限于时代因素,《威尼斯商人》经文本“翻案”而歌舞伎化,这是被动的途径。虽然创作者采取了“一半西洋,一半日本”的折衷姿态,但情节嫁接至日本历史后,内核仍然囿于宋明儒学和武士道传统的道德观。因此,从启蒙的目的来说,这种方式限制了新思想的传播,是一场必然失败的实验。此后的译介逐渐由翻译剧和西式剧场替代。
若抛开启蒙主义意识形态,这部作品的“折衷主义”还可以看作对待外来文化的一种典型模式——将他者重组为书写自我的素材。当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足够陌生,陌生到尚未干扰自我的书写权力时,他者提供的叙事则容易模糊、失焦,当再次清晰时已经成为新奇、博人眼球的符号(如《胸肉的奇讼》)。内容上不符合习惯的部分可以被恣意摘除;选取的部分则有益于主体的话语建构(天道酬勤、善有善报的因果论),从而完成一次自我形象的重复、修补。与此同时,它在姿态上展示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关注。这样的作品容易获得本地观众的欢迎,观众感觉不到是舶来品,认为它新奇有趣,因为它同时提供新鲜感、丰富感与安全感。自我主体性的再书写则伴随他者的破碎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这种跨文化现象未必一定随时间而消失。经由全球化塑造的今天,类似的现象仍然司空见惯——因为时间并不能消除权力存在差距的永恒现实。
二、 足够西方,又足够日本: 《叶武列土倭锦绘》
20世纪末,明治政府实施全盘欧化政策的百年之后,日本不仅完成了现代社会转型,还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西方影响已经和日本现代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日本社会需要对西方重新定位,从而进行自我定位。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戏剧试图摆脱明治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终于,日本莎剧不再模仿英国舞台,而是让莎士比亚当代化、日常化。这是莎剧改编最自由频繁的狂欢期,却也是文化焦虑的沸腾期。1991年的《叶舞列士倭锦绘》就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1. 莎剧重返歌舞伎舞台
步入20世纪后,新剧一度包揽绝大多数莎剧演出,歌舞伎淡出视线。在1970年代以前,新剧严格使用翻译文本,遵从现实主义风格,尽量进口“正品”的英产莎士比亚。日本莎士比亚剧团(Shakespeare Theatre)(9)出口典雄于1975年创立的剧团,每月举行5天左右的莎剧公演。1981年5月,莎士比亚剧团完成了莎士比亚所有作品的上演,出口典雄也成了日本导演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的创始人出口典雄对20世纪中期的日本莎剧有这样的总结:“当时的莎剧演出以大、中剧场为主,并且认为观众离舞台越远越好。他们认为我们和莎剧很生疏,并把莎剧当成和我们无关的世界里的故事来演……他们染着头发,戴着假鼻子,尽可能向西洋人靠拢。”(10)出口典雄. シェイクスピアは止まらない.講談社,1988,p.96.
而196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先锋戏剧和小剧场运动动摇了新剧的统摄性地位。此外,包括1973年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仲夏夜之梦》在内,世界各国的莎剧作品开始频繁赴日演出,动摇了日本对英国古典主义的“正牌”情结。(11)[日] 濑户宏: 《莎士比亚在中国: 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史》,陈凌虹译,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第293页。莎士比亚开始被当作“同时代人”来看待,更多通向当代政治和社会批判的改编涌现出来。1988年,模仿莎士比亚环球剧院(Globe Theatre)的东京环球剧院(The Globe Tokyo)(12)东京环球剧院于1988年开业,以普及莎剧作为剧场运营的基本方针,上演了来自英国、瑞士、加拿大、罗马尼亚、中国、澳大利亚等多国的莎剧。它模仿伦敦的环球剧院,是三层的圆形空间。运营曾一度中断。2002年重新开业后,它成了一个普通的剧场。作为专门演出莎剧的剧场开业。1990年,光是《哈姆雷特》就在日本上演了18个版本。
在这一强调多样性的时期,日本莎剧又开始关注与歌舞伎、能剧、文乐等传统剧场的融合。在能乐领域,宗片邦义组织了英语能剧莎士比亚研究会,1982年以来多次用英语上演能剧《哈姆雷特》。(13)他将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改为“生存还是毁灭,这不再是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is no longer the question),以表达超越生死的悟道境地。文乐领域有来自《暴风雨》的《天变斯止岚后晴》(1992),以福斯塔夫为原型的安土桃山时代故事《不破留寿之太夫》(2014)等作品。而在歌舞伎领域,最受瞩目的就是1991年在东京环球剧院上演的《叶舞列土倭锦绘》。
2. 百年前的“翻案”底本
《叶舞列土倭锦绘》的文本来自假名垣鲁文于1886年在《东京绘入新闻》上连载的“翻案”小说,与《何樱彼樱钱世中》的写作仅相差一年。1886年8月,明治朝野组建了“演剧改良会”,主张(从剧场建筑样式到剧本)一切西洋化,按欧洲的标准改造歌舞伎。当时,假名垣鲁文听闻《哈姆雷特》在改良会的上演名单内,就拿出旧稿重新撰写。(14)本間久雄.『ハムレット』移入考: 『葉武列土倭錦絵』のこと.實踐文學,1966,29,pp.4—12.旧稿即鲁文在1878年9月的《平假名绘入新闻》上连载三期的小说《叶舞列土》(15)“叶舞列土”即和式汉字发音的“哈姆雷特”。,当时评价惨淡。鲁文认为读者无法接受未经调味的西洋文学。因此,在1886年的新稿中,鲁文表明了他对戏剧改良的态度——兼顾知识分子的欧化愿望和保守的大众文化趣向(16)吉田弥生.『葉武列土倭錦絵』をめぐって.文京学院大学外国語学部文京学院短期大学紀要,2006,5,p.269.,为歌舞伎舞台定制了《哈姆雷特》。
鲁文的和洋折衷主张决定了其写作倾向。他按照歌舞伎的脚色和衣箱(如“御家物”“前发”“赤姬”)来设计人物,还将原文戏中戏的段落调整为叶丛丸(哈姆雷特)的“物狂”(17)兴奋状态的歌舞演绎,在日本古典戏曲中常作为高潮戏。独舞。此外,叶丛丸向叔父复仇的动机被改为替父报仇的忠孝之道,叶丛丸以切腹的形式自戕是为偿还杀人的罪恶。哈姆雷特的四段独白因不符合歌舞伎的表达习惯被一概删去——人类心灵的浑浊状态难以在歌舞伎舞台呈现。哈姆雷特在基督教环境中禁忌的、出格的自杀,在鲁文笔下被改写为符合儒教的伦理要求和武士道精神的死亡崇拜,可见其强调保守价值和歌舞伎主体性,边缘化莎士比亚。
明治时期这部作品没有被提倡全面欧化的演剧改良会采用。一百年后,莎剧的歌舞伎化再受关注。假名垣鲁文传统文学教养深厚,善写河竹默阿弥式的七五调台词,对“谣曲”“狂言”“今样”也轻车驾熟。(18)山本いずみ.それぞれのハムレット.名古屋工業大学紀要,2004,55,p.67.他为歌舞伎量身定制的《叶舞列土倭锦绘》,在古典写作遭受断裂的20世纪末成了演出歌舞伎版《哈姆雷特》难得的底本。
3. 折衷主义的失效
《叶舞列土倭锦绘》的首演于1991年3月6日在东京环球剧院举行。织田弘二担任脚本改编和导演,河竹登志夫担任顾问,市川染五郎担任主演。阵容豪华,评价却多有质疑。
在鲁文的文本基础上,主创团队做了内容加工,如通过坪内逍遥的译本补充了哈姆雷特标志性的独白片段;市川染五郎兼扮了叶丛丸(哈姆雷特)和实刈屋姫(奥菲利亚)两人,希望以此体现他们悲剧命运的相似性——都因父辈的影响而迷失、牺牲自我。主演同时扮演“若众”(年轻男性)和“女形”(19)由于日本历史上禁止女演员演出歌舞伎,江户后期以来的歌舞伎由“全男班”出演。因此,男性演出的女性角色被称为“女形”。是歌舞伎中常见的戏点,然而这也是这部作品为人诟病的一点。学者芦津香认为,市川染五郎同时兼扮男女主角导致双方无法展开对话,失去了应有的紧张感。(20)芦津かおり.日本の『ハムレット』受容―その多様な変貌.文彩,2007,3,〈小特集: シェイクスピア万華鏡〉特別寄稿,p.14.此外,门野泉还提出,这部作品的关键问题在于过分强调歌舞伎丰富华美的形式,如兼扮男女主角的歌舞伎明星、《忠臣藏》风格的壮丽开场、叶丛丸的“物狂”独舞、歌舞伎大道具“浅葱幕”等等,轻视了剧本的“戏剧性”。(21)門野泉.歌舞伎とシェクスピア.英米文化,1994,24,p.55.门野泉所称的“戏剧性”(ドラマ性)泛指戏剧情节的严谨性,例如,叶丛丸身穿鲜艳的华服登场,如果考虑戏剧情境,他应当穿丧服。同时,叶丛丸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跳出了“若众”的脚色范畴而显得乖离。芦津香也提到,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指出“这不是文化的融合而是文化的决裂”(22)芦津かおり.日本の『ハムレット』受容―その多様な変貌.文彩,2007,3,〈小特集: シェイクスピア万華鏡〉特別寄稿,p.14.。门野泉的批评中对“戏剧性”的重视体现了长期以来西式新剧对日本人戏剧观念的改造。现实主义戏剧剧场强调的可然律、必然律、情节的整一性成了观众理解莎士比亚的出发点,但对于歌舞伎美学程式的强调更加放大了它与现实主义逻辑的差异,两者各行其是,无法榫接。
实际上,《何樱彼樱钱世中》与《叶舞列土倭锦绘》面临的困难是相似的——莎剧文本的意识形态与歌舞伎形式所附着的意识形态难以共处。它们处理的手段也是相似的——“翻案”与“折衷”。然而前者大受欢迎,后者多遭质疑,因为莎士比亚在日本社会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经过百年现代化,莎士比亚从一个外乡人成为现代日本的“同时代人”。莎剧的人文主义与浪漫主义,以及古典主义戏剧范式已经被写入日本现代意识的框架。在20世纪末,跨文化的折衷主义失去了合法性。折衷主义期待取各方的中点,以笼络多种立场。如果各方处在同一平面,那有可能求取中点;如果各方处在不同平面,那取中点本身就是伪命题。当年《何樱彼樱钱世中》可以隐藏折衷主义的问题,因为莎士比亚的精神还没有进入日本的社会意识,它看似是折衷,其实是将他者纳入自我话语体系,将多维的问题平面化。20世纪末,和洋折衷的矛盾性暴露在高度西化的日本社会中。
4. 进入文明中心的愿望
尽管《叶舞列土倭锦绘》在日本国内的首演受到评论家质疑,然而1991年9月,该剧还参加了英国的“日本戏剧节”(Japan Festival),在伦敦、都柏林、纽卡斯尔等地巡演,可见团队期待获得国际观众的认可。这个规划的野心不仅在于“融合”东西文化,还在于将歌舞伎与莎士比亚一起向国际社会捆绑销售。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文化领域的心态转变——从以精确“再现他者”为原则的新剧到“表达自我”的民族戏剧新尝试,莎士比亚从一个偶像变成一套语汇。
由于《叶舞列土倭锦绘》的影响,1995年日本莎士比亚协会、大阪大学、日本演剧协会、歌舞伎协会共同举办了一场以“莎士比亚和歌舞伎”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日本国内与海外的研究者们尤其关注歌舞伎中的“女形”与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男扮女装的对比研究。会议的重点之一就是从伊丽莎白时期的莎剧与歌舞伎的比较中论述二者相结合的意义。(23)平辰彦.日本シェイクスピア協会·国際会議『シェイクスピアと歌舞伎』報告.比較文学,1996,38,p.190.换言之,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成为吸引国际关注度和认可度的一个方法。
由此看来,1990年代对莎剧歌舞伎化的再度关注反映了日本人进入世界文明中心的要求。用民族戏剧歌舞伎来演绎《哈姆雷特》表明日本人有与西方人同样的莎士比亚阐释权,日本的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平等的、同样优秀的。同时,充满东洋美学风格的歌舞伎也在提醒他们的“不同”——既足够西方,又足够日本。这意味着接受、适应西方搭建的文化秩序的同时,也要干扰他们的权威,从文化差异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强调多元性与独立性。尽管当代的莎剧歌舞伎在这层意义上很有价值,但该尝试对文化差异的处理仍然缺乏经验和创见。折衷的立场也是自设困境——“足够西方,又足够日本”的框架是以“和洋”二元对立为前提的,而在保持“和洋”各自真实性,即维持二元结构的同时无法追求折衷,因为一方或双方的任何形变、折损都是对二元前提的破坏。
三、 既非西方,又非日本: 《NINAGAWA十二夜》
在莎剧歌舞伎中,最成功的作品就是《NINAGAWA十二夜》,它在日本国内和西方世界都广受瞩目。导演蜷川幸雄因善于制作“日本风格的莎剧”闻名东西,收获了“世界的蜷川”等荣誉。他善于使用东方元素为诠释莎剧找到新的入口。尽管蜷川幸雄从小就是歌舞伎观众,但他没有受过行业内的训练,游离在歌舞伎系统之外的身份使他的创作格外灵活。《NINAGAWA十二夜》是他唯一的跨界导演尝试。
1. 蜷川的莎剧品牌
蜷川的戏剧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他在高中毕业后作为研习生演员进入了“青俳剧团”。后来,蜷川离开了“青俳”,与十个同伴创立了“现代人剧团”。在新左翼运动(24)当时,由于1960年和1970年《美日安保条约》的续签,日本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运动,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新宿正是政治热点地带。剧场外的游行队伍和机动队不断冲突。“现代人剧团”的成员们一边参加游行,一边演戏,排练场里总是放着几顶安全帽。正是在这场左翼运动中诞生了日本的小剧场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铃木忠志、唐十郎、蜷川幸雄、土方巽等。的热潮中,蜷川幸雄以导演作品《真情满溢的轻薄》(25)清水邦夫撰写的《真情满溢的轻薄》于1969年在新宿文化艺术中心首演。蜷川幸雄甚至还让假扮的机动队冲入正在观看演出的观众席,一些观众误以为真,发生了乱斗。高调出道。在学生运动潮后的1973年,东宝株式会社的经纪人中根公夫找到蜷川幸雄,请他执导商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蜷川第一次接触市川染五郎这样有身段程式傍身的歌舞伎演员。同时,商业戏剧也帮助他实现视觉性的舞台装置。之后,他在东宝继续导演了《李尔王》(1975)、《俄狄浦斯王》(1976)、《王女美狄亚》(1978)、《哈姆雷特》(1978)等充满个人风格的莎剧作品。
蜷川幸雄早期最负盛名的《NINAGAWA麦克白》(1980)就显示出蜷川氏莎剧成熟的美学格调。整个剧场设置在一个巨大的佛龛里。两位老婆婆缓慢地打开佛龛,舞台上出现歌舞伎“女形”风格的三个魔女,以及绚烂的樱花森林。在结尾处麦克白被敌人包围的场面,蜷川把学生运动时期机动队在东京大学对“全共斗”(26)“全学共斗会议”的简称。1968年至1969年间,日本各大学学生自然聚集而成的左派学运组织。学生放出的催泪弹录音当作音效播放。然而在当时,别出心裁的蜷川还没有在日本声名远扬,直到198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和英国爱丁堡戏剧节的公演在国际上带来了“蜷川传说”(27)秋島百合子.蜷川幸雄とシェイクスピア.角川書店,2015,p.16.。
1983年,蜷川幸雄第一次携作品《王女美狄亚》赴欧洲公演,开启了他的国际路线。《王女美狄亚》和《NINAGAWA麦克白》在西方声名大噪——海外走红对蜷川幸雄以日本元素排演莎剧似乎是一种文化授权。2016年蜷川在排练《量罪记》时去世,至此他一共排演了32部莎剧。蜷川系列莎剧已被打造成了独特的文化品牌。
2. 《NINAGAWA十二夜》与身份的彷徨
《NINAGAWA十二夜》于2005年7月7日在东京歌舞伎座初演,获得了“读卖演剧大赏”等一系列戏剧大奖。2009年3月24至28日,该剧又赴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公演,受到热烈欢迎。此前,歌舞伎在英国被分类为“舞蹈”,这是歌舞伎第一次以“戏剧”的身份在英国上演。
该剧采用了小岛田雄志翻译的《第十二夜》,由今井丰茂担任歌舞伎脚本改编。尽管故事架空至历史上的日本,却几乎完整地遵照了莎剧的人物形象、情节线索——双胞胎兄妹遭遇海难而分离,妹妹琵琶姬(薇俄拉)为求自保化身男装改名“狮子丸”(西塞里奥),被大筱左大臣(奥西诺)收为侍童。女扮男装的狮子丸对左大臣心怀爱慕。而左大臣对织笛姬(奥丽维亚)单相思已久,派狮子丸向织笛姬送情书。织笛姬错把狮子丸当作男儿身,对她芳心暗许。最终兄妹二人重逢,织笛姬与哥哥,妹妹与左大臣有情人终成眷属,舞台在大团圆中落幕。(28)在日语中“琵琶姬”的发音“Biwa”和原名微奥拉(Viola)很相近,“狮子丸”的发音“Shishimaru”与西塞里奥(Cesario)相近,“织笛姬”的发音“Oribue”与奥丽维亚(Olivia)相近……每个人物都与原文一一对应。另外,戏弄暗恋织笛姬的执事的喜剧线索也完整保留。
这部作品对文本的选择和处理是审慎且巧妙的。《第十二夜》这一富有嘉年华气息的喜剧本就荒诞、俚俗,情节设计概念化而无视常规,它与歌舞伎的嫁接在俗文化的方向上找到了榫卯。由于情节不具有严肃性,人物形象的程式化、脸谱化反而有助于科诨效果;前两则案例中人物形象在“翻案”中道德化的问题也得到了规避。此外,原文在人物和情节上充满对称的设计,蜷川幸雄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为形式的探索打开道路。最值得称道的是巧用《第十二夜》的性别题材与歌舞伎的性别扮演生发新的主题——身体的多重构造与暧昧性。这是很有当代眼光的着笔。
因剧本涉及琵琶姬女扮男装的身份转换,再加上双胞胎兄妹外貌酷似,兼扮哥哥、妹妹、妹妹乔装的狮子丸三者的菊之助制造了性别扮演的三次转换问题。演员菊之助在海难一场先以哥哥身份亮相船头,浪涛中回到船舱,快速换妆(29)歌舞伎术语为“早替”,是一种常见的歌舞伎换装技巧。为妹妹,以“女形”姿态再次登台。这时只涉及男性演员分饰同性和跨性别性角色。当琵琶姬以狮子丸的身份登场时,“一个男性身体所扮演的女性角色假扮男性”这样的双重转换问题出现了。但两次反转并不抵消彼此,菊之助让观众看见三种身份的叠加——女扮男装的狮子丸在伪装男性的同时,又时不时暴露琵琶姬的女性特征,比如尖细的声音、小碎步等。凭借歌舞伎程式,性别扮演有足够的表现力和区分度。几种身份之间的彷徨、摇摆、犹疑成了全剧的戏眼。而舞台上身份政治的展演不仅有关性别,还涉及东西方文化。
3. 虚拟世界与“第三空间”
在蜷川对开场的处理中,东西文化的“杂交”(Hybridity)显而易见——在日式风情的樱花雨里,唱诗班的小男孩演唱着西洋音乐;他们身着日本传统服饰,却又戴着伊丽莎白头圈;伴奏交叠着钢琴和日本民乐……尽管这是一场歌舞伎演出,蜷川却从大幕开启的一刻就提醒观众,他所展示的并不是一个纯然“日本的”空间。显然,蜷川所制造的虚拟世界不属于任何单一的文化范式,里面既有古典又有当代,既有西方又有东方。
剧场空间的设计也表达了文化之间的渗透、杂交。舞台背景全程镜面的设计对身份的双重性这一主题进行了绝妙的视觉化处理,每一个形象都背对另一个自己。蜷川在采访中说,他对镜面的运用来自对歌舞伎美学和西方写实主义剧场的反思: 歌舞伎的舞台是横向且狭长的,包括大道具中的推拉门、廊道等,日本古典审美习惯于横向展开一个平面的世界,而他这一代人所学习的现代戏剧讲究来自西方的远近透视法。于是,蜷川在横长的歌舞伎舞台上布置了巨大的镜子,从而完成增加景深和透视的效果。镜子中的景物会随观众的视角千变万化。这既不是传统的歌舞伎舞台,也不是写实主义的西式剧场,更不是东西之间一个勉强的“中点”,而是打破“东方”和“西方”的固定范式之后搭建的一个新的虚拟空间。这个空间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充满流动性、不确定性。它指向了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中的“第三空间”(Third Place)(30)“杂交”(Hybridity)和“第三空间”(Third Place)都是霍米·巴巴提出的后殖民概念。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虽然自称反对本质主义,但难免又陷入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立立场与反抗思维。霍米·巴巴则用“杂交”来描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以超越泾渭分明的二分法。“第三空间”是与“杂交”相配合的概念。法侬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有一个著名结论——被殖民的黑人在心理上只有两种选择: 成为白人,或者消失;而霍米·巴巴则认为,还有一个暧昧的、相互渗透的“第三空间”,这是真正需要探索的领域。、一个走出二元对立的新空间。
虽然日本并不存在被殖民的历史,但在与西方的动态关系上,后殖民理论却很有参考价值。欧化之后的日本游离在西方和自己的过去之间,其暧昧的文化形象使人不安。在被“洋风”大型改造后的日本社会,人们翻找确认:“这是日本固有的东西!”上文中蜷川对日本审美意识的分析也带有这种倾向。如果稍作谱系学考察,“横长”的审美习惯或许并非日本固有,也可能是受到汉文化书写系统的影响。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现代世界中,以地理分界为原则的文化分界往往导向本质主义思维,将这片土地上曾出现的文化现象当作固有的民族资产(比如上文的《叶舞列土倭锦绘》就格外在意歌舞伎在美学领域的“炫富”)。相比之下,蜷川幸雄没有对文化的占有与自矜,而是构造一个“既非西方,又非日本”的“第三空间”。
4. 文化无边界
实际上,“既非西方,又非日本”是蜷川系列莎剧一直以来的风格。蜷川与编舞花柳锦之辅一路合作了《王女美狄亚》《NINAGAWA麦克白》《暴风雨》等作品,锦之辅的肢体设计使蜷川如有神助。蜷川自述:“我要求的是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不纯然强调样式也绝非对写实的表演,锦之辅先生一定煞费苦心。”(31)[日] 蜷川幸雄: 《千刃千眼》,詹慕如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6页。再如,《NINAGAWA麦克白》虽然将剧作背景迁移到了日本安土桃山时代,但人名却全部保留英文翻译,仿佛刻意提醒观众切勿把它看成一个日本故事。在《克利奥兰纳斯》中,蜷川声明他选择了一个虚拟的城市,并从泛亚洲文化中借用了各种元素……蜷川有意识地破坏任何文化单元的纯正性(authenticity),他拒绝依傍既有的文化遗产标榜身价,而是在“第三空间”的构筑中发现新的价值。
1991年《叶舞列土倭锦绘》的演出已向我们揭示,折衷的立场无法在当今处理跨文化问题。笔者认为,和洋折衷是基于二分法和本质主义思维的一种贪欲: 一方面它默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本质,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其中任何一方,期待最大限度地占有这两者(的市场价值),实用至上则“一半西方,一半日本”,胃口更大则“既要西方,又要日本”,代价是一方或者双方的形变,这必然破坏观众对纯正性的期待。蜷川幸雄的“第三空间”与和洋折衷的区别在于,他不要求对经典文化进行资产化,文化的纯正性并不向他提供价值。蜷川主动迎接暧昧、杂交和混沌——既然纯正性的价值被取消了,那就不存在对立的、不可兼容的双方。换言之,折衷主义将日本和西方文化当成两个边界清晰的图形,试图寻求它们的并集;而在“第三空间”,文化根本失去了边界和形状。
当然,蜷川案例的成功因素有很多,包括喜剧的包容性、蜷川处理莎剧的名声使问题的复杂性得到简化等。但不可否认,跨文化处理仍然是《NINAGAWA十二夜》的核心任务。而蜷川幸雄对跨文化问题举重若轻的态度或多或少提示了一条开放的路径。
结 语
上文分别讨论了1885年的《何樱彼樱钱世中》、1991年的《叶舞列土倭锦绘》和2005年的《NINAGAWA十二夜》三部莎剧歌舞伎作品。这三个跨文化戏剧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思潮带来的影响。《何樱彼樱钱世中》诞生于东西方戏剧的接触期,它以猎奇的心态纳入他者的素材,但外来文本遭到本地话语权力的过滤与规训。《叶舞列土倭锦绘》与《NINAGAWA十二夜》同处在对民族戏剧再发现和再定位的时期,日本戏剧遭遇西方剧场征服百年,通过跨文化尝试重新锚定自我与他者,以及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
从创作思路上看,这三部作品反映了三种跨文化心态——“一半西方,一半日本”“足够西方,又足够日本”“既非西方,又非日本”。通常来讲,西方是他者,日本是自我;此处的自我和他者,是一对地理上的概念。然而以地理的分界理解文化的边界很容易陷入本质主义的思维——将自我看作某一区域历史上文化现象的集合,并认为其存在固有的精神、美学等,以作为自我身份的锚点。由于时间维度的存在,“自我”在历史上长期变动,与外界的交往使“自我”的疆界不断受到挑战、更新。因此,自我与他者不应仅仅被看作二维的地理概念,时间这第三维度也应被纳入框架。西方固然是地理上的他者,同时,在某些方面“传统的”“民族的”日本也成了时间上的他者,与这两者的距离共同对当代日本进行定位。由此看来,进行跨文化剧场创作的时候,如果能把传统从自我中剥离出来,进行对象化,这也许能使我们将沉甸甸的文化遗产从背上卸下。蜷川幸雄对东西方同时他者化的做法向我们提示了一条并置东西方文化的途径,可能不是唯一的路,却是一条轻盈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