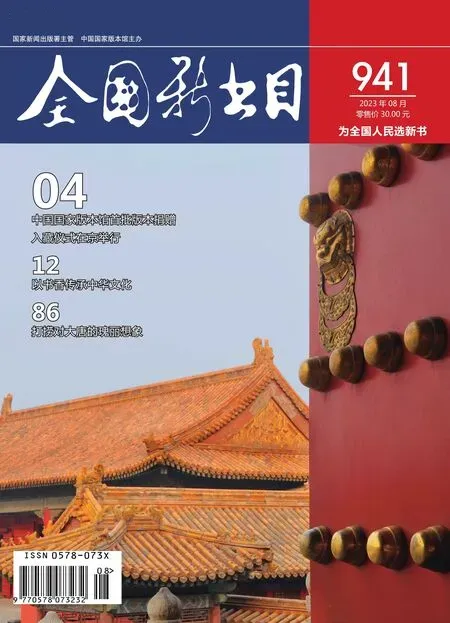中国绘画在艺术上的彻底觉醒
陈传席
美术史学家,美术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精文学,通古文,工诗文,善书画,曾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多年,现治中国艺术史和人文史。已出版学术著作70 多部。

《六朝画论研究》(增修版)陈传席 著/岭南美术出版社2023.5/148.00元
顾恺之的画论强调以“传神”为中心,提出了“天趣”“骨趣”等著名论点,以及“骨法、用笔、用色,临见妙裁,置陈布势”和临摹等具体的绘画方法。在传神的刻画上,他又特别强调眼睛的刻画,以及体态动势、人物关系、环境衬托,乃至于用笔用墨的轻重、构图的效果等。他还提出了“迁想妙得”。“迁”字是变动不居、上升之意,古时称官职提升为“迁”,又《周易·系辞》有云:“变动以利言,凶吉以情迁。”“妙”字就是《老子》书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妙”,顾恺之所谓绘画的奥妙就是“传神”。“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即无关于“传神”处,因“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得”字在老子、韩非子的书中常见。顾恺之评《伏羲神农》:“居然有‘得一’之想。”“得一”就是《老子》第三十九章中“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的“得一”,这里顾恺之是赞美这幅作品的作者笔下的“伏、神”两位古代“侯王”有“天下贞”的气魄、神态。“之想”乃画作者之想,也即“迁想”的“想”。“迁想妙得”指出画家要在努力观察对象的基础上,根据“传神”的原则,反复思索,包括对对象的分析理解,必得其传神之趣乃休。因此,谢赫说他“深体精微”“笔无妄下”。如果这样的解释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顾恺之已经认识到画人、山水、狗马都可以“传神”,只有“台榭”难以“传神”(这一错误之论已经为后人所纠正)。
以上这些都说明顾恺之对绘画已有了相当的研究,这在他之前是未有的。他的理论标志着中国画在艺术理论上的彻底觉醒,这一意义非同小可。《东方朔画赞》中有“嘘吸冲和,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世登仙”几句话,倘用以说明顾恺之的画论影响,是很合适的。
对此我们可以做比较,魏晋以前的绘画我们不打算介绍得过远,张彦远说:“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始得而记。”其实秦汉绘画不论是各种各样的画像石(砖),还是出土的墓室壁画,或者作为“升天图”的彩绘帛画,大都是简单的、外在的、形式化的。秦汉之前的战国绘画已比以前大为进步,但所画的人物仍是一个简单的轮廓,符号化的现象依然存在,甚至用五根短线代表五根手指,作人面多侧面。西汉时个别人才认识到“君形”在绘画中的作用,但不是在专门论画的著作中论述的,而且是偶尔一提,在绘画界几乎未有什么反响。今日从石刻上看到的东汉绘画也大都是靠动势来表现的。
而且,魏晋以前的绘画主要是由画的故事来体现其意义价值,其表现的是神灵、明君、贤相、忠臣义士、孝子贤孙,以达到“成教化,助人伦”“恶以戒世,善以示后”的目的,如出游图、牛耕图等也是为死者服务的,这是求意义价值于绘画自身之外。汉画像石乃是靠表现忠臣孝子之类的故事而存在,是牌坊的一部分,它的主要价值不在本身的艺术性。尽管此后的绘画作品有一些也属于依附性质,但情况并不一样,因为一旦发现了绘画的艺术本质,明确了绘画自身的艺术任务,绘画的发展便有了自律性,虽是依附品,艺术表现上却有一定的独立性,会按照艺术的规律去创作,以自身的艺术去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和靠故事内容去决定其意义价值不同,魏晋前后的绘画就有这种“蝉蜕龙变”的差异(当然不是全部)。
艺术的规律是否被揭示出来,对艺术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愈是早期的艺术愈是有其一致性,愈是后期的艺术愈是有其多样性。
魏晋之前还很少见到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绘画,绘画多属依附品,到了吴曹不兴画屏风、晋司马绍画《洛神赋图》,绘画作品才真正有了独立审美意义。王充说:“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论衡·别通》)艺术品的使用价值首先在于欣赏(艺术的社会功能必须在审美中得以完成),王充认为绘画无用,是不懂得绘画存在的基本价值是画的艺术,但当时的绘画也确实未有太高的艺术。所以,“形容具存,人不激劝”。
顾恺之总结了前人绘画的经验,加上他自己深入的研究,指出人物画艺术的关键在于“传神”,而外形、动势、服饰、用笔等皆是为了达到或有助于“传神”。这就突破了原来的绘画只是描写外形(尽管形中有时也包含一定的神),或是描写象征符号形式的外形,而发现了艺术描写的本质。
顾恺之这一发现代表了绘画艺术的彻底觉醒。
对人物画来说,第一形体乃是人的外形,第二形体方是存在于人体中的神。而对于一个人来说,神是更重要的,躯体的本质是相同的,精神的本质却绝不相同。艺术上的神是可以通过第一形体流露出来的,不仅有第一形体不同且第二形体不同,也有第一形体相同而第二形体不同,文学上的张飞、李逵、牛皋第一形体相差无几,而第二形体绝不相同。对此,沈宗骞讲过一段有意思的话:“今有一人焉,前肥而后瘦,前白而后苍,前无须髭而后多髯,乍见之或不能相识,即而视之,必恍然曰:此即某某也,盖形虽变,而神不变也。”(《芥舟学画编》)宋陈郁说得也好:“写屈原之形而肖矣,傥不能笔其行吟泽畔,怀忠不平之意,亦非灵均,写少陵之貌而是矣……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否则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贵贱忠恶,奚自而别,形虽似何益?”

洛神赋图卷.东晋.顾恺之作.宋摹本.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诚然,人的神是复杂的,略早于顾恺之时就有人说:“夫貌望丰伟者不必贤,而形器尪瘁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抱朴子·清鉴卷二十一》)但反映在艺术上却有一定的典型。我们常说某人的作品概念化,人物刻画缺乏个性,内心世界未表达出来,就是说他只刻画了第一形体,这是不能称为艺术的;反之,有个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被再现出来了,就是说他注意到了第二形体,注意到了艺术的本质。艺术家如果不能从人或物中发现第二形体并把它表现出来,他的作品必是失败的。
但顾恺之之前的画人尚不能在理论上明白这些,他的“传神论”使艺术家明白艺术只能成立于第二形体之中。“以形写神”其实就是以第一形体写第二形体,而第二形体才是实质,才是目的,第一形体只是实现第二形体的手段,得“鱼”是可以忘“筌”的。陈去非《墨梅》诗云:“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九方皋把马的牝牡骊黄都看错了,却发现了马的本质,犹如X 光略去人的皮毛骨肉,一眼看出内脏的质地是有病的还是健康的。
顾恺之的“传神论”代表了魏晋时代绘画的大飞跃,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指明绘画艺术的本质是传神,而不是写形,为画家进行艺术创作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让画家有了正确的努力方向。魏晋时,中国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人物画不再是由画的故事来体现其意义价值,画的意义价值不只在于画自身,而是通过形以表现被画的对象之神来决定其意义价值,画的基本价值在于本身的艺术性。这一基本价值得以保证之后,才能考虑其他的价值,否则便不是艺术品。
中国绘画在艺术上彻底觉醒之后,才真正地有了美的自觉而成为美的对象,顾恺之之功不可谓不大。从此,中国画自觉地摆脱了附庸地位,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日益起着重要作用。千百年来,顾恺之的绘画理论在中国画的创作和欣赏上起着指导作用,“传神”遂成为中国人物画不可动摇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