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漫漫回音
谈炯程
在我们的时代,弗兰茨·卡夫卡其人其书,就如同死海古卷一般,被从咸水湖底的淤泥中剥出:即使只是残篇断篇,也足可为我们的精神重新划界。我们如同测量员一般潜入卡夫卡词语的地层,挖出一些零星的意象,它们连缀在一起,是《地心游记》里展现在岩层中的进化论图谱:变成虫子的推销员、一匹同时是律师的马、阿拉伯人、会说话的猿猴、耗子民族、地洞里不安的某种生物……阅读卡夫卡便意味着打开,打开身体,打开边界,让他坚硬、笨拙的句子通过,磕碰你过于矮小的精神之门。你的意识是一道海关,总会有意无意地嗅闻这些文字里夹带的违禁品。
反思冷战的学者,诸如布莱恩·K. 古德曼在其著作《不墨守成规者》(The Nonconformists)中所认为的,“Kafkaesque”(卡夫卡式的)一词,常常纠缠在诸多意识形态话语之间,被政治化地滥用。卡夫卡外在于极权主义,他早在战间期的一九二四年就去世了,他原所属的国家奥匈帝国,在战争中如盘古般死亡、分解、融入大地,孵化出新的民族国家。随后这些小国,又被逐一蚕食。这一切,使得在怀着历史的后设之见的我们看来,卡夫卡的语言拥有了穿透党派分歧的力量,既可以是批判性的,也可以是启示录式的。而他是否预知到二十世纪的灾异并不重要,你完全能够看到一个巴纳斯派的卡夫卡、存在主义的卡夫卡、精神分析的卡夫卡、超现实主义的卡夫卡、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卡夫卡,以及作为“单身机器”的卡夫卡……而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詹姆斯·伯纳姆就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发表了一篇题为《卡夫卡观察》(“Observations on Kafka”)的文章,论及从卡夫卡作品生长出的理论之树,已将其辖域化,纳入文化工业的内部并加以反刍。八十年过去,它们愈发枝繁叶茂,如今,简直不可以再用树来比喻它们了。卡夫卡如同一片锚地,同时容留着洞见与呓语。这些自生产的理论是榛蘑,从一粒孢子开始,兀自生长出一个世界,菌丝在地下彼此牵连,分享本已匮乏的营养。于是,“肿胀开始了。先锋派像一个警告般出现。小杂志发表文章与评论。一个派系逐渐形成。教授们到各处反复讲演,连半专业的出版商也决定冒险一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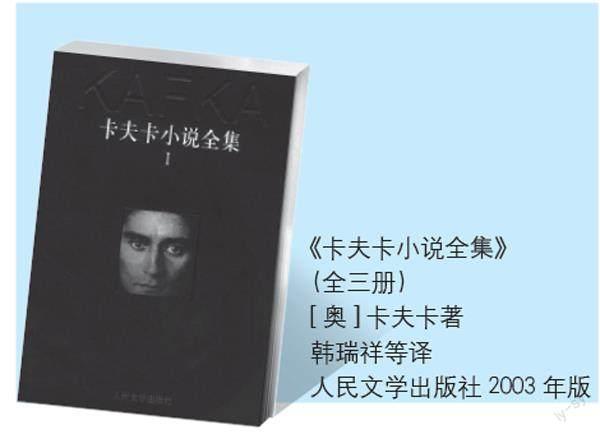
一种传记式的研究方法,如若作用于卡夫卡,就等于是把一整块表皮细胞放在显微镜下,使之显出地层般的结构,但如此,却难以窥见细胞中早已流失殆尽的血,正是这血使表皮鲜活,足以抵挡外部环境的污染。但这血又太过微妙,涌流于一丛丛、一簇簇毛细血管中,赋予皮肤颜色。我们已经有了无尽的细节,即使卡夫卡自己从事卡夫卡学研究,也很难再给我们提供一些全新的、有启发性的掌故:卡夫卡亲友的生平因为他而有了被考证的价值,这些资料皆已被穷尽。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卡夫卡的私生活,他以文字在其原欲上织成的摩耶之幕亦被无情揭开。利用卡夫卡慷慨馈赠给我们的日记、书信,即使已能逐日复现卡夫卡的行踪,也很难攒出一条完整的叙事之流,使血液回到这枯死的材料之中。他的生活,就如同这夹在玻片里的细胞一样静止,因为传记中的时间,往往要打满历史的绳结才能被读解。但卡夫卡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的日记中却分明写道:“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上游泳课。”这条日记,常被看作是这位夜班作家不关心政治的明证,其实未必。战争在此刻,并没有构成一个精神性的事件,卡夫卡与挚友马克斯·布罗德身处的布拉格文学圈子,还能够尽可能地漠视战争。布罗德写道:
对我们来说,战争似乎可与其他一些已经慢慢淡忘的人类空想相提并论,比如永动机、万能药、炼金术士的炼金配方、不老仙丹,等等。打仗,顶多在文明世界的边缘,在落后的巴尔干地区,在殖民地还有可能。而在安居乐业、彻底文明化的民族中间,战争不过就是乌托邦式的瞎折腾……(《好斗的一生》,轉引自莱纳·施塔赫《卡夫卡传:关键岁月·1910-1915》)
现在,它只是像头狮子般趴在报纸头版,张开血盆大口。为什么不谈论纯粹的艺术,印象派、理查德·瓦格纳和若利斯·卡尔·于斯曼,而要关心从这片欧洲大陆的幽暗中苏醒的玛尔斯?故而,当莱纳·施塔赫在其著作《卡夫卡传》(Kafka)三部曲中,巨细靡遗地铺陈出历史事件时,他就像是为了衬出一只琉璃碗的剔透,便将整个房间刷成了蓝色一样,历史事件与卡夫卡的生平,有时仿佛两条平行展开的线。对于尚未被卷入无尽暴力之中的作家们来说,他们宁可透过赫拉克利特的格言“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来理解一个作为生成的、抽象化的战争,也不愿看到从凡尔登的泥泞中吮吸人脂而长出的草木。同样来自布拉格的诗人里尔克在战争结束后陷入精神危险,其写作长时间停滞。而他也曾在战事初起时写诗来歌颂战争。他们理解战争的方式,就像惠特曼理解美国内战的方式—一场治愈与救赎之战,威尔逊总统所承诺的“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

但一九一四年之于卡夫卡,无疑是一场滑向地洞的单向旅行:个人情感的地洞、写作的地洞、精神的地洞。正如在八月二日那则著名的日记中,破折号如同假肢上的铆钉,既划分开铁一般坚硬的历史和寓居于血肉中的生活,也把它们铰接在一起,让它们围绕一个隐秘的核心转动,让力在它们之间互相作用,彼此牵连。这破折号同时也是伤口上结出的一条痂,一个地洞行将坍塌的入口。
卡夫卡的地洞
这位幽居地洞的写者,进入了某种无根状态。因此,如何为卡夫卡编写一个词条,就成了疑难。似乎无论怎样编写,这个词条看起来,都会像是福楼拜《庸见词典》(1874)在二十世纪的续编。一般来说,只要胪列国籍、生卒年月、主要作品,就可以勾画出一个作家的大致成就。但那些热衷于把卡夫卡去政治化的理论家,在将其置于一条以居斯塔夫·福楼拜与尼古拉·果戈理为坐标的小说技术发展轴线时,也总强调,与福楼拜、果戈理相比,卡夫卡是一个没有,抑或丧失了“国籍”的人。但即使奥匈帝国已化作尘烟,新生的捷克也总能将这个生于布拉格长于布拉格的德语作家,引为自己文明的财富,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也的确成了这个新国家的公民。围绕着他,制造出无数塑像、博物馆与展览。但透过橱窗,看向这些被简洁如棺钉的导览辞缝在一起的日常用品、手稿和相片,却让人感到莫名怪异。灯光照向这些展品,这灯光,连同馆中的一切陈设、色彩、游客的呢喃,组成一张绵密的话语网络,它试图网住卡夫卡,给予他一个身份,把他反锁在一个新“国籍”里,却总不成功。
布拉格是多语言的城市,而卡夫卡也是多语言的言说者。除去从学校里领取的那过分端正的德语,他也能流畅使用捷克语口语。另外,在布拉格,也通行德语与捷克语的混合语以及“Mauscheldeutsch”(一种意第绪语化的德语),后者的表达方式,时常像补丁般缀在卡夫卡父亲的德语里。相较使用人口占比达百分之八十的捷克语,布拉格德语是一种次要语言,不断地被边缘化,趋向缄默,如同一滴水滞留在没有摩擦力的斜面上。在脱离其文化母体后,一个布拉格的德语使用者,必然要调适其句法,切削其词汇,以适应同捷克语使用者对话的需要。譬如,受捷克语影响,他们常用与捷克语动词“dati”(给予)对应的德语动词“geben”,替换“legen”(铺陈)、“setzen”(摆置)、“stellen”(放置)与“abnehmen”(移除)等一系列动词,原本朴质的“geben”,在此种语言的解域过程中被胀开,所有可能的转喻义纷纷滑入这个词,使其所指无限扩大。当这些所指,与它灰扑扑的能指相错时,某种微妙的张力就得以涌出由这破碎声音沉积而成的地壳。只有在一个纯德语的社交小圈层里,说德语的犹太人们才能寻回自己精心塑造的发声器官,但他们在布拉格社会处于半哑状态,于是,一些人就会在纸页上操练出一种高度书面化、绚丽、恢宏如雕花石柱的德语,他们耗费着那些连德国人看来都十分艰涩的词语,如一场夸富宴,也正如布罗茨基对来自加勒比小岛国圣卢西亚的大诗人德瑞克·沃尔科特的评价:“一些时候,维系文明的工作落到来自外省、来自边缘的人身上。与流行看法相反,边缘不是世界终结之处—而恰恰是世界铺开之处。这影响语言不亚于影响眼睛。”

卡夫卡的文体与他们不同,在其词语齿轮下,运转着一种德勒兹所说的“次要文学”(littérature mineure)。透过接纳布拉格德语相对正统德语的残缺,卡夫卡塑造了一种自为的匮乏,并且愈来愈深地将自己卷入缄默之中。对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地区》(Zone)一诗中描写埃菲尔铁塔的妙喻—“牧羊人,哦,埃菲尔铁塔,桥梁之牧群今晨咩咩低鸣”,卡夫卡态度十分淡漠。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述的《卡夫卡谈话录》(Gespr?che mit Kafka),辑下了卡夫卡对这句诗的回应。他承认这位法国诗人是一位诗艺上的能手,但“能手由于有骗子的熟练技巧而超越于事情之上”,与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剧作相比,“阿波利奈尔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一部文字电影,它是使读者产生輕松愉快的图像的骗子。作家不会如此,只有耍花招、逗乐的人才如此。作家总是力图把他的幻觉纳入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为此,他采用看似平淡、读者非常熟悉的语言”(《卡夫卡全集·第4卷》“随笔·谈话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若要勘测卡夫卡语言与思想母题的纵深,写于一九二三年初冬的小说残篇《地洞》(Der Bau)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在彼德-安德列·阿尔特看来,被编码进《地洞》的材料,不单源自西线堑壕战的幽闭体验,受伯恩哈德·克勒曼的战争小说启发,并为他自身的经历所加强—一九一五年时,他曾亲眼见证过这泥泞、狭窄如橘丝的地下迷宫。在《地洞》中,卡夫卡也调用了他潜意识层面的恐惧,随着叙事的推进,这恐惧拥有了梦呓般的强度。但战争只是为卡夫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象征,若将《地洞》视作一个被困堑壕的士兵的独白,无疑是极荒诞的。它有时让我们想起安部公房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小说《砂女》:同样有一个地洞,同样有被地洞同化的主体,外部世界对于这两部小说中的叙述者而言,的的确确是一种悬置,也如此真切地唤起陌异感。可以说,安部公房的“沙子”完成了卡夫卡。将《地洞》与《砂女》交叠在一起,像校正显微镜的两片透明的舌头般,调整它们的焦距,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清晰的母题。安部公房在《沙中的现实》一文写道:“当然,‘沙子指的是女人、男人,以及这个难以捉摸的现代世界中包括他们在内的一切。然而,即使我写完了小说,‘沙子仍然不肯放开我。”
沙子涌动、掩埋、吞噬、堆积,制造出噪声与图像,沙子的存在,表征着语言的存在,而语言一旦被抬上言说者的舌头,就会开始松动:它原本是沙丘,看似亘古长存,其实内里的每一粒沙子都在被风更新着,当它被投入使用,它就可以是一种威吓,一道阀门,语言不断变形,播撒差异。当《地洞》中的那个无名生物开始挖掘时,他就制造出语言。卡夫卡坚实的文本里包裹着一层密写的逻辑,它如沙子一般流向我们,反刍我们。卡夫卡全部的写作,都可以被视为挖掘地洞的一种尝试。那个生物建造完地洞后,说道:“尽管地洞有着这样多的天然强加于它的缺陷,但毕竟是我亲手所创;虽然事后才认识到这些缺点,却认识得这样精确,那就让它保留着吧”,这时,它来到地洞之处,就仿佛来到了一个语言之外的位置,它赤裸着,缄默让它的赤裸更加危险。它又告诉自己,“地洞是为我自己,而不是为访问者而挖筑的”,写者在语言中挖掘出自身的形象,这个形象拥有着他人难以穿透的密度,地洞是他的身体,就像所有统治者都在他们的陵墓里摹写着秩序,仅仅构造地洞的这一计划,就足够赋予他秩序:坚硬的洞壁、舒适的地下城郭。但在小说最后,一种永不撤销的噪声的出现中止了这秩序。我们可以将它视作声音中的沙砾,被从无垠的缄默中剥出来,像一道符咒,困住我们所有人:起初,是缄默使我们不得不开始言说,但最后,我们却被言说所困。
流放地中的机器
和他所有成功的作品一样,《地洞》的写作是很流畅的,据说卡夫卡伏案一整夜,怀着极强烈的热情,完成了这篇底稿。在这里,卡夫卡终于将他对装置的偏爱推向极致。《地洞》全文都是如连珠炮一样的独白,喋喋不休地围绕着一个装置,在噪声这一元素引入叙事后,这些句子近乎强迫症发作般盘旋于纸页,产生了一种制幻效果。如此谈论一件装置的叙事技术,并非只在《地洞》里出现。事实上,正是透过发明这一技术,卡夫卡的叙事,才得以挣脱狄更斯式现实主义文学越来越致密的束缚衣。吉尔·德勒兹敏锐地发觉了这点,不过,他用其独有的“机器”(machine)一词代替装置。他认为,在《司炉》(Der Heizer)中,机器就作为一种绝对值存在:“司炉的行当一直没有得到就事论事的描写(且不说船已经停驶),因为机器从来就不是单纯技术性的。恰恰相反,它的技术性仅仅来自它的社会性,因为它把男男女女都卷入了它的传动装置。”(引自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
如同德勒兹的绝大多数概念,“机器”一词的来源错综复杂,并且像细胞膜一样持续吸纳着阐释。不过,当他用“单身机器”(Machines Célibataire)来概括内嵌于卡夫卡文本的艺术装置时,他其实征引了米歇尔·布鲁热在其著作《单身机器》中的论述。在此,布鲁热将卡夫卡《在流放地》(In der Strafkolonie)中的行刑机器与马塞尔·杜尚晚期的现成品艺术《大玻璃》(Le Grand Verre)相比。卡夫卡的机器“由三个部分组成。随着岁月的流逝,每一个部分都获得了通俗的称呼。底下的部分叫作‘床,最高的部分叫‘绘图师,在中间能上下移动的悬着的部分叫‘耙子”(《卡夫卡全集·第1卷》)。营地的军官以一种病态的兴奋向旅客介绍这台由前任司令官发明的机器。在他的讲述中,司令官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因其缺席而变得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既是士兵、法官,又是设计师、化学家和制图师”。受刑人伏在铺满特制棉花的床上,由带有齿状尖针的耙子在他背上犁出他所违反的戒条,而“绘图师”在高处,如骨灰匣般容纳着司令官的律令,却也是这机器的构成要件中唯一以人,而非以物命名的部分,以至床与耙子都可以视作它的延伸。但实际上“绘图师”同样非人性,它接受命令,让命令穿过自身,滤去其中含糊不清的地方,把它拧干成一个简短的戒条。它用自己仅剩的自由意志克服了人性,透过一种清晰、绝对的语言,遮蔽法本身的不合法,以使下属机构可以仅凭设定好的程序运转,正如《卡夫卡谈话录》中记叙的卡夫卡对官僚系统的酷评:“今天,一个诚实的、按照公务条例得到丰厚薪水的公务员就是一个刽子手……他们把活生生的、富于变化的人变成了死的、毫无变化能力的档案号。”《在流放地》中的那架机器,无疑是一架法律机器,它太过直接地向我们暴露出现代生活的残酷,即使我们的肉体不处在耙子的正下方任其啮咬,我们的精神也会被文化工业的诸多预设与规约刻写。

而《大玻璃》其实是一个更细致的构建,几乎抵达现成品艺术所能表达的极致。这种极致不能透过技术,即雕镂艺术家所使用材料的方式来达成,它径直以命名的方式为自己啄出一片术野,现成品艺术唤起了语言的本质:不在于交流,而在于施加命令,為事物编码、分类、制作索引、划出轮廓、奠定其意义的疆域,因此,它们在语言及观念层面运转,正如法国艺评人克里斯蒂安·施密特所说,现成品,尤其是《大玻璃》,不能以“古典美学和‘视网膜的方式来理解,而是按照典型的杜尚式心理过程”。杜尚于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间在纽约创作了《大玻璃》。一九二六年,它在布鲁克林博物馆被短暂展出后,交由艺术赞助人凯瑟琳·德里尔保存。但在一九三六年,《大玻璃》因其脆弱的结构不幸损毁,杜尚保留了一九二三年原作的碎片,并将它们装进更厚实的玻璃板内。但在杜尚的设想中,《大玻璃》是一个无法用句号封缄的现在进行时的作品,围绕《大玻璃》产生的诸多笔记,理应被视为该作品的一部分。杜尚于一九三四年以《绿盒子》为名出版了这些笔记,但却没有将它们整理、驯化为印刷文本。他只是全盘复制了那些载有他笔记的纸片:连同其上修改、涂抹的痕迹也一并保留,以散页的形式储存在一只盒子内。《大玻璃》是杜尚的欲望机器,但首先,它也是杜尚的书写机器。当他最终停止《大玻璃》的创作时,他便以书写来赋予其最终的形式。在《大玻璃》中,书写与命名具有任意性。这台机器被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银河”(voie lactée)和“新娘”(mariée);下部是“九个苹果模具”(neuf moules m?lic),又称“单身汉”(célibataires)、“巧克力研磨机”(broyeuse de chocolat)和“眼科见证者”(témoins oculistes)。
正是这抽象的研磨结构,使布鲁热联想到卡夫卡。卡夫卡的机器里自上而下倾泻的权力意志,幻化成自下而上、周而复始的涌流,在这涌流中,布鲁热窥探到了暴力、死亡与欲望于现代神话里的三重变奏。隔开机器上下两部分的加固结构,如一枚分隔符。杜尚对作品的命名往往是双重的,这两个命名之间的关系,就像印第安人用绰号避讳自己的本名一样,一个名字自另一个名字涌出,覆盖并加固它。这时,分隔符的用法,就既分开两者,又将之融合。《大玻璃》被设计为一台机器,这意味着,作品中的各个部件应该透过一种流动被连接在一起,而非孤立地被堆积在玻璃背景内。作为单独的作品,《九个苹果模型》创作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但当它被纳入《大玻璃》时,它又成了“célibataires”,不同于英语中的“bachelor”和德语里的“Junggeselle”,这个法语词具备一种多义性,既可指未婚的男性,又可指贞洁、禁欲的男性。它是《大玻璃》的核心组件,借由它,《大玻璃》被定义成一架纯粹的欲望机器,抑或一架禁欲机器。这当然是一个悖论,压抑欲望的尝试反而生产出喋喋不休的欲望话语。一股气流被运送进这些“单身汉”的圆锥形身体,在他们细小如书脊锁线的玻璃血管内冻结,切成亮片,然后坠入“眼科见证者”的区域,从那里,由气流凝成的亮片向上输送到新娘板块。新娘是一朵云,高悬于顶点,她按捺涌流的同时,也使它冷却。这股涌流使《大玻璃》拥有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叙事性,但发出与接受涌流的主体,都被去人性化了。卡夫卡的叙事也正是如此,它在一个密封的玻璃结构中循环:《在流放地》赋予这种叙事方法一个坚实的核心,但在《审判》中,无处不在,却隐形着,才是这架机器真正的形态。

作为精神事件的卡夫卡
面对卡夫卡的文本时,常有一种想以最传统的传记批评切入它们的愿望。纵使再服膺细读法,也不得不承认卡夫卡的存在击碎了细读法所预设的文本神话,即文学文本是孤立、纯粹、完满的,超脱于历史、社会与生活,每一粒词、每一个句子,都被作者牢牢把握着,彼此扣合。卡夫卡的作品破碎、未完成,有时甚至会失控,虽然这些问题不至于损害他文本的质感,他已根据设计完备的草图建造出这词语之屋,只是未及拆去脚手架。而当埃利亚斯·卡内蒂发现卡夫卡时,这位犹太作家已移居伦敦多年。一九六八年,卡内蒂撰写了《另一种审判》(“Prozesse, ?ber Franz Kafka”)这篇重要文章。除此之外,他还留下了大量有关卡夫卡的笔记。“卡夫卡一生中曾经有三次订婚,以及三部未完成的小说。”运思《另一种审判》期间,他在笔记中写道:“《美国》和《审判》属于菲利斯时期的。这两部小说的放弃,它们的未完成,似乎与这两次订婚的失败有关。”我们当然也可以承认卡夫卡对法的关注,源自他法学博士的知识背景。但将他的生平与作品一一铺开,如做连线题一般勾画出对应关系,也只是在作品外围敲敲打打。卡内蒂以及受其影响的德勒兹,都强调书信与日记之于卡夫卡文学的重要性。他们研究的是作为现代性的精神事件的卡夫卡其人,而非仅仅是他的作品。但卡夫卡何以成为一个精神事件?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四日的日记中,卡夫卡写道:
“文学”这个字眼被用在指责当中,是语言上一种强烈的简化,乃至于它逐渐也带来思想上的简化(也许从一开始就含有这个意图),这种简化使人无法有正确的视角,也使得那个指责远远地偏离了目的。
丰裕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复杂、精细的社会蜂巢,使得文学处在危机之中,或许,它正是这危机的产物,但如荷尔德林语:“哪里有危险,哪里就生出救渡。”文学本身包含着克服此危机的承诺,正因这个承诺,它才得以被消费,成为危机的一部分背景噪声。由此,我们也能理解卡夫卡何以成为后世现代作家的原型,是卡夫卡发明了作为苦役与救赎的写作。他敏感地意识到了文学走向匮乏的趋向:文学所展示出的过分的技术性阻挡了思想,正如思想一词也总会被简化为倫理与说教。在杜尚的欲望机器中,正如克里斯蒂安·施密特所说,“艺术不再是物体或它的形式,而是一种神圣的仪式,通过拒绝/恢复的过程制造出变形”。卡夫卡在构架他的文学机器时,也愈发强调写作作为逃逸与仪式的功能。他的书写正是《在流放地》的那一架行刑机器,将绝对律令刻在自己的手背。在夜班写作的长久折磨下,他愈发被卷入语言的幽暗之中,他的词语愈发成为回声般的存在。因其未完成,卡夫卡的每一部作品都留下长长的回声,他处理它们,就像处理一地刨花:生活研磨过他,从他的意识里刨出这些材料,而他将它们黏合在一起,像一个幽灵般,倾听融在自己血管里的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