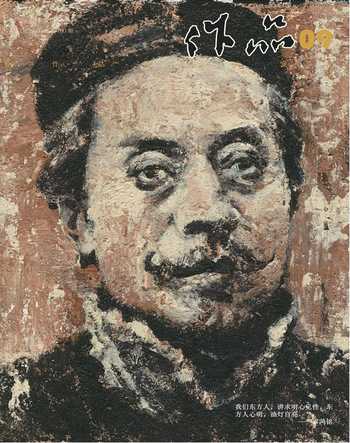长句歌同人生曲
李旭
一篇优秀的诗作不应是被对仗工整挟制,满是晦涩引经据典的章段。当本世纪的歌颂者们走到乡下去,闯入生活里,写出意象俱全的长句赞歌,才能拓下深埋且广泛的大众共情点。
“此时的父亲像一位爱尔兰泥炭工,/天生的农民/不管大地多么洁白”
作一个跨越国籍的宏大比喻,如王年军在《电话》(刊于《作品》2023年第五期)中写到。长大的子女纷纷离家,遍布在除却故乡以外的天南海北,只能靠着细长的电话线勾勒父亲的近况。思欲更甚,于是在异乡遥遥千里,每每留心佝偻劳苦的身影,便总同自己的父亲两两串联。“他的身上总是沾满泥浆”苦难同生活相随,洁白/泥浆相对,作者笔下的苦难是长期性的,在以每一年为周期的循环中,父亲的形象总要立在家中的梁柱位上,即便“冒着牛羊粪便炙烤产生的热气”,岿然未动。
“姐姐仍然说:‘弟弟越长越像个外国人’/我在异乡待的时间开始长于家乡”
读书、考学、到大城市去,作为每一个村庄少年的三部曲梦想,年轻害羞的“诗人希尼”,夸张地表示想要将自己诗化的语言跟“平仄、文雅”划清界限,但仍旧逃不脱亲人的疏远及嗔疑。作者的现实描绘中掺杂了抽象,各色听者收取到的,同自己毫不相干的奇怪故事,却能让每个人挣扎在结尾中,给自己曾几何时的抉择论一次对错。作者让诗句的延伸,以某种把亲情作为纽带的关系递进,朴实的家庭關系在其中潜移默化的变质。
“不再在自己家庆祝,我们说话时也常常谈论/微波炉,辐射,‘尴尬’,某某某去某地‘旅行’……”
对现实关系的最平静陈述,飞黄腾达的喜悦和离岸的不安,在一次平常的家宴中碰撞,转盘桌上摆着一行酒水,歪歪斜斜,像极了泾渭分明的两端。一端坐着“微波炉,辐射”看似奇怪却十分合理的家常。另一端坐着尴尬和攀比心,占据着熟人的席位,但满脸写着外来,洗去了故乡赐予的泥壳子,露出珍藏多年的玻璃心。作者的行文止于意象,再落笔,分不清是对忘祖失本的责怪还是对毅然斩去故土的可怜人的深表同情。
“电话那头,父亲越来越礼貌,问一些古老的问题”
再次返回父亲的形象,年迈的父亲“涉及遥远的童年”为了逐渐抓不住的子女改掉了半生信奉的习惯,“古老的问题”等同于“过时”,即便努力地做出调整,一时的成果同样填不满时间遗留下的代沟,反而似“精神分析师”的滑稽动作。作者笔下的父亲威严不再,岁月让他变老、变佝偻,礼貌的父亲会陌生、可怜。寥寥几句神态写意,一位局促、翻找幼时回忆延续话题的父亲。
“人已不再是物候性的了,尽管父亲依然/给我寄来十一月的杨桃。”
“已不再;尽管”父亲的坚持从来改变不了生活从某种本质上的变化,作者语言上用“已”作为强调“不再”的修饰语,仿佛这样的境况自从很长的日子之前便开始的,更显坚持的单薄。父亲单一的生活在每一年的过去中井井有条,甚至于容不得任何一项变数的突然融入。“花了好几年,才学会存电话号码。”可以想象,几年后的生活方式又将大不相同,这样焦虑,稀疏的发梢又花白几分。
《电话》悠长的句子从大场面入手,在四季流逝当中笔者在远方,电话中的父亲一次次的愈发衰老,却在臃肿的生活中腾出时间来,习得那些“新鲜事物”。诗作最后,藤上的瓜在岁月的洗礼中成熟,仅有的细长、脆弱易折电话线样貌的藤蔓相连,于是枯萎的躯干入了炉火,“哔哔剥剥”。
诗人的话语像在讲一段故事,白话通俗的语言,意象、背景、时间线,穿成串延续,发展饱满。世上的父亲大都如此,有的句子唤醒遗憾,有的遗憾钻出命运,鸣响刺耳的钟。
——意群—动态对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