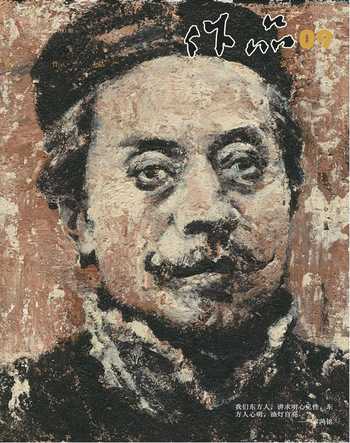镶着金边的姆妈(短篇小说)
赵照川
一
霞子尖着细嗓子喊:太阳落土哒,屋影子连到门前的苦楝树哒,姆妈(母亲)要收工哒,憨子有奶子吃哒!
霞子跑到屋后,踮起小脚望姆妈。平时,姆妈就在霞子的远望中,由蚂蚁般的黑黑的一个小点,慢慢地变成憨子那般大,又变成霞子这般大,再变成老妑(曾祖母)那般大,再大,就变成了姆妈。姆妈匆匆走在镶着金边的云彩下面,她的身影也镶上了金边。
镶着金边的姆妈,从西边的湖野而来,她穿过远处的庄稼,走到白田(旱地,相对于种水稻的水田)这边的尽头,霞子的喊叫声,她就能够听见了。
姆——妈——
霞子哎——
姆妈一答,霞子便飞一般地冲下墩坮,把细细的黄辫子跑得横飞起来,辫梢上的红头绳,就在夕阳光下,划出一道镀着金边的红色波影。姆妈就远远地叫霞子别跑。霞子哪里肯听,冇得一次不跑得气喘吁吁,黄瘦的小尖脸一阵儿红,一阵儿白。有时,霞子会跑得跌跟头,还把鼻子嘴巴或膝盖摔出血来。衣裳穿得少的时候,小路边的锯齿草、棉条荆、枸杞刺,会将霞子的胳膊腿杆剐出血痕。霞子不顾这些,一哈扑进姆妈的怀里。姆妈一把抱起霞子,心疼地责备:叫你不跑不跑,跑了不又要走回去吗?又说,你轻得像一片枯荷叶,几时能长点儿肉啊。霞子便说:我不长肉,长肉了姆妈抱不起的,姆妈出工本来就很累呢。姆妈就叹:我的霞儿啊……霞子说:把我放下来,快滴走,憨子老早就要吃奶哒,老妑哄不住他。姆妈心疼地叹:我的老妑妑啊……
姆妈把霞子放下地来,霞子这才看见远处收工人群的黑影。姆妈每天收工回来,都把其他的人甩在白田那边,甩在湖田那边。这个时候,西边天的红光就收得差不多了,远远的人群身上,就冇得姆妈身影上镶的那种金边。
霞子心里说:姆妈真好,只有姆妈会镶金边呢!
但是今儿,霞子的脚都踮痛了,还是不见姆妈的影子,更别说镶着金边的影子。霞子回到屋里,见老妑一边摇摇窝,一边嘟囔:憨子的姆妈,你哪么还不回来哟,你莫不是落到湖沟里哒哟,老妑今儿死也不晓得,明儿死也不晓得,怕是引不成憨子喽。
老妑八十五岁了,一脑壳白头发,一脸核桃皮,皱巴巴的皮间,长着密密的雀屎斑。老妑嘟囔:憨子哎,冇得奶吃的憨子哎。
七老八十的婆婆,话真的是太多。
老妑说:老妑老糊涂喽。
霞子说:老妑耳朵聋哒,眼睛花哒,背驼得像乌龟哒,但是老妑吃藕粉都不糊涂呢。
老妑就笑起来。老妑一笑,喉咙里就发出嘶呵嘶呵的声音,跟老得不得动哒的牛发出的一样。老妑的颈脖垂下的老皮,比老黄牛脖子下的皮还要长呢,还一直颤颤地抖呢。
老妑说:哎哎,鬼霞子,你嘴巴太活荡呢。除了你妑妑(祖母),這长堤垸里,就再冇得这么活荡的嘴巴啦。
霞子立刻皱起小小的鼻子,说:哼——我才不要像妑妑呢!
老妑连声说:是不要像她,是不要像她,要像你姆妈,又漂亮,又能干,又明事理。哎哎,老妑哪里是吃藕粉都不糊涂,还冇得我们霞子的嘴巴会说话喽。
霞子说:不是我的嘴巴会说话,是我姆妈说的。
老妑伸出枯丝瓜一般的手,摸着霞子稀稀的黄头发,叹道:你姆妈是个遭孽命啊。
老妑,姆妈还不回来,我饿。
你刚喝过粥呀。
这菜粥照得出人影子来,跟喝水一样呢。跟水一样照得出人影子来的菜粥,能喝得饱吗?
你个鬼霞子,一张嘴巴哪那么多的话,说那么多话不要力气?不耗费粮食?你呀,就是说话说饿的。
老妑,我真的饿,我冇有说话的时候就饿哒,不信你看。霞子揭开衣服的下摆,露出黄黄瘪瘪的肚皮。因为太瘦,衣裳一揭就揭到胸脯以上了,露出胸脯上一对胭脂花般的小晕片。这指甲大的淡红的小晕片中间,两粒芝麻大的小凸点还不太现形呢。老妑就直摇头,摇得颈脖下的老皮像风吹晾晒的床单。
霞子看上去才三岁多,其实五岁了。霞子瘦得大眼睛咕咚,细细的肋骨,就像剐了皮的兔子的肋骨,一根根看得索索利利。
老妑叹道:这日子哪么往下过哟,这一世的人……肚子都糊不满哟。
霞子说:老妑,不能说这样的话,被人听到,让你吃斗的。
是的是的,老妑不该说这样的糊涂话。霞子你记得,今后老妑说这样的话,你可要提醒老妑。不然,老妑抓去坐牢哒,憨子就该你来引哒。
我哪么引得好他呀,他饿起来尖咹鬼叫,乱蹬乱造……再说,我还不会煮米汤呀,我也冇得奶子给她吃呀。
老妑笑道:所以呀,你得时刻提醒老妑不说错话,也不说你妑妑的不是。
妑妑的不是可以说,我不会告诉她。她从来抱过憨子吗?她抱队长家的圆子都不抱憨子!
霞子啊,不要说她的不是哒啊,再说,她就不给饭老妑吃哒,你不是怕老妑死吗?
好好好,不说她的坏话哒,等你死哒我再说她。
老妑懊悔地说:唉,你这女伢子,都怪老妑老糊涂哒,撩起话说。
二
霞子第五次到屋后望姆妈,西边天的红光已经冇得了。
霞子叹着气回到屋里,憨子哭号得更厉害了。她揭开憨子身上的粗布单,尖声叫道:老妑,憨子又屙哒。说着,霞子就扯憨子屁股下的灰袋子。灰袋子不只是尿湿了,还沾着黄绿色的稀㞎㞎。哎呀,好臭!憨子的两条麻秆细腿乱蹬乱造,稀㞎㞎造到摇窝的垫子上了。老妑颤巍巍地拿过一块尿布片,一手提起憨子的细腿,一手擦他瘦瘦的尖屁股。霞子便抽出垫在摇窝里的脏灰袋子。霞子从门前的篱笆上收下一只干灰袋子,将撮箕里备好的灶灰装了进去,来给憨子更换。
快点噻老妑,憨子脸都哭红哒。
老妑手脚笨,得慢慢来。慢工出细活。你看你姆妈的手工多细,灰袋子的针脚,比别人家做的衣裳还要匀还要密。唉……你姆妈是太掐尖哒,遭到婆婆——你妑妑嫉恨……唉唉,灰袋子铺平哒吗?
铺得平平的。
好好,我的霞子长大,又跟你姆妈一样。唉,老妑眼睛一抹糊哒哟,黄土盖齐下巴子喽,今儿死也不晓得,明儿死也不晓得喽。
我姆妈说,去年老妑八十四岁冇有死,今年家里失火也冇有死,你要活一百岁的。
是的,老妑要活到我的霞子嫁人家,活到我的憨子娶媳妇,呵呵……
霞子也咯咯地笑。
霞子拿出门角里的一个缺碗,抓起里面的土灰,小心地抹在憨子的屁股缝和大腿根,还在他的小雀雀周围也抹上了。这是姆妈从老土墙上刮下的土灰,跟滑石粉一样好用。
老妑说:哎呀,霞子做事真过细。
憨子哇哇大哭。霞子加紧摇摇窝。憨子反倒哭得更厉害。
霞子说:他又吃手指头哒,手指头都被他吃扁哒。
唉,又饿哒啊,这米汤哪里能饱肚子,稀汤灌大肚,肚量越灌越大呀。七个月哒,还像个三斤猫儿,遭孽呀……
老妑坐在摇窝边,轻轻地拍憨子的肚子。憨子不缓劲,一边用红红的牙床啃嗦自己的手指,一边涎水直流地啼哭。
老妑老妑,他的气肚脐子又鼓起好高!
是哟是哟,鼓得像根空柱子哟,都是哭成这样的呀。
霞子着急地喊:别哭哒别哭哒,再哭,你的肚脐子就要被气胀穿,那样你会死的!哦呀——崖崖(爸爸)几时从城里回来啊,他会给憨子带牛奶来呀,还会给姆妈带猪蹄子呀,姆妈喝了猪蹄子,就有奶水哒呀。哦呀——爹爹(爷爷)几时从油田回来啊,上回姆妈吃了他从湖里找的蚌子和野鸭蛋,就有奶水哒呀。哦呀——舅崖(舅舅)几时从汉口钢铁厂回来啊,姆妈每次喝了他抓的鱼汤,就有奶水哒呀。哦呀——他们为什么都不回来呀,是不是不要我们哒呀?
霞子学着大人哄奶伢子,说说唱唱,有板有眼。
老妑叹道:憨女伢子呀,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哪会不要我们呀。你崖崖去螺山修泵站去哒呀,你爹爹和你舅崖,去的去潜江,去的去汉口,都上三线工程去哒呀。他们一时回不来呀。
老妑说得也像唱歌。
老妑说:不行不行,这样哭,真会把肚脐子哭穿呢。霞子别摇哒,老妑来抱抱他。
老妑好不容易才把憨子抱起来,贴到胸口上,憨子还在乱蹬乱造。老妑疼惜地说:饿成这样子,还有力气哭,还有力气造,将来肯定是匹刁马……一匹刁马哎,刁马是好马呢。霞子,你把灶里点燃,我来把奶瓶里的米汤烫热。
我来烫。
你灶都够不着呀。
我搭凳子。
……好吧,反正老妑活不长哒,迟早都是你的事。小心一点啊。
霞子爬上长板凳,从芦苇壁子上拿了火柴,将谷草把子点燃,然后又踩着板凳,往锅里放了两瓢水,再将装着米汤的奶瓶放进锅里煮。一会儿,霞子用锅铲把奶瓶盛到木瓢里凉,过一会儿,再将奶瓶浸到水缸里。只有半瓶米汤,奶瓶就浮在水缸里,像一只小小的鸭子。霞子的玩性上来了,不停地将奶瓶往水里按,奶瓶就不停地从水下冒起来。老妑问:还烫吗?霞子醒悟过来,捞起奶瓶尝了一口,不烫哒。老妑便喂给憨子。憨子喝了一口米汤,马上吐了出来,哭得更厉害了。
霞子说:嘴巴真刁!
老妑说:不是憨子嘴巴刁,这早上的米汤,到现在都陈哒,又冇得糖。
霞子说:冇得奶吃,不吃米汤吃甚么!
老妑说:说得是。吃啊憨子,吃啊。你生的不是时候,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你姆妈差一点饿死。刚好一点,又是放卫星,又是物资提价,又是支援越南,又是学大寨。你姆妈怀你时,屙哒好久的血。来,吃。唉,哪天怕是米汤都冇得喝的呢。
憨子不吃,吐得满下巴都是。
霞子说:老妑,憨子不肯喝米汤,你又把你的奶子给他嗦噻。
老妑叹道:老妑哪来的奶水哟,这是逼公鸡生蛋哟……
三
老妑抖索着手,好半天才解开斜襟衫最上面的袢扣。憨子已哭得声音嘶哑。霞子就凑上去帮老妑解绊扣。
老妑的奶子解出来了,像两条长长的茄瓜——不,像两只细长的空皮袋子,还像两截猪肠子,瘪瘪的,真难看。老妑怕走起路来这两只长长的皮袋子乱晃荡,就用一根长长的黑布条从背后绕上前来,两头各在一只奶子中间绕上一圈,然后再在胸前打一个结。前阵子,霞子看见挨斗的坏人游街,坏人光着身子,五花大绑,霞子回来再看老妑绑着的奶子,就说老妑的奶子挨斗游街。老妑的脸笑成一朵大菊花,颈脖下的长皮乱跳乱抖。老妑笑得咳喘起来,差点就笑背气。老妑说:不把老妑笑噎死哒,笑噎死哒,就该你自己引憨子喽。
老妑的奶子软塌塌的,只剩下皮,哪里像有奶水的样子。霞子顾不上这些,抓起老妑的奶子,将干枣般的奶头送到憨子嘴边。唉,老妑的奶头都陷到奶皮里去啦。霞子只好一手将老妑的奶皮往上捊,一手将奶头往下扯,扯出来了,就往憨子的嘴里塞。
憨子,吃,吃,你吃噻。霞子一边说,一边自己一下一下地张嘴,好像是要替憨子吃奶,或者是想用自己的嘴巴,带动憨子的嘴巴。
憨子像餓慌了的黄嘴雀伢儿,小嘴急急地往前叉,却总是叉不住老妑的奶头。霞子耐心地将老妑的奶头稳住,憨子才终于叉着。憨子使劲地嗦,但是,嗦进去的只有他自己的涎水和鼻涕。憨子一边发出上了当似的大哭,一边用劲嗦奶头,还发出咂咂的声音。他自己的涎水和鼻涕被嗦完了,冇得了来源,便伸出小手抓老妑的奶子。这一抓,奶皮被抓了下来,奶头又缩到奶皮里去了。
霞子生气地叫:哎呀,你乱抓么子!
老妑说:算哒算哒,还是让他喝米汤。
他不喜欢喝啊。唉,要是我有奶子给他吃就好哒。霞子大人一般地叹气。
老妑,我的奶子甚么时候长大?明年长得大吗?我要它快点长大,长得像圆子的姆妈的奶子,像冬瓜那么大,都叫她冬瓜奶子呢。我要当憨子的姆妈,让憨子有吃不完的奶水。圆子比憨子还小一个月,长得比憨子大一圈都不止。老妑,都说圆子蛋有半个天那么大,圆子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去年北京生了个圆子蛋,还爆炸哒。北京是哪个呀,哪么生那么大的蛋呢?要是我的奶子像圆子蛋那么大,该有多好。
老妑嘶呵嘶呵直笑,却流出眼雨来。老妑总喜欢边笑边流眼雨。
霞子唱道:一边哭,一边笑,两只黄牯打惊叫。嘻嘻……老妑你羞不羞呀?
老妑抹了一把眼雨,说:憨女伢子啊,说些痴话。要是命好,你自己都还在吃奶呢。你爹爹五岁的时候,还扯开老妑的衣襟子找奶吃呢。你崖崖也是,四岁哒,还一天吃三餐奶?
霞子说:有奶我也不吃,我要让憨子吃。哎呀,我的奶子老不长大,我太想当憨子的姆妈吔!
四
憨子哭累了,老实起来。他一边吸米汤,一边还在伤心地抽泣。
老妑喊:哎呀,又屙尿哒!
霞子一看,老妑的胸前湿哒一大片。霞子唱起谣歌:
撒尿宝,
卖灯草。
灯草青,
换块金。
灯草黄,
娶婆娘。
灯草不青又不黄,
撒尿宝说要起新房。
霞子说:你个臭憨子,灰袋子屙湿哒,老妑的身上也屙湿哒,你这个撒尿宝,长大连茅草棚也冇得住的,还起新房呢。
老妑说:可别小看我们憨子,他长大哒会有出息的。你崖崖教中学,他将来要教大学。
我崖崖不是冇有教中学了吗?不是去修泵站哒吗?
哦……是啊……不过……修泵站只是暂时的。你崖崖一个教书先生修甚么泵站,他的学问大着呢,在中学里教最大的学生呢。
那将来,憨子教的学生,不都是大人呀?
是啊,大学生就是大人哒,你崖崖读师范时,就已经和你姆妈成家哒呢。
霞子说:老妑,我们一起去望望我姆妈吧。
老妑说:望也白望。又说,你姆妈哪天收工,不是火急火飘往家里赶?
老妑,去嘛,去望望嘛。我们一望,我姆妈走得就会快很多。
老妑说:望到哒也白望的,你姆妈的奶水,每次都不到一小口,憨子的嘴巴都打不湿。憨子不吃奶还好,吃哒不够,哭得只会更厉害。他这气肚脐子,就是这样哭起来的。
我姆妈说,早要是晓得奶催不下来,当初就该一口奶都不给憨子尝。憨子不晓得奶水的味,就不会想奶吃,就会乖乖喝米汤。
憨女伢子啊,你哪里懂得做姆妈的心呐。哪个做姆妈的,不都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儿女。
霞子说:老妑,去望我姆妈吧。
我这胸前一片尿,哪么好出门。
我来帮你扇干。
霞子找来一把破蒲扇,在老妑的胸前扇了起来。
老妑说:别扇哒,会把憨子扇惊风的,老妑跟你去望你姆妈。
霞子找到锁头,要老妑锁门。老妑抱着憨子,腾不出手,说:不必锁它。霞子把门带拢,说:破家值万罐(贯)。老妑说:你呀……甚么都晓得。
一道芦苇壁子,将茅屋隔成两间。里间支着两块门板当床,外间一个土灶,一张小饭桌,一把竹椅,两条板凳。这点家什,还都是亲戚邻居送的。憨子一出生就喝米汤,身子虚,天天尿床。四个月前的傍晚,憨子尿湿了摇窝,又尿湿了床。姆妈把火盆放在床上,罩上烘篮,再将被子盖在烘篮上,这样,垫的盖的可同时烘干。憨子那天又发烧,姆妈便抱上憨子,带上霞子,去找离得不远的赤脚医生,打算快去快回。那夜,爹爹去队里铡牛草了,累了一天的老妑早早困了,妑妑也出去串门了。事后妑妑说,见她养的黑猫卧在被子上取暖,也冇有在意。四代同堂的三间草屋烧得一干二净。好在村人把老妑救了出来。妑妑恨死了姆妈,一家人没法住一起了。爹爹只好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搭了两间茅屋。大茅屋在老坮子上,爹爹妑妑和老妑住;小茅屋在新坮子上,姆妈带着霞子姐弟住。
五
西边天冇得一点阳光了。老妑抱着憨子,像一只巨大的老乌龟,颤巍巍地往墩坮后面走。墩坮本是河堤,村里的房屋都建在这河堤上。往墩坮后面走,实际上是在下堤坡,老妑哪敢走快。
老妑往野外望去,望见长满棉花的沙田上面,升起一片淡蓝的雾霭。雾霭那边,是一望无际的湖田。湖田以前是大片的湖荡与浅滩,鱼虾菱藕吃不完,野鸭獐子时时有,即使在荒年,人们也不会饿肚子。现在,湖荡都围成了稻田,稻子长得像癞子的头发,交的公粮又多,竟然时常吃不饱。老妑便长长地叹气。
霞子转过身来说:老妑,你快点噻。
老妑说:憨子在吃我的颈脖皮,我更走不快啊。
果然,老妑颈脖上垂下的老皮,被憨子当成了奶头,他正用力地嗦着。
霞子学着大人的口气说:遭孽佬。
白田那边走上来一个人,霞子很兴奋,近了,却是保管员寿爹。寿爹说:瞿妑,你们这老的老小的小,在望霞子的姆妈?不望哒,今儿开夜工脱谷粒,我上来给大家弄点辣酱去就粥呢。霞子听了,哭了起来。霞子是个懂事的女伢子,她只是小声地哭……
回到家,老妑将中午剩下的菜粥热了,让霞子垫肚子。霞子叫老妑也垫肚子,老妑不肯,她不愿占霞子家的口粮。老妑的口粮在爹爹妑妑那儿,为这,妑妑跟爹爹还吵闹过,说是老妑帮着引重孙子,就该在霞子家吃。爹爹骂道:你的心还是不是肉长的?儿媳妇饿得奶水都冇得,我们帮不上也就算哒,还忍心让老妑去吃她的口粮?
老妑喂憨子又喝了点米汤,憨子又哭闹一番,终于困着了。霞子说:晓得他是困着哒,还是饿昏哒。老妑听了不吭声,她后悔自己跟霞子的姆妈说这话,让孙媳妇心酸,现在霞子也学会这样说了。
老妑便让霞子守着憨子,她要回家吃晚饭了再过来。
六
憨子又屙了尿和稀㞎㞎,霞子拍了他的屁股一巴掌,㞎㞎也沾到了手上。见憨子哭得快断气,霞子又只好哄他。霞子说:姐姐再不打憨子哒,憨子你不要哭哒。
天开始发暗,霞子左等右等,却等不来老妑。她有些害怕,便抱起憨子去找老妑。她虽然瘦小,但憨子更像一片枯荷叶,她还能勉强抱得起。
出门往东,过两户人家,就是一个大堰塘,走过堰塘,就是老妑住的屋子。堰塘边原有一个小尼姑庵,霞子还冇有出生的时候,队上强拆了庵子,尼姑便在塘边的柳树上吊死哒。有人说,深更半夜,常见堰塘边有个女鬼敲木鱼。霞子怕鬼,但是更怕待在屋子里。霞子见过屋顶的茅草上,有四脚蛇向她张望过,也见过屋后的土墙边,大蛇蜕下的白色长皮。心惊胆战地经过堰塘,霞子心里直发毛。一只癞蛤蟆呜哇一叫,霞子的心儿,缩得只有麻雀蛋那么大了。好在憨子大声哭着,倒是给霞子壮了一滴胆。
霞子抱着憨子,一身虚汗地到了爹爹妑妑的家。霞子喊妑妑,冇得人应声。又喊了两声,还是冇得人应声。霞子不喜欢妑妑,但姆妈说过,再哪么说,她还是你的亲妑妑,她对你不好,但你的礼数不得少,遇上她或去她家,首先得叫。霞子想,她肯定又去找圆子的姆妈去了,她们都做沙田里的轻活,收工早。
妑妑不在家,霞子暗暗高興,也就忘记了一路上的害怕。
霞子的力气快用完了,几乎抱不起憨子了,憨子的脚都拖到地上了。霞子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把憨子往上耸了耸,说:憨子不哭,哦哦不哭,姐姐让老妑又给奶子你吃。哦哦憨子乖,老妑刚吃饭,肯定有奶水哒,让憨子吃得饱饱的。
憨子只是个哭。
老妑!
老——妑!
老妑吔——
冇得人答应。
霞子进到屋里一看,老妑躺在饭桌下困着了。老妑的背好像直了不少,身子也长了不少。饭桌上,一只翻着的粗碗里和碗边,是几只鸡蛋大的菜疙瘩。这菜疙瘩里混着一滴米粉子,白的白黑的黑,像偷吃了生米的狗拉的屎,怪难看的。只要爹爹不在家,妑妑就给老妑吃菜疙瘩。有一次,霞子来找老妑,老妑让她尝菜疙瘩,菜太糙喉咙,吞不下去,霞子的眼雨都吞出来了。老妑笑着问:好吃吗?霞子吐掉菜疙瘩,说:不好吃!老妑笑着笑着,眼雨就出来了。
昏暗中,霞子看着又冷又硬的菜疙瘩,喉咙不由自主地作起哽来。
霞子喊:老妑不要困地上,你不是说困地上要得病的吗?起来噻。
老妑不醒。霞子轻轻踢踢老妑,老妑还是不动。霞子就将憨子放在地上,任由他去哭。霞子去拉老妑的手,刚触到,不由赶紧一缩。
老妑的手又冷又硬,像棱冰。
霞子迸出直声大叫:
姆妈耶——
责编:周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