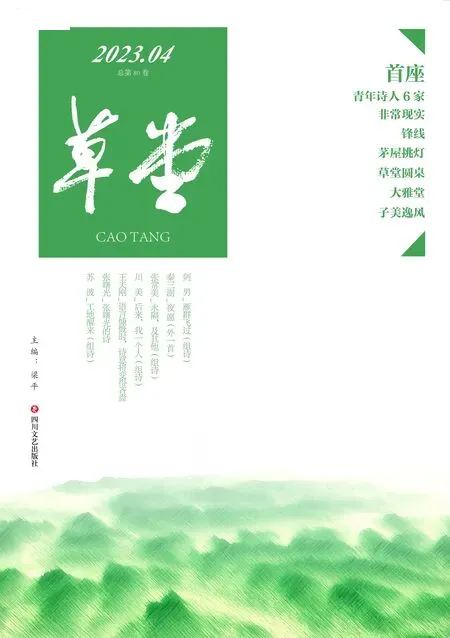语言慷慨时,诗意将变得吝啬
◎ 王夫刚
2019 年夏天,我去了一趟川西高原。先乘飞机到成都,次日上午,一行人坐考斯特沿岷江溯流而上,过都江堰,过汶川,过茂县,过松潘,一路攀升,至傍晚方才抵达高原小城若尔盖。于我而言,此行充满陌生的激动和预设的期冀,事实也的确如此,整个行程不失现实的壮阔之美和历史的细节支撑,为若尔盖写下诗篇,则从采风的“格式条款”悄然转化为内心的暗流涌动(尽管当时我还不清楚如何在诗中与若尔盖遭遇)。过了几个月,我写出组诗《高原上的深呼吸》,它们是“我能够完成的诗篇”,但首先是“我愿意完成的诗篇”,《栖山或者余烬》即为其中一首。《草堂》诗刊要求我在这篇文字中谈谈一首诗“为什么这样写”的理由而不是“为什么写这首诗”的原因——依据这个限定性栏目规则,上述文字当属跑题,而且是明知故犯。下面进入本文正题。一首诗的诞生,存在多种可能或曰不确定的因素,我的写作不绝对推崇技巧,但也不抗拒写作技巧带来的文本福利,《栖山或者余烬》大致体现了这种心态和诉求。这首写实性的短诗记录了若尔盖的一次篝火晚会,星空下的草原,我独自走动,越走越远,难言的单纯和寂寞迎面而来,耳边回荡着博尔赫斯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谈话:“人群是一个幻觉,它并不存在,我是与你们个别交谈。”在这首诗中,我不想尝试任何冒险(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也没有设置阅读的障碍用以考验读者(考验读者本质上是考验作者),高原的广角美德、心灵的瞬间惆怅和命运的免费教诲呈现了这首诗的全部责任。作为一首直接面对和“个别交谈”的短诗,它中规中矩,一目了然,似乎没有抒情也无所谓象征,我甚至有些回忆不起如何完成了它,只记得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有迹可循的,连扎西措和白玛措都在对号入座的背景中失去了意指的可能性。诞生于本能的写作初衷自带一种天然的局限,从一开始便会丧失选项功能,想象力遭遇不公平的粗暴对待,诗歌的歧义则被扼杀于对隐喻的无理漠视——这里有点愧对博尔赫斯先生,他认为诗人只要使用语言,就不得不使用隐喻。不过还好,整首诗基本实践了我的写作理念,好的诗篇理应无一字没有来历,无一句没有来历,这意味着这首诗是“真实呈现的文本”而非“强制呈现的文本”。前者起码是一种自主流淌,后者顶多算是外力下的蠕动,其诗意浓度和健康指数不可同日而语。这首诗虽然简短,我个人以为文本结构上并不欠缺什么,面孔尚且清晰,呼吸也没有失去节奏,尽管诗的结尾暴露出一些情绪化的主观色彩,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个结尾缺席了这首诗的建设,这次写作还能不能形成可控的闭环管理呢?在我这里,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这个结尾并非可有可无,它必须存在——有时我甚至想说,我写下这首诗的前面三段,只是为了安慰年久失修的膝盖,让它在若尔盖草原上经历一次对遗产、备胎和纪念品的难得背叛,而这种偶然性的时空启迪,与北京东三环的车流和三里屯的酒吧也许永远不会产生交集。草原承办了人类的狂欢节却拒绝参与人类的狂欢,草原上每一棵风中晃动的小草其实只愿意与另一棵风中晃动的小草窃窃私语,这算不上人类的羞耻,却有可能是人类的无奈——生活需要妙语连珠,生活的妙语连珠未必是诗歌的有益证据和终端命题,语言慷慨时,诗意将变得吝啬,这可真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求证。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孤独是一种永恒的自知之明,当我的脸上无力镌刻我们的喜怒哀乐,我就会成为“缺失的我”在时代的舞台一角手足无措,表现在这首诗中则是,我想唱一首自我之歌,却没有获得出场机会;我试图不偏不倚地记录个体生命在“这一刻”的局部感受献给时间截面上的我们,却发现“我们”不过是一个虚拟的集体更适合背影出镜。看起来这是一个悖论,但悖论作为诗歌写作的常见手段和语言策略,早已不再构成对写作者的苛刻要求。狂欢过后,篝火渐渐熄灭,海拔3400 米以上的余烬顽强而善解人意地温暖着一群瑟瑟发抖的异乡人和异乡人瑟瑟发抖的孤独,这匪夷所思的夏日情景对奉想象为圭臬的诗歌同行来说堪称降维打击,而我选择的语言路径,依旧是自己喜欢和习以为常的模式:“夏日的寒冷不肯妥协时/藏袍挺身而出”,或者,“星空下面,有人念了一首短诗/献给命运”。多么幸运,妥协,命运,挺身而出,这些看起来显俗的词汇在我的写作中每次都能得到公平使用。如果这种语言路径没有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抵达一首诗的终点,我完全理解,但不会为之感到遗憾,它只说明读者和作者的语言趣味存在差异,或者读者借“阅读的失望”含蓄暗示作者的艺术创造力有待提高,而语言趣味的差异并不存在一个立见输赢的擂台,也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恒定状态,更不会构成对一首诗的终审裁决,这是艺术自身携带的光芒所产生的魅力:李白曾是杜甫的偶像,但“李杜”才是诗歌史上的“专用名词”延伸并丰富了“双峰并峙”的语义。当然,视阅读为一种创造或者再创造通常也不是一个错误,读者介入一首诗,就获得了作者的一次间接授权,这首诗可以是动态的随意赋形,也可以是固体的削足适履。借助作者的单边阐释完成读者的有效阅读无可厚非,但上佳选择未必如此,因为这样做无意间冒犯了诗无达诂的古老传统。按照这个逻辑,我对《栖山或者余烬》的解读将充满各自为政和敝帚自珍的味道,对于开放的健康的诗歌来说,这委实称不上一种特别值得推广的味道,因此,我愿意谈论“余烬般的孤独”和“孤独般的余烬”之间的非语言差异,愿意谈论有限真实和相对虚构对诗歌所贡献的各表一枝的钙质和含金量,愿意接受剔除了情绪暴力和语言恶意成分之后的指责、诟病乃至讥讽(博尔赫斯先生说过,一个诗人应当把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不幸,视为对他的馈赠),但读者要问我诗中的遗产是什么,备胎是什么,纪念品是什么,游子般的空旷又是什么,我将对这种浅尝辄止的阅读介入产生深深的怜悯而不把这种怜悯告诉阅读者本人——几乎所有成熟的诗人都会凭借经验构建语言中的道路并予以隐形命名,完成心灵史的长途跋涉,而诗人的先验却很难在读者那里获得完全对等的理解乃至置换。
附诗:
栖山或者余烬
诗歌朗诵会的露天舞台长满了
青草和疾风;篝火
是唯一的灯光尚未点燃
夏日的寒冷不肯妥协时
藏袍挺身而出;若尔盖撞身取暖时
扎西措也叫作白玛措
星空下面,有人念了一首短诗
献给命运;星空下面
有人走向游子般的空旷——
不过是余烬,不过是孤独
不过是年久失修的膝盖
挣脱了遗产、备胎和纪念品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