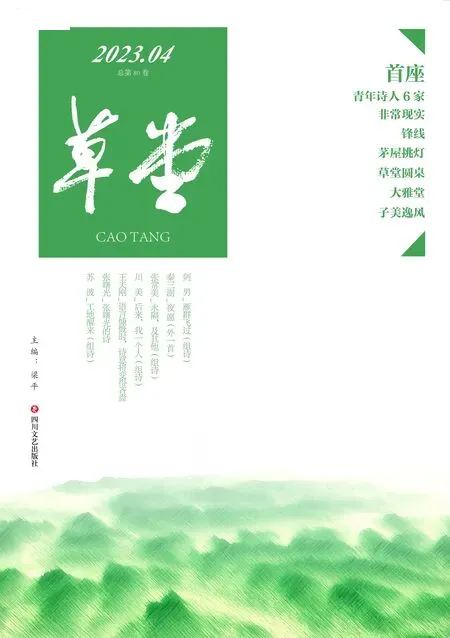雁群飞过(组诗)
◎剑 男
[开满荷花的湖面]
荷花终于开满了半个湖面
在第五天早上,终于开满了整个湖面
和苇草、荷花、鸟雀为伴
苇草并非我想象中的腹中空空
荷花也不全是出淤泥不染
早上走在湖边,一只苇莺在湖上徘徊
我看见它的悲哀和我一样
在不停奔波中找不到昨日停驻的地方
我们都羡慕那些低飞蜻蜓
毫不费力就停在它想停的荷尖
不像我出走半生,最终还是回到这里
苇莺从这朵荷尖到那朵荷尖
最后还是在湖边的苇尖上停了下来
湖边有我小时生活过的老家
湖边苇丛有苇莺衔草编织成的巢穴
在生命各自经历的新居和旧寓里,我们
都选择了好好恋慕自己的故乡
[旧时山路]
新建的高速公路旁有一条小路
快被草木掩盖,像是新路丑陋的陪衬
一条新路偏离旧统,在这个高速奔跑时代
取了捷径,这似乎让人欢欣鼓舞
但我还是愿意走在旧时山路上,看着自己
一步一个脚印翻越生活中的崇山峻岭
[椴木林和乱石滩]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河谷,石头叠着石头
不分高矮胖瘦,我从没见过
这么多椴木,一株株从乱石中长出
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河谷不远处是一座明代书院的遗址
据说是用河谷中的石头建造的
乾隆年间曾经囚禁过众多桀骜不驯的书生
如今书院仅存的石头泛着青光
河谷中的石头仍裸露着苍白的身躯
书院中的石头穿过遥远的时光像受到教育
椴木在河谷石头下扎根,仍显示出
石头冥顽的本性,有人说和
书院遥遥相望的乱石滩是沿途不甘
命运的石头投身洪流的结果,这是否也是
一种自我教育:人间从来没有
石头自建的集中营,也没有椴木自织的樊笼
它们不过是我们不测命运的象征
[天兴洲]
天兴洲是长江中的一座狭长的小岛
上面有花草树木和各种禽鸟
我大学时坐轮渡上去过
那时江水宽阔,天兴洲以瘦弱身躯
分开江流,我们都对它
以一己之力砥柱中流充满敬畏,又
满怀同情,如今它露出
被江水浸泡过的身子,干瘦、嶙峋
像时光深处生命的褶皱
因此我坚信它一定比江水更早出现
在这里,坚信在江流底部
一定有一条路连着江边的谌家矶
坚信那时的天兴洲并不孤单
也从不曾想过要阻挡浩荡的江水,它只不过
是因坚守自我而被流水所围困
[雁群飞过]
大雁出现在瓦棚镇上空的时候
上街铁匠铺里的老年铁匠夫妻仍然在打铁
池塘里起鱼的男人仍然在起鱼
作坊里的女人们仍然在炸麻花和打月饼
只有学堂里留守儿童望着窗外
停下读书声,只有那个年轻的女教师走到
窗前,然后又低下头缓缓背过身去
[黄昏读书]
一个人从故纸里来到我们中间
在黄昏,加重了旧的痕迹,他带着故事
但光环是落日加给他的,我们
完善了他故事中空白的部分,同情他的
贫寒身世,苦难童年以及落魄
发奋的中年,承认那个虚构女子是他的
红颜知己,承认他的世俗和我们一样
承认他的高洁让我们望尘莫及
我们像文物修复师,把他模糊了的形象
清晰地还原出来,拂水照花,又
把他塑造成我们渴望见到的样子,至此
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读书不是试图
理解他人,而是为塑造自己
无论用多少文字对自己进行刑讯逼供
我们都无法将他出卖,他在那里
是我们心中的朝阳,但此刻要像落日一样,承担
人世悲凉薄暮中虚幻、温暖的部分
[走在山中的少年]
初秋幕阜山的天空一贫如洗,但
有着梦幻的蔚蓝
山中茱萸的果实像涂满口红的唇
但还藏在成簇的叶片中
那藏着金子的山坡,还在流水的
空响中把黄昏送远
那雁群飞过之后,还有一只孤雁
远远地落在队伍后面
那个悲伤的少年走在山中
走到父亲坟前,他
流下了眼泪,为他父亲的一生
还不如草木一秋,走到
母亲坟前他又流下眼泪,为母亲的新坟
这么快就被荒草所覆盖
[大道和歧途]
大道的宽阔端直,是以很多曲折小径的
消失为代价的,歧路的趣味在于
选择,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它的复杂性
连接着我们的生活。——“林场
是老瓦山心脏,不止大道,每一条小路
都可以通往那里。”如今,通往
林场的路由大道变为小路,空寂无人中
我仍能听见有脚步在走动,可见
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只是
并非所有小路都能通往它的中心
为了尽快找寻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我抄一条小路上山,路走到断头
也没有见到林场,只见到一座残破小庙
在山崖边临风而立。山崖下面是
江西,山崖上有一条小路,崎岖、陡峭
黑山羊走在上面如履平地。都说
所有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其实山中有
人走出的路,也有麂子走出的路
黑山羊走出的路。你站在山崖上面看到
一条旅游公路在群山中一骑绝尘
而父亲曾独守的小木屋却渺无踪迹,你
说哪里是大道,哪里又是小径?——想想生命的
虚妄无常,世间道路又有多少不是歧途
·创作谈·
自然和人的尺度
写作是个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重建,包括和自然、社会、他人及自我关系等的重建。
世界广袤无边,个人在其中只是一个微小的存在,在物理意义上,这个关系极度不对等——每个人都是沧海一粟,都逃脱不了被汪洋淹没的命运。但就人自身而言,他又是自己的全部,不会因为汪洋就失去自己。因此,这种关系是微妙、神秘且充满内省的。
作为一组和自然相关的诗歌,它和我近年来希望通过诗歌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写作理想密切相关。大家从这组诗可以看到,我总是想通过个人的存在指认什么,又总是对之充满疑惑。在自然和人的尺度之间,我尊崇的是我的内心,试图以自我的偏狭达成人和这个世界诸种关系的理解。
胡适谈到诗歌写作时曾说:“凡是抽象的材料,格外应该用具体的写法。”我非常认同胡适的这个观点。这组诗歌除《雁群飞过》《走在山中的少年》外,其他几首都介入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抽象的东西。其实我对这种主观的介入是非常警惕的,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很难回避这种感受的自然生发。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説,我们首先是被自己的观察充满着的个人,诗歌既要展现我们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立性,又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独立于自然和社会之外生活与写作,我想诗歌不外乎就是我们个体生命在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反映,我的这个所谓的创作谈和诗歌相互印证,可能也正显示出我渴望通过诗歌重建人与自然关系力所不及的地方。
但我想说明的是,诗歌的背后一定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无论是对自然的书写还是对社会的书写,我们所看到的万事万物无非都是人的尺度,是我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支撑着我们的文字,写作行为一旦发生,我们都是在与自然和社会彼此观照、相互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