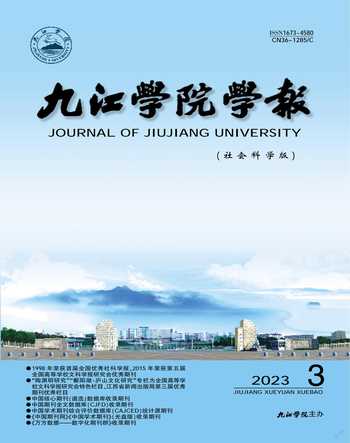论陶渊明诗文中的“新性分说”
王铱婕 徐国荣
摘要:陈寅恪提出陶渊明思想为“新自然说”,是否属于“旧义革新”的“孤明先发”,引起广泛讨论。通过对陶渊明作品中有关“性分”问题的分析,结合郭象哲学中的“性分说”,从“性”和“分”两方面探讨,可以看出陶渊明之“性”包含自我之意志与自然之性两个层面,既突破了郭象所言天命之“性”的束缚,重新回归到人本身,同时又剥离了郭象“性分说”中的社会属性;“分”是陶渊明体认自我本性之后认为自己所应守的职分,故以委运任化的生命观应对“性”的无可奈何之处,追求性情的自足自适。陶渊明“新自然说”主要也是通过对“性分”问题的认识分析而得出的,非脱胎于旧自然说,实则可称为“新性分说”。从陶渊明作品中不断出现的“性分说”角度来看,确实在郭象的基础上进行了“旧义革新”,谓之“孤明先发”亦有其合理性。
关键词:新自然说;新性分说;陶渊明;郭象;旧义革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3)03-0001-(09)
DOI:10.19717/j.cnki.jjus.2023.03.001
陳寅恪先生于1945年发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承袭了魏晋清谈演变结果,同时又受天师道影响而创设了“新自然说”。此说既非“名教说”,又与“旧自然说”不同:
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推其造诣所极,殆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1]
此论一出,学界对此争议颇多,赞成者众多,同时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朱光潜、汤用彤等。若站在“旧自然说”和“名教说”的角度,陶渊明的思想确有其“新”之所在,从《形影神》组诗中看,他继承了魏晋清谈之精神,不与政治势力合作的同时又创造了一种与阮籍、嵇康等“旧自然说”不同的思想,即“外儒内道”的“新自然说”。但此“新自然说”可否称得上“旧义革新”的“孤明先发”,或者直接名之为“新性分说”,却是可以探讨的。
在陶渊明之前的郭象就曾作《庄子注》以“明内圣外王之道”[2],以其“崇有”哲学下的“性分说”将儒道思想影响下的“名教”与“自然”合一,追求“性分之内”的自由逍遥。郭象的《庄子注》在陶渊明的时代已广为流传,“性分”在陶渊明诗文中也多有体现。据统计,在陶渊明的作品中,至少有二十四篇诗文都言及“性”或与“性”相关,十九篇都在“分”的范畴内,可以说陶渊明确实关注“性分”之辩。学界对于陶渊明思想的认识其实大多也是通过他对于“性分”的认识分析,只不过,他的“性分说”出于郭象而又并非等同于郭象,与其说他的思想是“新自然说”,倒不如说是“新性分说”。
“性分说”由“性”和“分”两部分组成,“性”是天性所授,是偶然中的必然,天性是自然生成,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人无法违背只能顺从它,具有命定意味;“分”则是“性”落实到个人之后,人对“性”的应对方式,是人的“本分”和其位于社会中的“职分”。对于陶渊明而言,“性”既是他的天性所在,也是他自我意识的体现,他不断“反本”认识自己,执着于顺应本心,回归自由天性。“分”则是他“委运任化”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他以豁达随性的态度应对人生中的必然性,追求性情的自足自乐,适性自然而不假他物。他的“性分观”从郭象脱胎而来却又不同于郭象,有其独特之处。我们先追溯“性分”之渊源。
一、“性分说”溯源
“性分”一词为郭象所创,《庄子注》中出现了十三次,是郭象“崇有”哲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概念。“性分”当脱胎于魏晋时期的“才性”问题,汉末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颠覆了汉代例行的“察举制”和“征辟制”中“用人以德”的标准,这一问题由此在汉末魏初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由于人物的评价标准在当时亟需重新构建,“才性”关系被广为讨论。前有刘劭的《人物志》将“德”与“才”并举,认为人有“五常”“五德”,把人按照才性分为“兼德”“兼才”和“偏才”。后有“才性四本”论:“(钟)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3]随着时代的转变,“才性”论由汉魏之际的以“才”为重点,逐步向以“性”为重点转移,人们的关注点从一开始的用人问题转向对“性”之本体的探求,“才性”问题于是进入了“名理学”的范畴,转为“性情”之论。王弼提出“性其情”,何晏在《论语集解》中注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4]郭象则提出“天性所受,各有本分”[5]的“性分说”。
魏晋玄学在正始时期,以何晏、王弼为首,王弼以“得意忘言”的方法提出“以无为本”,主张“崇本举末”以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至竹林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士人从宇宙论层面发展了“崇本息末”的思想,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向秀则以《难养生论》反驳嵇康所崇尚的“少私寡欲”,他把人的欲望看作“人之性”,“人之性”则为“天理自然”,并引入“自生”的概念。西晋元康时期,郭象与裴頠发展了向秀的理论,郭象取消了万物之上的更高存在形态“无”,而通过主张“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6],肯定“常有”。在否定“无”为本体的同时,郭象也需要给万物的存在找一个根本原因,于是出现了“性分”。“性分说”虽未直接回答“才性问题”,却是在这一背景下对“才性”的接续之论,既是郭象自身哲学系统的重要一环,也是他对“才性之辩”这个时代问题的个人回答。
(一)“性”之辨义
在郭象看来,万物存在的原因就是万物自身,他否定王弼所认为的更高“造物主”形态的存在,主张万物都是自生自化,万物存在所依据的根本是万物之“自性”,“物各有性,性各有极。”[7]“性”是自然形成且不可改变的,“性”的形成兼具偶然性与必然性。一方面“物各有性”的产生缘由不是来自于造物主,所以物性不同只能归结于发生状态的偶然性:“皆所以明其独生而无所资借。”[8]“死生出入,皆欻然自尔,无所由,故无所见其形。”[9]“欻然自尔”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偶然变化。而另一方面,“性”也是天生天成、人为无法改易的,所以其中又隐含着物性发生之后的必然:“性之所能,不得不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为;故圣人唯莫之制,则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10]“性”所规定的范围既包含人的自然属性,也包括人的社会属性,既是对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解释,也是对君臣有分、上下有别的阶级社会的合理性解释:“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11]
郭象将儒家伦理所规定的社会关系赋予“天理自然”的名分,用《庄子》印证“名教”的合理性。郭象迎合当时社会崇尚玄风的潮流,看似在解释《庄子》,实则是从“名教”出发对《庄子》进行重新解读,以论证“内圣外王”之道。他的“崇有论”是对“本末体用”关系的重新界定,也是对“崇本息末”思想的彻底否定,没有“无”这个“本”,“有”即是“本”,便没有本末之分、体用之别。但是同时他也要为万物的存在和变化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和理论依据,于是他归结为“物各自生”、物“性”自然,万物本身就是其存在的解释,不需要更高层面的“第一原因”。而顺物之自性即为“无待”“逍遥”,“无待”以应物则可进入个体生命独立自足的境界,即“独化”。
(二)“分”之辨义
“性”已既成,人和物应该如何对待“性”?则是人、物之“分”。“分”的出现,首先意味着物与物之间性各不相同,各有其性。每个物都是独立而自足的个体,其生死变化与他物截然分明,没有相互依待的关系:“然则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12]得之自性的人,在外部條件下不受到“道”这种于物之上的更高存在的帮助和给予,在内部条件下,自性也不受到主观上自我动作的左右,生死变化各自独立,无所依凭,自然而然。
其次,“分”是“性”落实到现实世界层面的表现,是物的“本分”与“名分”。“夫臣妾但各当其分耳,未为不足以相治也。”[13]“名分”,产自汉魏之际的“名分之理”,最初指的是在社会治理问题上,选拔人才所追求的“名实相副”,后演变为“辩名析理”的“名理之学”。郭象在这里是说臣子应当做到“臣”之名所要求的“本分”,各自守其本分,那么天下自然能够安定。“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14]郭象所称的“逍遥”境界与庄子不同,庄子认为“无所待”才能称作“逍遥”,而郭象则将“物任其性”“各当其分”称为“逍遥”,认为人要顺“性”而为,不可超出“性”的范畴,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
第三,“分”也是“性”之限制性与命定性的规定。“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15]万物的本性天成,生来固有,不能够逃避或后天去改变它。“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16]“至分”“定极”都是对“为”的限制范围,对于人而言,“性”的活动范围是有边界的,人只能在“自性”的范围之内去施为而不能超越其性。
(三)郭象“性分说”的局限性
而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到底什么是“性分”?这一点郭象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标准,可从一些例子中窥见一斑。如《马蹄》篇中郭象对马之“性分”的解读:“夫善御者,将以尽其能也。尽能在于自任,而乃走作驰步,求其过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驽骥之力,适迟疾之分,虽则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众马之性全矣。”[17]他认为马的性分不仅在于其自然属性,即庄子所说的:“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18]自然属性之外,马之真性更在于人类对马驱使得当:“马之真性,非辞鞍而恶乘,但无羡于荣华。”[19]
事实上,郭象对马“性”解读的出发点并不在马自身,而是以人本位,将人类对马的驱使强加于马身上并称之为“真性”。所谓“真性”的标准并不在于马自身,而是在于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于郭象及其所处的人类社会。“夫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虽无错于当而必自当也。”[20]这段话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以天高地卑的自然现象解释君臣上下之等级关系,说明郭象赞同儒家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并认为其如同天地存在一样理所当然;第二,郭象认为为君者为贤,为臣者只因“才不应世”,君臣分明,并且谁为君、谁为臣也是由“性分”所注定的,人们的身份等级在性分之内,生而有之,不可改易。为臣者是天生的臣,为君者也是天生的君,后天不可为超出性分的事,如臣子篡夺君位。“夫物情无极,知足者鲜。故得止不止,复逐于彼。皆疲役终身,未厌其志,死而后已。故其成功者无时可见也。”[21]郭象主张人应当知其性分而守之,当止则止,才不会陷入终身疲役中。再进一步来看,所强调的实际上就是“安命”:“夫安于命者,无往而非逍遥矣。”[22]
由此看来,郭象所谓“性分”,实质上就是将“名教”的社会关系包裹上名为“自然”的“外衣”。所谈的“性”,不仅包含了人的自然天性,更包含了对名教所推崇的社会关系、等级制度合理性的解释。并且“性”由于其“分”的限制,具有了命定论的色彩,王侯将相是天生如此,也是“性分所至”。郭象巧妙地将等级秩序、人伦职守等“名教”中的概念加于“性分”之中,赋予其内在生成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并用一种看似贴近“自然”的方式解释出来。而“性分”的具体范畴实质上是由郭象和他背后社会的高层阶级所规定的,这也就意味着郭象所说的“性分”在很大程度上与具体物的真实“天性”并不相同,甚至可能为了迎合社会的需要对其“性”进行重塑。
“大凡一个社会的存在已成为不合理的时候,当权的统治者往往要强调其统治的社会的合理性,同时某些士大夫出于其主观的愿望也会来制造现实社会合理性的哲学论证。”[23]郭象的“性分说”既是其“崇有论”哲学体系中必不可缺的一环,也是其为调和“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合理性解读之一。
二、陶渊明诗文中的“性”
及至东晋,随着佛教的广泛传入,佛教徒们在清谈中以佛释玄,“才性”问题仍然是清谈重点话题之一。《世说新语》中记载支遁和殷浩在司马昱府中谈及“才性”一事:“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24]
“才性四本”发展至东晋时期仍备受关注,《世说新语》载有殷浩于“才性”偏精:“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25]自汉末魏初之际至东晋时期,关于“性”的探讨从未停止,直至南北朝时期,“性”仍然受到重视。范晔在《后汉书》中谈及隐者之归隐原因时便以“性分”作为解释:“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26]范晔所说的“性分”来自郭象“性分”说的哲学范畴,这里是指隐逸者选择隐于山林江海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喜爱鱼鸟林草,只是各有本性,性之所好而已,因而隐逸只是守其本分。范晔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相近,东晋时期郭象的《庄子注》广为流传,“性”作为整个魏晋时代中被普遍讨论的对象,“性分说”自然也对陶渊明、范晔这些读书人产生着影响,通过对陶渊明的诗文进行分析,可以大致将其“性”分为“自我之意志”和“自然之性”两个方面。
(一)自我之意志
自我之意志即是陶渊明站在“己”之立场,通过对自身和社会外物的认识,反观自己的本来面貌,如:
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
总发抱孤念,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
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连雨独饮》)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饮酒》其九)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份,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九)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其十一)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并序)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27]
从以上诗文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具有强烈的自我意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本性所在,并且坚定地顺从于自己的意志。在陶渊明对自我本性的认知中,他是一个性“刚”之人,“刚”意味着他不愿意做违背自己心意的事情,而他的心意或者说本性,往往是不合于俗的,不合于俗而不愿融于俗,于是多将自己之性称以“孤”“介”“贞”“刚”。认识到自己与众不同至少需要两点:第一,他对自己的“性”有所了解,即“性”对于陶渊明来说是可知的;第二,对于自己的“性”,陶渊明持有肯定的态度,并对自己的本性拥有绝对的掌控权,他爱自己的孤介、贞刚之性以至于能够坚守其性而不趋流俗。
这一点与郭象对“性”的认识有所不同。郭象说:“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而横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28]郭象将“理”赋予于“性”,“理”即一事物之所以为此事物之必然性,他认为物“性”的生成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同时也是不可知、不可求而得的,因此,一个人一生中的种种身体行动与性情感知以及他所有、所无、所作、所遇的任何事情都不由于自身,而是由“性”之必然決定的。如果对这些事情产生好恶偏向,则会产生“失自然”的结果。这是一种“无我”之思维,郭象肯定“性”的绝对性的同时消解了“我”在其中的主观意志。
而陶渊明则以“有我”思维肯定“我”之“自性”,立足于“我”的意志对除“我”之外的“物”进行审视,而后得出难合于俗,即“于物多忤”的结论。无论是对自我还是对外物,陶渊明都进行了极其主观的价值判断,并具有他的价值倾向性。他对本性的认识消解了郭象的“性分说”中“天命论”的色彩,而更多地返归于自我,通过不断叩问内心、深入地自我认识从而掌握本性所在、决定本性去处,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
(二)自然之性
另一类“性”即是陶渊明将“己”融于自然之中,以更加广阔的视角反观自身,使自己回复到一种脱离世俗的自然而然的自在状态,更接近于“原初”形态,姑且将这类“性”称作“自然之性”。陶渊明在表述自然之性时常常以物我相融的方式,将自己喻为飞鸟、游鱼、孤云等脱离人类社会的生命,以更加贴近自然形态的方式表达原初的情感体悟,如: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颃,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归鸟》)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
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拟古》其三)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咏贫士》其一)[29]
这种自然之性还体现在陶渊明对人性真、淳、朴、素的追求和回返,如: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感士不遇赋》)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其二十)
三五道邈,淳风日尽,九流参差,互相推陨。(《扇上画赞》)
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桃花源记》并诗)[30]
自然之性,有着“适性自然”的特点,在陶渊明看来,正如鸟有归巢之本性,鱼有游水之本性一样,田园、丘山、自然也是他的本性所在,因此归返田园正是顺从于他的本性。这里对“性”的描述比起第一类中言自己心意之性更具有“天性”的特点,天性是生来俱有、自然而然的,也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万物面对天性只能顺从不能违背,陶渊明可以决定于自己的意志,但是无法左右天性。
从这一点上看,与郭象所主张的“不可逃,亦不可加”的“天性”有相似之处。但同时也有细微的区别,区别在于陶渊明主张的“天性”更贴近于物的自然属性,而剥离了其社会属性。以陶渊明对“鱼”和“鸟”的天性的认识为例,他认为,鸟之性在林,鱼之性在水,这无疑是动物的自然属性,与此同时又言:“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31]人类对鱼和鸟进行网罗的作为是对鱼鸟之性的伤害,同理,陶渊明认为自己的本性也在于田园不在朝堂,让他违背本性去为官也是对自己自然之性的损害。同样是动物,郭象则认为马之真性在于人类对其的役使:“马之真性,非辞鞍而恶乘,但无羡于荣华。”[32]甚至正是由于人的役使才使马之性得以全备:“若乃任驽骥之力,适迟疾之分,虽则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众马之性全矣。”[33]
马是如此,人亦然。陶这句诗暗讽东晋朝廷裁密网、制宏罗导致达人纷纷归耕隐居,对政治进行批判的同时也肯定了逃禄归耕的隐居者。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朝廷的黑暗行径才迫使有才有德之人不得已远离朝堂,隐居自保以守其性与命。而郭象对隐居却持反对态度:“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当涂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34]对于隐居的不同态度背后源于郭象与陶渊明对“性分”的不同界定,前者将人的社会属性纳入“性”,将社会分工融于“分”,所以无论是人对物的塑造还是人对人的利用归根结底都促使物或人“全性”。而后者以天生天成为“性”,追溯“性”的原始化和去人为化,即返归天性之自然形态,同时追慕上古时期真淳素朴的本性。在对自然之性的界定上,陶渊明更倾向于庄子在“至德之世”中所描绘的未经世俗污染的自然天性和儒家理想社会中的真淳民性。
三、“分”之所至与委运任化
在“性”的理解上,陶渊明与郭象有相似之处,却也有不同,那么落实到“分”上,在对“性”的实施过程中,陶渊明又表现出怎样的特点呢?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其十一)
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咏贫士》其一)
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咏贫士》其六)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其八)[35]
对待自己所难以掌控的天命、天运、死亡、未来、人事、宇宙等诸多自古以来令人伤怀又无可奈何的因素之时,陶渊明以一种豁达随性的态度应对,他任凭诸种人力范围之外的因素存在,自己只恣意随心,听任自性而为。他将这些难以掌控的因素放置于己身之外,而只掌握自己所能掌握的,只追求性情的自足自乐。
将自身看作独立自足的个体,不为外物所扰的思想受到郭象“独化”论的影响。郭象所说:“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36]“玄冥之境”是物“自生自化”的精神场所,也是“独化之至”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意味着绝对的独立,物与物之间各自生化,不受外物影响,在“玄冥之境”中,“有”是根本也是唯一永恒的存在,因此所有存在于“有”之中的对立概念都将各自消解,无论是“朝”还是“野”,无论是“外”还是“内”都将不再对立,并且以“有”为基石融于一体。进而等同“内圣”与“外王”、“游外”与“弘内”,最后可证“名教”合于“自然”。
当然,陶渊明并没有将这些对立概念的界限完全消解,从他与郭象对“游外”与“游内”的认识可知。郭象说:“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37]郭象认为“内外相及”,圣人形体劳使却神气自如,处理俗务却能淡然自若,通俗地说就是身在朝堂、心于山林而逍遥自得。陶渊明无疑不认同也做不到,他认为“内外不相及”,并认为这是“以心为形役”的做法,多次归田也能反映出他无法将“游外”与“弘内”等同看待。同时陶渊明却能做到“心远地自偏”,这也是他守其性分、自足自乐的表现,“分”是他体认自我本性之后认为自己所应守的职分,任其“性分”的豁达随性实际上就是他委运任化人生观的外在表现。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
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其十五)
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于王抚军座送客》)
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
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38]
陶渊明对待人生的态度可以总结为“委运任化”,这既是他的人生观,也是他应对具有必然性的“性”时,所为之“分”。“分”是他认为自身所能达到的层级,既是天性所然,也是天赋所致,因此认清之后需要委之于运。“委运”之“运”指的是天运、天理,也指一切自然变化着的事物其中的必然性。面对无法左右的必然,陶渊明以顺遂“天道”、乐天安命的方式开解自己,他认为万物“化迁”,不能左右,因此不能通过修炼长生等方式阻碍“化”来达到“形尽神不灭”的境界,同时也不能通过皈依佛教、不以情累神而达到“神不灭”。
委运任化可追溯至庄子,《德充符》一篇中庄子假托孔子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生死变化的看法:“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庄子认为若能“守其宗”,即保全自我之精神,则可达到不为物迁的境界。郭象注曰:“人虽日变,然死生之变,变之大者也。彼与变俱,故死生不变于彼。”人变,死生亦变,若人能与化共往,那么相对于死生就没有变化。
四、从“性分说”看“新自然说”的“孤明先发”
“性分说”之外,诸多学者都曾以不同视角探讨过陶渊明与郭象之异同。徐声扬在《也谈陶渊明的哲学思考──兼与袁行霈先生商榷》一文中提到袁行霈先生认为“陶渊明就是代表老庄和郭象讲话的”[39],他自己则站在“自然”的角度解释陶渊明与郭象之异同,提出陶渊明受郭象的哲学思想影响很深的同时,二者却对“自然”的理解不同:“陶渊明所谓的‘自然,不同于郭象所谓的‘自然而另有概念。”[40]龚斌在《陶渊明传论》中认为陶渊明委运任化的人生观来源于庄子和郭象哲学中的“与化推移”义,并论证了“新自然说”之“新”在于陶渊明“扬弃了神仙长生之说和借名教以求富贵的虚伪哲学”[41]。李昌舒在《自然与自由——论陶渊明“自然说”与郭象哲学的关系》中从陶渊明任运自然的人生态度出发,通过《形影神》组诗分析陶渊明之“自然”与郭象及庄子的异同,认为郭象与陶渊明都具有“自然而自由”[42]的思想。蔡彦峰在《玄学与陶渊明诗歌考论》中提到郭象的“独化论”影响了陶渊明的“自然观”及其思想中有关“真”的概念,且其委运任化的人生观也是受到郭象“与化为体”玄学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所以陶渊明的‘新自然说又无法脱离道家和玄学的影响,特别是郭象玄学成为陶渊明‘自然观的主要思想渊源。”[43]那么从“性分说”的角度,陶渊明诗文中之“性分”既有对郭象“性分说”的继承,又有新的发展。就其诗文中所表现的“性分”来看,回归到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新自然说”上,郭象之后的陶渊明是否还能够被称为“新自然说”之“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者呢?
从前文引述陈寅恪先生对“新自然说”的解释来看,“新自然说”的表现有两点,一是“不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郭象和陶渊明都符合这一点,陶渊明以委运任化的人生观处事,他随性而为,欲仕则仕、欲隐则隐;郭象喜好弄权,且其学说也是为了“明内圣外王之道”,因此自然不会抵触名教。另一点是:不养“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这里涉及到陶渊明的生死观,试对郭象和陶渊明的生死观分别进行分析。郭象的生死观建立在其“独化”理论上:
卓者,独化之谓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则死生变化,惟命之从也。[44]
“独化论”又是“性分说”引申的更高范畴,若一物能守其“性分”,为“性分”要求之内的事,便是“无为”,为“无为”意味着物可“自足其性”,一旦“性”各自满足,那么所有物的生长死亡过程都是独立自足且无待于他物的,物和人只需顺应这种自然而然的变化过程,任其自化,“无心以顺物”便可达“玄冥之境”,即“独化之至”。以“独化”来看物的死生,由于每个物都能独立自足,所以物的生死变迁也是各自独立的,一物之生死并不由他物决定。就此物来看,他的存在源于“有”而非“无”,那么他的死亡亦不能变为“无”,因为“有”“无”并不能相因,“无”在郭象的哲学体系中就意味着“无意义”:“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45]换句话说,“有”是事物常存的状态,那么所谓“生”“死”则都是长久地处于“有”这个状态中的不同形态。就算是“死亡”,也只意味着事物形态的改变,这个事物仍然独立自足地处于“有”中,“生”和“死”共同处于“有”的语境下并没有任何分别,因此人只需同等地看待生死,“夫圣人游于变化之涂,放于日新之流,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化者无极,亦与之无极,谁得遁之哉!夫于生为亡而于死为存,则何时而非存哉!”[46]
陶渊明对“化”的认识与郭象有所不同。郭象认为物化无尽,常有不尽:“夫有不得变而为无,故一受成形,则化尽无期也。”[47]而陶渊明虽然也认同人之生死寿夭自有“性分”,但他同时也认为大化有尽头,也会终结,人死了就是空无,就是什么也不存在的“尽”,所以陶渊明言“形尽神灭”“应尽便尽”,认为人应该直视变化的尽头,即死亡本身。“任化”的含义一方面在于对“化”的客观存在的肯定,即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包括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這种变化是必然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逃避。另一方面在于面对“化”,人应该放任自流,以顺其自然的态度淡然地面对,而不能试图通过修仙以图长生或是求佛以求神不灭的诸种方式避免。陶渊明以一种更为坚决的姿态肯定死亡与尽头,从这一点上看,他委运任化的人生观与前代确有不同。一方面,他虽认同郭象之“性分说”,认为生死祸福各由“自然”,但却否定了郭象的“常有”论,认为物有尽头、应尽须尽,不把无可预知的死后未来当做可以了解的对象,而只将全部关注集中于“生”。另一方面,主张“形尽神灭”论的陶渊明自然不认同“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
由此看来,陈寅恪先生所主张的陶渊明“新自然说”确有其“新”所在,但“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的表述似乎不太贴切,因为陶渊明并不认为精神可以永恒存在,更不认为死亡之后精神会融合于自然界。而郭象却持有这一观点,如前文所说,郭象所持的“常有”观点决定了“有”之永恒存在,那么人若能守其“性分”进而“独化”于“玄冥之境”,生死之对立性自然得以消解,人纵使是死亡也处于“有”之状态,“化尽无期”乃至“存亡更在于心之所(措)耳,天下竟无存亡”[48],自不必“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只需守其性分,在“常有”的状态下自然得以“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若引以上种种为据,郭象的思想可以说符合了“新自然说”的第二点立论,即:
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49]
如果单从这一点上来看,郭象确实比陶渊明更早地创造了“新自然说”,更是“孤明先发”者。而从陈寅恪对“自然说”的定义上来看,郭象的思想并不能称作“自然说”:
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50]
原因有两点,其一,郭象在《庄子序》中所言明的他作《庄子注》的论点:“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51]他的目的是“明内圣外王之道”,在郭象的哲学体系中,他将内圣、外王等同起来,认为二者没有分别,即所谓“内外相冥”:“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52]他将内圣外王背后的自然和名教等同起来,这并不属于“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之“自然说”的范畴。其二,郭象本人并不像陶渊明那样不与政治势力合作,恰恰相反,他不但积极与之合作,更喜权势,《晋书·郭象传》说:“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53]《晋书·荀晞传》也提到:“东海王越得以宗臣遂执朝政,委任邪佞,宠树奸党,至使前长史潘滔、从事中郎毕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权,刑赏由己。”[54]《世说新语》中亦载:“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55]其中更引《名士传》曰:“郭象字子玄,自黄门郎为太傅主簿,任事用势,倾动一府。”[56]郭象虽口谈玄远,而其人却热衷于追逐名利与权势,被时人所诟病。从他的行为上看,更倾向于名教而非自然。因此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郭象都不能被称作陈寅恪所定义“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的“自然说”。
既然郭象的思想并不属于“自然说”,当然也就不能说郭象比陶渊明更早地创造了“新自然说”。而从“性分说”的角度来看,陶渊明确实在郭象的“性分说”的基础上进行了“旧义革新”。在“性”方面,既突破了郭象所言天命之“性”的束缚,重新回归到人本身,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同时又剥离了郭象“性分说”中的社会属性,主张原始化和去人为化,重新复归至庄子笔下的天然之性,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无束缚。在“分”方面,则以委运任化的生命观应对“性”的无可奈何之处,用“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应对古今生死困境,追求性情的自足自适,“乐天委分,以至百年。”[57]相较于郭象,陶渊明之“性分”更为关注人之自足而非社会之自足,更加重视个体精神自由而非社会运行的逻辑自洽,并且“性分”不仅在他的诗文中多有体现,更在他的人生过程中得以印证和践履,具有独特的精神烙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陶渊明的“新自然说”又可以称得上是“旧义革新”“孤明先发”了。而陶渊明的思想称为“新性分说”或许更为合适。
参考文献:
[1][27][49][50]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56-57.
[2][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8][32][33][34][36][37][44][45][46][47][48][51][52]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3-823.
[3][24][25][55][5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214-480.
[4]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74.
[23]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6.
[2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809.
[29][30][31][35][38][57]陶渊明著,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22:33-546.
[39][40]徐声扬.也谈陶渊明的哲学思考——兼与袁行霈先生商榷[J].九江师专学报,1999(2):69-76.
[41]龔斌.陶渊明传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37.
[42]李昌舒.自然与自由——论陶渊明“自然说”与郭象哲学的关系[J].江淮论坛,2005(1):71-75.
[43]蔡彦峰.玄学与陶渊明诗歌考论[J].中国韵文学刊,2013(1):14-19.
[53][54]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97-1669.
(责任编辑 吴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