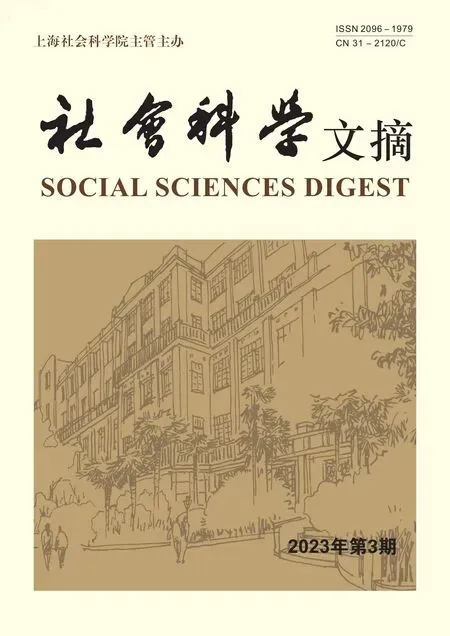论二里头乃夏朝后期王都及“夏”与“中国”
文/王震中
二里头遗址乃王都遗址,这在学术界并无异议。但它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说一度多种观点并存,但争论最主要聚焦于两种观点:一种主张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第一至第三期为夏代、第四期为商代;一种主张二里头第一至第四期均为夏代。然而,2005年以后,由于所谓“系列拟合”测年数据的提出,关于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又出现了新的争论。目前争论的焦点有三:其一,二里头遗址碳十四测定的年代与夏商两朝之关系问题;其二,二里头的地望与文献记载的夏都和商都所在地的关系问题;其三,如何解释二里头第四期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其已进入商朝纪年,而二里头第四期还新建有宫殿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三个方面的新争论,主要是近年来对二里头遗址的碳十四测年的数据的处理,前后发生了变化。面对这些新情况,本文欲全方位论证二里头乃夏朝后期王都,并进一步回答“中国”一词概念的前后演变以及“夏”与“中国”之渊源关系问题。
二里头王都的时代处于夏代晚期范围
(一)文献上夏朝年代范围
关于夏王朝的年代范围,一般认为是距今4000年至3600年,其中距今3600年是夏朝与商朝的分界,“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商之间的划界也是如此。夏商划界之年甚为关键,3600年是一个约数,若从文献的角度来看,夏商分界以及夏朝纪年主要有三种计算的结果。其一,依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夏朝从开始到结束的年代应该是公元前1994—前1523年,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其二,由公元前1027年的武王克商之年,再加上526年的商积年(《竹书记年》所言“二十九王”在位496年+帝辛在位30年),就是成汤灭夏之年——公元前1553年。再加上夏代471年,则夏朝开始的年代是公元前2024年,其结束的年代是公元前1553年。其三,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把武王克商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046年,并且对商朝的积年取526年而不是496年,再加上夏朝471年的积年,则夏代从开始到结束的年代应该是公元前2043—公元前1572年。
依据上述三种计算结果,笔者不主张夏商分界的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而是认为:或者是公元前1523年,或者是公元前1553年,或者是公元前1572年。这比公元前1600年向后推移了28~77年,而这样的推移,对推定二里头第三期乃至第四期究竟是在夏朝还是在商朝的年代范围是重要的。笔者倾向于认为夏朝从开始到结束的年代很有可能是公元前2024年至公元前1553年,因为《孟子》所说的“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与《史记·殷本纪》商代三十王之数,是相匹配的。依此,夏朝和商朝划界的年代可从公元前1600年下移约50年。
(二)二里头遗址碳十四“系列拟合”测年数据
就最新碳十四测定的二里头遗址的年代而论,对于二里头第一期的97VT3H58测年数据,碳十四测年专家曾拟合过两次,但这两次拟合的结果是不同的。一次是把它与二里头遗址2005—2006年测定的属于二里头第一、二期之交及二里头第二期的一些数据,同断代工程中测定的一些数据放在一起进行的拟合,即把二里头遗址本身的第一至五期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的拟合,其拟合的结果是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885—公元前1840年。另一次是把新砦遗址的龙山晚期和新砦期的数据与二里头遗址第一至五期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的拟合,其结果是二里头第一期的97VT3H58测年数据被拟合为公元前1735—公元前1705年。对于这两个所谓“系列数据的拟合”,笔者比较相信前一个结果,因为后者虽然有二里头第一期之前的测年数据,但这些不是二里头遗址的数据,而是新砦遗址的数据,它们与二里头遗址的那些数据根本没有地层上的叠压关系,拟合的条件是不理想的。特别是后一种拟合对于新砦期与二里头第一期之间的关系采用了二者是前后期关系的观点,殊不知有学者研究二者是同期关系,因而其拟合的可信度是有疑问的。
以《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二里头遗址碳十四测年“拟合后日历年代”数据,以及2005—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采自二里头遗址的18个木炭样品测定的数据为依据,以“二里头第一至五期拟合结果”为参考,对二里头遗址第一至四期的年代进行重新整理可知:二里头遗址第一期年代的上限应不超过公元前1880年,下限应不低于公元前1780年;第二期年代的上限应不超过公元前1780年,下限应不低于公元前1670年;第三期年代的上限应不超过公元前1670年,下限应不低于公元前1590年;第四期年代的上限应不超过公元前1590年,下限应不低于公元前1520年。二里头第一期至第四期约有360年的历年。
(三)碳十四测年与夏朝早、中、晚三期年代框架关系
若以前述公元前2024—公元前1553年作为夏朝从开始到结束的年代,对于这471年的夏朝积年,以早、中、晚三期来划分,每期约为157年,那么,夏朝早期应该是公元前2024—公元前1867年,中期应是公元前1867—公元前1710年,晚期应是公元前1710—公元前1553年。对照二里头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二里头遗址第一期(公元前1880—公元前1780年)大约在夏朝中期的范围;二里头第二期(公元前1780—公元前1670年)约在夏朝中期晚段至晚期前段;二里头第三期(公元前1670—公元前1590年)约为夏朝晚期后段;二里头第四期(公元前1590—公元前1520年),其部分已进入商代初年的范围。
二里头遗址地望与夏都之关系
(一)二里头遗址地望与夏王都之关系
关于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域内与夏人传说相关的地望,邹衡先生进行过全面系统的考证。其中与二里头遗址地望关系最密切的有:斟寻、伊洛、洛汭以及由“夏桀之国”所标示的后世所谓“王畿”之地等。二里头遗址的位置与斟寻的地望大体吻合。伊洛和洛汭,也是既与太康有关,又与夏桀有关。所谓“夏桀之国”,即战国时吴起说的夏的王畿之地,其核心区域恰恰是伊洛河内的二里头遗址所在的区域,这与二里头遗址乃夏朝中期晚段至晚期王都的推定是完全一致的。
(二)二里头不可能是“汤都亳”
从文献上看,商汤推翻夏朝后,在夏朝的腹地修建了都城,但并未建在夏都的旧址上。二里头遗址第二期的年代不在商朝的年代范围内,无论依据碳十四测年原本的数据还是拟合后的数据,即便是主张二里头主体为商文化说者,也只能从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开始把它作为商都。这就要求成汤推翻夏朝后必须以原夏都为自己的商都。然而,文献上没有成汤推翻夏朝后以原来的夏都为王都的记载,而是说成汤离开了夏都,又回到了亳邑。《史记·殷本纪》说:“(汤)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尚书·商书》也说:“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按照“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为殷都说”(或“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为商文化说”),作为都城的二里头遗址第二期属于夏都,从第三期开始变为商都,商汤只能把原来的夏都作为自己的商都了,这岂不与《史记·殷本纪》和《尚书·商书》的记载完全矛盾了吗?由此,也可以认为二里头不是“汤都亳”。
“商汤未迁夏社”与二里头的龙崇拜佐证其为夏都
(一)“商汤未迁夏社”与二里头第四期宫殿之关系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了从第四期开始修建的宫殿,例如6号夯土建筑基址等就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此外,诸如制造绿松石的作坊等遗存也一直延续使用到二里头第四期偏晚阶段,而第四期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属于商代初期。为此,有学者这样质疑:如果二里头是夏都,那么为什么夏朝已经灭亡了还在修建宫殿?这似乎难以理解。殊不知,二里头遗址第四期的居民作为进入商朝的夏遗民,其贵族并没有被剥夺在自己的居住地修建宫殿的权利,而这又可得到文献上的证明。
在历史文献中,商汤推翻夏王朝后,夏邑没有被毁灭是有线索可寻的。除上文所述《史记·殷本纪》和《尚书·商书》外,《史记·封禅书》曰:“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可见,商汤推翻夏王朝后,本想迁移夏社,但因“不可”而没有这样做,只是在夏邑作了一篇《夏社》。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商汤战胜夏桀后,既然连夏邑里的夏社都未迁移和毁坏,那么,对夏邑里的宫殿、手工业作坊等建筑物,当然也不会加以毁灭破坏。其二,若是迁夏社,便意味着连同夏都的夏人一并迁走;没有迁夏社,也就意味着夏都的夏人可以继续生活在这里,并祭祀自己的社神。
所以,有关商汤推翻夏朝后并未“迁夏社”的记载,完全可以说明夏桀的后裔和夏遗民依然生活在原来的夏都之中。这就意味着偃师商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都在二里冈下层时期成为商代前期的都城——形成“两京制”,而二里头的夏邑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不但原有的一些宫室得到延续使用,还建了新的宫室。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二里头遗址的夏遗民与新建的偃师商城并存,是不难理解的。
(二)二里头出土的龙形器可佐证其为夏都
二里头遗址先后发现许多带有龙形纹样的陶器和用绿松石片粘嵌的龙形器。最著名的是一件用绿松石片粘嵌的龙形器,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这条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龙,呈现出巨头、蜷尾、波状的龙身,是一条蛇形龙。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的文化特征,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它可以作为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的佐证。
在文献上,夏王族即夏后氏,对蛇形之龙的崇拜十分突出。例如,夏禹之“禹”的字形就是蛇形之龙,禹的蛇形龙图腾后来也成为夏王族的图腾。《列子·黄帝篇》说:“夏后氏蛇身人面。”说的就是蛇形龙是夏王族图腾。夏族姒姓,也可说明蛇形龙是其重要图腾。丁山考证“姒”字初形实即厶(私之古文),说它“象蛇身自环,史言禹为娰姓,无异言禹本蛇身……然则夏后氏祖禹而姒姓,当演自以蛇为图腾之神话”。此外,《国语·郑语》说:“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姒姓褒国两位先君“化为二龙”的神话,显然也是夏王族以龙为图腾传说的反映。
总之,从文献上看,夏族基于以蛇形龙为图腾而产生的崇拜是其文化的特质之一。在没有本朝文字记载本朝史事的情况下,二里头遗址一种重要的文化特质——对于蛇形龙的崇拜——在与文献记载相联系之后,所说明的问题凸显出更为重大的价值,完全可以作为二里头是夏代王都的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夏”与“中国”
(一)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与“华夏”
从秦汉至明清,“中国”一词已用来指称“大一统”的帝制王朝国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秦汉以来的各个朝代,“中国”所统辖的“边疆”区域时有伸缩,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但基本框架却是稳定的。而从秦汉上溯到春秋战国,“中国”这一概念,既指中原地区,亦指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民族。春秋战国时期,频繁出现的“华”“夏”“诸夏”“华夏”诸词,是已成为“自觉民族”的华夏民族的自称和他称。
(二)夏都之地域乃“最初的中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从西周上溯到商代,甲骨文中没有“国”字,也没有“中国”一词。但后来的周人却把殷商直接统治的地方称为“中国”,即商的王邦之地。从商代上溯到夏代,《何尊》所说的“中国”就是洛邑附近的“有夏之居”——夏代王都所在地。从《何尊》《逸周书·度邑解》和《史记·周本纪》来看,周武王和周公旦都是把作为洛邑的“中国”与曾经的“夏都”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目前我们从《何尊》“中国”向前追溯最为清楚的一点。
《说文解字注》说“夏,中国之人也”,既说出了地理上“夏”与“中国”之关系,亦体现了夏朝在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华夏民族称谓的“夏”“华”“华夏”“诸夏”中,“夏”字占有核心位置,是关键词。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华夏民族的形成是从夏朝起始的。
关于华夏民族的形成,以往主流的说法鉴于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华夏民族自称和他称的“夏”“华”“华夏”“诸夏”的频繁出现,认为华夏民族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然而,恰恰是在春秋时期,中原开始出现戎狄杂处、受戎狄侵扰的情况,而且有时事态还很严重,从而产生“华夷之辨”的现实问题,并通过“夏”“华”“华夏”“诸夏”与戎狄的对比,表现出华夏民族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为民族自觉的呈现,因而此时的华夏民族属于“自觉民族”。在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自觉民族”之前还有一个“自在民族”的发展阶段,而夏商时期出现的华夏民族就属于“自在民族”。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夏代形成,就在于夏王朝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这一复合制结构在政治实体上,既包含夏的王邦,也包括其他诸侯邦国;在民族组成上,不仅有夏部族,还包含众多的其他部族。而受夏王支配的夏朝疆域,特别是其核心地区中原,则是此时华夏民族的共同地域。
说到复合制结构,《何尊》“中国”恰恰表现出这种结构关系——“中国”是周王朝的中央之都城和中央之地域,它的外围有“东国”“南国”,以及“东土”“南土”“北土”“西土”等。在“中国”一词概念的演变中,《何尊》“中国”是最早的文字记录,其含义也表现出三代王朝国家的结构关系。从《何尊》“中国”向上追溯,无论是从其结构关系而言,还是从先秦秦汉人们对“夏”与“中国”相关联的认知而言,都可以得出“有夏之居”——夏朝的王都所在地——才是“最初的中国”。
就现有的证据看,笔者以为将二里头王都遗址中的第二期和第三期遗迹推论为夏代中期晚段至夏代晚期的夏都遗迹是最合理的,也是有说服力的。只有当二里头王都与夏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用二里头遗址来解说“最早的中国”以及“何以中国”,才较为彻底,才合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