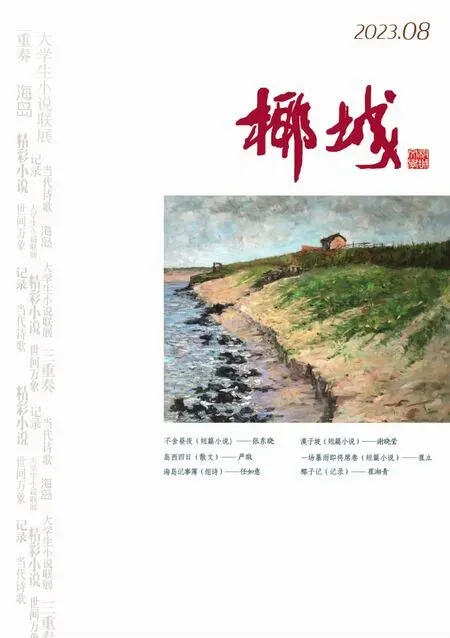流逝与不安
◎广 奈
使我感到不安的事物有很多,比如读到一首缺行的诗,不知如何将它填补完整;下雨天偶遇一只浑身泥泞的狗,看似目标坚定却又不顾东西地乱撞;在餐厅不小心打翻了盘子,面对碎片折射的反光,常使我面红耳赤瞬间结冰;又或者,坐地铁时不好意思向拥堵的人群借过,只好坐到下一站再折返。总是这样,生活使我局促。
因此,我对地铁不曾抱有太多好感。如果能步行,我当然不会选择乘地铁,不过这种想法在上海几乎不可能实现。“走路的奢侈”只存在于四五线城市,如同我的家乡南充,不管政府修了多少新干道,我永远只是在那几条老路上重复穿行,连接着父母的小店与我的学校,嘉陵江的夜景,充满火锅味的南门。亦或是我生活了四年的雅安,一年三百多天都浸在雨里,从地图上看,整座城市似乎只有沿江的两条主干道,一条属于老城,一条通向新区,去哪里都不必着急。毕竟,生活在只需十块钱出租车费就能游览全城的地方,太快到达目的地,反而会产生若有所失的遗憾。我就这样在小城镇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散漫日子,跟时间互相消磨着,不用考虑未来,脑海中没有世界的具体形象,对遥远的城市一概只熟悉名字,所向往的远方也仅是离家两百公里左右的成都和重庆。而我却误打误撞来到了上海,就像失足掉入卡尔维诺笔下千奇百怪的城市,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那些生活记忆迅速处于流逝的状态,让我来不及追踪,就已消失。
我不得不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体验大城市的生活,这种体验往往带着尴尬和讽刺意味,它们一步步瓦解我年少的幻想,将我朝着漩涡深处推进。如果我说我对城市最初的向往来自于地铁,这一定是句诚实的话。构建一个地下世界对男孩子来说充满了新奇挑战,尤其是生活在没有地铁没有防空洞甚至连地下超市都无比稀少的地方,想象毗邻地狱的管道在城市内部联通,好像抵达了某个奇境。在那里,石头印压出远古时代的花纹,鸟的尸体、恐龙残骸都有异变的可能,越接近地球核心越吸引着我去探索,能在地下行驶的列车自然成了巨兽复活的象征。小时候和朋友看《哆啦A梦》,大雄的父亲每日挤地铁上下班的场景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那时我还不曾想过“作为一个父亲的忙碌”和“成为一个‘社畜’的辛苦”,只觉得每天都能坐地铁是一件遥远而幸福的事。在地下幽暗处挖掘密道,有了光,有了列车进站时的呼啸声,自由穿梭其间,好像在玩一项隐秘的躲藏游戏,化身一条巨蛇逃向别处,令我催生告别平庸生活的强烈渴望。地铁与时光机、任意门有着同一种魔力,它们在小孩子眼中属于奇迹,瞬间便能到达远方。
可在真正遭遇了地底冷气无情的对待、一片拥挤的人群混杂着死寂的沉默后,我丧失了对地铁的热情。它像一条代沟,不断拉远我和城市的距离,却又像个野兽四处开口,等着我自投罗网。我第一次坐地铁是在成都,不会买票进站,不知道如何换乘,理所当然地以为需在中途出站买另一条线路的车票再进站换乘,在地下错乱盘旋,胆战心惊地寻找出口,还担心闸机出故障无法出去会被人怀疑逃票,总之是难堪的体验。我渐渐理解了那些害怕弄脏座位而只好坐在地上的工人,他们和那时的我一样,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如何去接近一个大城市,对我来说,过程往往伴随着内心的焦虑与不安。
我学会了乘地铁,听上去是件不值得骄傲反而还有点可笑的事。但是,所有结果看似简单的事情,我总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适应。骑自行车、安装电脑、洗袜子、垃圾分类、买咖啡、认识新朋友、在领导面前说话不打颤、拒绝别人、适应沉默气氛……这些微小事件,常令我苦恼,最后也都慢慢习惯了。只是关于地铁,有一件事我始终不能适应——它总会让我感到疲惫。地铁就像一个有生命的物体,将人们的活力完全吞噬,只要进入其中,我就会立刻困倦。它封闭了外部世界的所有景象,人们只能在地下想象头顶的城市布局,根据站名,做出微妙反应。我相信不会有人比我更无聊了,企图闭上眼睛构想出一个新世界,以此抵消现实的落寞。从地铁关门启动的那一刻,直到列车停靠,行驶的声音被我拆分成许多细小的碎片:风声、海浪声、天鹅划过水面、冰块破裂的瞬间、银杏叶落在地面、爱人密切亲吻、烟头熄灭……这样看似能让我感到安心,但其实,通常情况下闭上眼睛只会让我更容易睡着,所有短暂的想象都抵挡不了困倦侵袭。而地铁,无疑是令我疲倦的根源。我体会到了作为一只‘社畜’的累,再精致的幻象都显得疲惫。有次夜里坐八号线回学校,我睡得肆无忌惮,醒来时发现车里空无一人,晃动的车厢被黑暗包裹,唯有我周围明亮而耀眼,顿时激起时空错乱的恐慌。朝着列车前进的方向望过去,似乎会有什么不明物体立刻蹦出来。明明是回到熟悉的地方,我却觉得莫名荒凉,不知道自己会到哪里去,如同被世界抛弃了一般。所幸我成功到达了终点站,返校的公交车已停运,只好回程坐到江月路搭另一班公交。不断与目的靠近又不断远离,大概是这座城市有意在为我设计迷途,必定要我去面对各种不安与困倦。佩索阿曾在《不安之书》中写道:“启程的地方不是我认识的港口,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港口,因为我还不曾到过那里。而且,我这仪式性的旅行,目的是寻找不存在的港口——所谓港口,只是一个进入点或者被遗忘的河口或者跨越不能抵达的虚伪城市的海峡。”或许我可以把这港口变成地铁口,用来理解我的不安,解释我对城市与地铁的排斥心理。我曾进入许多陌生的地铁站,但我都已遗忘。从不认识的地方启程,一路省略所有风景,忽略地面千万条道路,直至另一个“港口”下车,就是这样,地铁的意义不是经过,不是抵达,仅仅在于偶然连接陌生的两端,它只是一项交通工具,消磨了我的童年梦想。
我曾以为,不安会永远伴随我。而我却渐渐习惯了刻薄,习惯了在出站后点上一根烟假装深沉,习惯用冷漠的面孔看着比我更冷漠的事物——建筑在人群中发霉,等待坍塌之日,一切的坚固看上去都脆弱易碎。我熟悉了不同城市的生活节奏,从容地进出公共空间,乘坐地铁时也不再慌张。成都的地铁总是冰冷的,夏日站在地铁口冷气不停地往外冒;重庆的轻轨大多建在地上,沿着江北到市区,夜景尤其美丽;武汉的地铁像是半途而废的工业园区,拥挤的人潮混入极其不便的交通设施,屋顶天花板吊儿郎当地遮遮掩掩;西安的地铁倒是有特色,一股子温厚的中原味;厦门的地铁崭新,然而线路太少,总是无法抵达想去的地方;至于上海的地铁,似乎孕育着忧郁情绪,每次乘坐八号线,车厢里都带有海潮湿热的霉味,车窗外郊区景色颓废地晃过眼前,两个烟囱苟延残喘地冒出废气,天空辽阔,没有山脉阻挡视野。一排破旧的平板房上挂着漏字招牌,屋顶郁积着远处扩散而来的工业灰,宛如一个大型贫民窟,实在无法将这块土地与“上海”联系在一起。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将自己与上海联系起来,我知道自己迟早会离开它,这只是我临时经过的一个地方,没有生活,也没有属于生活的事物,连生活的象征也不存在——我熟悉的路边摊、麻将馆、茶馆播放着抗战电影,河水流过鹅卵石,有人在其间游泳,人们累了便去树下休息,山比夜空还要黑,可是满城烟火味总不会让人寂寞——这些景象我很久未再见到,夜晚也没有熟悉的人沿着江岸散步,我确实想象不出自己对上海有多少热爱,甚至,我会比这座城市更刻薄更冷面无情——不是它在拒绝我,而是我有意与它保持距离。
我想起离家前那段时间,母亲总说想陪我一起去上海,把我安全送到学校。我说我知道怎么走,去过了几次哪里会迷路。母亲在一旁说,我是想送送你,顺便去看看你小姨,她在闵行的饼干厂打工,可以去看看她。母亲计划着如何与数年未见的妹妹相遇,讲述生活多少变迁。后来,她叹气说,可是我不会坐地铁,认不得路。我立刻想起了自己第一次乘地铁时的窘迫,这类属于城市的庞然大物,必定会让母亲感到恐惧,不知如何靠近。更何况,对手机导航一窍不通、又分不清方向的她难免会产生与世隔绝般的不安。我说,我教你怎么买票,很简单,到时候我把你送到火车站我再回学校。母亲变得忧愁起来,她说,我本来是想让你更轻松的,现在想想反而在给你添麻烦,反而让你来照顾我了。后来,母亲打消了陪我去上海的念头。她说,就把我的车费当作你的生活费吧。她始终没有离开家乡,对别人来说,最简单的生活甚至令人鄙视的生活方式,却是母亲不敢接触的幻想。地铁这道沟壑,在她与大城市之间划清了界限。《寄生虫》里被富人嘲讽的穷人身上的地铁味,或许是许多从未见过地铁还抱持敬畏愿望的人永远无法企及的生活终点。一直以来,我都期待着能够陪伴父母坐一次地铁,不管是在成都还是上海,从一个陌生的站口启程,为他们买好票,他们只需紧紧跟随我,呼吸来自地层的空气,在化石拼凑的地下迷宫周游,漫无目的换乘到另一条线路,好似走在一个辉煌的宫殿,一个只属于我们的世界,也许是朝向未来,也许是回到过去,听着野兽发出呼嚎声,宛如坐在时光机上,正在追赶流逝的时间,漫漫长途,最终抵达另一个陌生的港口,我们下车。然后我会不经意地说,看吧,其实也就是这样。不过越是简单的愿望越难以说出口,甚至有被人误解的嫌疑。
有时候我觉得,或许,我才是《哆啦A梦》中的父亲,承载他们的希望,在未知的城市里坐着地铁胡乱奔走。只要回到家,我就会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似乎我们都曾幸福地活着,似乎我已谙熟了一切遥远而陌生的路途。然而,只有我自己知道,在不断流逝的记忆里,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不管我已到达了多遥远的地方,使我内心安宁的永远是那走过了千百回的小街,空中飘着辣味,地沟油酸臭地流进肺里,菜市门口黄葛树遮住了月光,而我不再是旅人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