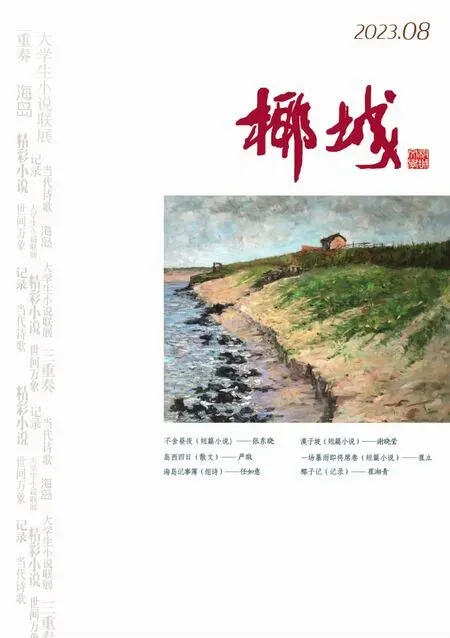西西弗斯的石头(评论)
◎石凌
读完张东晓的短篇小说《不舍昼夜》,我一下子想到希腊神话里的悲剧英雄西西弗斯推着巨石上山的故事。西西弗斯因为绑架了死神而触犯了众神,诸神惩罚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巨石横在西西弗斯前行的路上,如果他不推着巨石上山就寸步难行。每一次,西西弗斯推着巨石即将登上山顶时,石头就会滚下山脚,他又得重新开始,一遍又一遍,周而复始,不舍昼夜。西西弗斯推着巨石上山的故事既是隐喻也是宿命。当一个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无力改变命运的时候,他只有坦然接受命运。古今中外的作家对西西弗斯有不同的解读,在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之前,西西弗斯一直是被歌颂的悲剧英雄,他是敢于挑战死神的勇者,他日复一日推着石头上山,尽管是徒劳的没有意义的,他却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锲而不舍地进行这周而复始的劳作,这种坚持就是一种生活态度。海明威更是将这种硬汉形象发挥到极致,他在《老人与海》中创造的桑地亚哥形象就是西西弗斯的另一个版本,老渔夫桑地亚哥一次又一次出海捕鱼,徒劳无获,最后一次还差点被鲨鱼掀翻小船葬身海地,但他勇敢地杀死了鲨鱼,把命运的绳索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从西西弗斯身上看到了人生的荒谬,存在的荒诞,创作了散文《西西弗斯的神话》。在加缪笔下,西西弗斯不再是神,而是人类生活荒谬性的人格化。人无法抗拒宿命,巨石是横在西西弗斯前行路上的障碍,负担,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巨石,巨石是西西弗斯无法摆脱的宿命。反观现实,每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几乎都是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的翻版。面对生活的重担,如果你不咬紧牙根撑着,就可能被这巨石压弯了腰,甚至压得趴下。
小说《不舍昼夜》是作家张东晓向加缪致敬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子俊就像被迫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人到中年的子俊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位即将下岗女人的丈夫,一位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的老人的儿子……现实要求他做家里的顶梁柱、亲人的避风港。实际上,子俊是一个无力担当重压又无处躲藏生存困境的病人。他出身寒微,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学,为他成了家。父亲为供养他上学读书、成家立业熬干了血汗,晚年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需要做搭桥手术,子俊作为儿子却无力负担父亲的手术费。在父母面前,子俊是一个被宠溺者,又是一个逃避者。作为家里的男孩,他在成长过程中格外受到父母的宠爱。当父母晚年需要赡养时,他却因经济拮据一再逃避现实,把赡养老人的义务推给两个姐姐。作为儿子,他既没有在父亲的病榻前照顾,也无力负担父亲手术的高昂费用。小说以生动的细节描写揭示子俊矛盾而痛苦的内心。“走到路口,子俊猛然撞见一头白发。他顿时一怔,脑中轰然响起一记闷雷。他的身子很明显地抖了三抖,几乎跌倒。”当姐姐打电话告诉他父亲的病情时,他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让姐姐劝母亲不要太积极缴费。在父母面前,子俊是一个立不起来的弱者。面对一双儿女,子俊努力想表现自己作为父亲的的责任与担当。但是,当孩子向他要零食与生活费时,他不得不一次次掩饰自己因经济拮据而内心脆弱的事实。妻子被公司裁员,他除了说几句没有实质意义的安慰话外再无别的办法。
子俊是一个毫无责任心的人吗?显然不是。妻子在外打拼,子俊按时接送孩子回家,想方设法做孩子爱吃的饭菜;妻子回家迟了,他赶紧去厨房热饭;妻子被裁员心里郁闷,他柔声安慰;他虽无力负担父亲心脏搭桥的手术费用,但把父亲病重的事实深深记在心里……他深知,作为一个中年男人,无论压在肩上的巨石多么沉重,他都不能从言语上表露出辛苦。正因为子俊有深深的责任心,却无力付诸实践,他才如此痛苦不安,未老先衰,心梗,梦魇……
子俊就是当下无数中年男人的写照。他们少年时代因为是男孩受到过多宠爱,养成了阴柔而敏感的性格。与父母那代男主外女主内不同,八零后一代的年轻人接受了男女平等的生活模式。小说没有点明子俊的职业,但从字里行间看,子俊实际上是个没有正当职业的男人。他聊以自慰的是,他在家接送孩子干家务之余写的文章断断续续地发表。然而,现实坚硬如铁,在当下,没有一个作家可以靠稿费养活自己与家人。子俊也是,尽管他不时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但面对生活的窘境他无力突围。另一方面,正因为读书写作,子俊格外敏感。孩子的一句话就可以使他自责没有当好父亲,路上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就可以在他胸中响起“一记闷雷”,既而心绞痛发作……即使子俊真的心梗,他也不敢告诉家人,生活没有给中年人喘息的机会。
加缪说:“人生处在荒诞、荒谬之中,但,人生值得过。不管这个世界多么荒诞离奇,你都要选择活下去。”西西弗斯躲避不过面前的巨石,只能不舍昼夜地推着巨石登山。子俊逃避不了一地鸡毛的生活,只能日复一日痛苦地活着。
这篇小说最大的亮点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叙述手法的现代性。小说以双重时间序列的模式展开叙述。一重时间在现实生活里,自然是按顺序的方式推进,小说情节的展开集中在一个下午,从子俊接孩子回家、做饭,到子俊走进卫生间冲澡准备休息结束。子俊困在现实的牢笼里。现实的投影在他心灵上产生的潜意识、下意识才是小说叙述的重点。每每涉及钱的问题,子俊的手就不由地抖动起来。“……他猛然回头却见儿子和姑娘仍慢悠悠地落在后面,压抑一天的情绪瞬间袭来,心仿佛摇摇欲坠的大坝,俨然到了崩溃的边缘。”让子俊情绪崩溃的诱因是什么,小说没有直接告诉读者,而是在展示子俊日常生活细节的同时一点一点地渗透出来。第一次,当子俊意识到儿子已经长得齐他的肩了,“子俊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开来,像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眼神也不受控的向对面扫,似乎在寻找什么。”谁都知道,当下孩子的教育需要巨额费用,而他目前无力负担孩子成长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教育费用。第二次,“走到路口,子俊猛然撞见一头白发。他顿时一怔,脑中轰然响起一记闷雷。他的身子很明显地抖了三抖,几乎跌倒。”那头白发会不会是父亲母亲?心脏搭桥手术刻不容缓,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作为儿子,子俊深知手术的重要性,但又无力负担手术费,来自内心深处的道德谴责让他心惊,坐立不安,他虽一再掩饰,终究还是在梦魇中一一再现。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子俊的梦境。梦中,子俊在头上抓了一把,头发像黑色的雨滴一样纷纷坠落,母亲拿来一面镜子让子俊看看自己的模样,他看见一个秃顶的老头——那正是子俊心境的写照。一个在现实面前不断败退的中年人被“西西弗斯的石头”压得气喘吁吁,早早失去了生活的激情。
梦魇里的子俊像卡夫卡笔下被工业社会压得变了形的格里高尔一样,发落如雨,眼神呆滞,愁云惨淡,胸口插了一把刀……儿子质问他为何不给爷爷做手术,姑娘哭着让他赔镜子,父亲像山一样轰然倒地……只有母亲像一位哲人,告诉他生与死不过是物质的相互转化而已——这显然是子俊在自我安慰。
小说的结尾,子俊没有接父亲打来的电话,而是直接进了洗漱间。联系前文说父亲心脏病严重急需搭桥手术,可以想见的是,父亲知道自己此次手术或不手术都凶多吉少,他不过是想见自己的儿子而已。然而,就是父亲这个小小的心愿,子俊仍然没有予以满足。是子俊放下了压在心上的巨石,不再关心父亲的生死了吗?显然不是。子俊深知他也是个病人。他接上电话无力给父亲以安慰。他因为没有钱,逃避照顾父亲,也不想感受亲人的责难。他更怕自己在父亲面前心绞痛发作吓坏了双亲,抑或,他担心自己死在父亲的前头。小说以冰川原则结尾,“洗漱间内便传来哗哗的水声,其间隐约夹杂着歌声。”他压抑了一整天的情绪终于在夜幕下在洗漱间、在他赤裸裸地一个人时完全崩溃。这歌声是子俊压抑的哭声,抑或是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哭声故意播放的歌声。
对于子俊而言,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对于读者,又何尝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