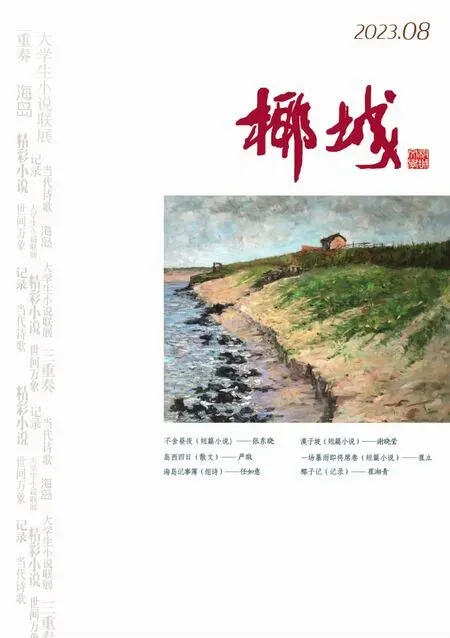漠子坡(短篇小说)
◎谢晓莹
没有比漠子坡更封闭的地方,也没有比漠子坡更神秘的地方,漠子坡生来就是要被忽视的。漠子坡是中俄边境的一个小县城,过了山脊,一只脚就到了国外,地偏,修路拉线都很迟。上世纪漠子坡称得上秀美桃源,到处是白雪,干净得一尘不染,偶尔有一些大湖泊出现在雪地,倒映着天色,像颤颤巍巍的蓝果冻。河太蓝了,吸引地质专家来勘测,几撬子的时间,漠子坡挖出了全东北最丰富的铜矿。
马田从俄罗斯跑过来做工,发了工资就买酒喝,喝多了,倒在沙袋堆或者窝棚里。一觉醒来,星星已经撒了满天,野虫“蛐蛐”叫着,拍拍袖子起来,有不多的寂寞。
漠子坡窝在地图最北边的犄角旮旯,在这个半数是冬天的世界,待在矿场是不错的选择,晚上铜炉熄灭,但气喘吁吁的锅炉还散发着余温,覆盖到工人身上,更不用说燥热的白天,他们可以只穿长袖的单衣在这里做工,雪山矿场的矿工是漠子坡最受欢迎的工作。
许小军出门的时候,不是个好天气,外面几乎被冰冻住了,雪原上赤条条扎着几根潮湿又光秃的黑树枝,一半已经没有生气地弯曲在雪地里,因为冷,空气中有一种近乎粗粝的雾气在弥漫,许小军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一粒一粒的,在空气中散动。落在鼠灰色衣服上的雪粒从他滑溜溜的衣服上坠下来,漏到口袋里,他冰冷的手装在口袋,走在雪地上,雪面不停歇地发出咔嚓咔擦的啃咬声。工厂会发给不住宿的职工交通补贴,用来乘坐车辆,但许小军不坐车,为的是把钱省下来。
到了工厂,许小军的样子大有不同,组长和马田看见他的时候,他蒙着一层很浓的水汽进来,工厂里突然有了寒气。高热的锅炉正在加热,拉风箱透露出呼呼的声音,他们穿着最长的袖子,以防飞溅的火星点把皮肤烧坏。在热气下,许小军头上、脸上的雪花全都融化了。
这个十九岁的青年人挂着满头水珠,它们频繁纷杂地跳跃下来,一路滑躺在他黝黑的脸上。那矿工的脸庞上,有一双不做恶事但往下弯折的三角眼,姨妈在出生的时候曾预言他的眼睛,三角眼的人多奸诈,不是好事,但全然没看破许小军会在十几年后长成最安静、最胆小的一个人,那兔子一样胆怯的眼神,和爬满忧郁的神情,中和了三角眼带来的锐利感。许小军脱掉外套,口袋里全是水,拿出来的外套湿淋淋的。他眨眼睛,试图把渗进眼里的水挤出来,瘦且坚韧的脸上没挂着一丝的赘肉,一个年轻人,他的胡茬长得飞快,总是像刚破皮那样青茬茬挂在脸上。
许小军有很多次想逃离矿厂。
矿工所像个蜂巢,马田脱光衣服,蹬着他圆胖的肚子和短腿,爬上一格一格的铁床,重重喘气,像一个圆滚滚的蜜蜂缩回了巢穴,铁床发出快要散架般的巨响。
矿厂建立了子弟学校,但子弟学校的人能读出去的不多,大部分职工的孩子还是会模模糊糊回到矿里。许小军一捧起书,只能看到那些黑字渐渐模糊,散落如屋外的黑鸟。离开学校到工厂做工后,许小军有很长一段时间吃不下东西,抬头看来看去,工厂都是三四十岁的人,大了一轮,没人可以讲话,只有一排排冰冷的行军床,一套二手的工服,头盔上装着矿灯,光的手在长隧道里摸索。
长身体的时候,许小军总是很饿,而他的胃口又过于大,对一切能吃进肚的东西都充满尝一尝的欲望,以安抚胀大的饥饿的胃。许小军喜欢吃干硬的列巴——从俄罗斯传过来的便宜面包,大个儿,管饱,好保存,但也硬得硌牙。他每次都狼吞虎咽吃掉自己的份额,连碎屑也不剩,不过相应的,它们会冷硬得让胃痉挛,刮擦他脆弱的胃壁,像用玻璃刮痛一个撑开的薄气球。
可是进工厂以来,他更少吃东西,不是不饿,而是工厂里堆满了工业废料,沤在大缸里弥漫着甜腥味,令人反胃。饿过肚子的人才会知道,那种滋味让人疯狂。
有野果的季节当然是最好的,户外有覆盆子、野板栗和伏倒在草地深处的小草莓,吃起来酸酸甜甜,开胃又果腹。但冬天,没有胃口的许小军经常看着工厂里的东西发呆。没胃口的他开始吃一些奇怪的东西,吃从水泥楼里伸出来的树枝——拔掉外圈树皮,许小军尝试过放在口中嚼,汁水腥苦的味道差点让他干呕。他又想别的办法,比如工地后院的墙皮——许小军蹲在地上很长一段时间,把墙皮挖进指甲里,偷偷品尝。也吃雪——摘下屋檐上的冰柱,放进嘴里,冰块咀嚼起来有嚼劲。
在千米深的矿井下,马田他们发现了一堆新的矿物——白色水晶,在头顶矿灯的照耀下,一面石壁的白色晶体水波流转,弥漫着流水一样动人心魄的波光,好像随时要变成花蜜流淌下来。马田碰了碰,吐了口水,“呸,一堆不值钱的玩意儿。”马田在地底偷运稀有金属,那些乌黑发亮、可以做军工武器的石头,马田捡它们来卖钱,当然是偷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矿里的资产,但拦不住一些工人偷偷挖出去卖钱。
许小军在矿洞里抠下了一块石头,那是白色水晶,从底部的白基块里往上拔出来,长得像一柄柄刀剑,表面充满天然的磨痕,让矿物质有了磨砂般的痕迹。许小军做贼一样把这块石头迅速扣下来装在口袋里,此后一直放在床头能够着的地方。等他特别饥饿的时候,就把水晶拿出来,它看起来长得和冰糖一模一样,许小军悄悄地把水晶放到嘴边,害怕被睡在一起的母亲和弟弟发现,他在黑暗中有些亢奋和着迷,水晶的表面很硬,在冷冻的空气中带有甜味,就像是走过下大雨下大雪的街道,空气中那种纯净的味道,沁着一丝丝棉絮样的甜,沁人心脾,让人忍不住深深吸一口气,吞进肚子里。许小军这样想着,总是忍不住重重地咬一口,在黑暗中痛得呼一声,很快,牙龈里渗透出的血腥味一下子浸满了他的口腔。
许小军抖了抖满是水的衣服,只要挂在架上,锅炉很快就能把它烤干,需要担心的反而是衣服因为过量炙烤变得薄脆,那样不仅保温能力下降,衣服也变成硬纸片一样直愣愣的,稍微搓洗一下,就成片成段开线。许小军望着楼下的黑锅炉,它和烟囱一样高,十几个人都无法环抱,长成葫芦型,下面开了四个侧窗口,可以不断添加煤炭,锅炉里叠着一个更小的全封闭大盆,用来炼钢,浓而红重的岩浆在里面流动。
红浆火烧云一样照在许小军脸上,他往下看,这是在五层,工厂就是围绕着锅炉建造的环形房子,那些悬在最上层的窗户透出寒冷淡蓝色的光晕。每一层做好地基,一层层的“回字”绕着缸炉搭建起来,从四角连线,延伸出四块靠近锅炉的铁皮板,没有防护,用来观察锅炉的状况。他清晰地看到岩浆内部翻涌,咕咚挤出一个粘稠的泡泡再破开,有时热火朝天,火焰也会“轰”一声响,火舌直往上卷。马田看许小军第一次靠近锅炉时发出粗嘎似乌鸦的大笑,“孬种!小心点往后退吧,掉下五楼你会摔成肉酱,掉进锅炉,你可就一点不剩了!”
许小军一连串倒退回来,只往前两步,那些热气轰然上涌,马田和周围工人的哄堂大笑,铁板没有防护,因为倒退发出“铛铛”的铁板声,下面深不可测,许小军缩成一团。
许小军就这样顶着工人们的嘲笑闷头做了很久,难过的时候,他一个人架着火堆烤火,一根钳子拨动着火堆。下班路上也会经过城镇。许小军想回家了,至少回家能看到莉莉。
莉莉是许小军尚未离开漠子坡的理由。
隔壁有五个孩子,莉莉是第四个,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夹在中间,但莉莉是最漂亮,也最受期待的那个。隔壁的木匠喜气洋洋地刨花,一片又一片的木头掉落在地上。小时候许小军和莉莉就蹲在旁边看,许小军蹲在地上,莉莉被放在一个平整的木台上,父亲专门给她做的,上面还用花被给她缝好了一个垫子,她坐在上面,低头看着许小军。浓烈如黑藻的披肩长发散落在她身上,葡萄般大大的眼睛,在阳光的照射下流露出淡黄色,长而浓密的睫毛,微翘红润的嘴唇无一不让她看起来像个精致玩偶。木匠喜气洋洋地看着莉莉,“这是我最好的一个女儿,等选上了山灵节领路人,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好了。”莉莉的母亲擦擦脸,眼睛里闪着光应和,“那时候我们会有新雨棚,你做木工的时候不用担心雨天和发霉,到时候我们说不定会有新房子!”邻居们也非常羡慕,经常夸奖莉莉,不吝啬在她身上使用任何美丽的词汇,人们等待她的十八岁,蘸取她的美丽和荣光,而她自己也在等待十八岁。莉莉听懂有人在夸她,高高地扬起脑袋,像一只骄傲的孔雀。许小军低下头,不愿听那些话语了。他看着她,突然感到自卑,从地上迅捷捡起卷曲的木块,飞快塞到嘴巴里,木屑闻起来像熟透的梨子,但吃起来的滋味,许小军已经忘记了。
封闭的漠子坡有一种风俗,一年两次的族祭,放在春秋两季,选漠子坡出生的女孩做领路人,许给山灵,领路人需要在庆典时站在队伍最前方,用树枝沾水洗尘。可保风调雨顺,灾难不存。
莉莉长大之后很骄纵,大家都对她好,镇上的年轻人对她的美貌即迷恋又敬而远之,她被雕刻得不像是在这个村庄存在的东西,人们以此认为,她一定会被选为领路人。
金钱匮乏,莉莉想要美丽的衣裙,可完全不够。父亲不肯给莉莉钱,钱都赌光了,就算有剩下的,也不会真拿来让她买裙子。莉莉有她的办法,她就在矿工下班的路上堵着。她在路上踢着石子,突然横手拦住路过的青年矿工,直接从他们兜里掏钱,莉莉昂起脑袋,看到的钱就是她的,拿得理直气壮。许小军的工资多半寄回家里,补贴家用,而每次省下的交通补贴,最后都到了莉莉手里。莉莉每次看到许小军出现在路口都叹气,一边拦一边问,钱呢?许小军摇着头说没有,她直接把手伸进许小军的口袋。数着数字,数两声就到头了,就这么点啊?她用稚嫩的声音说,就这么点钱,你平常也不够花呀。
年轻的矿工,多半是自愿去那里的,包括许小军。莉莉会站在那里拿钱,仿佛已经成了一件心照不宣的事情,年老的矿工知道,就不会再往那条固定的路回家,而是翻另一座山了。而年轻的矿工们,总是刻意走那条路,手中钱不多的,就只放能够接受的那点,每次月底发钱的时候,他们排着队去看她,但不索取任何。工厂的生活深不见底,活泼的莉莉是黑暗里顽皮的光斑,更何况她是山灵节的引路人,是光明的象征。
胆小的许小军看着她从自己的口袋里拿钱,两人是同一个院子里长大的邻居,她却没有一点不忍心的样子,直接擦一擦把钱装进口袋里,笑了。许小军看着她笑,忽然也浮现出一个微笑,那时候天地之间都是很安静的。许小军松了口气,还好现在只有我,没有人看到我的秘密。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莉莉觉得有些无聊,她踢了踢脚下的石头,嘟囔了几句,明艳的红裙是买不到了,柔软的手织毯也不够,她只好开口和许小军聊天。
“许小军,你在雪山矿场,是做什么的?”
许小军不好意思说他在矿厂的窘状,于是编造谎言。
“我吗,我是一个炼金术士。”
“真的?”
“真的,我们每天把成堆的东西放入红色岩浆里,你不知道它们有多么滚烫,一秒钟就能让一个人消失,大力士们排着队把矿物、泥土揉在一起,用三戟铁叉捞出来,就是钢铁,而我是矿工中最熟练的工匠。”
“真好,不像我,每天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待在家里,抄漠子坡民族的历史,等到族祭时拿出来用。”莉莉说。
“有时候我真想离开漠子坡,”许小军突然说,“我们已经在漠子坡待了太久,不是吗?”
“那只是你的想象,山的这头和那头,没什么不同。”
“外面没有山路。”
“夷平了,也还是从前的那条山路呀。”
许小军向莉莉提亲,这件事引起了雪山镇的剧烈轰动,这意味他率先打破了人们心照不宣的平衡,谁也不该拥有莉莉。雪山矿场的青年人全都被这一举动惊讶到了,莉莉本不该属于人间,尤其是雪山矿场。毫无疑问,莉莉拒绝了他,属于山灵的人将永远属于山灵,并以闭门不出表达了自己的抗议。
许小军家没有想到有这个情况,胆小的儿子怎么能突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带着许小军去给各家各户道歉,为他的莽撞和给大家添来的麻烦。许小军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头一次发起火来,叫嚷着,哪里都不肯去,于是他们建议,找一个修士来。
在旷野深处有个自行修行的修士,扎着长发,雌雄莫辨的模样,他活跃在各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父亲请修士来家里,许小军漠然看了对方一眼。修士长得很像猫头鹰,棕色带着白灰的蓬松毛发,长马尾像鸟,拿一截稻草绳绑着,前端一把头发很粗,越到尾部修得越细,一荡一荡的。修士突然伸手,落在许小军面前,他翻过来的手心出现了一根白色羽毛,在两个对视的眼睛里,羽毛滋啦滋啦点燃了,火光摇曳着,让两双眼睛呈波浪晃动。许小军这才发现修士一只眼睛是黑色,一只眼睛瞎了,瞎眼睛的玻璃体有些浑浊,灰白一絮絮浮在上面。修士先天眼疾,无法做工,所以他成了修士,为漠子坡的人们织造谎言。
修士撵着灰,喃喃自语,他的魂是不在了。
许小军冷笑了一声说,“还有什么把戏,都一起吧。”父亲连忙上前打圆场,“你这蠢货,别得罪了修士。”修士笑容温和,说:“看来,普通的方法是对你不大管用呀。”
老修士招招手,许小军感觉脖子上重重一下,像背上一座大山,喉咙里直泛恶心。“咕咚”一声,他又回到那片水域。在漠河中,一片巨大的蓝色果冻包围了他,光从天然的百叶窗中过滤,一条条落在他身上,上面浮着白沫和树叶,能看见走动的人影。人影踩在他身上,漫无目的,有的人掉下一块手臂,有的人掉下一截大腿……许小军看着,女贞树的枝桠全都幽幽浮现在水面,这些场景并不可怖,只是像树叶一样自然而然凋零。他的眼睛只剩下一条缝,划不动了,只能看到画面,听不见声音,他要沉到底下去了,河岸上有那么多人,却没人听见他的求救声,蓝色像月光一样幽幽,漂洗着他苍白的脸庞。
许小军想,其实他说的也没错,我是生了一些病。
许小军醒来的时候,手已经被反捆在了后面,他挣扎了几下,一指宽的麻绳牢牢缚着,周围昏暗得让人无法适应。修士的眼睛浮现出来,举着他的灯,怕黑的许小军往后退了好几步,直到身后碰上硬邦邦的墙壁,他才发现这可能是雪山矿场的一间杂物间。一把带水的米悉数撒在许小军头上,他的头发滴滴答答地淌着水,他想笑,也想哭,但吓哑了,没能说出一句话来,许小军倒在地上疯狂扭动,嗓子里发出的只有呜呜吞咽的野兽声。
他一个人关在这里。许小军靠着墙,窗外草簌簌而动,每一次舒展的声音都格外清晰,他的手指扣着墙皮,试图在墙壁折角处摩擦绳子,可绳子就像铁丝,许小军的手臂在墙上擦破了皮,淌出了血,绳子还是稳固。穿堂风冷飕飕吹进来,房子没有发出明显的哨音,可能是被墙壁阻隔,许小军闻到血腥味,突然很饿,呜呜哭起来,他抠着墙壁,突然开始狂热地吃那些泥土,他又感到饥饿了。
许小军饿了一天,因为手绑住,只好在地面上匍匐前行,突然哐当一声响,他脚碰到了一个碗,许小军立马调转过头,那是一个装水的碗。他扭动了一下,忘了自己双手双脚已经被反绑住,没能顺利用手扶起碗,反而听到肩膀咔擦咔擦响。许小军连忙把脸凑上去,闻了闻,没有味道,像清水,他急匆匆用嘴把碗衔起来,碗基本空了,水流了一地,一直漫到他胸口,打湿了衣服。他往旁边爬了两步,黑暗让人嗅觉更为灵敏,旁边的碗有面包的味道,许小军的肚子不争气地响了,本能反应来得如此之快。许小军挣扎了一小下,往前挪了一小步,把嘴埋进碗里,起初有些不适应,很快哼哧哼哧大嚼起来。
许小军吃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唱起了歌,因为分不清白天黑夜,他就不分时间地唱歌,雪山矿场的人吓了一大跳,那声音太过凄厉,像荒原上找不到家的狼,让人半夜也会惊醒,整个镇上的人都无法安眠。
第三天,莉莉终于来了,那些歌声缠绕在雪山镇日日夜夜的梦乡里,她走到许小军面前的那刻,歌声突然就停下了,许小军变得安静,像一只被驯服的铁撬巡鹿,他把脸放进她的双手里。
“可怜的许小军。”莉莉轻轻地说。
她伸开手给他解绑,那绳子捆得很紧,她点了蜡烛,在黑暗中帮他解绳子,许小军一下子就安静下来,那绳子因为挣扎会越捆越紧,贴着他的皮肉。莉莉解他脖子上的绳子时,感受到他脆弱的血管,手都在抖,最后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她轻声说,“对不起许小军,对不起……”
漠子坡有它的法则,人们不在意为什么要这样做,村庄的准则如果冒犯,就一定得有所惩戒,比如莉莉,比如其它。
“我的命运,在出生的时候就决定了,许小军。”
莉莉在小木屋门口送别许小军,他胡渣满脸,神情潦倒,和平常一样接着回去做工,他比以前更沉默,更内敛,也不再住在家里,而是在矿工宿舍埋头苦睡。他比以前大胆,更卖力,能扛着百斤重的钢铁走到炼钢台,上上下下如履平地,也不再害怕了。许小军成了最卖力的一个,工头乐得合不拢嘴,经常夸奖他。
许小军上班、下班,毫无知觉,他突然变得不害怕疼痛,不害怕重量,一夜之间变成了大力士。野修士果然是有用的,父亲露出了微笑。许小军踩着铁楼梯上上下下,铁皮响动声如此丰富,让人痴迷,包括火光,他也不再害怕,它们热切温暖,如同太阳,咕咚咕咚冒着最粘稠的泡泡。就像在睡梦中,总有一道光刺破黑暗,在溺水的河里,会有人伸出手……
“许小军!许小军!你疯了!”
许小军感觉自己的身体被重重一甩,整个人被拉后一甩,随即被打了两个耳光。马田站在他面前,又狠狠加了一拳,许小军这才腿软地发现,他刚刚手里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差点笔直走到锅炉钢铁里,在坠落的前一秒被马田扯了回来。
许小军的心扑通跳得飞快。无数个矿工的脑袋围着他,许小军这才真的醒过来。
许小军决定离开雪山矿场,去外面打工。雪花落在脸上,他长长呼出一口白气,当下决定离开。许小军在晚上打包了行李,外面的世界总会更好的,会有很多的机会,会有新的冒险和奇遇!他会有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他能靠勤劳的双手发家致富。弟弟妹妹绞着手指,看许小军收拾东西,那是一个下雪的晚上,父亲问他,“真的要连夜走吗?”
许小军点了点头,迅速收好他本来不多的东西,推开大门,浓黑色的夜空中坠落雪粒,他看到莉莉有些局促不安地站在他家外面。
“你要走了。”
“我要走了。”
“你等一下,许小军。”莉莉站在路灯下,她深黑色的头发像块绸缎一样披在肩膀上,“等下,许小军。”莉莉叫住他,雏菊花一样站在路灯下,许小军从没看过她如此柔和的眼神。
莉莉注视着他,突然开始唱歌。
在军营之前
在大门之前
有着一盏灯
至今依然点着
我们要在那里再见一面
就站在那座灯下
正如从前,莉莉玛莲
正如从前,莉莉玛莲
我们两人的身影
看来像是合而为一
那是情侣一般的身影
被人看见也无所谓
所有的人看到也是一样
只要我们在那灯下相会
正如从前,莉莉玛莲
正如从前,莉莉玛莲
哨兵已经开始呼喊
晚点名号也已吹起
迟了的话是要关三天的禁闭
我必须立即归来
只好在此道别
但心中仍然盼望与你同行
与你一起,莉莉玛莲
与你一起,莉莉玛莲
我能认得你的脚步声
你的步伐有着独特的风格
夜晚变得令人燃烧不耐
我忘记了是如此的遥远
我将遇到如此悲伤的事
此刻你会跟谁在那座灯下
与你一起,莉莉玛莲
与你一起,莉莉玛莲
不论在这个安静的房间里
或在地球上的任何一片土地
我都渴望梦见
你那令人迷恋的双唇
你在夜雾之中旋转飞舞
我伫立在那座灯下
正如从前,莉莉玛莲
正如从前,莉莉玛莲
“好了,”莉莉唱完歌,把手放下,含着笑容说,“许小军,现在走吧。”
雪花扑在脸上,差点熄灭他的灯。许小军拢紧他鼠黑色的长衫,走在雪中,旁边鬼影重重般的黑巷子,空洞洞的,风一吹,像口琴一样发出幽远的回声。许小军走着,走着,路过屋子,老婆婆和小女孩燃起篝火,在夜晚烤着。再走远一些,他路过矿厂,那栋巨大的黑色建筑矗立在风中,烟囱漫出白烟,都被他甩在身后。一棵孤独的树和许小军打招呼,没有得到回应,房屋渐渐消失,只剩下白茫茫一片雪地,和泥泞里刺条般的树枝,在荒原上,许小军开始走了。